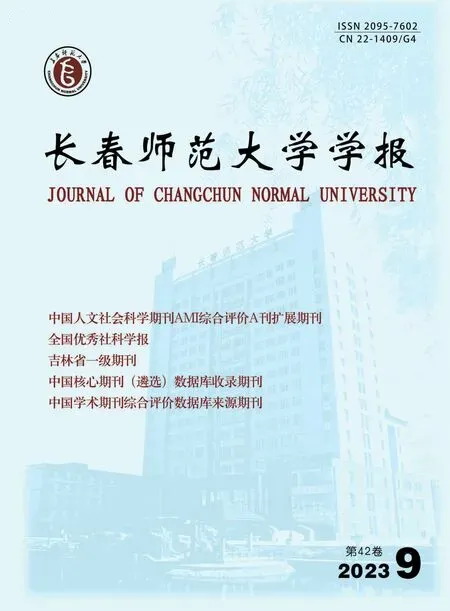寻找自我之旅
——论《奇幻山谷》中薇奥莱的身份认同
张明涵,贺 萍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作为杰出的当代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接骨师之女》等多围绕移民至美国的华人母亲与生长在美国的华裔女儿间的矛盾展开,通过母女间的矛盾展示中美的文化差异和华裔群体在两种文化间的挣扎。母女的最终和解,标志着女儿们在两种文化间找到了合适的生活空间。出版于2013年的《奇幻山谷》(TheValleyofAmazement)与谭恩美之前的作品在背景设定上有所不同——它将故事的主人公设定为主要生活在中国的混血儿薇奥莱(Violet),讲述了1897—1939年近半个世纪间她与美国母亲路路的动荡经历和情感困惑,薇奥莱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与找寻贯穿文本始终。我们可以从薇奥莱的成长过程中看到熟悉的父爱缺失、母女冲突与和解。
“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1]38面临两种文化的碰撞,薇奥莱对中美两种文化而言都是“他者”。一方面,在强势的美国文化影响下,童年时的她趋向于美国文化,同时被封建保守的旧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她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因为明显的中国特征而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双重文化背景注定她无法获得单一的文化身份认同,但是“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2]11,它取决于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薇奥莱通过扮演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建构起混杂可协商的“第三空间”,重构了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
一、无忧下的懵懂:路路之女
“七岁的时候,我对自己是谁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女孩,从人种、习惯,到讲话方式都是。我的妈妈叫路路·明特恩,是大上海唯一一个拥有自己的顶级妓院的白种女人。”[3]1在作品开篇,薇奥莱这么定义着自己的身份。母亲路路将“秘密玉路”装饰成有天堂般魅力的宫殿,同时利用自己的人脉将客人通过利益联系起来,帮助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使得客人惊叹不已。因为没有父亲的陪伴,童年时的薇奥莱把母亲作为自己的标准与榜样,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母亲的影响。她的行为举止和打扮也趋向于美国女孩,再加上棕色的头发与绿色的眼睛,她认为自己异于身边的大多数人。
当得知自己的父亲还没死并且是个中国人时,她会好奇自己的中国父亲,会观察来往的客人,从而试图描摹父亲的样子。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中国特征,最明显的仍然是外貌。她的眼睛是绿色的,但是眼睛和嘴唇的形状是中式的。当仔细照镜子的时候,薇奥莱意识到中国父亲带给她的不只是中式的五官,同时还有她无法抹去的中国文化印记。这个时候的薇奥莱已经感受到身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中的焦虑和不安。尽管薇奥莱一再强调自己身上美国文化的那一部分,但她也明白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中国文化的存在。
二、困境中的挣扎:妓女、冒牌妻子与小妾
社会时局的动荡改变了薇奥莱的人生走向。薇奥莱被路路的相好拐卖到妓院,路路认为她已经死了,母亲的亲信迫于黑帮的威胁也无能为力。她从秘密玉路老板的女儿薇奥莱变成了妓女薇薇。
起初薇奥莱不断反抗,受到不断的毒打。后来她遇到了旧相识宝葫芦,在宝葫芦的教导下,薇奥莱开始学习怎样成为一名高级妓女,使自己更好地生存下去。
首先,薇奥莱意识到自己反抗越激烈,生存状况就会越凄惨,于是她明面上开始与妓院的人维持和谐关系,以获得生存空间。她接受了妓院对自己身体的规训,身上的西方特征被抹去,东方脸庞被突出,按照要求伪装成满族人的后代,以满足亲清派客人的情感需求。后来,薇奥莱的外貌特征被赋予不同的来历,比如她因拥有绿眼睛而被被说成是乾隆妃子的后代。在妓院为她举办的初次社交晚会的舞台上亮相后,她成为各个小报的头条报道对象,达到了妓院的目的。
其次,薇奥莱明白自己无法摆脱身体被商品化的现实后,开始主动利用自己的身体谋求更多的利益。在宝葫芦指导下,薇奥莱学会了怎样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一部位、每一器官去迎合男人的想象,满足男性的欲望。宝葫芦用亲身经历告诫她,“在成为一个名妓的同时,避免小气鬼、错爱和自杀”[3]139;“你必须为四项必需品而努力工作:珠宝、家具、一份带薪水的季度合约和一份舒适的退休生活。忘掉爱。你将会得到很多人的爱,但没有一个会长久。爱可不能当饭吃……”[3]147作为妓女的薇奥莱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她的身体作为被规训和凝视的商品,以满足男性的欲望;但同时她学会了利用自己的身体来为自己谋求生存空间和利益,不沉溺于靠身体换来的爱语和承诺,头脑更加清醒和坚定。
当被介绍给爱德华时,薇奥莱并未想到自己会与这个美国人坠入爱河,并且收获一份真挚的感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不顾宝葫芦的劝阻,自己交了一大笔赎身费嫁给她。他们生活幸福,有了一个女儿弗洛拉,但出生证明上母亲是密涅瓦——爱德华在美国的合法妻子,薇奥莱成了爱德华的冒牌妻子。好景不长,爱德华因西班牙流感去世,为了抚养女儿,薇奥莱冒充密涅瓦领取了爱德华的遗产,并且改头换面扮演一位美国母亲。她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只讲英语,不仅剪短、烫了头发,还换上了保守端庄的衣服,参加美国人的俱乐部,为俄国难民筹款。这个时候的薇奥莱外表上是美国人,但在美国人俱乐部太太午宴上与她们因青岛问题看法不一时,意识到“不管我本人有多么像个美国人——或者不如直接说,我有多希望自己像个美国人——然而在我心里,中国才是我的故乡。”[3]292薇奥莱为了能够抚养女儿做出了一切努力,但是在爱德华去世的三年半后,密涅瓦跟爱德华的母亲找到了她们,用法律和孩子的出生证明夺走了弗洛拉,薇奥莱成为失去女儿的母亲。
在动荡的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薇奥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强忍着失去挚爱的心碎与绝望。她作出了14岁以来自己能自由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去应聘翻译学校的英语教师和家庭教师,但是失败了。于是她重回风月场,变成了班卓琴手。在老奸巨猾的诗人常恒的步步引诱下,薇奥莱跟他来到距离上海三百英里远的月塘村。到了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后,她发现常恒口中所谓思念亡妻、娶她为正妻都是骗人的,就连之前给她写的情诗也是用的李商隐的诗句。她还见到了被常恒用同样借口骗来的前名妓香柚,也见到了常恒为了贪图钱财而娶来的相貌丑陋的正妻。香柚告诉她常恒的暴行和之前小妾的死亡,薇奥莱知道自己彻底被骗了。她开始假意奉承常恒,以获得逃走的信息。当常恒不再遮掩自己残暴的本性,对她进行凌辱、殴打和性虐待时,薇奥莱表面认命,内心却坚持告诉自己要竭力抗争。最终,她们根据之前逃走的小妾留下的信息,找到了从这座山村出去的路。当常恒面目狰狞地追上时,她们推下山上的石头,结束了这个衣冠禽兽对自己的折磨。
从无名雏妓到引起名流关注的高级妓女,薇奥莱学会利用自己的身体谋求生存空间和利益,但是她从不沉溺于靠身体带来的承诺与繁荣,不再遮掩和否认自己的中国特征,逐渐接受和融入中国文化。作为冒牌妻子的薇奥莱珍惜与爱德华的真挚感情,为了女儿弗洛拉而冒充美国母亲在公共领域活动,此时的她意识到在自己心里中国才是自己的故乡。作为小妾的薇奥莱在发现自己被欺骗后,面对常恒的暴力始终没有低头,而是利用自己的智慧逃出了魔爪,获得新生。
三、新生后的和解:翻译、妻子与母亲
回到上海后,薇奥莱再次找到方忠诚。她要去找一份工作。在方忠诚下意识地反应是帮她找一个妓院时,她自信笃定地告诉方忠诚:“我想在你们公司里当翻译,参与你的外贸生意。我不会像那些在英语学校里学出来的翻译一样,仅仅翻译字面意思……如果我表现得很出色,并且可以胜任其他的工作,你可以提拔我;如果我达不到职业要求,你也可以把我发配到那些无聊的职位上去,或者干脆开除我。要么我也可以自己辞职。”[3]538两周后,原本只是觉得在开玩笑的方忠诚宣称薇奥莱的翻译无比精准,薇奥莱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助手。她依靠之前从母亲那里积累的谈判技巧和对中西语言、文化的掌握而不再是自己的身体来谋求生存。
这个时候的薇奥莱已经能够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薇奥莱既承认自己的思维习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也承认中国才是自己的故乡。中美文化都塑造了她的性格,影响了她的选择。在身份和生活的动荡中,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罅隙性空间”[4]28,即“第三空间”。这个空间里面既不是完全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完全的美国文化,它是一个两种文化可协商的空间。而薇奥莱的文化身份认同就是从这个“第三空间”中重构,建构出一种混杂性文化身份。作为翻译的薇奥莱也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往来的桥梁,进一步促进两种文化的协商。
与方忠诚重逢后,他们再次开始了亲密相处。这个时候的薇奥莱接受着方忠诚的追求与示好,但不依附于他。她不再因为方忠诚不回信而惴惴不安,也不会因为看到方忠诚给其他女人准备的礼物而忍气吞声。当她觉得方忠诚满足不了自己想要的情感需求时,首先提出了分开。她与方忠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之前出卖身体时的金钱交易,而是地位平等的情感交换,薇奥莱的底气来源于自己的经济独立。方忠诚意识到此时薇奥莱的感情不再像之前那样用金钱就能换来,她也不再是自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当他身患癌症时,薇奥莱对他不离不弃并且到处寻医问药,康复后他不顾家人反对与薇奥莱结婚。婚后他因为能够得到薇奥莱的认可,成为弗洛拉的忠诚叔叔而激动,也会主动给薇奥莱倒茶。作为妻子的薇奥莱凭借自己的独立和真诚,换来了方忠诚的平等真心相待。
薇奥莱跟她的母亲路路一样,缺少丈夫的陪伴,失去过女儿,成为思念女儿的母亲。幼时的薇奥莱觉得母亲对自己逐渐冷淡,甚至怀疑她不爱自己,所以当偷听到自己还有个素未谋面的弟弟时,下意识地以为母亲最爱的人是弟弟。尤其是在被母亲的情人拐卖到妓院后,她更加怨恨母亲,认为她是为了去洛杉矶看弟弟,知道自己去世的假消息后可能只悲痛一会儿,就逐渐把自己忘掉。“正如薇奥莱属于我,完全属于我一样。我失去的只有她这一个孩子,哀哀想念的只有她这一个孩子,徒劳无果日日追寻的,也将只有她这一个孩子——就算她已经死了”[3]531。母亲的信破除了她童年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弗洛拉的出现使薇奥莱以母亲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母亲路路。在失去女儿深陷困境时,薇奥莱也是靠着想念女儿坚持了下来。“我是以母亲的眼光来看芙洛拉的,而这让我能够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妈。我们都害怕我们的女儿会以为妈妈不爱她们,故意抛弃了她们。芙洛拉可能已经几乎完全把我给忘了,只记得我松开了她的胳膊。我想让芙洛拉知道、感觉到,她一直都是被我爱着的。我已经准备好要告诉我妈,我知道她很爱我,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恨她。”[3]539
作为母亲的薇奥莱对当初路路失去自己的无助与痛苦感同身受,理解并相信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当初喊着“我会永远背叛你”的小女孩现在长大成为母亲,同时也原谅了自己的母亲,母女得到和解。当母女二人时隔30多年再次联络时,把她们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下一代弗洛拉。薇奥莱在母亲的帮助下找回失去已久的女儿,她收到了弗洛拉的来信,看到女儿说发现密涅瓦不是自己的母亲,提到原来自己喜欢吃中国菜是因为有中国血统。最终,路路、薇奥莱和弗洛拉于1939年在上海重逢。
四、结语
从高档妓院老板的女儿到妓女再到女翻译,从爱德华的“冒牌妻子”到常恒的小妾再到方忠诚的妻子,从误解母亲到成为母亲再到理解母亲,经历了被拐卖、被凝视、被毒打、被欺骗,薇奥莱始终没有屈服,她不断适应着身份的变化与生活的动荡。一方面,薇奥莱在生活的曲折与艰难中奋力挣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在困境中得以逃生,与母亲达成和解,获得了经济中的独立与情感中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薇奥莱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中构筑起“第三空间”,由此建构出一种混杂性文化身份,摆脱了文化碰撞带来的眩晕与混乱,消解了身处文化夹缝中的身份焦虑,重构了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
——艾丽斯·门罗《逃离》中弗洛拉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