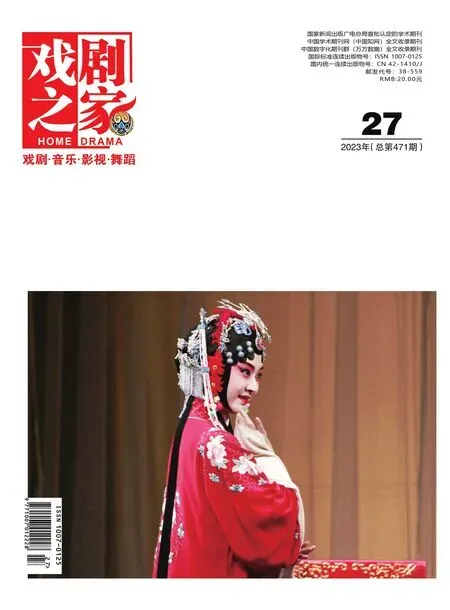李睿珺电影中的乡土影像叙事
张临亮,王丽莎
(青岛电影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20)
1935 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此后,“乡土”“农村”作为具有特殊标识意义的概念进入文艺批评范畴,而在后期发展的电影批评理论领域,“农村题材电影”与“乡土电影”也主要来源于文学批评概念的延伸。学界关于“乡土电影”的概念辨析比较丰富,学者凌燕对“乡土”与“农村”的概念辨析进行相关论述:“乡土似乎更多联系美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而农村似乎联系着贫穷落后的社会学意义、守旧的文化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因此,可以说‘乡土’可以归入文化层面,而‘农村’则是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前者重主观情感,后者偏重于客观叙述。”[1]学者路春艳则将“乡土电影”定义为“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影片,不仅包括常提的‘农村题材’,也包括那些表现历史中乡土社会生活的影片”[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逐渐将“农村”与“乡土”的概念边界消融,21 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农村”“乡土”的概念争议渐熄,其探讨的案例多是既能深刻捕捉并凸显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乡土风情,同时也富含时代烙印,饱含深厚的社会学内涵的作品。本文乡土影像叙事的概念基于“以乡土生活为主要叙事背景,以表现乡土人物的生存、伦理与情感状态以及乡土社会裂变为主要叙事内容。”[3]80 后新生代导演李睿珺从自身成长环境入手创作了诸如《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路过未来》《隐入尘烟》等作品,借助西部乡村、耕地、老人等元素完成乡土影像的画面诠解并通过展示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化发展冲突进行文化反思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强烈的作者视角特征。本文从导演现有的几部影片着手,综合叙事空间设置、符号隐喻与诗意美学风格等角度论述分析李睿珺导演的乡村影像叙事的外在美学表达以及内在文化意义。
一、叙事空间:乡村影像的景观塑造
乡土电影的题材本身带有鲜明的地理空间属性,这决定了其空间叙事的特性相较其他电影更加明显,“乡土”是导演常用的叙事空间,它是城市的“他者”,同时也蕴含着“前现代”性的乡村文化图景。对电影文本的影像文化意涵分析主要借助影片中的画面表达进行,通过影像所指分类将其划定为影片中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指的是出现在影片中的自然界景观;而人文景观则稍显复杂,指的是那些能够体现人性、文化、情感信息的影像画面。”[4]李睿珺导演的几部乡土电影皆以自幼生长、熟知的乡土环境为叙事背景,通过对风光元素的使用,不仅表现了乡土影像的自然景观,展示了独特的艺术和审美感,更是寓言性地反映了乡土的人文精神和情感底蕴。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展示了枯燥荒漠的“沙丘”,与肥沃丰饶的“草原”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双关式呼应通过影像张力将影片主题含义进行了升华。在《老驴头》中,电影画面充斥着无尽的黄沙和广袤的沙丘。主人公鞭策着瘦弱的毛驴从遥远的地方运送冰块,为他所种植的红柳和草地浇灌。电影通过诸如“沙丘、祖坟、毛驴……”等符号意象将老驴头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事物的执着追求,从平淡的视角展现了这种徒劳的挣扎,揭示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消逝以及社会现代性进程中乡村景观的消解。
李睿珺还善于运用魔幻的表现主义手法“制造”虚拟的影像景观。阿多尔诺在《美学理论》曾对模仿“自然美”的“艺术美”作出论述,他认为具有真实性的现代艺术的意义在于对异化的社会现实具有反思、批判、否定的功能。李睿珺则通过“人为的”影像画面将他自己感知、审视社会的视角浓缩在镜头叙事中,从而构建出带有“人文审美”的乡土影像景观。西北村落是李睿珺所有影像创作中最为突出的一点,闭塞的环境造就了荧幕中人物的性格、村落文化特征,因而当时代发生变化、社会文明的发展进入矛盾后,“与常规空间对抗”的新型景观被赋予了新的解读意义。在《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通过对“仙鹤、坟墓、烟囱冒烟”等人文景观的展示,揭示了底层群众根深蒂固的归土意识以及在社会制度变革下命运所面临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与无能为力的恐惧。土葬不仅是对殡葬文化的认同,更是乡土背景下现实苍凉与小人物生活的悲喜呈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通过叙述裕固族寻找精神之乡的故事,将死的骆驼把孩子带到水草丰茂的地方这种超现实的画面描摹,借助空间景观上的象征完成人物精神归宿的指引,同时也展现出导演的乡土情结及其背后的浪漫精神。
二、符号隐喻:乡土影像的文化能指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结构进行处理,将符号与其指代物总结为“能指-所指”的关系,“能指”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层面,即电影中的影像文本,而影片中的“所指”是以“相似性”为原则的“实在物”本身,更包含其“语象隐喻”即创作者或观影者通过外在化“电影语言”解读文本而得出的内在化的表达意象。从景观意象的文化表达上来看,李睿珺导演的作品集从乡土出发,审视当下生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并保持绝对冷静的情感表达,立足乡土这一背景进行勾勒与传述,传递人文主题。无论是《隐入尘烟》还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还是《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其中都有不同空间的符号,或马或驴或白鹤、骆驼、尘土等。马在《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经常被解读为“物质清贫、精神无处归依”的困境暗示,这是人物生存境况的关照与思考,片中老马的执拗让人唏嘘;《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随着爷爷的去世与白马的不辞而别,原先马背上的希望逐渐消失,这既是旧文明消亡的隐喻也是新文明即将出现的讯息。爷爷生命消失后却化身白马奇迹般地出现,这种超现实主义手法的呈现展示着政策变迁发展的失衡与边缘个体生命生存权利被剥夺之间的矛盾;《隐入尘烟》中老马的那头驴是他生存下相互为伴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在遇见贵英之前的希望与寄托;《路过未来》中的白马既是耀婷生肖的一种链接,也是命运的一种暗示,她奔波劳碌了一生到头来却无法安身立命。《路过未来》是一部关于寻根与生命的主题影片与故事,通常创作者会选择情节张力较强的故事来展现这一主题,在李睿珺的创作中,他反而采用了散文式的风格借助生活感的结构与拍摄方式表现了就业、医疗与乡土之间的情感缔结;《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看似是农村留守儿童与老人之间的故事,实际上借助“白鹤”这一意象将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悲哀荒凉处境表现了出来,那种凄凉与无能为力是直击观众内心的重要因素;《老驴头》中土地被侵占、土地被沙漠淹没、老驴头无处可依地悲哀死去,这些场景都足够戏剧化且极具冲突性,但李睿珺仍然选择淡化戏剧性情节,强调自然的镜头,用一种近似于“冷漠”的客观视角叙述,借用现实存在的符号作为精神导向的景观,从而隐喻其命运的无力与苍茫,使观众在银幕叙事中从个体角度理解这类群众在社会时代变革浪潮中的悲哀,从而唤起更多的思考与共鸣。
扎根乡土叙事背景的李睿珺聚焦生活事件与松散的结构模式去反映较为真实的生活,以近乎生活底色的平和叙事口吻及节奏中创造出直击观众心灵并引发哲思的内在效果。正如作者以往的作品一样,他通过对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岌岌可危的处境的描绘,揭示了乡村文化在适应和抵抗现代化进程的压力下,其维持自我身份和传统的困难。它本质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累积起来的焦虑感,与其他乡土电影不同的是,李睿珺并没有将乡村建构成符合工业现代化想象的具有“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乌托邦,而是通过“乡村主人公”个体意志向“社会现代化”进程发起对抗的过程中反思个体与社会、自然的关系。
三、创作风格:乡土叙事的浪漫意象
李睿珺在采访报道中提到意大利新浪潮电影对其自身创作的影响,这也是他创作风格的参照根基,这种直接的、真实的记录拍摄方法从第五代导演后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巴赞美学”的证明者,从贾樟柯开始,追踪镜头、开放构图、长镜头、场景调度等细节处理构成了此类影像的独有审美。区别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艺术语言的使用与表达,李睿珺擅长采用冷静客观的长镜头视角与远景镜头客观展示“看到”的现实。这种现实区别于作者型导演的主观介入,反而渗透着一种明确的深邃与冷静,借用“观察与陪伴式”的镜头呈现凸显着现代性的批判与思考。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最后老马自己挖土的情节段落中连续使用了两个长镜头展示生命消亡的过程,冷静客观的表现使观众顿感压抑与凄凉。在其他导演的创作中,展示这一细节往往会采用特写、闪回、沉稳的镜头表现方式,人物的动作、表情细节被逐一放大,才能勾勒某些对抗生命的节奏,引人深思。李睿珺的作品中,除去乡土这一宏观大背景,人物的对话、行动、生活基本都完成了全景交代,仿佛人的眼睛观看着所有状况的发生,反而构成了一种奇怪的释然与无力。孩子天真地以为爷爷的不快乐是因为邻居爷爷有的他没有,当他们嬉闹着把老马的坑填上,夕阳西下,一切归于安静,没有人找得到老马了,这种诗化呈现死亡的方式更让人唏嘘。由此也可看出,李睿珺乡土影像所尊崇的艺术美感就是这广袤的具有强烈生命变迁与重生的土地。
《隐入尘烟》中的马有铁与贵英的无家可归的心酸、遭人嘲笑的窘迫、奔波的路途与被迫“献血”是农村底层苦难的真实显现,但大雨中的依偎,温暖的鸡舍灯,勤劳耕种反而形成人与人、人与土地、动物之间个体与个体相互依附的浪漫化表达,使影片本身带有的苦难情绪被弱化,而呈现了关于生命与时间的深刻思考。马有铁与贵英看似通过劳作“驯服”了房屋、麦子与鸡,同时也被更高的阶级“驯服”——抽血以及搬进楼房,但其中恒定的巨大力量则是时间与土地。《隐入尘烟》中人类个体生命(时间)的长度是有限的,即便上层阶级可以靠下层阶级的输血来实现“资本”与“生命”的延续,但其永远无法改变自然时间的延续以及物种代际的更迭。正如影片中说的“鸡蛋变成小鸡,小鸡变成大鸡,大鸡再变成蛋;麦粒变成麦苗,麦苗变成麦子,麦子变成麦粒,麦粒再回到麦地里。土变成泥巴,泥巴变成砖,砖变成墙变成房子再变成土。”这就是生命的无始无终的轮回,片尾,即便男主选择结束自己生命(时间),但手中的麦苗仍随着自然时间的延续而生长。这种对时间、土地的至高“崇拜”恰恰体现了乡土叙事中农耕文明世界观的浪漫表述。这种浪漫与克制并存的电影意识与风格使导演对世界的观察与表述最终指向了一种起于个体、止于族群,在克制与冷静中对时代进行全景记录的创作风格。
四、结语
李睿珺导演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出发,基于有限的资金以及技术条件将现实与电影意象结合,不仅体现了中国乡村的景观美感、诗意审美,更塑造了一种鲜明且独特的电影审美体验。李睿珺的电影语言丰富且精炼,通过长镜头、追踪镜头以及场景调度等艺术手段,使得电影的叙述不仅仅是现实的再现,而是一种唤醒观众深层次感知的方式。他以鲜明的乡土背景来深化人物的内在情感,同时又将人物的生活紧密地绑定于乡土,形成了特有的叙事风格。他通过对电影中人物与土地、时间关系的时代性描摹,不仅展现了他对乡土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农村生活困境的批判性反思,更展现了他对人类存在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双重反思,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生动的生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