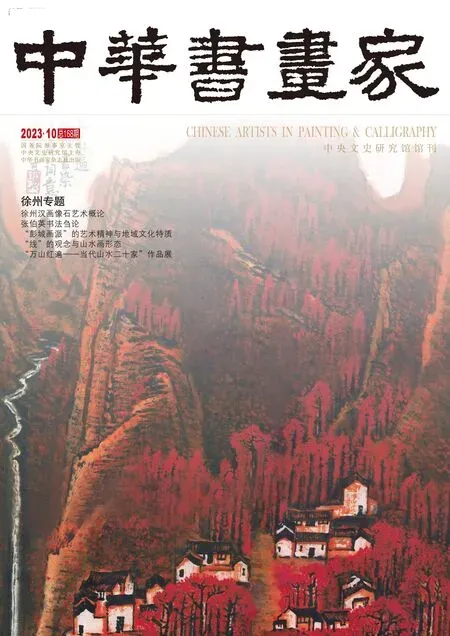“彭城画派”的艺术精神与地域文化特质
□ 李英梅
近代以来,彭城画坛涌现出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李可染、王肇民、朱丹、朱德群为代表的艺术大家,影响了中国美术史的走向,由此引发出多重启示。
一、三“魂”化一建殊世之功
1954年春,李可染请人治印两方,其一曰“所要者魂”。一个“魂”字,切中了要害,道出了真谛。我的理解,这是个体之魂、民族之魂、美术之魂三“魂”化一,方可建殊世之功。验之彭城画坛的诸位大家,无一不是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钟爱的事业之中,处处彰显出个体生命的超拔之魂,时时闪烁着超拔之魂的熠熠光华。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自然生命,更是社会性的生命、时代性的生命。因此,在他们的个体之魂里总是化入了民族之魂。在他们身上,这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他们都是自觉地肩负大义、勇于担责,民族之魂化入个体之魂,个体之魂融进民族之魂。那是忘我的、无私的、个体之魂与民族之魂浑化一体的至高至上的境界。个体之魂与民族之魂浑化为一地从事美术活动,献身于美术事业,具象化为美术之魂。也就是说,美术之魂正是个体之魂与民族之魂化一的物质形态化,是个体之魂与民族之魂化一的感性显现。
李可染在民族危难关头即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毅然决然地组织各类抗日活动,满腔热忱地创作一大批抗日宣传画、连环画,还曾兴办艺社、创办画报,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渗透着一个“魂”、都围绕着一个“魂”,其核心即最为珍贵的个体之魂、民族之魂、美术之魂三魂化一之“魂”。时至今日,《寒风中的难民》仍旧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是谁杀了你的孩子》一度激发起全民族的同仇敌忾。
怀抱此三魂化一之“魂”,李可染在适当的机遇之下进而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竭力倡导并躬行实践“为祖国山河立传”,这才有了另一方印“可贵者胆”的深厚蕴涵。李可染的山水画朴拙、浑厚,大气磅礴,却又暗暗涌流着一股灵动之气,尤其是《万山红遍》系列,灵动变幻,开创山水画新风。
抗日战争时期,刘开渠在杭州设计了《淞沪抗日纪念碑》,又在成都相继完成五座大型纪念碑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刘开渠担任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生命之魂亲自完成纪念碑正面的三幅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及其整体浮雕,从设计到完成,不愧为中国建筑雕塑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愧为呈示生命之魂、民族之魂、美术之魂不朽的里程碑。又一次作出卓越贡献的刘开渠,亦不愧为新中国雕塑艺术的奠基者。

王桂英 城里的孩子跟我学剪纸
王子云眼看大片国土沦陷,无数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破坏,有胆有识地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建议并获得批准,组建了以他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时五年,行程数万里,考察搜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制作300余幅壁画摹本,2000余张洞窟照片,近千幅写生稿件,5万余字《唐陵考察日记》,成为我国艺术文物考古史上的创举。正是以这一次和后来的多次考古以及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根基,才有了那么多独创性的学术论著,如《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伯国考》《敦煌佛窟建筑体式》《秦汉瓦当艺术》《中国美术史教材》《中国古代画论》《中国雕塑艺术史》。直到94岁高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王子云仍是写作不辍,以至溘然长逝于书案之前。这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个体之魂、民族之魂、美术之魂三魂化一之境。
现在要更深层次究问的是,为什么徐州籍走出来的艺术家都有如此之魂?为什么“所要者魂”可以看成彭城画坛巨匠共同的本质?任何社会现象、艺术现象都不是纯粹偶然的、孤立的、无来由的,都笃定有其深藏于现象背后的历史必然的成因。张晓凌谈到王子云时分析说,这可能跟徐州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天下苍生,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而不是说仅仅为了个人的艺术创作。我认为这一分析颇有道理。还有更为值得赞赏的是,田秉锷追根溯源,上溯到远古时代,上古三代以“淮夷”“徐夷”“徐戎”为代表的“东九夷”,大禹九州中的徐州,夏商时代的大彭国,终结于周代的古徐国,最后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凡徐州推出的艺术大家,均具有强烈的“主体意念”或“主导意识”,亦可称之为“王者气度”“王者风范”。正是靠着这样的气度与襟怀,他们不甘于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是坚持不断探索、不断寻觅、不断创造、不断超越,终于以自己的艺术实绩,登顶扬旗,为天下景仰。
在我看来,以天下苍生、国家民族为己任也好,主体意念、主导意识也好,王者气度、王者风范也好,至为关键的就是李可染的“所要者魂”。而按照我的理解,这里的“魂”字应该就是个体之魂、民族之魂、美术之魂三魂化一之魂,也应该就是“彭城画派”之所以能够成就其为“彭城画派”之魂。
二、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多样化合
一讲到“彭城画派”(也有许多人说到“彭城画坛”),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强调其地域性,这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凡是以地域命名而具有影响力和辐射性的画派(画坛),除了地域性的一面,还必定具有超越地域性的一面,而且这超越性的一面还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可是,“彭城画派”超越地域性的这一面,迄今仍是鲜有涉及。
王桂英的剪纸艺术可以算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她是自幼在徐州土生土长的农民,是文盲,似乎没有多少“文化”。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却授予她“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文化部授予她“中国杰出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她还曾多次应邀到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举办展览,现场创作。徐州剪纸也因此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王桂英则被确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继承人。

[汉]缉盗荣归图 拓本
王桂英的剪纸的确是北方气派,主导风格是粗犷而热烈、夸张而抽象,不像南方剪纸那般细腻、精致。她最擅长表现的就是普通日常的劳动场景、生活场面、凡人琐事、花鸟虫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铰的是生活。”她对生活的表现,常常又带有写意性,不那么讲究形似,率性而作,不遵循固定的章法,以简约的铰法进行独到的巧妙的构思。所有这些,简直跟徐州汉画像石有一种神秘的暗合。比如,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汉画像石,徐州汉画像石更加执着于现世生活,风格粗犷,突出写意手法。就连空间处理方式,两者也有相似相通之处:都能以平面的构图表现出层次感,甚至有些立体视觉效果。
显然,王桂英的剪纸是地地道道的地域文化的表征,带有浓郁的地域性特点。然而,作为一个从小不识字、前几十年从未出过家门的民间艺术家,她的原生态剪纸却在承续传统和现代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具有超地域性。首先,王桂英的剪纸“无意识地”继承了两汉遗风,这一艺术现象本身就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的意义,连外国观众都惊叹不已,可见其剪纸也已具备超国度的价值。其次,王桂英的剪纸从内容到手法又有着相当鲜明的现代意识。她突破传统表现方法,赋予静止的画面以动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有一幅女孩儿踢毽子,刀法简洁却又栩栩如生,姿态各异而又带有装饰性,生活情趣盎然。有一幅作品,竟然为一只鸡剪出朝向不同的三个头,巧妙地表现出鸡在吃食时左右寻觅的动态,令人叹为观止。
李可染的绘画,则可以视为地域性和超地域性完美融合的典型例证。如果说王桂英所受到的地域文化的浸染陶冶以及她的领悟体验是无意识的、无迹可寻的,那么,李可染对地域文化的接受则带有了一定的自觉性。据李小可讲,他父亲小时候常看乡土气息特别浓的地方戏“拉魂腔”,后来到江南写生,提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这个“魂”就来自“拉魂腔”。依我看,这个“魂”既是地域性之魂,又是超地域之魂。正如李小可所说,“拉魂腔”那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那如泣如诉的乡土腔音,催人泪下,动人魂魄,给李可染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少年学艺,师从徐州老先生,自然也是浓郁的地域性熏陶。幼年陶染和早期教育铺就了李可染终生绘画的底色。他“为祖国山河立传”的山水画,尤其彰显其主导风格:朴拙、浑厚、大气磅礴,却又暗暗涌流着一股灵动之气。那强烈的震撼力,深层涌动的正是徐州地域文化内在的深厚蕴涵,直让人感到有一股“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气氤氲鼓荡其间。
李可染22岁到杭州艺专学习,接触到开放的、多元的艺术之窗,林风眠深邃纯净的艺术境界深深地打动了他。其后,李可染又汇入抗日洪流,这时候的作品更多慷慨奔放。他40岁拜师齐白石、黄宾虹,从国画到油画再回到国画,两位大师的人格魅力和笔墨分量潜移默化地融入进来。他把白石老人看作一座雄浑无语的大山,其实他自己也已成长为大山身旁的另一高峰。
李可染的美术之魂从徐州走出去,却又无时无刻不是魂牵徐州。“把生命力投进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都带着徐州人的执着和倔强,根底里则是暗藏着民族的韧性和自强不息。还有不时流露的儿童情趣、田园诗意,既有乡土味,又有普适性,堪称地域性和超地域性完美融合的典范。
朱德群是与王桂英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他于1999年荣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是能够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成为国际认可的大师级人物。一般可能认为他的艺术创造只有超地域的成就而失却了地域性,实则不然,他的艺术之根仍在徐州故土。
朱德群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酷爱书画,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他在35岁旅居巴黎之后开始由具象绘画转向抽象艺术创作,但是他的创作并不是西方式的,而是始终洋溢着东方意味,甚至可以说这是他获取巨大成功的“秘诀”之所在。有的专家说,尽管朱德群在巴黎生活几十年,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他骨子里面还是流淌着徐州的这种浑厚博大的血统。
朱德群的目标是要寻找中西之间能够融通的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是要把中国的带有抽象性、写意性的书法绘画同西方的具象艺术融通起来。中国的书法绘画、斯塔尔德的现代视觉结构、伦勃朗的光,这三大元素融化为一,终于成就了朱德群的梦想,建构起一种超越东西方艺术之上的全新的视觉结构。他的作品是中国书法线的结构和线的运动中所产生的张力,在画面中跃动着。他的抽象绘画中随处可见中国书法的逸趣、中国画的意境,鼓涌着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古典韵味,洋溢着中国古典诗词的诗意;加之他习惯在作画时听音乐,他的作品里充满着音乐的旋律感,这又是西方绘画难以比拟的。恰如徐沛君分析的那样,色彩和图形只是朱德群的审美创造所赖以呈现的媒介,他的画境恍兮惚兮,渺幻如梦,似乎蕴涵着故土的情韵,在精神上一直与祖国的文化、故乡的血缘息息相通。借用范迪安的说法,朱德群将东方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语言与西方抽象绘画的优长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东方艺术精神和内涵的抽象风格,反映出一种超越时空和跨文化边界的创造。观赏那颜色的挥洒、光与色的组合、构图的方式和韵律,仿佛是朦朦胧胧的山水画中涌流着古典诗词味儿和东方音韵味儿。
王桂英、李可染、朱德群,他们各自代表一个类型,却都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有机化合,哪怕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原生态本土化的,却也具有超地域性的一面(王桂英);一个是表面上全盘西化,骨子里却仍是故土情缘(朱德群);李可染则是将两者完美融化为一体的典型。在这三大类型之间,则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过渡性的不同“比例”的区间。认清这一点,有利于艺术家发挥自己的特长,自觉地有意识地走向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有机化合。比如说,如果是仅仅为了突出地域色彩,就去单纯地机械地模仿汉画像石,急功近利地追求两汉遗风的效果,那就会舍本逐末,适得其反。
综上所述,“彭城画派”具有个体之魂、民族之魂、美术之魂三“魂”化一的艺术精神内涵,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多样化的地域文化特质。站在未来文化发展的立场上来探讨“彭城画派”这一命题构建,才能成就融合传统与当代、游弋东方与西方、引领时代走向的大家与艺术家群体,以及蔚然深秀的文化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