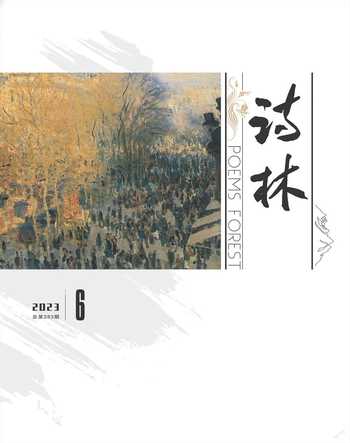与博尔赫斯同行的滋味儿
桑克
同时看几本书曾是我的好习惯,因为那时我年轻,有劲儿;现在则是坏习惯,因为身体早就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但是精神上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没办法,只能将就自己。如果把这种“将就”视作爱,我也会将就承认的——脸皮太厚了。
我坦白,我现在同时在看的书有《博尔赫斯与我:一场邂逅》,上下两大册的《米沃什传》,《九家读杜诗》(还牵连了一本《杜甫评传》),《乌鸦简史》,《论诱惑》,《渤海上京地区考古重要收获》,《普雷维尔不是诗人》,《Louise Glück Poems 1962-2020》(企鹅版的,一时图便宜就买了)……不能再坦白了,我此刻已经开始恨我自己了。
其实好坏之别还在于读完没读完。读完就值得表扬。《博尔赫斯与我:一场邂逅》(以下简称《博尔赫斯与我》)我读了很久又搁置了很久——为什么搁置我也不想说明——直到我的内侄杨钧杰在我和书的作者之间搭了一架木桥,让我换了一副脑子才再次启动——庆幸的是这次终于读完了,而且边读边写了笔记。我愿意和《诗林》的读者分享它的妙处。
《博尔赫斯与我》的作者是诗人杰伊·帕里尼,我之前读过他和别人主编的英文版《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绝对的高头讲章——现在好像不时兴读这种玩意儿了,现在更时兴读韩炳哲那种一眼看过去就透着聪明气息的小册子——我自己也是一晚上就把韩炳哲的《山寨》看完了。因为之前没看过杰伊·帕里尼的诗,杨钧杰就从帕里尼送给他的诗集里找了一首After Terror给我看,第三句是“每一扇窗也都系紧了螺栓”。杨钧杰动手把全诗译了出来,我和他还为此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前些日子见面,我们又为此进行了粗略的交流。对诗中的一个难点All that jazz,杨钧杰当面向帕里尼请教过。老帕说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俗语,意近“all that good thing(to happen)”。菲利普·拉金写过All what jazz,我当时译成“一切都是爵士乐”,也是没问题的。诗的讨论没有尽头,根本不必在乎“一切都已改变”,因为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
帕里尼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诗歌为何重要》,坊间有吴万伟先生的译本。老帕在文章里说:“我思考诗歌,我常常在日记里做注释。”作为一名非著名日记作者,我从来不在日记里做注释,虽然我非常欣赏老帕非常欣赏的罗伯特·洛威尔的说法——日记始终散发出“精确的优雅”的光芒。“精确的优雅”——这给爱写日记的人脸上贴了多大的金啊。老帕在文章里还引用了斯蒂文森的诗歌定义,我忍不住抄了下来——“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诗歌不神秘,生活也不神秘,谁不想过不挨揍的日子?谁不想写一首或者一万首想写就写的诗?说穿了,诗的本质非常简单,简单到没有更简单的东西比拟它。当然它也复杂,复杂到没有更复杂的东西比拟它。有人不服说,好话坏话都让你说了。确实啊,所有的词都可以用来说诗,所有的词都不可以用来说诗。说穿了一点儿都不玄。
《博尔赫斯与我》里讲到帕里尼的老师晚年痴呆,深信自己默写出来的莎士比亚诗句是自己写的。长叹息啊短叹息。这让我想起“江湖夜雨十年灯”也曾被当代的谁谁谁当成自己写的诗。一个辛酸的笑话。帕里尼还谈到房东罗斯小姐,“她穿著厚厚的羊毛裙,能挡雨,也许还能防弹”。呵呵呵。笑到这里,我必须向读者推荐法国人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写的《搅局者》,幽默,复杂,写得太棒了,译得太棒了,你们赶紧买一本吧。我等不及专门写文章吹嘘它,就在这里横插一杠子,闪吹一下。对了,忘了交代,书里写了不少诗人的奇闻逸事。八卦非八卦,严肃非严肃,应有尽有。
话头儿还是收回来,博尔赫斯是在《博尔赫斯与我》将近100页的地方出现的。从全书结构来看,似乎前面都是前史或者铺垫,其实不然。前面还写到帕里尼与诗人阿拉斯泰尔·里德见面谈的写诗经,正经都是武林绝招儿。需要说明一下,阿拉斯泰尔的写诗经是从格雷夫斯那里趸来的。你问我格雷夫斯是谁?我就转述罗莎·蒙特罗说的一句话给你听,“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年轻而又心理脆弱。嗯,有问题,暂时忽略吧,你们记住格雷夫斯是个天才就行了。奥登曾在《感恩节》一诗里描述过自己的诗歌谱系,“叶芝是个帮手,格雷夫斯也是”。连奥登都把格雷夫斯放在与叶芝并列的重要位置,还有啥好说的。现在就不妨把格雷夫斯教给阿拉斯泰尔、阿拉斯泰尔又教给帕里尼的写诗经单独提溜出来,让大家参详参详。写诗经的原话我不重复了,只拣干货说。第一条,把诗里的形容词全都划掉,改成名词。这些名词是“不需要修饰词的名词”。很多人都这么说过。据我所知,写得不错的人大都是这么干的。第二条,把副词换成动词。“如果你还需要形容词或副词,那你仍然有待找到正确的名词或动词。”还是原话精炼。第三条,不用被动语态,要用主动语态——这个读英文诗的时候感受特别深。此外还有阿拉斯泰尔自己的绝招儿,比如结尾时不要用“智慧的调调”——这个你们自己体会,万一我解释错了咋整。再比如阿拉斯泰尔的儿子转述他的话,“写得好就意味着不能有陈词滥调”——按照我的意思就是绝对不能写套话,绝对不能写别人说过的话,绝对不能写成语——成语太毁诗了。
阿拉斯泰尔与博尔赫斯是在1971年5月见的面,随后他介绍年轻的帕里尼和年老的博尔赫斯相识,并且无意之中促成了他们的结伴旅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在《日记中的博尔赫斯》里曾经写到,1971年9月14日博尔赫斯向他转述了阿拉斯泰尔的父亲关于滑稽模仿大诗的观点,而我手头的三部博尔赫斯传记对帕与博的高地旅行都没有提及。
在《博尔赫斯与我》里,我意外看到裤管夹bicycle clips这个词儿的译者注,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当初我译拉金《上教堂》的时候,正经为这个词儿辗转反侧过。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对这玩意儿完全不了解,造成我对这个词儿产生了困惑。小时候我被自行车夹过脚,倒不是因为没有裤管夹的缘故。词语来自词典,其实也来自生活经验。我们这代写诗的人大多写过经验。前些日子听说不时兴这个了。也挺好。诗嘛,写什么怎么写都行。帕里尼完全可以写自己逃避战争,写抑郁症——书里把这个归因于北方的气候。确实,冷地方更容易得哮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抑郁症?我不懂不瞎说。但是动画片儿《长安三万里》中有几处瞎扯还挺让我感动的——方式方法明显突出——行家们可能都这么想。
帕里尼终于见到了博尔赫斯。与其他崇拜博尔赫斯的年轻人不同,帕里尼既不可能为了博尔赫斯学习西班牙语,也不可能为了陪伴博尔赫斯而不在肚子里犯嘀咕。在帕里尼的眼里,博尔赫斯就是个话痨,就是个书虫子,他总是滔滔不绝,总是引经据典,从这本书聊到那本书,并对自己的英文发音非常自负。我个人以为他有自负的资格,因为我看过一段1977年他接受采访时的活动影像。他的英文发音真的是棒极了,他的笑容真的是美极了。他甚至在摔倒受伤的时候都不忘了引用弥尔顿关于“坠落”的说法。幽默。
与大多数诗人一样,博尔赫斯喜欢美酒美食,“他浅蓝色的宽领带上遍布橙色瀑布、飞鱼以及不少饭菜残渍”。博尔赫斯的这副形象,倒让我想起年轻时遇到的一位著名同行,远远看上去是非常干净的一个人,但是走近一看,衣服上下全是污渍。能将干净和污渍集于一身,怪得让人忘不了。然而博尔赫斯并不是什么怪咖,而且也没有因为自己盲目而滋生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可以称得上睿智,虽然博尔赫斯喜欢奇迪厄克·蒂奇伯恩的一首诗《挽歌》显得多少有点儿古怪。我从蒂奇伯恩中译本里看到的一个句子还不错,“虽然活着,我的生命已告结束”。不明觉厉。而博尔赫斯在和帕里尼交谈时随便一说的“描述就是启示”简直就是一种美学原则,完全可以将之在一首或者两首诗里贯彻到底。
在业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出了圈儿啥也不是的现象,老江湖们全都见怪不怪,因为成功学的市侩特征妨碍的只是市侩。有的人看中的并非博尔赫斯的学识和写作,只是他外在的名声。这么说可能没什么说服力,但是落实到具体生活中就会构成各种滑稽问题。比如博尔赫斯在旅行中碰到的一个刻板的卡内基图书馆管理员。按理说,他们都当过图书管理员算是同类,即使没有惺惺相惜,至少应该有点儿共通之处。事实却是同类的不理解和反感。博尔赫斯博学可以接受,但是用舌头舔书确实荒诞不经,即使他是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盲人。
真的喜欢听博尔赫斯谈书谈诗,耳提面命的机会啊。比如他描述“奔流的浪涛”是“水上的白马”——电影《魔戒》干脆把这个比喻直接给演出来了——就是丽芙·泰勒饰演的精灵公主阿尔温念咒召唤河水那段儿。意想不到的还有帕里尼和博尔赫斯的交叉点之一霍普金斯,这让我特别感慨。当年老臧棣曾经对霍普金斯下过功夫,并建议我也研究研究霍普金斯。他甚至复印了一部霍普金斯原版诗集寄给我。看似古典的霍普金斯其实蕴藏着珍贵的现代性。在英诗里,还有一个人与他非常相似,那就是托马斯·哈代,老古董外套里装着一个新人。读他们的诗就是体验他们的人生,更何况是帕里尼与博尔赫斯共同经历的各种旅行细节,真的是生活恩赐啊。尤其当时间拉开距离的时候,这一点就变得非常突出。《博尔赫斯与我》完成后,帕里尼的妻子德文“似乎特别喜欢”描写基利克兰基的“小便之夜”。我读到这一章也不时嘿嘿笑。你们自己看吧,我就不转述了。博尔赫斯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年轻的帕里尼视角完全就是读者视角。这种陌生感带来的描述更有意思,只是太麻烦博尔迪·布莱德夫人了。年轻人和老人相处都挺难的,更何况和这个相当有原则的女房东呢?
帕里尼说《博尔赫斯与我》是一本“小说式的回忆录”。回忆录我是领教了,但是小说元素呢?主要物证我猜可能就是帕里尼和女房东(不是布莱德夫人)一起乘船前往奥克尼岛拜访作家麦凯·布朗的章节。难道这一章更像小说?老实说,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犹如面对一个盲盒,我硬着头皮猜里面是一场暴风雨或者一场哭泣可能并无意义。这一章没有博尔赫斯,因为在此之前博尔赫斯和帕里尼去尼斯湖泛舟,他手舞足蹈地谈论《创造之歌》把船晃翻了,差点儿把自己淹死。他要留下来休养,所以没去奥克尼岛。而作家麦凯·布朗,在我看这本书之前对他一无所知,但他在书里说的一句话足以证明他也是一个得道之人,这句话就是“重复别人的话非常危险”,和阿拉斯泰尔反对陈词滥调的说法同义不同调。
博尔赫斯告诉帕里尼,他曾被某个阿根廷大头领从图书馆馆长降职为家禽检查员。这事儿大多数读者包括我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博尔赫斯用的“家禽”这个英文词儿却让帕里尼误以为他的新职务是“诗歌检查员”。博尔赫斯用的单词是家禽poultry,和诗歌poetry是谐音梗。这个知识点可以让我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多一点点谈资。真的是又滑稽又辛酸。类似的谐音梗还有修车师傅说fair mass to cover(走这一段可够受的),帕里尼听成ass to clover(用三叶草遮一下臀部)。我在翻译爱尔兰诗人卡文納的长诗《大饥荒》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短语。这类谐音梗英国人超爱用,比如电影《诺丁山》里的休·格兰特。
在说完第一个谐音梗之后,博尔赫斯对帕里尼讲述了“同一首诗”的道理,但是当时的帕里尼没听懂。博尔赫斯不仅讲清楚了“原创性这个概念”(解放“原创性”),还强调说两首爱情诗的“区别只在于语境”。此外,我还想请写诗的人有必要记住博尔赫斯说的这句话,“各种想法各自独立地产生自同一个神秘的源头”。帕里尼真的很幸运,他也许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他和博尔赫斯这次高地旅行的真正意义。我用两个“真正”真的不是废话,而是表明每一个读者包括我自己都可以成为参与帕里尼和博尔赫斯高地之旅的第三人。而且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重新经历帕里尼的幸运,正如帕里尼引用的梭罗的话,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生活”。说的真是太好了,可惜当时帕里尼没完全懂,“但我以后会的”。庆幸的是帕里尼后来真的懂了。所以我们也必须庆幸我们遭遇过的任何事情,因为它们都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释放出自己的光泽,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在旅途中,博尔赫斯有时把帕里尼叫桑丘,把帕里尼开的莫里斯迷你汽车称为洛西南特(杨绛先生把这个词儿译成“驽骍难得”),虽然博尔赫斯自己并不承认,但还是有把自己当成堂吉诃德的小心思。在我眼里,博尔赫斯确实是一个知识英雄,当然换个词儿就是书呆子。书里的结尾附了一张黑白照片,前景是博尔赫斯与一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是诗人阿拉斯泰尔·里德的儿子贾斯珀,他在书中的言行完全就是一个读书甚多的成年人。照片后景里,环抱着胳膊的年轻人我猜是年轻的帕里尼,但是照片没有任何说明,我也不敢断定是不是他。照片的核心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博尔赫斯,他穿西装打领带,右手拄着拐杖。他从容不迫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在不足千字的短篇小说《博尔赫斯和我》开头说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另一位,也就是在那一个博尔赫斯身上发生的。”好吧,博尔赫斯化身千千万。
2023年7月4日-8月1日
——读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乌尔比纳的一名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