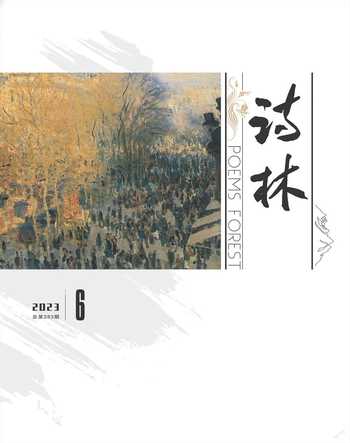岁月的香气
姜超
爱因斯坦晚年狠狠批判了“凡是不能观察到的,都是不存在的”这一说法,提倡“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靠直觉和本能写诗而放弃理性思索,大概率会陷入迷途。本栏集苏历铭、徐晓阳、陆标、包临轩的近作,既对世界摹其外貌,又摄取神理,这些篇什充盈着沧桑岁月的香气,展现汗水向下垂落之姿,又显灵魂向上升腾之态。四位诗人在与岁月打熬拼杀过程中涉过松花江水,悄然写下一首首思索的诗,各自有不同的特色。
苏历铭的诗穿行人间四季,烟火气浓郁,在生活现场保持着低视点的观察,却有超拔凡尘之意。他注重表现羁旅客居的经验,诗中的“火车”“超市”“虹桥”等意象本应有哀怨的色彩,但诗人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经验牵连在一起,对自我与他人皆付出同理心,人间属性就变得倍加浓郁。几经风霜情自真,苏历铭咏沧桑叹悲欢的出口选择率真表达,他深情凝眸于日常生活,为读者呈现了“子路之勇”。时代里的仓皇终有停驻处,诗人让真纯、自然成为心里的恒常的“在”。所謂“诗法”,就是紧贴实物的世间道,苏历铭对世间道的精勾细染值得期许。如此,苏历铭的诗是不顾一切重返原初的写作,世界的美好也随之诞生。
品读《大雪》《深秋》等作品,既有陈子昂式的喟叹,表达了世人面对宇宙时空强烈的惶惑感;又颇多杜甫式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被抛感。
也许,只有面对自然风物时,苏历铭们才会忘却时间,生发出久违的诗意,从“此在”的风景愉悦出发,在接近灵魂“彼在”的路程中,让诗歌主体“安在”——在身寄自然时达到心有所归、神有所定、志有所寄、灵有所托的境界。
徐晓阳如探身黑色的神,探寻人类的生存意义。夜晚书斋中的他从社会性的“集体时间”放松下来,开启了自我的“个体时间”。用“私人生活的灯光”照亮黑夜,作为孤独者的诗人选择单独思索的方式,于徐晓阳来说是一种迷醉,成为被珍视的精神存在。诗作《内流河》中,“干燥的季节”是显而易见的隐喻,而潜在的抒情主体保持着决然的战斗姿态。“相信会有一天走到你的窗下/聆听你与孩子的清谈/并且企望有一句诗激动我自己”,穿越岁月的风雪,诗人以笔为旗,蘸血为墨,以不妥协的姿态踏过现实的泥泞,向理想的殿堂艰难朝圣。徐晓阳的诗中总是涌动着理想与现实纠缠的氛围。这种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诗人产生了“变异”,使其成为一种不在“当下”的存在,表现在诗歌文本中,就是形成了一种缓缓拉开的噬心的张力。
《向季节告别》等作品仿佛有一个假想敌。胜负未定的前夜,诗人徘徊不已,心涌苍茫。在不断更新的语境下,徐晓阳的作品继续“古老的敌意”,坚持在当下芜杂的世界显现出高贵的气质,始终在现实中点亮内心的灯盏。他一次次提醒读者——世界陷于黑夜,此夜之外则是更辽阔的黑暗。
陆标的诗作意象密集蜂拥而来,诗意转换迅捷,带领读者与诗人一起领略审美的巅峰体验。这些诗歌中包含了诗人浓郁的思想感情,虽然这些感情与思想的表达依旧是通过诗人以往诗歌中惯常出现的意象完成的,但这些意象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而生动的画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别具匠心的用意。陆标将已经熟识的意象通过再次组接与勾勒,生发新鲜的意义。还必须提及的是,意象密集形成的轰炸美,确实来自危险的探索,需要较好的诗歌平衡能力。陆标的很多诗歌呈现了这一点。诗人坚持“纵的继承”,即向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诗学致敬,择用典雅的意象予以现代化转化,在旧有与西来之间挥洒才情。
包临轩的诗作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化为诗性表达却从不炫词晒句。他的诗严肃细致,采撷生活给予的生命细节,注重瞬间迸发的感受,将饱满细碎的经验与深邃沉稳的思考相融合,在日常事物上阐发出新鲜而又峻拔的诗意。他不断挖掘新奇、深邃的心理感受,生发独异的生命经验介入诗歌,使诗拥有血肉丰满的形态、超拔高旷的神姿。他的诗作时有光芒朗照,充满着生命与哲学的对撞、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作为习诗多年的诗人,包临轩总在寻求“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即千方百计寻求“陌生化”。面对未经省察的人生和唾手可得的诗意,包临轩郑重选择诗意的唤醒,做一个清醒的劝诫者,坚持对潜在的倾听者温柔诉说。这些坚实硬朗的主观感受,需要主体找到恰切的审美意识,它以内在的精神之力唤醒与之相配的形式,以上佳的品相显现。写诗是形式敞开的过程,形式逼迫诗人来寻觅并安稳它。这组诗让显现的形式、形式的出显共同发力,而接洽点是不同寻常的想象力。
包临轩的人生图景,不记叙表皮的疼痛,而抖开内心的渊薮,关注灵魂的激荡,作品始终有较强的沉痛感。包临轩的诗歌起于情感,饱含深情且节制有度,又以哲思偎近灵魂,选择做真挚的爱者。诗人保持仰观宇宙之大的姿态,超迈尘土飞扬的现实现世,可称之为“异己”;又时常俯察品类之盛,作品平添温暖之色,这依赖于“本己”。包临轩竭力将“本己”与“异己”共冶一炉,努力摆脱“事物之诗”的惯性,寻求着更新鲜更独异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