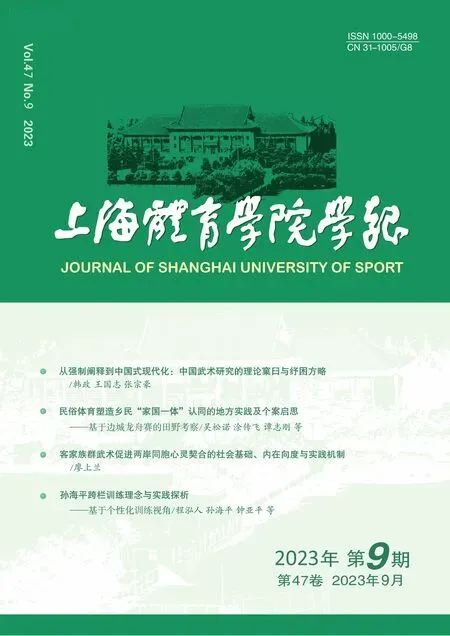客家族群武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社会基础、内在向度与实践机制
廖上兰
(赣南师范大学 体育文化研究基地,江西 赣州 341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 周年纪念会上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根本要义在于不断夯实两岸交流的社会基础,促进族群交流的互联互通,强化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性。从源头上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点,探析文化所关联的地域与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增进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及关系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此破除台湾青年一代文化身份的“迷惘”状态[1],也是当前立足于传统文化建构两岸融合发展之路的重要环节之一,即在给予台湾社会更多政策支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升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正面观感,激发台湾青年尤其是客家青年对中华文化及客家族群的热爱之情,建立中华民族以及各族群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增强文化认同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共同建设伟大祖国”是一项国家战略实践命题,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武术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功能与价值,对此已有众多研究者撰文验证。例如:张银行[2]认为,“武术认同的内涵和指涉因时因势而易,是一个与两岸发展史演进相呼应的‘层累’过程,也是一个随‘情境’而变的内在心理过程”;彭响等[3]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扮演着各族人民沟通交流的使者角色,成为族际互动与交融的重要桥梁”;郭学松[4]认为,“两岸宋江阵参与者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影响他们的认同观,在身体展演和故事叙事过程中促进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血缘身份形成认同”。综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可为两岸同源研究提供新视野,更能成为“两岸一体”的有效文化载体,凸显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5]。
客家族群武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结两岸同胞“一家亲”的文化纽带,对于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与文化认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
础,构建两岸共同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客家族群武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这一实践性命题进行理论探索,以推动客家族群武术文化的社会价值与理论创新。此外,通过梳理海峡两岸客家族群武术的交流、互鉴与融合的历史脉络,为“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这一当前我国“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1 两岸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的缔造与再造: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社会基础
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本质是从“我”到“我们”的一个心理构建与想象,是“我们是谁”的共同体认同,表现为人们对对象的归属感、认同感的情感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共有的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相互认同的血缘、地缘与精神基础’。”[6]客家族群武术文化往往通过客家拳种、武术民俗的技艺传播、交流互鉴,促进客家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两岸客家族群武术的谱系认同。以台湾地区的客家人、闽南人为例,他们虽在族群认同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皆是由中原前往南方以及台湾地区的汉人,从二者的种族渊源来看,皆源自中原望族。为此,客家人、闽南人带去的客家武术或南派武术与中原武术文化是一脉同源的,就此而言,中原武术、客家武术、南派武术与台湾客家武术有着明显的传承谱系特征,两岸客家族群武术具有同根同源性。因此,以客家族群武术为媒介,促进海峡两岸的地域互通、族群互嵌与文化互鉴,可为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为方便对“客家”“客家族群武术”有清晰的表达与认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须明确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客家人的身份认定问题。一般而言按照血缘、文化、语言及自我认同的方式来进行身份认定,台湾的《客家基本法》规定:“具有客家血缘或客家渊源,且自我认同为客家人者。据台湾地区当局统计,截至2012 年岛内现有客家人超过419 万,占台湾地区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7]就数量而言,客家族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台湾地区的政治领域[8]。二是客家族群武术的认定问题。凡是可考的,主要在客家族群内部传承的武术体系均被视为客家族群武术;经考其源头不是客家人,但目前只流传于客家地区,或绝大多数为客家人所传习的,亦将其视为客家族群武术。
1.1 求生存,抗侵略:缔造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
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历史上并未有大规模的迁台移民,当地以少数民族为主。明郑政权对台湾的垦殖经营吸引了众多对清廷统治不满的汉人,即使在康熙一统台湾之后,福建、广东一带的客家人因在当地生活不易,仍不断以“偷渡”的方式移居台湾。资料[9]显示,广东客家人有规模的渡台可追溯到明末清初,至清康熙、乾隆时期达到高潮。早在明郑垦殖台湾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开垦农田之余派武将教授农民习武防身:一方面为了培养“反清复明”的势力;另一方面以“军屯”的方式保证兵源,巩固其统治地位。早期台湾的拳种虽然相对繁杂,但其共同特点在于能够灵活运用生活周遭的各种器物——板凳、椅子、雨伞、烟斗以及农具——作为武器,技击技法也呈现出生活化、军旅化的特征。
求生存是迁台客家人最为重要的主题。清廷的消极治理导致当地治安恶化,加之移民汉人争夺土地、水源等,“土客”“客家、福佬”之间械斗不断,逐渐形成了以地缘、血缘为核心的“护庄团练”,成为最早的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其本质是利用武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传承关系,打造“类血缘”的武术共同体。这些团练组织不断从福建、广东聘请客家武师入台教习武术,如云林西螺七嵌所习练的就是客家武术,其甚至一度被视为近代台湾武术的发源地之一[10]。西螺七嵌武术的创始人是清道光八年(1828 年)从福建诏安(纯客县)渡海去台的刘明善,当地人称“阿善师”,其于1831 年创立振兴社武术馆[11]。西螺七嵌的武馆以振兴社、勤习堂最为出名,他们不仅教习客家武术,也调解居民纠纷、仲裁是非等。
相较于其他移民族群,客家移民社群的特点在于“在一位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之下,组成具有平均主义的共同体。群体的自治和互保是将他们凝聚成为具有准军事性质帮群的纽带”[12]83。此外,帮群首领还利用各种传统仪式展示自身的魅力与权威,以此加强对共同体的控制与凝聚,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不断利用传授武术进行信息联络和发展教众;另一方面,家族、宗族团体在武术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娱乐性的大众化演武仪式,这既可强化家族成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又可对外展示宗族的势力,在地方利益的争夺中获得优势地位。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13]记载:“台湾过去,频起盗贼、民变及分类械斗,地方常在不安动荡。乡庄虽有些防备(庄围、隘门),亦须连庄且师军事训练,始能保卫乡土。”另据台湾鹿陶洋“客家江氏”的《江氏祖谱》记载,约于公元1721 年清康熙时期,自福建漳州诏安县霞葛村迁移至现址楠西区鹿陶洋[14]。漳州诏安客家人是极为尚武的,据江家后人自述:“祖先因为靠养鸭赚很多钱,当时附近山头土匪很多,会下山来抢,为了保护庄民及家族的土地财产,因此成立宋江阵。”[15]当地宋江阵已有300 年的发展史[16],显然,演武的“阵头”既是武术训练又是武力展示。
在统治相对混乱的传统社会,“拳头”就是话语权。聚族而居、耕读传家成为客家人在台湾生存的基本形态,为此,客家族群武术呈现出血缘与地缘交织的特征,即军旅化、生活化、阵头化以及南拳化,其原因在于:①早期的客家移民武术是明郑垦殖时期的军官所授;②在清朝统一治理期间,台湾当地习练武术并不为当时的清廷所喜;③阵头化一方面源自军阵的操练习惯,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群体械斗;④由于地缘的关系客家族群武术与南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架势小,擅长贴身近打,腿部动作较小”等特点。正是由于以上特征,客家族群武术具有团结族群、聚族而治的社会功能。房学嘉等[17]认为:“传统的客家社会,由于宗族之间争夺经济利益和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械斗,某一个或一个小群体凭借高超的武技,或可成为一个宗姓或一房的支柱。”西螺地区流传的俚语“可过西螺溪,难过虎尾溪”,说的就是西螺当地七嵌之间通过武术团体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这也为后来客家武术群体抗日运动的开展打下了武术群众基础以及社会基础。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后,日军虽然攻占了台北等大城市,却在三峡、大溪、中坜、龙潭、新竹、大湖一带的客家庄落遭遇手持冷兵器的客家人的顽强抵抗。客家“六堆”各堡的奋力反抗延缓了日军的脚步,今天六堆长治乡被称为“火烧庄”就因日军火烧村舍而得名。除此以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 年始,台湾客家民众先后组织了十余次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直至1915 年“西来庵事件”之后,客家人的反日武装斗争才告一段落。
日本殖民统治者也发现,他们的统治之所以被不断抵抗,是由于台湾客家地区有着诸如振兴社、勤习堂、凤山馆、武野馆等一批客家族群武术组织,这些组织在客家民众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团结力。日军为了加强殖民统治,逐渐禁止台湾民众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又于1906 年在台创立了“武德会台湾支部”。日军通过“武德会”对台湾武术界进行渗透:一方面鼓励客家狮团加入武德会,以此钳制客家武术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入会狮团的祭典或演武大会,推广以剑道、柔道为主的日本武术,“目的在于借由‘武道’训练从中提高台人对日本文化的认同,对于后期皇民化政策的推动,可以说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18]49。客家武馆逐渐化明为暗,西螺七嵌各村的武术据点也从大街上消失,转而以“暗馆”的方式私下传习客家武术,自此客家武馆有了“明馆”与“暗馆”之称。由此也表明了客家族群武术的顽强生命力,同时标志着客家抗日运动从“武斗”进入了“文斗”阶段。
为了对抗“皇民化的武术”的侵蚀,客家人充分利用日本殖民统治者“禁拳禁教不禁阵”的政策[19],发展了“藏武于阵”的客家武术传承模式。如1905 年《台湾日日新报》上《狮阵横行》一文记载:“艋舺狮阵中人。有自立为武德会者,以八甲庄拳狮杨番仔为之魁。党羽众多,动辄用武。畏事者无不退避三舍。”直到20 世纪30 年代,随着客家狮艺表演被限制或取消,客家族群武术在台湾的发展进入了退潮期,其主要原因有二:①日本推行的柔道、剑道、相扑等日本武术具有统一的规则,容易传播;②客家族群武术内部门派众多,且由宗族势力发展起来的武馆各自为战,容易被各个击破。
尽管如此,海峡两岸客家族群武术组织团结一致、顽强不屈、抵抗侵略的文化基因深入客家人的血肉,成为两岸客家文化的共同组成部分:一方面台湾客家族群武术是由大陆迁台客家人带入的,其所蕴含的师承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两岸客家人共御外侮的历史能够形成守望相助的情感共振,进而推动两岸客家族群武术的文化谱系认同。
1.2 寻出路,谋发展:再造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
随着国民党政权迁台,约有200 多万军民随迁入台,其中不乏身怀绝技的武术名家、客家民间武术高手。尤其是军中的武术高手在解除军职后,部分人员陆续前往台湾各地传授武术,加之当时台湾地区局势动荡,客家人又延续了历史传统,由家族(乡族)聘请拳师开馆授武,一来增强自身的防卫力量,二则凝聚青年人的团结意识,防止盗贼事件发生。比如芎林地区的客家狮团逐渐盛行,时常到各地进行舞狮表演。但与此前不同的是,由于北派武术的盛行,台湾客家一如大陆客家地区也开始修习北派武术,以太极拳和少林拳为盛,如福建客家连城拳传承人黄林就自述,连城拳源自“少陵拳”,实为南少林拳。彼时,台湾武术整体上呈现南北融合的趋势,如七嵌勤习堂以太祖拳为入门拳种,但其改变了太祖拳在北方以腿见长的特点,转而重视下盘的稳固,强调上肢和手型的丰富变化[20]。
台湾客家族群武术技术上的“南北交融”并未带来真正的武术繁荣。台湾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统治,军警系统视客家武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一度从“暗馆”转为“明馆”的客家武馆纷纷关闭,习武风气开始没落,终而演变成专门治疗跌打损伤的武医馆。原因在于,台湾当局加强了对武馆的监控,武馆学徒如果有作奸犯科的行为,警察就会找武馆师父的麻烦,他们或面临无妄之灾,从而削弱了武馆授武的动力。部分客家武师开始以“走江湖”的形式表演客家武术,目的却是卖“内伤药”,客家族群武术发展由此进入了停滞期。
从武术社会史的视角来看,客家族群武术的赓续与其自身的社会功能、价值以及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与武术技击本身呈弱相关。随着法制的健全、科技的发展,台湾客家地区社会治安法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时期客家族群武术“拳打脚踢”“保境安民”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台湾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生存的需要,多数年轻人需要到外地打工谋生,缺乏青壮年的支持导致客家狮团逐渐消歇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社会治安管理的加强,客家族群武术的技艺传承被弱化。一项对台湾地区国术馆的调查研究[21]显示,“根据1993 年以前国术馆的特质与成员背景,可以发现当时的国术馆所经营的取向,大多以损伤接骨的物理治疗为主,较少有从事武艺相关的教学”。如台湾客家流民拳传承人李光铭著书立说,出版了《流民拳武医养生道》,并于2009 年回到福建龙岩市开设了养生馆,为众多病患解除病痛。
自1987 年7 月台湾当局正式废止“戒严令”之后,台湾行政部门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22],台湾籍客家武师接踵回到祖国大陆创业,不仅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强了两岸的文化与体育交流。此外,以探亲之名促使两岸客家族群武术交流愈发频繁,尤其是随着“世客会”的兴盛,客家族群武术由最初在恳亲大会上的表演项目逐渐发展为融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于一体的活动载体。2018 年至今,连续举办了3 届的“客家武术大会”就吸引了来自我国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众多客家武术爱好者;全国武术之乡连城县隔川镇隔田村的“天穿盛会”已未间断地举行了358 届[23],其所传习的连城拳远播海外,全国各地的民间客家族群武术交流会进入蓬勃发展期。
不仅如此,2002 年随着台湾着力发展社区营造与文化产业,“原先沉寂已久的客家狮团纷纷重组,有些逐渐转型变成以‘社区发展协会’的模式出现,并且大多受到政府相关单位的支持,借由民间团体的力量保存‘无形文化’。客家社区产业的再造,可以说结合了地方的文化活动与地方(社区)的节庆活动,重新赋予客家社区文化资源的意义”[24]。在社区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推动下,客家族群武术随着狮团的再次兴起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影视艺术、民间文学等也对客家族群武术形象进行了重新构建,其中布袋戏及影视剧《西螺七剑》将西螺七嵌的武术精神予以传奇化演绎,成为客家人不易磨灭的历史记忆[25]。由此,台湾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进入转型再造期。
总体而言,海峡两岸客家族群武术是一脉相承的。①最初因生存需要,客家人将客家族群武术带入台湾地区,并在客家地区乡村不断传承和扩散。②台湾地区客家族群武术的主要拳种来自祖国大陆,尤以闽西的上杭、诏安等地为最,如闽、客民系的流民拳、金鹰拳、布鸡拳、白鹤拳等。③台湾客家族群武术反哺祖国大陆。在清代前期,客家移民大都是“候鸟式”的迁徙,每年多次往返于海峡两岸,将大陆武术携带入台,又将在台湾所学武技带回祖籍地[26]。例如,1924 年曹彪彰将清末传入台湾的五枚花拳再次回传泉州。④客家族群武术在特定的共同群体中形成的互动社会关系是以血缘为核心要素的,为海峡两岸客家同胞的互动交流、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成为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社会基础。
2 客家族群武术的同根同源性: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内在向度
从历史来看,明、清两朝收复台湾均由军事途径实现。然而,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军事力量,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海峡两岸同胞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共同文化根脉。客家人虽然不是最早赴台开垦经营的族群,但“他们为台湾输入劳动力、带去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将文化传播至台湾”[27],其中包括客家族群武术以及民俗武术展演。可以说,客家族群武术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客家移民群体的必备生存技能,而互动性的民俗武术展演(客家青狮、攻城炮、宋江阵等)是交织着血缘、地缘、神缘、文缘、业缘等多重关系的演武活动[28]。客家族群武术的赓续不仅验证了两岸同胞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为新型客家武术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2.1 以武互通:客家族群武术可夯实文化共同体认同之基
林美容[29]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群人长期的共同生活经验的累积,但文化也用来保留历史,传达一群人共同的历史经验”。台湾客家区域“由于地形上的限制,这些沿山聚落多以散村分布,在农业社会容易形成以家族的单姓村落聚居,一旦家族人丁繁衍到一定程度,为了巩固家族本身的力量,便会聘请拳头师父来教拳授艺,是为‘家族制’;或者是借由地方头人来号召成员共同习艺,是为‘头人立馆制’;倘若个人要使自身武艺更为精进,亦会专门向武馆从师,成为‘武师立馆制’的型态”[18]2。客家人创立的武馆多以堂、社、阵、团命名,主要教授拳、医、狮艺,武馆的成立与武术的传播是以拳师为联线的流动实现的,成为台湾客家武术共同体的主要特征[30]。客家族群武术兼具血缘性、地缘性、族群性等特征,在促进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独具优势,它不仅蕴含了身体技击、强身健体的实用价值,还有着族群观念的仪式化表达与内在性特色。
此外,通过对海峡两岸一些共有的拳种传承谱系以及客家青狮、宋江阵等客家武术民俗仪式展演的考察发现,客家族群武术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观念“赋予—再生产—共享—扩展”的情感互动仪式链,从而实现客家族群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总之,“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只有在各种象征仪式、仪典中才能被民众真实感知”[31],于族群、民族、国家认同而言,客家族群武术运用的背后体现的是文化的力量、价值与意蕴,使以上三者从不可触转化为可感、可知、可见的共情状态,即为文化共同体认同。
回看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政府之所以对客家狮团的习武活动进行钳制,一方面日本人发现客家族群武术的传播具有团结族群、团结民族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推广日本武术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客家族群武术与日本武术对弈的过程也为重新认识武术政治价值提供了一个参照性视角。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方面,武术具有“群体性”“具身化”的功效,这也是日本在台湾不遗余力地推行日本武术的根本原因。在日本人看来,经历“两代人”的努力,台湾地区的“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整个雾社地区的番族已经被‘文明化’了”[32]。但事实上,客家人始终没有变成“日本人”,予以还击的是一次次武力抗争。客家族群武术成为抗日斗争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如徐骧(武生)、林崑岗(武秀才)、简大狮(开武馆,力大超人)、林少猫(好武)、柯铁(有臂力,善斗)等各义军首领多善拳技,广泛渗透于闽台基层社会的帮派组织,不同族群搁置边界区隔,汇聚到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行动中。
伯曼认为,“现代环境和经验跨越了地理和民族、阶级和国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全部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联合了全人类”[33]。从晚清开始,台湾治安混乱、盗贼四起,西螺客家人请拳师传授武功,将西螺二十五个村庄组织为七个区域(七嵌)的自卫组织守望相助。正当台湾以客家武术为主要斗争手段兴起轰轰烈烈的义民运动时,祖国大陆也兴起了一场“国术救国”运动。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变强”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武术由传统的调适地域性族群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国家社会治理领域,传统武术也逐渐从民间走入官方,丰富和发展了全社会对武术精神的认同。单纯的武力斗争虽未改变台湾50 年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但以客家武艺反抗异族侵略的英勇精神与世长存,为客家族群武术从“救国图存”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演进过程奠定了历史主体精神,且在海峡两岸反帝反殖民的历史抗争中不断被强化。客家族群武术的传承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提供了以武互通的公共文化场域。
2.2 以武互联:客家族群武术可促进文化共同体共识形成
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谁?多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都在追问,并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答,而与之相对应: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帝国主义是20 世纪出现最为频繁的公共话语词语,萦绕其上的是通过什么路径爱国、强国,“统一中国”无疑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需要。1955 年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方式作出了基本判断:台湾的回归无非两条路,一是战争的方式,二是和平的方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优方案,是海峡两岸人民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也最容易得到两岸同胞的共识。所谓共识,其本质是一种集体的心理状态,而共识需要物质载体。与其他许多现代文化活动相比较,客家族群武术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视角去理解“家”与“国”的认同变迁,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体育对塑造国家认同和归属感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34],美国视棒球为“国球”并将其作为美国人精神的典型代表[35]。
中国台湾文化事务部门早在1995 年就曾拟定《加强两岸民族艺术及民俗技艺之传习与发扬》的计划,并派专人前往闽西、粤东地区调查客家族群武术的发展情况以及学习交流,将当地的客家族群武术拳种资料带回台湾,积极推动两岸文化寻根之旅,不仅在技艺层面进行交流,还在文化层面寻找认同。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地理阻隔、殖民割据、政治分歧等因素并未阻断两岸一家的大势所趋。可以说,客家族群武术认同既服务于族群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也是海峡两岸客家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心理基础。
其实,台湾当局曾试图标榜“中华文化正统”,积极向海外打“客家文化牌”,同时借助闽台的地缘优势,利用客家武术团体提升其在海外客家人中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台湾曾一度在“对外交往”中获得优势,其缘由在于,“近代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侵略者的对抗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民族整体的形成所赋予的海外华人群落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2]。犹如孔飞力[12]24对于方言的认识:“同一方言是维系中国人手足情感的重要源泉。”客家族群武术也如客家方言一般,是身份的标志,并且与亲缘、乡缘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客家族群的情感纽带。
此外,作为闽台大型民俗武术展演项目,宋江阵、客家青狮、攻城炮等是祖国大陆与迁台移民(闽南人、客家人)共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集武术技艺、健体强身、乡土文化认同于一体的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宋江阵,已成为海峡两岸民间喜闻乐见的民俗武术展演。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台湾当地将宋江阵纳入《台湾省加强推展社区全民运动五年实施计划》[36],之后又逐渐在大、中、小学进行推广,成为学校社团与课间休闲游艺活动之一,部分高校还相继成立了宋江阵社团组织[37]。数百年来我国台湾同胞通过这样一类仪式性体育项目表达与强化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宋江阵以少林武术为基本动作,以强大的阵法纷呈展示,是公认的闽南文化‘稀世之宝’,也是闽台文化同根同源同俗的历史见证”[38]。
当下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其中来自民间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高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就被公认为海峡两岸最具盛名的宋江阵展示活动之一,“四月高雄内门观宋江,十月翔安内厝看宋江”,“闽南乡下每逢传统节日,拳头馆必出阵弄狮及排宋江阵”[39],充分展现了海峡两岸同胞“以武互联”的文化传统。林良菽认为,“宋江阵在推动两岸民众之间沟通交往的同时,也把大家的心紧紧地牵连在一起,形成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共同奋斗的一股民间力量”[40]。客家族群武术文化中还有众多类似于宋江阵的民俗武术展演,它们不仅涵括了海峡两岸客家族群共同的信仰,更能通过客家武术技艺的交流与相互印证,达到一种“寻根问祖”的文化体验。如此,能不自觉地唤醒客家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历史记忆,进而使其自觉意识到客家人、中华儿女等文化身份,并在重复性、周期性的民俗武术展演互动中持续确认和强化,以此加深台湾同胞对“故土”的热爱,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3 客家族群武术的文化共同体认同: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实践机制
“机制是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且机制与结构紧密关联。”[41]以客家族群武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客家族群武术文化的实践与体认中形成强烈的族源、文源认同基础,并不断内化为共同性、集体性的凝聚心理状态。从社会学理论出发,海峡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借鉴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机制、滕尼斯的共同体机制、帕森斯的系统机制、哈贝马斯的沟通机制、卢曼的制度机制、吉登斯的共同在场机制以及马克思的发展命运共同体机制等。受此启发,笔者将七大机制应用于客家族群武术的文化共同体认同构建,提出“以拳固根”的互鉴互赏交流传承机制,“以拳铸魂”的包容式参与发展共享机制,“以拳塑群”的增强共同性、同一性的沟通交往机制。
可以说,互鉴互赏交流传承机制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前提条件,以此打破长期互相隔绝的状态,促成“共同在场”;包容式参与发展共享机制是关键,通过两岸客家武术文化的相互切磋与互通有无,才能促成两岸民众的相互理解、知识与价值的共享;增强共同性、同一性的沟通交往是提升机制,构建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以发展促融合、以复兴促统一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和内在要求。
3.1 “以拳固根”:互鉴互赏的交流传承机制
客家族群武术是客家族群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日常生活化表达方式之一,是客家人千年来形成的珍贵历史记忆。事实上,在传统的“大中华文化圈”中,除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文化外,还包涵了众多“子文化”,这些“子文化”同样影响着华人社会,如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有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甚至非华人社会如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很多武术拳种在这些区域广泛流传,武馆成为华人争取权益、“抱团”发展的地方,海外华商协会大多倚靠着大大小小的武馆。由此,也传达出一个“潜意识”的武术文化共通性,即“拳头捍卫生存”。这样的判断或许失之偏颇,却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海外华人的苦难生活及其与祖国命运相联的史实。
事实上,台湾客家族群武术的发展与祖国大陆的武术传播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其蕴含了中华武术的“根性”,即以内在的血缘关系——族群为“纽带”,不断在世界华人社会开枝散叶、繁茂生长;另一方面,这一切又离不开“根”的牢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中国人的认同从开始的种族确定逐渐延展到‘文化中国’的共识”[42]147。其实,也正因“同是中国人”,海峡两岸才得以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打开相互交流的新局面,在台掀起一股“寻亲”“寻根”热,客家族群武术的“寻根”成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如台湾著名的客家流民拳传承人李光铭在他的祖籍地龙岩开起了武医馆,同时传授客家流民拳。追根溯源,客家流民拳是200 年前由客家先祖汀州府上杭县移民入台时带入台湾的,现今客家流民拳受到台湾各界的认可,并获得诸多竞技荣誉。
对祖国大陆客家族群武术“根”脉的认同是台湾客家人固守其族群身份的重要表征。“台独”势力曾企图以嫁接西方文化的方式对两岸文化进行“割裂”,最终将造成海峡两岸文化共同体肌体的枯萎。为此,挖掘与整理包括客家族群武术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可能复原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血肉,牢固客家族群武术这一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支点。应认清客家族群武术在两岸文化共同体认同上的重要价值,在中华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延续的前提下,通过“武术共同传承”这一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价值实践,融合具有民族复兴要素和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两岸客家族群武术文化理念,其构成逻辑是从“共同传承”到“共同复兴”,以此进一步协调统一海峡两岸的政治性、伦理性和文化性。
3.2 “以拳铸魂”:包容式参与发展的共享机制
新时代以来,如何更好地回应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成为当前客家族群武术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在通过客家族群武术守住“根脉”的同时,固守客家族群武术精神之“魂”,进而实现海峡两岸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的时代目标,或可成为应对当前所谓文化“本土化”号召的“文化台独”的有效方案之一。“倘若不及时、有效地对‘文化台独’进行反击,除了会进一步割裂两岸之间的各种连带,‘文化台独’的后遗症也可能给国家整合带来长期隐患。”[43]从本质上而言,“文化”的问题应以“文化”的方式解决,如倡导“学武术,做中国人”的认同理念,以此破解当前台湾社会存在的认同“他者”还是认同“自我”的二元对立的矛盾结构,进而进行以“尚武崇德、爱国守法、尊师重教、谦和诚信、刚毅自强”为核心理念的客家族群武术文化治理的顶层设计。
客家族群武术之“魂”是中华武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之一。客家族群武术发展至今,对每一个客家人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保家卫国、征战沙场、保护族群、强身健体、防身制敌,更重要的是客家武术所凝聚的客家儿女的精神信仰。佐原笃介等[44]就曾以“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评价义和团运动,其中值得思考的是,身份地位如此复杂的农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梳理史料发现,华北地区乡村拳教、门派通过教拳影响当地农村的公共生活秩序,特有的武术文化传播形式为乡民提供集体认同感、宗族观念、价值和思维模式的认同,以“演拳”为核心的武术价值观在乡民中迅速传播,使分散的乡民聚集在一起成为可能,进而形成共同的社会追求目标。当客家武术从民间走向“殿堂”,经过小说、电视剧、电影、短视频等的传播,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共同想象”,承载了客家文化性格中深层心理结构上的武道精神,进而强化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此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客家族群武术师徒观念是客家家庭、血缘关系的向外扩展。家庭和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加上客家族群武术文化,有助于海峡两岸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如前所述,客家人散布于全球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客家商会与武馆或者一体化,或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客家武术体系中的师徒关系也成为商人之间重要的信任凭证。这种“私交”信任的建立不是通过契约和法律文书实现的,而是通过“类血缘”的亲属关系确立的,其在海外客家人的生意往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认为,“当人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42]148。显然由客家武术师徒传承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可以弥补法治、规则等存在的内部缺憾,以文化的方式解决社会关系问题更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
3.3 “以拳塑群”:增强共同性、同一性的沟通交往机制
邱丕相[45]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看,武术具有广泛的功能和社会价值,体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武术作为体育项目的组成部分,应称其为‘武术运动’”。《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6—2020 年)》也提及,要“探索创办‘讲武学堂’等武术普及服务机构,发挥武术文化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武术的时代价值”[46]。为此,从理念出发,以客家族群武术“文化根脉”为基础的两岸文化认同能够激发两岸同胞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从实践出发,固守客家族群武术文化精神之“魂”具有增进两岸和平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走出“以武术论武术”的一般认识,对客家族群武术乃至中华武术的价值重新认识与定位,才能搭建起两岸武术传承之桥梁,通过此“桥”发挥武术在“文化强国”“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功能与价值,进而增强海峡两岸人民的文化互信、政治互信。其不仅从法理上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从文化上证实:“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47]以此营造“有形”和“无形”的历史记忆之场来凝结强化客家族群武术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打破历史空间的局限,凝聚基于一个中国的国族认同感。
事实上,在搭建海峡两岸沟通交流的桥梁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自1987 年海峡两岸探亲正式开放以来,客家族群武术始终活跃于各种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交流活动中,即使是单纯的武术交流活动也逐渐从闽台客家扩展到全国范围,如举办多届的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始终秉承“弘扬尚武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理念。过去30 多年的两岸交流,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其中民间组织或民主党派组织参与的武术交流更具“亲和力”,如2006 年4 月中国致公党承办的“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就凸显出海峡两岸民主党派、民间团体在武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诸如“客家武术大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赛”“第一届海峡两岸南少林传统武术交流大赛”“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等,加之大陆官方日益宽松的对台政策、武术国际化发展的需要等,都为两岸武术发展回归一统预设了路向[2]。
可以说,近年来以“武缘”为基础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积累的客家武术交流经验为当下继续夯实客家族群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族群性武术文化具有血缘、地缘、神缘等优势,在实践中,可以基于客家族群武术之间的“亲缘”关系,建立客家族群武术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关联海峡两岸客家族群武术生态旅游的产业发展,“为民铺路”,“以拳塑群”,打造民间新型客家族群武术共同体,其着力点皆在于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4 结束语
“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48]可见,如何解决殖民割据、地理阻隔、政治分歧导致的台湾部分民众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当前我国实施两岸文化治理与增进和平统一的巨大挑战。“客家认同形成的关键不在于特定地域或独特的文化,其性质具有多元化,既有经济原因又有政治色彩。因此,客家认同意识从政治、经济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并通过与客家同乡的交流,从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族群认同上升、扩大至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49]为此,从客家族群武术传统与共同传承出发,以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为基础,在客家族群武术文化中汲取养分以推进和维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认同是一条可取之路。
以客家族群武术文化参与海峡两岸共同体的建构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文化自信”理念和精神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客家族群武术以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的价值为引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通过“守根”与“固魂”的创新之路,搭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认同的桥梁。
[17]房学嘉,肖文评,钟晋兰. 客家梅州[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74
[18]汤承翰. 新竹沿山客家武艺之研究[D]. 桃园:台湾“中央”大学,2015
[19]李长莉,左玉河. 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15
[20]林荫生. 中国南少林[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263
[21]苏士博. 台湾地区国术馆现况分析[J]. 台湾体育学会体育学报,1993(16):169-175
[22]张春英. 海峡两岸“三通”政策:从博弈到共识[J]. 中共党史研究,2009(10):120-128
[23]连城举行“天穿盛会”弘扬传统武术[EB/OL]. [2023-02-16]. https://jingji.cctv.com/2023/02/16/ARTIRSXzAQxem OHLhkQc8j4h230216.shtml
[24]张维安,谢世忠. 经济转化与传统再造:竹苗台三线客家乡镇文化产业[M]. 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员会,2004:285-286
[25]陈木杉. 云林县布袋戏发展史暨布袋戏宗师黄海岱传奇[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61
[26]郭琼珠,李丽. 明清时期大陆移民对台湾武术形成与发展影响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7):8-11
[27]刘小新. 文化同根:闽台文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68
[28]郭学松,曹莉,刘明云,等. 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维度与路径:基于两岸民族传统体育宋江阵文化视角[J]. 体育科学,2022,42(10):77-86
[29]林美容. 彰化妈祖的信仰圈[J].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90(68):41-104
[30]张银行. 闽台武术文化研究[D]. 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2:178
[31]杨宏伟. 国家仪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77-80
[32]周斌,厉震林. 台湾电影:历史、产业与美学[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66
[33]瑞贝卡. 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M]. 高瑾,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66
[34]徐国琦. 奥林匹克之梦[M]. 崔肇钰,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32
[35]SMITH A,PORTER D.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M]. London:Routledge,2004:145
[36]廖文志. 罗汉门宋江阵的涵化现象[D].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3:57-70
[37]沈志君. 传统民俗宋江阵与大专创意阵头之初探[J]. 屏师体育,2005(9):202
[38]兰自力,谢军,骆映,等.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研究[J].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