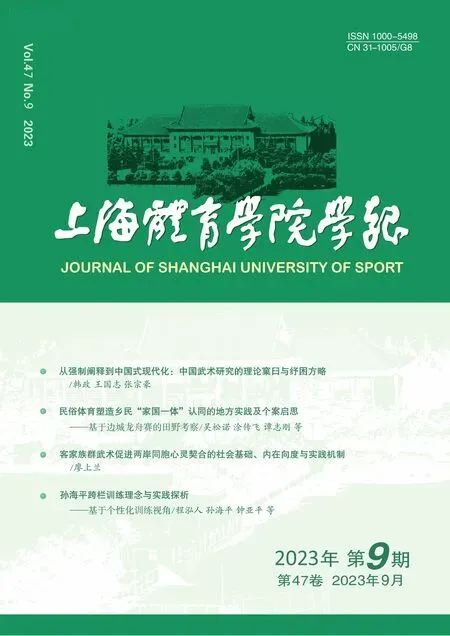近代武术“以用为主”的学术转型
刘红军,刘 洪,戴国斌
(1. 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2. 上海政法学院 警务学院,上海 201701)
从习近平[1]总书记关于构建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目标的重要论述来看,当下民族传统体育学所面临的学科定位不明确[2]、学科交叉[3]与学科内部认同危机[4]等问题,需要按照费孝通[5]提出的文化自觉来理解,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考察当下以武术为主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如何进行学术转型,形塑具有中国式学科特色的学术经验,以至于影响后来的武术学术发展,可为构建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术体系奠定文化自觉的基石。
近代以前存在以武术训练为中心、以“掌握武术技术方法、训练武术技能、涵养武德规范”为过程、以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的武术本体性发展,试图在拳种与门派上达成一种“成人”的目的[6]。武术“在昔不齿于缙绅,鲜传于史集”[7],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多关注武术技术,不仅形成武术拳技“无专史可考”“几失真传”[8]的“鄙弃无余”[9]之状,也给人以“保守无进步,不能利用以增国防之色彩”[10]的印象。随着清末民初西方新的知识类型与学术方法的全面引介,传统学术面临着解体的命运[11]。因西方列强蚕食中国,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传统学术开始表现出外向发展的大势[12],对“救亡”的关注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13]。传统学术开始由“四部之学”转向西方的“七科之学”,从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转向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14],再造了一种“新学术”[15],出现“科学救国论”“技术救国论”等学术思潮。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也推动了中国武术的学科化体系发展,并为武术“以用为主”的学术转型奠定了学科基础。
1 知识重组与近代武术学术转型
近代武术的知识重组与救亡图强相关,不仅形成了以西释中的武术新知识、新理论、新话语体系,也改变了武术的价值取向。在救亡图强、知识群体重组、以西释中的共同作用下对武术的体育化理解成为主流。在“改造国民身体”的实践中武术的健康功能得到发展,在“最后五分钟”的功能定位与“进军队”的实践中强化了武术的技击功能与国防要义,在以尚武重塑民风的新民运动中重释了武术的精神作用。
1.1 救亡图强与近代武术学术转型
救亡图强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国情[16],也是人们认识与发展武术的出发点与落脚点[17]。在近代“东亚病夫”意象下形成的救亡语境形塑了武术在健康、尚武与国防等层面的新功能与新意义,并以此引领着武术的学术转向。
(1)救亡图强源于“病夫”话语。“病夫”话语从严复眼中的“国家问题”[18]逐渐变为国民的“体质问题”[19],其后对“病夫”身体的改造成为近代体育的历史担当,以及扭转重文轻武历史惯性的新力量。同时,作为近代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自我评价与证伪的一个参照[20]61,“病夫”与健康紧密关联,形成提及健康就会联想到“病夫”的心理定势[21]。为“病夫”雪耻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22],也是“强国强种”的重要方法[23],因此,时人将习练武术视作拯救“病夫”的良药[24]。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在身体技能层面破除“病夫”诅咒成为武术的时代使命[25],致使“国民身体改造”成为新思潮[26]。以武术实现“国民身体改造”的第一步便是确立武术促进健康的合法性地位。其中,既有将武术“打”之用转变为卫生之方的健康认知[27],也有将武术视作与体操一样均以健康为目的的运动[28],以“寿世寿人”为价值导向[29],确立以“却病、健体”为主旋律的习武目标[30],描绘出“新体魄、新健康”的新蓝图[31]。
(2)以武术拯救“病夫”身体既是对国民身体的健康化改造,也是对社会尚武风气的精神重塑。时人通过军国民体育的实践[32]、“尚武精神”的社会舆论[33],知行统一地实施以武术救亡图强的社会运动,并形成了精神武术与肉体武术的新区分[34]。在以健身与尚武为功能导向的“国术救国”过程中,时人发现,与西方体育一样,武术是文化精神的载体[35],身体锻炼也是精神的锻造[36],并形成了“健全精神栖于健全之身体”[10]的新阐释。在近代武术从体操化到体育化的改造过程中,时人既试图以“国民身体改造”实现武术救国的目的[37],也时刻不忘武术对人之精神的锻造功用[38]。
(3)救亡图强语境促使武术重新与国防产生关联。在体育与强国的关联性分析中,时人重新找回武术与军事的联系。例如:谢强公[31]不仅将日本之强大归因为体育发达,而且还对日本将武士道视为“国家生命”[39]表示向往与认同;孙中山[40]以短兵相接之“最后五分钟”的决胜时刻,强调武术技击功能与民族自卫之道的关系,进而将武术重新与国家军事相关联。重回“国之大事”的武术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相关,成为民族自信的一种体现[41]。于右任将国术的意义定位于强国、救国,李宗仁将国术视作“一洗从前软弱”的希望,谭延闿认为国术是可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力量[42]。还有人将武术训练的目的单一化为军事作用,旨在增加战士的战斗力[43]。时人将服务军事战斗力训练视为习练武术的目的,强调武术的技击功能,在“存亡呼吸”之间储备“坚韧之实力”[44],积极探索“实地练习”的训练经验[45],使“武术救国”话语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种“国之大事”的立意既是中央国术馆立馆宗旨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民国成为武术发展“黄金时代”的重要原因。
总之,救亡图强的时代诉求充斥于武术学术话语,重释了近代武术在健康、精神与国防等层面的功能与意义,对武术功能与价值的新认识与新发展也引领着武术学术转向“以用为主”。
1.2 知识群体重组与近代武术学术转型
作为推动近代武术学术转型的核心力量,近代武术群体在救亡图强语境下进行了重组,其大致可分为以技术教学为主和以武术研究为主的两大群体。他们虽在西学与中学、技术与学术上存有不同的学术倾向,但都与近代体育学家一起推进了近代武术的学术转型。
(1)习武日久的传统武术人怀抱武术知识传统,注重武术传统技法的研究。例如:吕光华[46]对“基本拳”技法等武术教学文献进行整理;陈敦正、胥以谦等致力于国术技法宣传工作[47];在武术套路的继承与创新性整理方面,金一明[48]对剑术、棍术等技法进行整理,赵连和、陈铁生等对达摩剑[49]、谭腿[50]、五虎枪谱[51]以及降龙棒[52]的武术技法进行整理与创编;在技术方法与身体训练方面,姜容樵[53-54]对太极拳、青萍剑、八卦掌等技术,以及国术“四步工夫”“四层用法”等训练方法进行探索;在武术理论方面,田镇峰[55]对形意拳劲力进行研究,金一明[56]对国术技击理论进行总结与扩充等。该群体的研究与探索为日后武术挖掘与整理、非遗保护、武术技术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2)具有西学知识背景的武术人以“科学”为名开展武术研究。一方面,以留学日本的唐豪为代表,他们受科学主义和疑古派影响,引入当时的实证主义理论和历史理论,对武术之真进行了辩伪性研究。其间,虽有如向恺然、许禹生等秉承我国乾嘉学派的考据精神对拳术源流进行考证,但以西释中的研究思路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推进武术的教育化研究,不仅以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研究传统武术的技法与理论,如吴志青、谢强公等以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为参照对武术技法等理论进行了新诠释[10],而且积极推进武术理论的尝试性建构,如陈家轸[57]试图以生理学、心理学、力学为武术建构“科学之理论”。以上两类研究成为日后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既是武术历史研究尤其是拳种起源研究范式的基础,也塑造了武术教学、训练、健身机制研究的解释学框架。
(3)关注武术的体育人以现代化为主题对武术进行新思考。他们既能客观看待武术历史、认识武术的文化魅力,也能指出武术体育化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如在徐一冰、郭希汾、吴蕴瑞等的体育化武术研究探索中,近代武术研究既形成了“体操教育化”[58]的发展路径与“体育学术化”[59]的研究大纲,也成为中国体育史[60]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此类体育化武术研究既解决了武术现代化发展的隶属问题,也为现代武术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总之,作为近代武术学术转型的核心力量,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虽观念与立场不尽相同,但都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武术现代化学术转型过程中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1.3 以西释中与近代武术学术转型
在以西释中的语境中,西方体育成为理解武术现代意义的参照,对武术的体育化理解也成为时代主旋律。由此,武术学术研究浸染西学色彩,体育化的认识与发展也成为武术学术转型的底色。
(1)以体育视角理解武术的现代意义。在认识上,时人开始以体育为参照系,将武术阐释为一种“中国体操术”[58]、“国粹体育”[61]、“中国式体育”[62]、“土体育”[63]等,提出了武术的体育教育价值;以“近代教育程序”[64]、“教育原则”[65]论证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可行性;从武术的“新生命”与“新趋势”[66]出发,指出近代武术顺应时代发展而演变出的与体育相关的新功能、新意义,确立武术的科学化与学术化发展方向,试图重新打造一个类似体育的无弊端、有组织、讲科学的现代武术发展“新环境”[67]。
(2)按照体操之方式、教育之程序推进武术的当代化发展[68]。在实践上,马良以体操的口令、分段、团体教学法改革武术教学训练[69],邓莹诗将拳术、器械纳入四川体操学堂的教学内容[70],京兆地区依照“简要易行,与体育要旨既不相背,与生理卫生亦无抵触”[71]拟定武术教材,开展学校武术教育。可见,西方体育知识的引入既为武术的体育化认识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武术的知识重组与学术转型指明了方向。
(3)以运动生理与解剖学知识重释武术动作意义与运动价值。刘殿琛[72]以解剖学“筋(肌)肉”学说解释武术动作机制。章乃器等[73]以生理学中的呼吸系统知识解释太极拳“意”“气”“力”等现象;徐棫[74]以力学知识论述武术动作的重心与发力问题。沈家桢[75]以力学原理分析太极拳的动作原理;徐致一[76]以心理学知识解释太极拳“用意不用力”之说。麦克乐[77]以运动生理、人体肌动学为标准选择教材,以体操式的运动、神经肌肉合作为训练原则拟定武术教学大纲。
(4)将武术纳入体育系统并对武术运动进行重新分类。在继续强调武术的内家与外家之异、南方与北方之别、武当与少林之分[78]的同时,学界对武术进行了重新分类,如马良[79]根据体操分类方式将武术分为徒手之拳术与摔跤、器械之棍术。此外,既对武术服务不同学龄习练者[80]、男女有别[81]的功能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新的区分性论证,也将武术纳入中国体育史范畴进行重新分类。例如,陈咏声[82]在《体育概论》(1933 年版)中将武术分为徒手、器械以及游艺类,郭希汾[60]在《中国体育史》(1919 年版)中将武术分为导引、角力、拳术、剑术、弓术等。
总之,近代以西释中的学科知识重组促进了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并在“以用为主”的西方科学思维影响下产生了以下观念:凡是科学知识能够解释的武术问题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凡是“实用”的都应保留,那些不能被西学解释的则是需要去除的“糟粕”[83]。
2 近代武术群体的声音
在近代,传统武术从以武术人为对象、以训练为中心、以技艺传承为目标的本体性发展转向以大众为对象、以教学为中心、以身心改造为目标的功能性发展。由“体”而“用”的功能性转向在话语上促使“以用为主”群体成为主流,“以体为主”群体相对弱化,并在实践中形成以功能叙述为主的武术认识与发展观念。
2.1 体用之间的群体认同与话语权
近代体用观转变所引发的学术转型与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与话语权相关。主张“以用为主”的徐一冰、吴蕴瑞、张之江、谢强公等所呼吁的武术体育化、民族化发展以及普及大众武术知识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主张“以体为主”的唐豪、徐震、向恺然、郭希汾等从“何为武术”的元问题出发探究武术本体、描绘武术发展蓝图却只能局限于学界,并未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反响。
(1)主张“以用为主”的群体独领时代风骚。他们利用西学模式积极探索武术的现代化改造,如陈咏声[82]、宋君复[84]对武术科学化的提倡、对武术进入学堂的重要性的认识赢得了学界与社会的双重反响,既符合当时国人西化趋新的心态,也促进了武术知识的体育化理解,还由此获得了教育领域的体育话语权。同时,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在“东亚病夫”污名化焦虑下,武术的国家化、民族化设计[85],以及以“国术救国”话语、“国术”之定名对武术进行现代化诠释,促进了武术民族化知识的再生产。
(2)主张“以体为主”的群体矢志不渝地坚守传统。虽然“以用为主”成为近代武术研究的主流,但中国哲学向来讲求“体用不二”[86],在近代武术学术史中也不乏主张“以体为主”的群体的武术本体性研究。既有唐豪、徐震、向恺然等对武术历史的考据,也有郭希汾等对中国古代体育的研究,他们以“冷板凳坐十年”的精神耐受了“无用”研究的社会反响,为随后的武术历史研究、武术文化研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87],奠定了今日武术本体性认知的基础。另外,他们还借助社会影响力,积极创办武术组织与刊物,如谢强公、吴志青在上海创办的“中华武术会”及《武术》期刊,许禹生在北京创办的“北平体育研究社”及《体育》期刊等,积累了武术学术组织建设和学术交流的经验。
总之,不同群体的武术研究影响力不同,既体现了近代武术“体”与“用”的张力、“以用为主”的学术导向,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国情,在救亡图强、“病夫”话语的影响下更需要武术之“用”的研究。由此,主张“以用为主”的知识群体掌握了重要的话语权,而主张“以体为主”的学术群体较难得到社会回响,无法具有与前者相匹敌的话语权。
2.2 功能性发展为主,本体性发展为辅
近代中学与西学的交融经历了“中体西用”的分工之后,在民国时期“全盘西化”成为主流[88]。其后,“西用”作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促成近代武术形成了以功能性发展为主、本体性发展为辅的新局面。
(1)健康功能的发展促使武术成为“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现代医学知识和体操、体育的引入似乎改变了原先以气论、脉学、禅学、方术等传统认知组成的身体观念,逐步形成了以“劲力”“血管”“意念”等为话语的武术现代科学知识[89],甚至连拳术的改革也要以“明了生理之拳术家”或“佐以生理学家”[90]方可推行。事实上,近代武术的健康化发展还以延续千年的导引养生为基础,这是对中国养生观的现代化改造,也与西方医学的健康标准接轨,对武术健康价值的重新挖掘反映了近代“病夫”焦虑下人们对“国民身体改造”的急切期盼。
(2)教育功能的发展促使武术成为新民再造的手段。武术人形成的“格拳致知”的教育文化遗产[91]在近代成为改造“不武”之国民性的手段,促进大众健身、增进国民元气[92]成为武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以武术增强体质、以尚武改造思想的新民运动一方面以由外而内、内外并举的国民身心重塑为“以民之新完成国之新”的联动发展提供支撑,通过培养“军国民之资格”[93]进入教育体系,使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合于近代国民身心塑造的时代洪流;另一方面,救亡图强理念下传统“成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促成了武术教育可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认知[94]。
(3)体育功能的发展赋予武术“身体教育”的意义。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武术体用观遭遇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体育相关,出现以体育之“用”作为武术之“用”的新指向。卞人杰[95]认为,虽然武术的技击功能会随着“文化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而消失”,但其体育的“新意义”能得以延续和发扬。体育赋予武术的“新意义”主要体现在武术的体育功能上,这既从身体、生理、肌肉、心理等新角度使作为国粹的武术重新焕发生机,也使其应接不暇。在现代化进程中,寄身于体育的武术被赋予多种体育功能,但在其体育化、竞技化发展之后,制度建设与文化融合并未得到完善,致使今日的“体教融合”还在试图弥补这种历史遗憾。
(4)在武术本体性发展中存在争论。其中以武术是“打”还是“演”的争论最具代表性。晚清时期,人们对武术是“制胜之要”的认识逐渐脱离了拳种“门类”的束缚,开始仅从技击动作“拳掌肘脚,进退闪转之运用”看待武术的本质[79]。在近代人们对武术本体论的认知演替中,关于“武术是什么”的问题已发生改变。当时围绕武术赛事是“打”还是“演”的“张褚之争”其实是对武术本体论视野下两套武术符码系统的寻认[20]169-170。武术本体认知的演替在近代呈现为“打”与“演”谁更能代表武术的唯一性问题,至当代竞技武术中转变为套路运动与散打运动的并存问题。其本体性发展中的争论因在认识上存在套路的散打化衡量、散打的套路化评价倾向,使人们对现代武术赛事的探索存有既没有所谓的“打”也没有所谓的“演”的质疑[96]。
总之,近代武术的健康、教育、体育等价值逐步显现,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功能性发展认知,也存在本体性发展的争论。近代武术“以用为主”的学术观念转变,以及以功能性发展为主、本体性发展为辅的格局仍影响着当下武术的发展。
3 近代武术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与时代相关的学术转型是以不同的学术路径、范式展开的[97]。就近代中国学术而言,无论是精神、旨趣,还是方法、语体、文体,都处在扬弃旧范式、创建新范式的转型阶段[98]。该时期的武术学术研究从传统上对本体发展的关注转向以“救亡”为功用的实践研究,在这种“以用为主”的观念转变中,近代武术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以理论性研究为辅,初步形成以教学、健身等功用为主的“术化为主、学化为辅”的新趋向。
3.1 应用性研究为主,理论性研究为辅
随着武术体用观的转变,在“以用为主”的观念影响下,武术学术研究出现了以教学、健身等应用性研究为主、以历史文化等理论性研究为辅的发展新趋向,奠定了武术学术体系最初的格局与研究旨趣。
(1)“以用为主”的体用观对武术功能的挖掘、应用性知识的生产发挥了引导和规范的作用。例如:近代中国在“救亡压倒启蒙”[99]的历史语境下开启武术“打”之“用”的探索,如金一明[100]总结“各家之打法”,提出了武术“打”的技术与方法;也有对武术教学训练的探讨,如王怀琪[101]对拳术初步练习方法的整理,金一明[102-104]在动作图解化、教学方法化基础上编成的《拳术教材》等。但在武术应用性知识“打之用”与“健之用”新生产中还出现了脱离打的“实用”目的,更多是被赋予“强种”“健强四肢”等与健康相关的功能性解释的发展趋向[105]。救亡语境中武术应用性知识的生产既有外向性视野下“以作将来对外之预备”的“打之用”[106],也有内向性视野下对“病夫”身体的改造[20]34-39,并在内忧重于外患的趋势下将个体身体健康延伸至民族与国家的健康[107]。这种话语的转变进一步丰富了武术的健身价值与功能,形成了武术知识在运动训练、教育教学与生命健康等多个层面的转捩点,凸显武术应用性研究的重要性。
(2)武术本体化发展的新探索衍生出“何为武术”的理论性研究趋向。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以西变中”思潮致使疑古学派大行其道,武术历史发展、拳种起源研究也将证伪作为主要范式。如福民[108]对武术派别的考证,金一明对拳术内外家源流[109]与少林拳源流[110]的梳理、对搏击[111]与摔跤的考据[112],陈泮岭[113]对苌家拳的源流考等,既奠定了近代学术转型理论性发展的基础与发展方向,也使传统武术一度被质疑为“神拳”与“鬼道”[114]。此外,近代武术“以西变中”的学术转型也存在走向异化为“中学不能为体”[115]的“反失其故”之路的可能性。
总之,近代“以用为主”的体用观在学术倾向上形成了以教学与健身等应用性研究为主、以历史与文化等理论性研究为辅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作为术科的武术以“术”为先导、以“学”为总结的学术发展特征。
3.2 术化为主,学化为辅
学术之学是在“体”层面的知识积累、理论创造和思想体系建构,学术之术是在“用”层面的可操作性考量[116]。在近代武术学与术的双重建构中,“以用为主”的体用观最终形成了“术化为主、学化为辅”的研究趋向。
(1)就近代武术术化为主的学术建构而言,在武术著作出版中主张“以图传技”便于看图自学,进行“义取浅近”“便于指授”“图各有说”的新探索[117]。这不仅使传统武术“户各一门,家各一派”[118]的缄默性知识[119]演变为“不避师父秘授之论”[120]的普遍性知识,还形成了近代武术“术”化研究的新原则。关于教学之用的“术”化建构,谢强公在1931 年出版的《科学化的国术》一书中将“生理义理、符合心理、教育程序、实用”4 项原则作为“研究武术之大略”[10];关于健身之用的“术”化建构,1935 年《求是季刊》刊登田镇峰[121]编辑的《太极拳》一书的广告语,其将技击用法的“实地研究”、健身的“生理原则”、运动负荷的“动作有节”作为有别于传统武术的“不务神奇”之处。可见,近代武术研究的“术”化转型既是对“国民身体改造”实践的呼应,也是对武术教学、锻炼之用的术化建构。
(2)就近代武术学化为辅的学术建构而言,面对拳种难以考据的现状,时人以科学实证主义、乾嘉学派的考据精神进行武术新研究,如唐豪、许禹生与徐震等对少林拳、太极拳等拳种的实证研究,形成了拳种起源“故为依托,自炫神奇”[122]的附会与假托之辩证[123]。同时,鉴于“拳技之进化,本无专史可考”[8]的现实,时人既以西学视野进行武术起源的新研究,如《国术理论概要》以“生理、自卫、革命”作为武术起源的动因说[124],也对武术史料进行了基础性整理工作,如唐豪[125]“参考世界各国的体育方法”,以“军民两用”为目标,进行传统武艺目录学整理。可见,近代武术的学化研究为随后的武术研究及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难能可贵的基础。
总之,近代武术的学术转型虽从对传统武术重术轻学的不满起步,面对“若推论武术发生的原因与生理之关系者,如凤毛麟角,实不多见”,在痛感“惜无原则昭示,终有理论乏缺之感”之际,将“有原则定律”的近代科学作为近代武术学术转型发展的目标[124]。但实际上并未撼动近代武术研究以术为主的发展格局,其“学化”努力仅是“术化”系统建构的辅助。如其间少林拳“是不是来源于达摩”的考证、“武术有没有健身功效”之论等,还未能在“学”的层面展开对“为什么”的“深描”。时至今日,这种术化为主的学术倾向仍影响着武术研究的选题、设计与成果。如此作为术科的武术,其学术构建可能不得不建立在“术”的基础上,其“学”应是对“术”的特征的理论化。
4 结束语
回到李泽厚提出的救亡与启蒙话题,在以西释中与救亡图强语境下、“国民身体改造”的实践中出现的“以用为主”的近代武术学术转型既是对“武术何为”的“用”之新实践与新认识,也有对“何为武术”的“体”之实践与认识。虽然二者存在主次之别、强弱之异,也呈现出以“用”为中心、以功能性发展与“术”化研究为主旋律的特征,但无论是体育人(如吴蕴瑞)、传统武术人(如吴志青),还是现代武术人(如唐豪),其在推进武术功能性发展、“用”之导向的研究时,也对武术的本体性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当然,学术转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近代武术以功能性发展为主、本体性发展为辅的发展格局,术化为主、学化为辅的学术态势可能正是其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其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本质。今天以武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传统体育学正因服务于不同时代与社会需要,才赢得其本体性发展的可能,正因其“术”之基础,方有其“学”之特色与主体。
新时代高质量的武术发展与学术研究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目标中,以文化自觉的姿态进行武术之“用”的新开掘,继续进行“术化为主,学化为辅”的新探索,以此推进以武术为主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建设,走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作者贡献声明:
刘红军:收集资料,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校对论文;
刘 洪:收集资料,撰写、修改、校对论文;
戴国斌: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提供理论指导,修改、审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