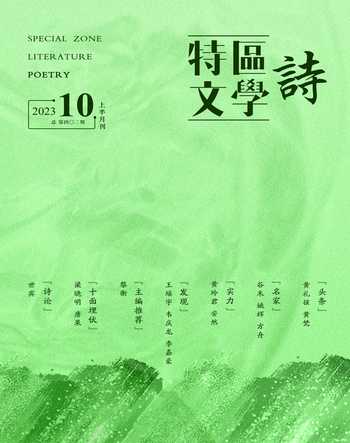诗的杂记
黄梵
好诗人不受时间的影响,
时间只会让他们深思,寻找不同的途径去深入诗歌这个文体自身……
一
藏在诗中的诗意,是看不见的,读起来却能感知。老有人做傻事,想一劳永逸,欲借定义的“无所不能”,和盘端出诗意的所有家产。他们刚把过去时代的诗意家产摆进盘子,新时代的家产又在来临。诗意会随时代嬗变,无法拥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贡布里希已在早期艺术中发现,艺术会随时代、地域嬗变。为了避免定义失效,贡布里希索性宣布,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言外之意,不同时代、地域,艺术家做的作品,就是艺术。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的汉语词典,为了避免罗列诗意家产的尴尬,换了法子来解释,它说诗意是“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类似贡布里希说的言外之意,艺术是艺术家做的作品,但诗意不是“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的全部,只是其中“给人以美感的意境”这一部分。如是将了解什么是“美感”“意境”的任务,推给了读者。美感和意境的含义不只随时代变迁,它们深邃的程度,较诗意也不遑多让。为了避免把此问题推给彼问题的接力赛,我打算另起炉灶。
二
迪萨纳亚克发现,早期艺术(含诗歌)也是身体需要——身体对陶醉、舒服、触动的需要。现代诗在初期为了我行我素,把传统、大众、世俗生活视为敌人,一味孤高,无形中将诗只看成语言现象,将诗与身体需要割裂开来。这一流毒,至今随处可见。我认为,不管现代诗人如何羞愧于谈论诗的生活效用,竭力要让诗丢下生活不顾,竭力把诗只视为一场场语言的大小革命,诗还是不会忘记它与身体需要的早期联系,谁要以为这一联系如今已不复存在,那说明还未懂文明。诗既然是文明的一种嗜好,就必是身体需要赋予的,就必有人类学的依据,必会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种种行踪的蛛丝马迹,令我们可以找到诸多的人类学证据。早期诗如此,现代诗也概莫能外。毕竟诗不是为石头写的,是为人写的,藏在诗背后的人性,从古至今没有变,仍是怂恿创造那些语言现象的“教唆犯”。就像人性创造的文明,会维护人性的发展,诗作为文明的体现,也会与人性的需要保持一致。那些与诗相关的人性需要,必会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引起身体的一些特殊感受,或陶醉,或舒服,或触动等。维科在《新科学》中说,“诗人们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感官”,看来,他已觉察到诗性与身体需要的联系。
三
我自己的写作,经历过若干风格。一开始,以为找到了个人腔调,可是里面隐着太多公共腔调,写了四五年,我注定走向了公共腔调的反面,这时又丢失了对客观特性的尊重,令作品只是个人编造的密码,并不试图让他人解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对歌德说的客观特性,有了体悟,它就像自由诗里的声音结构,可以说服任何人,说服任何时代,只要处理得当,你可以像古代格律诗人那样,同样找回自己的个性。歌德屡屡谈及,受限中的自由,不少中国读书人将之视为鸡汤,殊不知歌德触到了人性的核心:悖论。不管人既求安全又爱冒险的悖论,是来自心酸的原始生存史,还是来自社会和个人的博弈,人的这一本性,实则“规定”了人类命运、文化、奋斗的风格。比如,它“规定”着人对自由的“合度看法”——自由的可贵就在,有拒绝的自由。拒绝本是让自己受限的行为,比如拒绝利诱、功名等,可是退后一步的生活里、自我限制的生活里,有更舒展的精神自由。格律诗人因为遵从格律,且格律化入了血脉,不再焦心对声音结构的搭建,诗人就获得了表达内心的自由。相反,一些写自由诗的诗人,因为无视自由诗中的客观特性,企图夷平一切,在废墟上写作,结果恰恰激发了读者对不安全的恐慌,造成阅读排拒。没有安全背书的自由,或没有自由的安全,都会成为写作中的暂时工程,是争得一时而不是争得一世的“最后晚餐”。这些都来自对人性的无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是对个性解放的期待,让他们产生幻觉,以为只要人解放了,人的共同体就会走向正途。殊不知,确立一种善,也会损害另一种善。比如,你爱子,给他过多的钱,爱之善,会损害自食其力的善。你为情义,提拔友人,重义之善,会损害公平之善。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乍看是命运所为,实则是人性所为。追求个性解放,就得接受人性幽暗的解放,任何追求没有杂质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因为它违逆人性,这是人跟机器的根本差别。所以,受限中的自由,指出了尊重人性悖论时,调节个性与客观特性的正途。歌德早年为“狂飙突进”呐喊,开了个性解放的风气,晚年他用古典艺术中的客观特性,来约束个性,寻求限制中的解放,可谓成就了《浮士德》。两个时期的差别,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可见一斑。当代作家普遍弃《维特》,选《浮士德》,印证了歌德晚期主张的耐久。
四
我目前诗歌的写作风貌,应该说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我基本结束了探索期,从此前自诩为先锋派的语言诗,开始转向所谓“后卫派”的生命之诗。这么做的结果是,我的诗从探索新诗的可能性,转向完善某些可能性。九十年代初在参与“原样”期间,我已留意诗歌完成度的问题。一方面,车前子的语言开拓天赋和勇气,令我震撼,自叹弗如,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就藏在我诗中的经验意识里,迟迟不肯退场。直到一九九六年,当我分出部分精力写小说,伴随生命的经验之力就突显出来,也一并改变了我的诗歌。意象大量出现,并非是始料不及的事,八十年代我已着力此道,只是那时,对语言实验、意象的各自功能,认识不清。我以为,我个人的诗歌转向,与新世纪新诗的整体转向,是同步的。“后卫派”与“先锋派”的并存,或说相互容忍,也成了新世纪新诗值得称道的景观。这样我就有机会,把本雅明式的前现代诗歌救赎思想,“诗言志”“天人合一”的中国信念,与悲观无常悖论的现代经验,融为一体。我之所以调侃自己为“后衛派”,就是着眼完善之责、之事,把上述“杂念”融入诗歌时,会逼迫自己做到了无痕迹,仿佛那只是主题的本性而已。显然,我只在少量诗作上做到了,多数诗作并未达到预期。当我回头审视自己的诗歌,很吃惊意象一直贯穿其中。如果跳入潜意识的大海,大约能看到祖父对宋诗的无尽抱怨影响了我。
知道用议论也能写诗,与知道用议论写诗的局限,完全是两回事,其中的不寻常的道理,我写诗多年后才了然。前者依据的是文学史,后者依据的是人性,谁会根深久远,可谓一目了然。祖父认定宋诗不如唐诗,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他把宋诗的议论,视同读者“猜谜语”之前作者就亮出谜底,不像唐詩擅用意象暗示,让读者既有感官感受,也有猜的余地和余味。意象可以避免与人性冲突的道理,我已写入《意象的帝国》一书,不在此累述。但我想略微提及,意象与现代诗的关系。千百年来,一直听命于旧诗词的意象,还能成为现代诗的主体吗?记得十多年前,我写过《诗与事》一文,认为意象的天地,仍是值得当代诗人抢占的天地,除非像宋人那样,面对唐诗收割完意象后的低产田,只能转而求其次,开始朝诗里注入过量议论。我以为,用议论写出好的当代诗,是天才和勇者的事业,不是我这样的“后卫派”可以染指的。上天给我的任务,似乎是去完成意象的现代化,以问心无愧的古典式明晰,来接近当代意识的变动不居,甚至即兴的瞬间体悟等。思想哪怕再智慧、深刻,如果不能成为意象的助手,而是喧宾夺主,我仍会将之视为自己诗作的缺陷,视为思想向形象的转化并未彻底完成。就如最近才译入中文的美国诗人罗特克所说,“在诗中要把思想当成是附加的”(王单单译)。这一认识的起源在人类早期,诗歌在文明进程中,会落下文化负载太多的毛病,让诗想起它的初衷,不时回到它的原始审美,是更新文化负载的明智之举。
五
面对开垦才百年的新诗意象,我会将之作为写诗的首选。用意象来更新“诗言志”中的“志”,这事做起来并不简单,可能需要一种摆脱文学史的思维。比如,按照文学史分类,用意象写诗,只是意象诗、叙事诗、哲理诗、抒情诗、自白诗、投射诗、即兴诗等中的一种,但如果让视线穿过这些概念,抵达诗句本身,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诗中只有两种东西,一是直抒胸臆的议论,二是客观的或主观的意象。叙事诗也可以看作是由意象和议论合作的诗体,只不过与抒情诗相比,客观意象会在叙事中占据主导。显然,这是回到诗歌原点的思维,能让人看清诗歌的底层逻辑。当然,我习诗四十年也得承认,就算营造意象的技艺已娴熟自如,我仍需要一些神秘的时刻,来让意象抵达化境。那时,面对瞬间想出的神奇意象,我会有宿命的感觉。也正因为有宿命之感,思想或情感堆积的时刻,又常常找不到心仪的意象。有时看别人的诗,也能看出那些困难的时刻,有的“别人”等不及最佳意象出现,就拿次好的意象交差。我过去常这样“优待”自己,令诗句或诗作的完成度打上折扣,现在我对自己严苛起来,会花时间摸索或等待那些时刻。写出次好的意象,只需要技艺娴熟,写出最佳意象,还需要因缘际会。困难不只来自有无天赋,还来自心绪的注意力够不够、对生活的敏感度够不够、生命的体悟到不到位。
总之,按照我祖父的语汇,在该做“唐人”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提前做“宋人”。但对那些勇于跳过“唐人”,去做“宋人”的当代诗人,我会怀着敬意,持续关注他们竭力为新诗打开新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