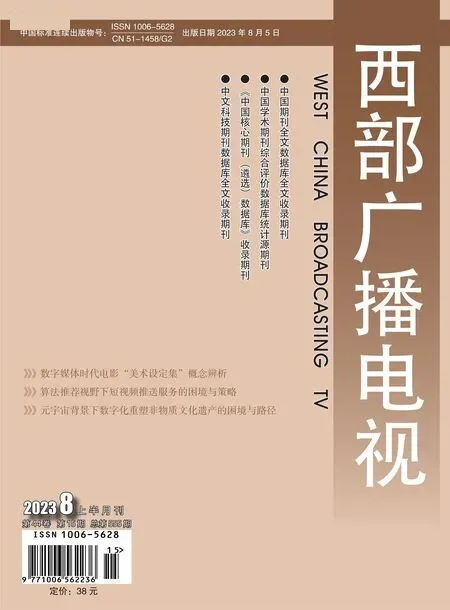探寻“自我”之路:电影《唐人街探案3》的主体性消解
金蒙兰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从2015年《唐人街探案1》(以下简称《唐探1》)的横空出世,到后续通过电影与电视两种媒介扩充构建的故事宇宙,“唐探”这个品牌符号已经发展成熟。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以下简称《唐探3》)以45.23亿的总票房位列中国电影总票房排行榜的第六位,“唐探”系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成功案例。《唐探3》延续了前两部的“喜剧+悬疑”的路线,在“犯罪大师”(Crimaster)排行榜这条中心线索下,主人公秦风与唐仁受野田昊的邀请前往日本探案[1]。
在类型片中,角色性格的塑造与人物的正反阵营划分总是十分清晰,而在整个“唐探宇宙”中,许多角色却定位模糊。《唐探3》全片将日本黑老大密室被杀案与“Q”集体设计秦风杀人两案嵌套在一起形成“案中案”叙事。而推动构成《唐探3》“案中案”叙事的人物情感线索也有两条:一是本影片主要角色小林杏奈对父亲渡边胜的亲情复仇,二是铺垫在“唐探”系列故事中的基本设定,即主人公秦风对完成“完美犯罪”的渴望与“Q”集团不谋而合。“善与恶”的阵营选择是悬疑罪案类型片主人公永恒的追问,《唐探3》中的主人公同样随着“案中案”的层层嵌套递进而探寻着“自我”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角色的主体性不断被消解,统一与理性的主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是先天存在且具有碎片性的“自我”。
主体性的讨论来源于近代主体哲学的兴起,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变成认识的主体。随后尼采宣告了“上帝之死”,彻底斩断了超经验物对人进步的阻碍。米歇尔·福柯在尼采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证明了人的有限性、历史性以及不充分性[2]。当主人公唐仁和秦风在日本东京涩谷街头撒钱通过最后一关考验之时,巨大的电子银幕上出现了这句话——“我是谁,我在哪,我让你们走了怎样的路”。这似乎有些探寻主体哲学终极的意味,角色的“自我”探寻和善恶选择更加扑朔迷离,为影片的悬疑部分添光增彩。
1 选择与扮演:统一与理性的“自我”缺失
巴什拉认为,认识是不连续的变化过程,现象世界和个体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全片表意上建构了两个完美犯罪,影片的第一个案件便是渡边胜、苏察维、小林杏奈三人的密室案。影片将渡边胜这个角色设定为日本的黑帮老大。然而当案件抽丝剥茧,他的身份转变为了一个不正视历史、抛弃家庭的懦夫。到了最终,他变成了一个愿意替女儿顶罪的父亲。这种角色的定位由强转弱,这一变化除了增加故事的悲剧性、创造情感价值之外,也是对这个角色主体性的一次消解。
而故事的内核将渡边胜这个角色内心最深层次的痛苦设定在更宏观的家国背景下。二战结束后日本移民被遣送回国,他们的孩子却留在中国变成了“战争遗孤”[3],渡边胜与小林杏奈这对父女的悲剧来源于这个宏大的时代问题。女儿小林杏奈作为“战争遗孤”的后代在法庭上回忆起自己与母亲在日本的苦难生活,不仅在叙事上将影片推向高潮,也让渡边胜这个父亲形象的复杂度加深。他本是日本先遣团的后代,却被留在了中国,随后又将这种苦难转嫁给了自己的妻子与女儿。他的妻子和女儿不被日本社会接纳与重视,而他却在另娶后重回日本精英阶层。尽管影片最后角色阐述作出这一切选择的身不由己,但是这一悲剧还是基于渡边胜所作出的选择。
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考古学方法”,通过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来达到对历史主体的批判,最终达到“消解主体”的根本目标。影片通过文身、社团聚众等叙事隐喻展示渡边胜这一角色所拥有的权力,暗示渡边胜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小林杏奈对第一案的解密,渡边胜抛弃小林杏奈母女的过往也被揭开,他变为一个战争背景下“无情”的男性。而最终他愿意替女儿小林杏奈认下罪责,并悔过当初抛弃家庭的举动时,他又变成了一个“有情”的父亲形象。渡边胜这一人物的形象转变又可视为是其“自我主体”确立的转变,渡边胜黑帮老大的身份正是由“抛弃”家庭这一选择而来,影片最后替女儿认罪的行为似乎更像其为了重新确认“自我”的救赎。米歇尔·福柯认为主体是被选择的,是被知识建构的,是被权力规训的[4]。在《规则与惩罚》一书中,他提出每个人都会被规训成现代文化所需要的个体,每个人的身份也都是权力关系所导致的结果。每个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力。渡边胜在黑帮老大、丈夫、父亲三重身份之间转换,涉及两个国家、家庭,乃至阶级。究竟哪一重身份是渡边胜真正的“自我”,影片并没有给出答案,在多重身份的扮演之中,角色主体的统一理性不复存在,主体具有了碎片性。这是影片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第一重回答。
2 选择与规训:“自我”的非本质性与非同一性
影片的支线案件是“Q”集体对秦风的考察,这个“Q”是整个“唐探宇宙”叙事最神秘、反派阵营最鲜明的角色形象。“Q”与主人公秦风的较量从《唐探1》进展到《唐探3》,在《唐探3》中“Q”邀请主人公秦风加入并设置了三个关卡对其进行考验。这些问题与考验是对主人公智慧与体力的测验,也是其人性明暗面的选择展示。主人公秦风回应“Q”的过程,就是他追逐“我是谁”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主人公秦风作出的一次次选择对其先验主体的瓦解起到进一步支持作用。
“Q”集体的思想是“这个世界是由一小部分的精英推动”,从整个“唐探宇宙”的故事核心上来看,“Q”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掠夺,才是真正的完美犯罪[5]。他们在考验前先向秦风抛出了一个问题:三个穷人分两块面包,只切一刀,如何实现公平正义。影片借由野田昊指出了其核心: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呼应了影片开头出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重隐喻叠加在一起引出了“Q”真正想问秦风的问题:什么是公平?秦风作出的选择是杀掉一个人,两块面包分给两个人就是公平,这个选择使得角色明暗面的定位更加模糊。将这个问题设置在三个关卡之前是“Q”在寻找秦风身上的“Ursprung”(起源)。米歇尔·福柯认为寻找起源就是在寻找对方的同一性和本质性,但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这些本质是个体建构出来的。唐仁、野田昊代表的正向世界认为主角秦风始终是正义的,而“Q”所代表的反向世界通过这个问题的设置看到了秦风人性中的恶面,正如影片结尾秦风手上拿着的莫比乌斯环所揭示的一样:善恶并非对立而是彼此纠缠。主体有着局限性,而“Q”却认为自己所代表的精英阶层有权力对公平正义作出审判,而这恰恰才是不公平的根源。
“Q”集体为秦风设置的第三个关卡是在涩谷街头数绿灯期间通过的人数,但是由于三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在红灯时匆匆通过人行道,主人公秦风在第二次机会回答错误。在米歇尔·福柯的主体哲学中,权力机制本就是一种规训手段,红绿灯是这种权力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规则的精细化后更精准地用来规训人主体的技术。“这就是人性,法规是没有办法控制人性的”,“Q”对这三位不遵守交通规的行人作出的评价恰如其正在做的事情一样,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权力)之上,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由意志或者其他途径获取自由。事实上,闯红绿灯的人即使闯了之后依旧被摄像头精准记录,人一直处于权力的规训下无法获得绝对的自由,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建构了“自我”,即这种“自我”是被建构出来的,是非本质性的存在[6],这一关的红绿灯探讨与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的“我是谁”隐喻了现代人在权力规训下“自我”主体性的逐步消解。
从中世纪的“神是世界主体”到笛卡尔、康德的“人是世界主体”,人被赋予了极大的尊严,有了几乎和神相同的地位。当秦风顺利通过三个关卡的考验来解救人质时,他又面临一个事关角色人性变向的重要抉择:只有杀掉绑架者才能解救被绑架者,牺牲部分人的生命来换取公平。村田昭诱导秦风杀掉恶贯满盈的他解救无辜的人质,“Q”借由村田昭说出了“现在觉不觉得自己和神一样”这句台词,彻底揭示了“Q”集体将自己当作了高高在上的神来审判世人。这个抉择其实同考验前“穷人分面包”的问题如出一辙,将电子屏幕上的游戏界面搬到了现实生活中切实需要牺牲个体生命的语境中来,然而“自我”一直处于变化当中,选择当然也会发生改变。影片的最后洗清了秦风并没有对村田昭动手,奠定了角色的正向基调,也佐证了米歇尔·福柯的“自我非同一性”的观点。纵观“唐探”宇宙,“Q”集团始终对主人公秦风有着莫大的兴趣,而在《唐探3》的影片中终于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因为“Q”觉得秦风与他们是一类人。影片利用秦风通过“Q”的三次考验的设定来强化这种联系,但是秦风在既想要达成完美犯罪又熟知“Q”的思维后,还没有加入“Q”这一“恶”的阵营,秦风在“善与恶”的挣扎中确定“自我”,影片也由此来引出更深层的思想内核:“法规”也许没办法控制人性,但人作出更“光明”的选择是因为他的人性本来就是“光明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作为个体来审判公平正义,这是影片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二重回答。
3 选择与追溯:人物群像的“自我”归属
“唐探”系列包含三部电影与一部网剧,“唐探宇宙”为角色塑造提供了多维度的叙事线索。用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可以从众多的线索、繁多的人物中梳理出人物的群像归属,以此抵达角色的内核。米歇尔·福柯指出,“谱系学是灰色的,是精雕细作和耐心的文献研究”[7]。观众在众多“唐探”文本中寻找散落的线索从而拼凑出角色完整的谱系,这是“唐探”系列作为悬疑罪案类型片的“悬疑感”在戏外的延伸,能够为“唐探”故事的延续增添活力。米歇尔·福柯认为:“谱系学则有一种不可或缺的谨慎:它在……被认为绝无历史的地方——情感、爱、良知、本能——窥伺着这些事件;并抓住它们的重现……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8]由此可见,追溯角色的情感与性格是窥见角色谱系的必由之路。
整个“唐探宇宙”中事件的主人公可以划分为少年、草根、权威[9]。少年是秦风,草根是唐仁,而权威在《唐探3》中则是多面的,他是陷入密室杀人风波的渡边胜,是背叛警察体系的田中直己,是绑架者村田昭。电影对人物的塑造摒弃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表面上秦风只是一个热爱推理、说话结巴的高中生,当用谱系学方法去探寻人物内层的“自我”时,他高中生身份的天真无邪让他对善恶难以彻底区分,他对真凶有着惺惺相惜之感,对许多侦破案件的线索是自然而然感知到的。这背后隐藏着对这个人物设定的最大疑问:他是否也拥有着和凶手一样的思维?唐仁这个角色的定位是草根,草根也就是普通人。唐仁贪生怕死、贪财好色,喜欢耍小聪明,在影片中主要起到娱乐气氛的作用,消解了探案时紧张的氛围。当用谱系学方法去探寻人物内层的“自我”,人们又会被他的真诚、对待外甥秦风的重情重义所感动。权威是出现在生活中的他者,他会与你同行,也会与你分道扬镳。高高在上的黑老大渡边胜、正直的警察督长田中直己、恶贯满盈的村田昭,随着影片叙事的展开,用谱系学的方法能够梳理出这些角色的背面,寻找到其群体中的独特之处。在电影世界中,整个“唐探宇宙”将人物归为三大类进行人物群像归属划分,又通过谱系学的方法让观众揭开角色背面的“自我”独特之处。银幕中角色游弋于不同群像归属边缘,不同的群像通过案件产生交集,相互认同又相互背离。米歇尔·福柯反对现代自我观,即有意识、统一的主体才是自我,“主体性”是指人的主动、能动和创造性。但是在米歇尔·福柯这里,自我是没有“主体性”的。当“自我”不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而是由历史、文化和权力建构出来的时,影片开头所抛出的宏伟的哲学框架被支撑起来,银幕与现实世界的壁垒被消弭,观者在进行更深入人性的哲学辩证思索。
《唐探3》相较于第一、二部来讲弱化了推理,更强调“唐探宇宙”的整体架构,作为第一阶段的完结篇,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影片的关注点由案件转向对角色的思考,不论是因为年轻时作出的选择而造成十多年后父女悲剧的渡边胜,从最初就“想要创造一次完美犯罪”到现在终于作出正向选择、站在正义阵营的秦风,还是表面贪生怕死实际上对外甥秦风有情有义的唐仁,角色的塑造立体多面。影片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我是谁”“选择”之类的确定主体性的疑问,但最终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世界有明有暗,“自我”中也有着“善与恶”不同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