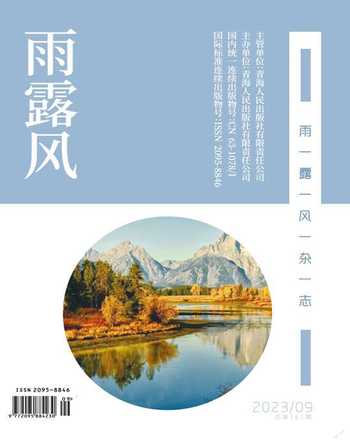论《十四行集》的成长隐喻
蔡雅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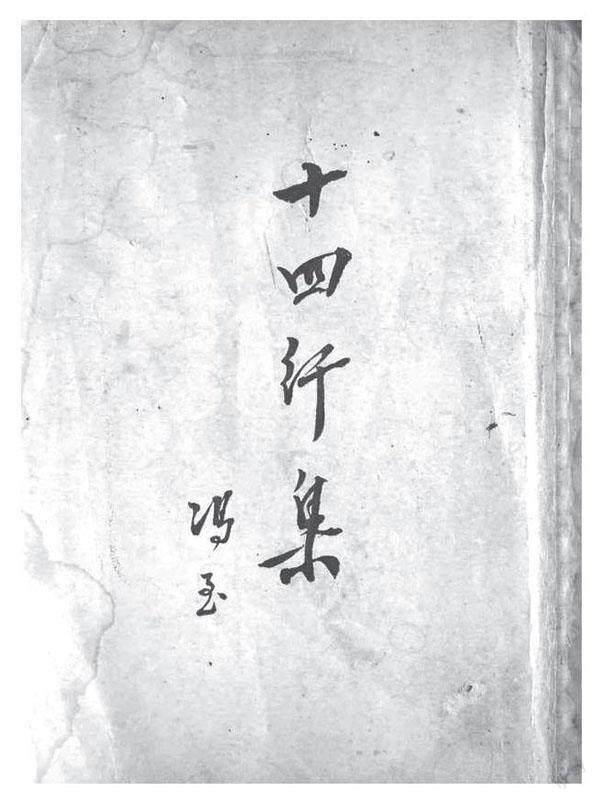
冯至(1905年—1993年)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十四行集》是他自身创作历程中的高峰。诗集展现了一个本真诗人在抗战救亡、民族矛盾激化的现实中“借异镜、磨己镜”的努力,暗含着精神成长的隐喻。这种隐喻并不局限在修辞层次,而是一种认知现象,对诗人的思维方式、语言使用和作品氛围构成主导性影响。本文将以《十四行集》为对象,探讨冯至笔下“成长”之题的隐喻,从中分析诗人如何在时代动荡中走向抒情的深化与自我身份的再确认。
一、成长命题的提出
受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1926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1832年)影响,《十四行集》所做的工作是将日常可见化为不可见的奥秘,再化为可见的诗篇。而本文将重点探讨从“可见”到“不可见”这一阶段中诗人是如何挖掘世间秘密的。这一阶段要求诗人不断“走一条生的”(第26首)路,而走新路的前提就是追问、探索、期待、创造。1941年,冯至写下的第一首十四行诗《一个旧日的梦想》正暗示了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这种追问精神与这首诗中的“陨石”意象有关。作为石头意象的一种,陨石本身带有“坚硬、粗糙、苍老等形而下的外形”。诗人便借陨石为旧梦赋形,完成由无形到有形的创造,让陨石作为艺术中介物传达梦与自我的沉默、坚硬与失落。诗人、旧梦、陨石三者合一,产生同频震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交流即使在沉默孤独中产生,也蕴含着一股新生的力量——石头具有创世、诞生的色彩。冯至在写成的第一首诗中提出陨石意象,显示出静极生动、无中生有的精神,暗示着《十四行集》是一场诗人不断开凿、思索与追问的精神成长之旅;也是人类不断探索并吸收天地精华而成长的寓言:《十四行集》以“追问”重新审视自我、他人、存灭、来去、变化等困惑人类千百年的难题,接通屈原《天問》的探索传统。例如“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第20首)等句。除直接的问句外,诗人还展示推演的过程,例如第15首为了提出“什么是我们的实在”这一问题,诗人从驮马——货物、水——泥沙、风——叹息、鸟——天空、我们——山水等几组关系中步步追问着。
在追问中,诗人处于从孤独茫然状态向自洽静默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追问因此成为一种“仪式”。人类“成长”本身需要仪式,以此确立自己进入下一阶段的身份。《十四行集》则以追问作为成长仪式,写出人类思想、感情、智力、道德、精神等方面不断走向成熟的各个阶段,并指向无穷开放的境界;且能从一己而至于人类,《十四行集》的隐喻思维本身也带着无限的延伸感。
二、成长寓意的深化
诗人所面临的不同阶段的历练可简单概括为:阵痛——顿悟——开放。
第一度成长,来源于考验中的阵痛:诗人必须以“整个的生命”承受恐惧与别离。《十四行集》第一首即以“彗星”意象比喻个人要承担的一切突发性事件:“我们准备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第1首)。”“彗”字的本义为“扫”,动词,暗示了一种强烈的力量,这与冯至笔下“狂风乍起”的意境相通;而彗星在历时性的语境中已成为灾难的象征,诗人却如“登九天兮抚彗星”(屈原《九歌·少司命》)一般,在恐惧、敬畏之中与突发事件同在。他用“承受”“深深地”等词表示自己生命的阻滞,只为迎来“更加强烈的喷射”(康德语)。诗人就在毁灭与诞生相互转化的辩证法中开启了《十四行集》;故而第一首诗作为诗集序曲是言之有理的。除了“彗星”降临的考验,诗人还在威尼斯忧虑孤独、在原野上聆听啼哭、在驮马队伍中思虑、在狂风暴雨中的小屋惊颤;他“忧患重重”……此刻诗人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他的问题充满了困惑与忧烦。
第二度成长,源于生命走向澄明之前的顿悟。诗人在物(有加利树、鼠曲草、小狗、静物)与人(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高)的启迪中发问,获得了真理体悟:宇宙万物、自然本身有一种静默运行着的秩序,它“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第13首)。在诗人看来,这种脱离语言而存在的秩序首先运行在一个凝固的时间里——瞬间化入永恒或永恒凝为一瞬。诗中小昆虫交媾的瞬间、我们拥抱的一刻是瞬间进入永恒;无时无刻不在生长与脱落的有加利树、没有停息的啼哭、“只感受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则是永恒化作瞬间。诗人的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农耕型社会安土重迁的稳定性有关。中国古代传统抒情诗成就高于叙事诗,也是由于受到这种循环生存经验的影响。然而,《十四行集》却并未走向传统的抒情诗。这是因为冯至在西方线性时间观影响下将“时间”重新阐释,达到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第17首)。”对于冯至而言,真理就存在于凝固循环与线性前进辩证统一的时间中。
在物理空间上,诗人认为真理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他呼吁“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即人对自然应保持缄默,不妄下判断。正如海德格尔认为要“让存在者成其所是”。这种态度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即是一种“静默”的心理动作。首先,诗人以静制动。他面对自然时总是保持着观察顺应、祷告祝福的沉潜姿态而非无限的扩张、解放。不管是“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第2首),还是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视有加利树为引导、向鼠曲草祈祷,人劳碌着的占有意志都得到暂时休息。其次,诗人还能以静促动——以静默之力促进自然呼吸之律动。例如“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第21首)、“深夜又是深山,听着夜雨沉沉”(第22首)表示自然间一切都在沉淀、酝酿,到了顶点才开始释放,“一天雨云忽然散开,太阳光照满了墙壁”(第23首)“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可是融合了许多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第20首)。也写出积聚后的分裂,还有不断向上生长的有加利树和不断向下沉埋的死者,自然就处在这积聚与释放、扩张与收缩的永续循环中。一虚一实,有无相生,万物由此而来。如《逍遥游》里所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人也在自然浩大的吞吐之间获得生命——“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颗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最后,自然通过呼吸与众生进行讯息交换。例如自然将光明信息带给初生小狗;吸进的气体“在身内游戏”(第25首);但我们的生长与忧愁也在呼吸间传给自然,“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第16首)。由此读者可以想象,《十四行集》背后蕴藏着一股由出纳、隐现、聚散等变化形成的恢弘气势与吞吐力量。
三、未完的成长历程
那么,这种存在于时、空中的秩序是什么?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是脱落与生长同在;是通过否定重塑自我;是与宇宙万物联结、沟通;是在蜕变中进入永恒……这些秩序有什么意义?1942年,冯至在《昆明日记》中写道:
“战争把世界分割成这么多块彼此不通闻问的地方。两三年来,到过这山上来的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一些不能通音讯,而且有的已经死亡。对着和风丽日,尤其是对风中日光中闪烁着的树叶,使人感到一个人面对着一个宇宙。”
可以说,秩序的意义正在于联结孤独的个人和旷远的宇宙。实际上,个人也是一个小宇宙。《十四行集》则进一步展现大宇宙对小宇宙的吸引力——“我们不知已经有多少回//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第20首)。故而诗人喊出“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宇宙”(第22首);并时常回忆起来自宇宙母体的原始记忆“海盐在血里游戏——睡梦里好像听得到/天和海向我们呼叫”(第25首);有加利树插入晴空、永向苍穹才能“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第3首)。诗人还以“彗星”“星辰”“星秩序”“陨石”等天文意象,展现对于宇宙精神、宇宙运行规则的向往;又以“长庚”“启明”隐喻蔡元培、以断线“纸鸢”形容战士。从表面而言,战士凋落了;但实际上, 诗人指出堕落的人们已不能“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第9首)。在《辞源》中,鸢为古代一种猛禽之名。“不能维系”与猛禽的内涵相通,传达出挣脱束缚、向大宇宙而飞的渴望与人的辽阔天性。这种永远向上的姿态才是成长的第三阶段。总之,当诗人一个人对着一个大宇宙,其背后的精神状态并不会永远停留在孤独茫然上,而是永恒的眺望与向往。最后一首十四行诗中的“奔向远方”“但愿”等语正暗示了这种动态开放的神圣之旅。
同时,从整体解读《十四行集》,会发现这三度成长在诗集中并不是线性铺开而是纠缠难分、反反复复的——成长之路向来迷途遍布。例如,在第6首诗中,诗人将啼哭、绝望作为负面因素纳入叙述,显示心灵的挣扎与愁虑;但在第3首诗中,诗人通过有加利树又看到了脱落衰败与成长壮阔的对立统一。它的生长越过单纯的时空,迈入广阔的宇宙——向四周敞开,又把有关联的一切聚拢于自身,构成了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有诞生和死亡、灾难和祝福、胜利和耻辱、坚韧和衰退……有加利树由此成为宇宙万物命运的象征与抚慰人心的力量。在第21首诗中,暴雨又“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诗人便试图从微渺的命运中走出,在爱情、亲密、夜晚三维构成的时空中,认识到自己暂时的生命中也“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第18首)。正是这种能力给了诗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骄傲,坚信能“在深夜吠出光明”(第23首)。总之,“奔向远方”的渴望与反复曲折的磨练激发出诗人向死而歌的勇气,也提示着成长永续、未完的状态。生存真谛最终在这种精神化时间、空间中翻腾延续。可见,在《十四行集》中,诗人是以对生命“内在的信心”对抗焦虑孤独的生存体验,使之不流于过分的感伤虚无或矫揉造作;另一方面,又以衰败、寂寞、死亡作为人生的底色,使乐观的信念不过于浮浅。这让诗集既沉痛又旷远,既洒脱又执著,既苦涩又明净,既日常又玄妙,展现出冯至不同于王国维、郭沫若、李金发、穆旦、海子等人的精神气质。
四、结语
《十四行集》在追问中成长,并以开放性的姿态指向一个盘旋蜿蜒不断向上的诗国,摆脱了早期现代汉语诗歌抒情泛滥、流于感伤或说教的倾向,走向沉稳而有节制的深度抒情。有学者指出,冯至“建立了另一片形而上诗国:积极、温馨、宁静,对生命持有内在的信心,对世界怀有广大的同情,他的形而上观念呈现一种积极的建设姿态”。而本文认为,这种积极的建设姿态正来自于《十四行集》由陨石意象、追问姿态而延伸出的成长主题。郑敏师承冯至,她的诗歌也倾诉成长的渴望:“一个灵魂怎样紧紧把自己闭锁/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为了就将向一片充滿了取予的爱的天地走去。”从冯至到郑敏,追问、沉思、挣扎、成长相互融合,让中国现代诗歌中形而上的诉求不至于过分流连虚无、阴暗与怀疑,而多了几分向死而生的勇气。
在朝不保夕的战争年月,死亡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但冯至“向上”成长的姿态并非远离时代、固守在西南联大的象牙塔中,反而是为了“向下”潜入时代深处,走出早期的浪漫,避开浮浅的叫喊,在诗歌内部挖掘与时代崇高相呼应的质素、与时代卑污相抗衡的力量。诗人就在与时代的疏离与紧贴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他和他的时代是共生与对抗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都曾有过类似的观点: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这种反叛者的身份也贯穿着冯至的一生。在冯至1991年写的诗歌体自传中,“自我否定”是一个关键词。如上文所述,诗人是一块陨石,开凿的力量正来自内部的否定。由此撬开的身心裂缝是促成冯至吸纳外部讯息、自我成长的重要力量。“他一生都在省审,都在寻求精神的故乡,都在与自己身上的孤独、怯懦作斗争。不断克服,使他总是从人生的一个境界达到另一个境界,正像他自己讲的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尽管有时这些克服仍为后来的克服所否定,但整体的过程却显示了一个现代知识者独特的精神轨迹,创造了生命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从《十四行集》到冯至“未完成的自我”,都向读者昭示:人类永远踏在一条开放性的完善之路上。
——冯至《蛇》的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