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细雨中呼喊》中虚构的心理空间的真实感与现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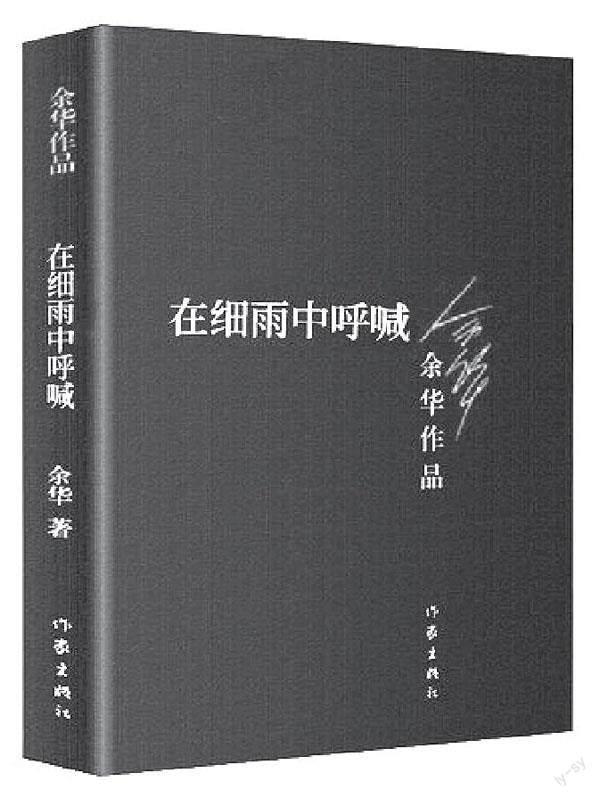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创作生涯中比较特别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名气和受到的关注以及被研究的数量远不及他的其他名作,但在笔者眼中,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细雨中呼喊》正处于余华创作的转型节点上,它不再是以前“拥有残忍天赋作家余华”的那种极端的先锋性风格,也不是后期更加“入世”的创作,比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的叙事内容转向日常,相对于之前的作品更显得平易近人一些,虽然这是一部转型开山之作,但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极为成熟,是一部完整且具有深度的作品。
它以叙述者的回忆作为线索,不断从现在回到少年、儿童时代,讲述“我”的内心经历和心理体验。但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纯心理小说又有明显不同,并不完全是一些感受,而是以恐惧为内核刮起的内心风暴,同时穿插着现实的生活。虽然它具有很强的心理性,是虚拟的记忆空间,但这一虚拟的记忆空间是以现实逻辑为基础,对“往事”进行的回忆与创造。通过创造新的回忆而不断游走于真实与幻境之间,创造出来一个新的虚构空间。
这个空间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具备令读者感同身受的真实感与强逻辑的现实感,主要由于作者的创作逻辑是以现实逻辑为基础,同时采用引发共鸣的心理描写。虽然是回忆的虚构空间,但极强的现实感与真实感使读者身临其境般地跟随作者的步伐,体验了一把作品中人物的人生。
本文拟从作品本身出发,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作家访谈,论述作品中虚构的世界所带的“真实感与现实感”。
一、关于余华本人认为的“现实”与“真实”
作家访谈中,余华曾经提到过,作为抽象观念的“现实”是指余华在先锋创作阶段,从西方哲学和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化中引进来的抽象的剥离现实经验的主观精神现实,是余华对于现实观念的重新认识。详细来讲,在先锋文学创作时期,余华受西方文学冲击以及自身经历影响,他开始质疑传统现实,认为传统现实主义与生活常理只对客观实际负责,忽略了人“内心真实”的精神力量。现实本是无序的,它并非是被经验秩序框住的“必然”,内心欲望发生的偶然“犯禁”正是真正的“现实”表征。
在余华眼中,真正的“现实”来源于人内心的主观精神,它们才是作为人的本质真实存在的,包括人内心的幻想、欲望、想法等,是种种客观规约下的“现实一种”。由此,余华试图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和日常经验规约的表面假象,叙写内心的真实。
正因为这种“内心真实”背离了现实存在的经验生活,它只是作为作家头脑中的抽象观念,因此余华自觉在小说文本中构建起与现实生活疏离的想象性象征世界,揭露现实真相。一直以来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堆积起来的审美样式不仅遮蔽了读者,更钳制了作家的创作。余华只有打破这一审美定势,才能书写内心真相。由此,他首先把搭建想象世界的形式逻辑建立在解构传统现实主义范式的基础上,他不仅以想象的视觉化来解构常理世界,还以时间的分裂、错位来解构传统线性叙述,以语法并置、颠倒的“不确定语言”冲破日常大众化语言的简单判断,在象征化的文本中显示他所理解的现实。这也是余华前期作品比较极端先锋化的原因。
这些关于现实,真实的思考,贯穿了余华所有的作品,余华的真实与现实绝不拘泥于传统生活鸡毛蒜皮的形式。笔者以为,《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以记忆为根基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是最符合余华所谓真正的“现实”来源于人内心的主观精神。
二、《在细雨中呼喊》的断裂的叙述时间线并没有影响虚拟空间的真实感与现实感
第一人称回顾视角是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视角。作者在这一视角中,投入了大量的经历,甚至扭曲了实际故事层面的时空,然而这样大胆的叙述时间线并没有破坏故事的主线以及故事的真实感和现实感。
从文本结构角度说,余华采用了两套逻辑,即宏观和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上,整部小说展现出一种不均匀、对称的封闭结构;在微观层面,小说在两个层面之间不断波动,以扭曲虚构的记忆和真实沉重的现实张力为两端,以记忆为轴,不断波动于这两极之间,构成心理空间的回忆与现实互相穿插纽结在一起的一条线。
从宏观角度看,故事情节首尾呼应,整体内容叙述清楚。从微观上看,真实的心理体验与感受,以及极其现实主义的故事内容,更使得整部作品有极强的真实感和现实主义张力。
从整体上来看,本书一共有四章十六节,每章都有基本的按时间排列的叙述顺序。第一章描述了“我”从孙荡回到南门到“我”和我哥哥长大成人的旅程。第二章描述了从中学时期与苏宇成为好朋友到苏宇去世的历程。本章的内容在时间上包含在第一章中,但侧重点不同。第三章讲述了我祖父的历史,也与第一章和第二章交叉,但作者将他的叙述局限于与我祖父密切相关的事件。第四章叙述了“我”在孙荡与养父母的事件。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一章的主要时间之前。显然,时间不是四段叙事结构的基础,而是“交流空间”,即“我”与相关叙事对象密切接触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就这样,四种记忆慢慢地从记忆的迷雾中“浮现”出来,它们的自洽围绕着相关人物的出现展开,并具有各自的时空特征。当然,作者对于作品的宏观调控远远不止于此。讲述四个记忆故事孤岛,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在这四个记忆孤岛之间建立联系。如果每章的前三节代表了整个叙事框架,那么每章的第四节就彻底成为了他的时间实验场。从每一章的规模来看,第四节都构成了本章主体的相应叙述。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有可能对本章的主要叙述进行某种反冲洗。基于记忆的“回顾”与“真实”(叙述者现在所存在的时空),这种二元对立在全书中成为一種结构性的普遍存在。
这种宏观上的调控,使得即便余华的叙述顺序如此不常规,也并未给故事的完整性带来破坏,一个故事最终还是叙述得有始有终,不仅如此,这样碎片化的穿插,带有心理体验感,反倒加深了作品的真实感和现实感。
三、微观上作品内容给作品带来的现实感与真实感
(一)内容上的现实感与真实感
内容上的现实性,给作品带来了略显残忍的现实感,究其根本还是作品虽然虚构,但是它内容上所有的逻辑都是符合客观现实生活的。以现实生活的底层逻辑为基础,构建小说作品中以回忆为主体的虚构的逻辑,因此它所具备的现实感,更多的是人间真实的现实,既现实又十分的真实。
比如跟着货郎的冯玉青,年轻时被男人哄骗睡觉,最后男方娶了别人家的女儿。冯玉青在婚礼上迷茫无助,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无法理解。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美貌又轻信男人甜言蜜语的悲剧女子形象赫然出现。最后她选择和货郎离开家庭,一起离开这个嘲笑伤害她的家乡,但是人生的真实就是,它是现实的,冯玉青又选错了。最后,冯玉青自己带着孩子,白天要打工,晚上要从事特殊职业,被抓时大言不惭地和警察对峙,“我自己的肉,我愿意陪谁睡觉就陪谁睡觉”。当年害羞的长发女孩再也看不见踪影了,有的只是被人生搓磨的中年妇女冯玉青。
哥哥與城里的朋友们玩得很好,城里的同学们每次来家里玩,都会给哥哥甚至这个家带来光芒。正值青春的哥哥喜欢一个性格较为强势的女生,他和他们吹嘘那个女生喜欢自己,结果城里所谓的朋友们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即便如此,哥哥依然要维持和他们的关系,甚至不会表现出不满。因为只有这样城里的朋友们才会来家里玩,哥哥脸上才会有光。
主人公本身的友谊也是,开始孙光林认为苏杭是自己的朋友,苏杭却从未真正地把他当作朋友,他们两个也不是很玩得来,主人公看不惯苏杭的流氓作风,而苏杭也并不是真的把他当作朋友。对于苏杭来说,孙光林更多的是一个拿来使用的朋友,为了追女孩,不惜在女孩面前以打他来显示自己的威风,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
“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的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这段心理叙述,使读者感同身受,而残忍的故事内容又透露出现实的冷漠。
孙光林小时候被家人送走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不得不回到自己原本的家庭,而同幻想中不一样是,他并没有因为刚回家而受到优待,他的父亲反倒十分嫌弃他。底层的现实逻辑是,一个孩子能够被送走,是因为他已经成了家里的一个负担,送走后再回来,自然是“负担”回来了。然而作者以第一人称回忆的角度进行叙述,孩子气般的委屈,看不透世故的口吻,使得真实感凸显。
(二)细微的心理描写给作品带来的真实感
微观上的心理体验描写,细密地叙述“我”的内心经历和体验。叙述视角就是“我”的回忆,他所有的心理描写,以及描写顺序也是以和他更亲近的人物按顺序排列。从“我”的角度来看,成长中经常充满奇怪的人和奇怪的事,而他自己也经常做出无意识的奇怪动作。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荒谬和可笑的。
在孙有元“快要死了”的时候,孙广才竟然表现出了对人生命运的不耐烦和漠不关心。他甚至在不确定孙有元是否真的断气的情况下,大声喊村民来帮忙抬尸体,引发了一场“诈尸”闹剧。他似乎已经放弃了道德,绝望地希望父亲早日去世。最后,孙有元去世后,孙广才手舞足蹈地说:“终于,终于,终于。”人性的丑陋和人心的冷酷让人觉得人的生命是如此不堪。
四、“陌生化”叙述手法带来的距离感使作品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凸显
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科洛夫斯基在他的《作为艺术的手法》中提道,“艺术的技巧是事物的‘规范化,是一种复杂形式的技巧,它增加了感觉的难度和延迟”。简单地说,它正在从普通变为新颖。他强调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区别,突出形式和使用。“陌生化”作为一个简单的美学概念,贯穿于《细雨中的呼喊》的整个作品,给读者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和美感,这种“陌生化”却不极端,它被控制在一个程度内,就是这种控制,使得这部作品更入世。
余华受现代作家的影响,语言风格很有现代性,他很擅长使用通感,这部作品也不例外。孙光林在家乡的最后一年遇到了鲁鲁,他在这段话中描述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鲁鲁的声音,清脆的声音让我想起了女孩头上明亮的蝴蝶结”。在这里,通感技巧被用来转换听觉和视觉,清脆的声音和五颜六色的丝带达到完美融合。
面对紧张的冲突事件或绝望的经历,余华总是用讽刺来描述,呈现极端对比的黑色幽默。在全家与王跃进的搏斗中,“在哥哥精神的鼓舞下,弟弟拿着镰刀大声喊着,显得非常勇敢。但当他奔跑时,重心变得不稳,重重地被自己绊倒”。“非常英勇”用来形容孙光明,他甚至说不清话。他的弟弟看起来既可怜又滑稽。这些黑色幽默和不常规的语言搭配,使语言陌生化,使作品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正是这种陌生化的语言以及黑色幽默,反倒突显了作品中的真实性和现实性。
作者简介:曲秋宁(1997—),女,汉族,辽宁沈阳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