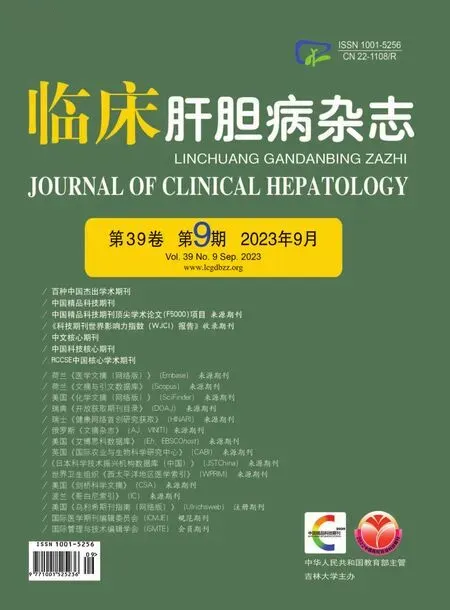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Yes相关蛋白(YAP)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调控作用
张华, 寇萱萱, 邓婧鑫, 张建刚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研究所, 兰州 7300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影像学检查证实肝脂质沉积,且排除继发性原因(如病毒、药物、自身免疫等)和过度饮酒(男性≥30 g/d,女性≥20 g/d)[1]。中国目前有超过2.4亿人患有NAFLD,占全球NAFLD人口的1/5以上[2]。NAFLD的病变涵盖范围较广,从单纯性脂肪变(NAFL)到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以及后期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细胞癌。此外,很大一部分NAFLD患者同时合并代谢综合征。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s,HIF)是由α、β两种亚基组成的碱性螺旋-环-螺旋同源域家族的转录因子,即主要活性亚基(HIF-1α和HIF-2α)和结构亚基(HIF-1β)组成的异源二聚体,在调控细胞代谢、增殖方面发挥作用。Yes相关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为Hippo信号通路下游效应因子,通过与转录增强子相关域(transcription enhancer associated domain,TEAD)家族转录因子结合来调节DNA转录,作为转录共激活因子,调控细胞增殖分化。最近,HIF-1α与YAP在NAFLD中的作用已逐渐引起关注。
1 HIF-1α与缺氧环境
HIF-1α是调节器官、组织、细胞适应缺氧微环境的首要因子。在常氧条件下,脯氨酰羟化酶(prolylhydroxylases,PHD)羟化HIF-1α氧依赖性结构域的脯氨酸残基,被羟基化的HIF-1α在胞质中由肿瘤抑制蛋白介导,经E3泛素连接酶泛素化后发生蛋白酶体降解。在低氧(O2<5%)条件下,PHD活性被抑制,稳定积累的HIF-1α与HIF-1β形成异二聚体并易位于细胞核,与缺氧反应元件结合后调控血管生成因子、促红细胞生成素、葡萄糖转运蛋白等促血管生成及代谢基因转录。除低氧环境引起HIF-1α转录活性上调之外,病毒、细菌诱导的氧化应激及寄生虫介导的铁损耗可直接上调HIF-1α转录活性[3]。此外,活性氧自由基(ROS)、机械刺激最近也被认为与HIF-1α活性上调相关。
2 YAP结构与功能
YAP是转录激活的辅助因子。Yes是一种Src家族蛋白酪氨酸激酶。1995年,Sudol鉴定并克隆出与Yes原癌基因产物Src同源结构域3结合的蛋白,该蛋白分子量为65 kD,富含脯氨酸,将其命名为Yes相关蛋白。YAP没有明确的DNA结合域,因此作为转录共激活因子与TEAD结合调控下游靶基因表达。Hippo酶联反应是最基本的YAP表达调节信号;当Hippo通路激活时,哺乳动物STE20样激酶(MST1/2)与调节蛋白SAV1结合形成活性激酶磷酸化并激活大肿瘤抑制激酶(LATS1/2),活化的LATS1/2磷酸化YAP(phosphorylates YAP,pYAP),pYAP在胞质中通过蛋白酶体途径降解[4],从而达到抑制器官过度增长的作用。当Hippo通路失活,YAP核易位与TEAD核转录因子结合调控基因表达。除经典Hippo通路,机械应力是调节YAP表达的另一因素,该因素似乎独立于Hippo通路,可直接激活YAP。
3 NAFLD
NAFLD逐渐成为全球慢性肝病主要原因。NAFLD相关肝移植率和病死率逐年增加,与肝外并发症共存相关,2型糖尿病患者的NAFLD发病率为47.3%~66.7%,肥胖患者中高达80%[5]。虽然NAFLD与上述因素呈密切相关性,但是其具体机制仍不清楚。从组织形态上观察,NAFLD涵盖疾病的一系列形态,包括伴有或不伴有轻度炎症的脂肪变性和伴有肝细胞气球样变的坏死亚型。从病理机制上观察,NAFLD是脂肪代谢合成功能紊乱的结果,肝脏是脂肪酸代谢的核心器官,主要通过血浆摄取及从头生物合成两种方式促进脂肪酸积累;正常情况下,肝脏以甘油三酯形式储存少量脂肪酸;而当脂肪生成增加或脂肪酸氧化减少则会导致肝脂质沉积[6]。脂质蓄积引起的脂毒性会导致肝细胞应激、凋亡、组织修复性再生和纤维形成,尽管研究发现脂质代谢障碍、炎症等机制参与调节疾病过程,然而对其调控的下游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4 NAFLD与HIF-1α/YAP
NAFLD在不同疾病进展时期均有相应的分子机制参与调节,其中HIF-1α/YAP信号通路作用于疾病全程,并逐渐成为NAFLD机制研究热点。除在肝细胞糖酵解中发挥关键作用,HIF-1α/YAP在脂质代谢重编程中也至关重要。YAP是一种强大的调节因子,受细胞生存环境变化而表达,在肝脂质积累、炎症发生、胶原沉积过程具有调节作用,与HIF-1α结合促进HIF-1α稳定表达[7],在脂质诱导肝细胞损伤修复中协调发挥作用。简要介绍高脂饮食(high fat diet,HFD)及棕榈酸(palmitic acid,PA)诱导HIF-1α/YAP轴激活在NAFLD及其相关纤维化中的病理机制(图1)。

图1 HIF-1α/YAP调控NAFLD相关机制Figure 1 Mechanistic diagram of HIF-1α/YAP regulation of NAFLD
4.1 NAFL与HIF-1α/YAP NAFLD是一种以肝细胞脂肪沉积为首发症状的疾病。长期摄入高脂肪饮食的小鼠肝脏出现疾病相关性缺氧,主要由肝细胞体积增加、肝脏组织血管床减少和消耗氧气的脂肪酸代谢增加所导致。HIF-1α是组织缺氧后适应性改变的主要调节转录因子,可防止NAFLD进展过程中肝脂质积累。具体表现为,当肝细胞特异性HIF-1α缺陷时,会促进HFD小鼠肝脂质沉积[8-9]。高脂环境诱导HIF-1α表达增加的机制尚不清楚,ROS增加可能是其原因之一。肝脏作为脂质代谢最大器官,当发生脂肪代谢障碍,肝细胞脂质蓄积,引起线粒体氧化呼吸链电子传递泄漏,ROS水平升高,诱导HIF-1α转录活性激活,随后上调的HIF-1α通过氧化还原因子的激活诱导PHD2,导致HIF-1α降低[10]。此外,HIF-1α通过诱导PDK1表达,促进有氧氧化转换为无氧糖酵解,这种能量代谢失衡导致HIF-1α下调,促进NAFLD脂质沉积。这些结果表明肝脂肪变性与HIF-1α的调控有关,主要表现为早期高脂膳食诱导HIF-1α上调防止肝细胞脂肪变性,随着高脂环境持续存在,HIF-1α活性下调,NAFL发生。Hippo信号通路调控YAP活性,除了控制器官大小和组织稳态,细胞分化、代谢重编程等生理过程也与Hippo通路有关。其中脂肪代谢重编程是YAP信号调节的中心点。YAP信号介导胰岛素受体底物2与丝氨酸/苏氨酸激酶(AKT)信号下调,从而预防小鼠肝脏脂肪变性[11],YAP和AKT协同作用维持肝脂质代谢稳态。YAP还直接与脂肪酸合成酶和30-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启动子上的甾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REBP-1c和SREBP-2)相互作用,刺激转录并诱导肝脂肪从头生成增加[12]。与上述发现一致的是,YAP也可以抑制糖异生基因表达而减少脂肪酸消耗,间接促进脂肪酸积累[13]。同样在饮食诱导的糖尿病小鼠中,进一步发现通过抑制YAP与SREBP-1c/SREBP-2之间相互作用可防止肝细胞脂质沉积和高脂血症[12]。这表明YAP调控脂质代谢,与脂质沉积之间存在联系。
4.2 NASH与HIF-1α/YAP 据统计[14],在美国人群中有3%~6%的个体罹患NASH,在代谢性疾病和肥胖患者中更为普遍。NAFLD疾病进展过程中,NASH阶段炎症浸润是导致纤维化的关键环节,高脂膳食、缺氧、代谢紊乱等是主要危险因素。随着肝脂质沉积,肝细胞发生坏死,NAFLD从NAFL发展为NASH,肝Kupffer细胞在此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高脂膳食引起的NASH中,游离脂肪酸是导致细胞损伤的脂毒性物质之一,主要通过内质网应激、氧化应激等不同途径诱导肝细胞损伤。正常情况下,Kupffer细胞通过上调自噬来维持细胞脂质稳态[15]。饮食诱导的NASH小鼠模型中,Kupffer细胞的促炎作用与HIF-1α水平上调,这些改变与自噬通量减少相关[16]。该结果进一步在人体样本中得以验证,经检测,NASH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相比,Kupffer细胞数量显著增加,HIF-1α上调,自噬通量受损[16]。HIF-1α通过自噬介导炎症反应同样在细胞中得以验证,表现为下调肝Kupffer细胞中PA诱导的自噬通量,并上调Kupffer细胞引起的炎症,这种炎症由HIF-1α直接介导,而不是由自噬通量介导[16]。这种因HIF-1α和自噬轴失调导致的炎症反应在NASH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另外,HIF-1α上调促进IL-1β、IL-6、TNF-α等炎症因子信号释放,激活肝细胞内炎症小体/caspase-1,促进NASH发展[17]。
氧化应激在NASH肝细胞损伤中具有关键作用,各种来源的ROS驱动NAFLD进展。有实验[18]表明,在高脂处理的肝细胞中,ROS可上调HIF-1α,促进缺氧诱导基因结构域家族成员1A的表达,减轻肝细胞高脂应激与损伤。而另一实验[19]则证明,当HIF-1α反义寡核苷酸抑制小鼠HIF-1α表达后显著降低肝脂质合成关键酶的表达,从而改善脂质稳态以及肝脏胰岛素抵抗。体内、体外实验结果相反,HIF-1α在NASH肝损伤中的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阐明。
NAFLD脂质积累促进脂毒性与线粒体功能障碍,继而引发肝细胞死亡、炎症、纤维化,其中肝细胞死亡促进信号分子释放[20],是NASH炎症进展的关键[21],NASH和NAFL的本质区别是前者存在肝细胞大量死亡[22],这种死亡常由游离脂肪酸诱导的脂毒性、内质网应激介导,因此,降低NASH阶段脂毒性,可能是缓解肝细胞应激的策略之一。在PA诱导人肝癌细胞系HepG 2细胞脂毒性产生的早期阶段,HIF-1α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标志物防止HepG 2细胞凋亡;若HepG 2细胞持续暴露于PA,则观察到这种保护效果消失[23],此现象可能由信号通路负反馈抑制HIF-1α引起。
Kupffer细胞肝脏浸润是促进HFD诱导的NASH发展重要因素[24-25]。除NOD样受体蛋白3/caspase-1/IL-1β经典通路介导NASH发展之外,Kupffer细胞通过Hippo/YAP通路调节细胞存活与增殖[26]。研究[27]表明,HFD诱导的野生型NASH小鼠肝Kupffer细胞YAP以及YAP介导的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TNF-α、IL-6等炎性因子上调,从而使肝脏炎症进一步加重,YAP在Kupffer中调节NASH肝脏炎症的作用为NASH治疗提供新靶点。
肝细胞是驱动NASH发展的主要信号来源,肝细胞状态转换的潜在机制之一可能是YAP信号通路的激活[28]。NASH肝细胞中YAP活性增加诱导肝星状细胞(HSC)转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促进炎症浸润及肝脏纤维化,说明肝细胞YAP表达水平与肝脏炎症、纤维化程度相关,并且肝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趋化因子作为YAP通路下游关键靶标,驱使巨噬细胞浸润,促进NASH炎症加重[29]。除此之外,一项关于NAFLD恒河猴的研究[30]发现肝细胞YAP的表达水平与肝脂肪变性和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其机制是YAP通过调节TGF-β/Smad信号通路,促进肝脏由NAFL进展到NASH或者直接进展为肝纤维化。
4.3 NAFLD相关纤维化与HIF-1α/YAP NAFLD相关纤维化的疾病表型由环境、遗传因素相互作用引起,肝细胞持续性脂肪沉积导致微循环灌注减少,引起肝脏损伤与损伤后修复,进而促进细胞外基质沉积。缺氧是HFD诱导肝细胞脂质沉积的结果与触发因素,而HIF-1α是缺氧合并NASH相关肝纤维化的信号调节关键调控因子[31]。
肝细胞内HIF-1α信号转导是NAFLD纤维化发生的重要因素。HFD喂养小鼠发生NASH,并伴有显著的肝纤维化,而肝细胞特异性敲除HIF-1α,小鼠肝纤维化程度明显减轻,胶原蛋白含量减少近80%[32],HIF-1α对NAFLD纤维化的调控作用在小鼠模型中已得到证实[33]。体外实验[32]进一步证明HIF-1α是NAFLD胶原交联所必需,已证实肝细胞肿瘤抑制因子(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下调可促进NAFLD纤维化,而HIF-1α作为上游关键调节机制,在PA诱导肝细胞脂质沉积细胞模型中,HIF-1α上调介导PTEN/NF-κB-P65信号通路促进胶原沉积。
肝内肌成纤维细胞积累是NAFLD纤维化中心环节,主要来源于活化的HSC,自噬、氧化应激、缺氧、脂质代谢和受体介导信号在内的多种途径揭示HSC活化的复杂机制,HIF-1α是介导下游相关基因诱导HSC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的信号之一[34]。研究[35]发现,HFD诱导的NASH小鼠HSC中HIF-1α表达升高时具有促纤维化作用,且与肝组织纤维化水平呈正相关。此外,研究人员在NAFLD患者肝脏样本RNA测序结果中发现,YAP在纤维化阶段表达上调。同时在HFD所致NAFLD小鼠肝脏中进一步证明,肝细胞特异性YAP敲除可降低NAFLD相关纤维化基因表达,表明YAP在NAFLD相关纤维化中具有致病作用[36]。
肝纤维化病理机制主要是损伤修复失衡及成熟肝细胞再生缺陷,多种信号调节反应肝细胞受损再生机制的复杂性。健康肝脏中,YAP调控肝体积大小与成熟细胞再生,在肝脏生长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在NAFLD肝脏中,YAP过表达并丧失调节肝组织正常再生功能;反应性导管细胞(reactive ductal cells,RDC)的积累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及肝硬化相关死亡风险密切相关;HFD诱导的NASH相关纤维化中YAP核阳性主要定位于RDC,这种细胞同时表达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是细胞外基质中的连接蛋白[37]。免疫组化双重染色显示OPN与YAP在NAFLD相关纤维化RDC核中同时强阳性表达,表明肝细胞损伤修复期间YAP上调促进RDC积累及OPN介导细胞外基质沉积,促进肝脏纤维化发展,而非功能型肝细胞有效再生[38]。HSC是细胞外基质主要来源,YAP同样在活化的HSC中表达;肝纤维化阶段细胞外基质沉积,细胞对基质刚度增加的感知会导致YAP核易位,HSC对基质感知依赖于整合素信号,YAP作为活化的HSC中整合素依赖性信号传导的重要效应因子,调节整合素与细胞外基质互相作用的稳定性,促进NAFLD纤维化表型,动物实验中抑制YAP后可改善纤维化[39]。
4.4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与HIF-1α/YAP NAFLD不仅仅是单纯的肝脏疾病,常与肥胖、血脂异常、2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40-41]。因此NAFLD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表现,属于MAFLD范畴。而最新定义的MAFLD,是指肝内甘油三酯含量≥5%,并且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即超重/肥胖、糖尿病和代谢紊乱[42]。部分NAFLD病患常伴有糖尿病、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等并发症。HIF-1α通过调控相关代谢变化促进NAFLD发展为MAFLD[43],在上述并发症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几项回顾性研究调查中发现,NAFLD患者常伴有心血管疾病[44-45]。动物研究[46]证明,HIF-1α是导致高血压疾病模型中肝损伤易感性增强的原因,在长期HFD环境下,HIF-1α介导心血管疾病模型中NAFLD进一步加重。在NAFLD合并代谢综合征中,有研究[47]显示HIF-1α激活促进胰岛素抵抗,然而也有研究[7]表明相反结果,即HIF-1α激活可防止肥胖和改善胰岛素抵抗,这种不一致说明HIF-1α调控MAFLD存在个体差异,可能与HIF-1α翻译后修饰相关。肝脏是许多生理代谢过程的关键枢纽,包括脂质和胆固醇稳态,然而,NAFLD肝脏功能被抑制,在脂肪变性的小鼠肝脏中,肝细胞HIF-1α通过介导水通道蛋白抑制肝细胞水分分泌,浓缩胆汁,促进胆固醇结石形成[48],HIF-1α上调抑制胆汁代谢,促进NASH期间肝酶表达升高。肝脏通过调节葡萄糖和脂质代谢,在细胞代谢中发挥核心作用,NAFL合并胰岛素抵抗是代谢失调的常见特征。Hippo通路失活导致多种代谢疾病发生[26],YAP可抑制调节肝脏糖异生的基因转录,即通过下调葡萄糖-6-磷酸酶催化亚基和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1[13],降低血糖水平,但同时间接抑制了肝脏脂质代谢。尽管HIF-1α/YAP调节NAFLD和糖代谢、脂代谢之间相关性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但可从现有证据观察到HFD通过HIF-1α/YAP轴促进NAFLD表型及相关代谢趋势变化。
5 展望
NAFLD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鉴于人口基数庞大及医疗条件有限,针对NAFLD患者的全面覆盖诊疗方法似乎不能够现实。且由于环境与基因互相作用,NAFLD疾病发展程度在不同患者间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因此,根据环境因素、易感基因、疾病发展程度将重点人员纳入监护至关重要。虽然HIF-1α与YAP在NAFLD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探索HIF-1α/YAP在不同阶段如何调控疾病发展是解决NAFLD的关键。尤其是HIF-1α/YAP在NAFLD表观遗传学中的调控作用。此外,肝脏疾病中HIF-1α/YAP在不同细胞中的异质性值得关注。随着研究人员对HIF-1α/YAP作用机制的不断探索,该分子通路或许可以作为NAFLD患者易感基因的一个新靶点,开发出靶向该分子通路的药物将为NAFLD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张华负责拟定写作思路并撰写文章;寇萱萱、邓婧鑫参与相关文献及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张建刚审校并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