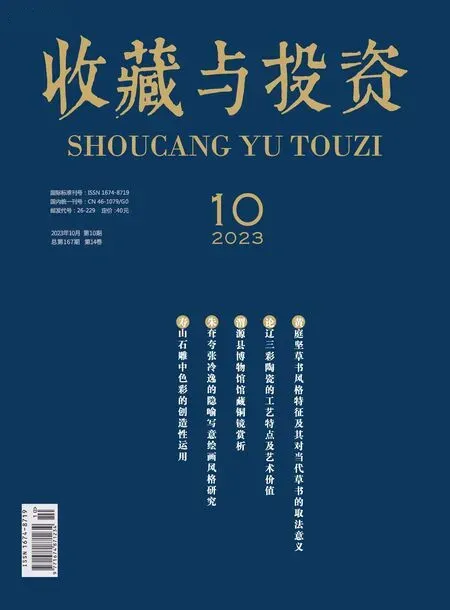红山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及未来展望
张铭珊,许豆豆(辽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红山文化,被视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主要分布在燕山以北的大凌河以及西辽河上游地区,鼎盛时期范围甚至向南延伸到燕山之外。与此同时,红山文化在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西部草原文化的频繁接触、交汇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晚期还产生了如牛河梁、东山嘴这样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群。其中,牛河梁遗址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产生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传承能力,使得“坛庙冢”“玉龙凤”等新因素因交汇融合而得以长期延续[1]。
该地区古人类文化的产生、变化和发展与地理环境及气候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因此,研究古人类文化的地理背景,即深入探寻文化的成因,是了解当时人类文化演变的重要途径。
一、红山文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30年代红山后遗址正式发掘开始至今,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已进行了90多年。本文主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清朝末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阶段是红山文化发现和探索期。第二阶段是建国之后,针对红山文化的科学调查与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一时期,红山文化被正式认定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并据其编制了红山文化谱系。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期间,大规模的田野挖掘工作展开,使人们逐渐加深了对红山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由此,红山文化被正式确立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中华文明探源系列工程各项研究成果的取得,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已进入初级国家文明阶段[2]。
在文化分期方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连续发展长达1500年,肇始于距今6500年,到距今5000年为止。在分期方面,本研究采用刘国祥的分期方案,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

图一 红山文化玉猪龙

图二 牛河梁出土红山女神像
距今6500~6000年为早期形成阶段,因此遗址数量较少。此时,彩陶开始出现,陶器则以筒形罐为主。在红山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距今6000~5500年,该文化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红山文化遗址数量达到最多,且呈现集中分布的特点。此时人口也迅速增长,出现了聚落分布密集的情况。同一聚落内开始出现等级划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彩陶样式也逐渐丰富,出现了陶窑遗址。这一时期盛行祖先崇拜的观念,出现了大量的小型陶塑和人头像制品,女性特征突出。崇龙习俗开始形成,玉雕技术水平提高,出现了C形玉龙。晚期阶段为距今5500~5000年,是红山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但遗址数量比中期要少。在这个时期,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超大型聚落出现了,而在聚落的内部,还出现了高等级社区。这种变化导致社会分层更加明显,并且特权阶层和一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开始出现[3]。考古学家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中发现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建筑展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特点。此时,彩陶业高度发展,出现了祭祀用和日常用两种类型的陶器。玉雕技术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制造出了一大批拥有独特造型、丰富内涵和专属功能的器具,其中,红山女神头像成为我国五千年前雕塑杰作的象征,是极具艺术价值的考古资料。
二、遗址内环境背景信息
动物遗存方面,在白音长汗[4]、牛河梁遗址[5]、红山后遗址[6]的发掘中,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主要有鹿、狍、獐、猪、牛、羊、狗、熊、獾、兔、鼠、雉贝类等。其中,牛河梁遗址中獐的骨骼鉴定标本发现37件,现生獐分布在北纬24°—34°、东经110°范围内[7],牛河梁遗址位于北纬41°21′、东经119°31′。獐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在植物遗存方面,莫多闻先生等学者[8]对牛河梁遗址文化层的样品及大凌河上游全新世沉积剖面进行了孢粉分析。研究者认为,在9000 aB.P.以后,辽西地区进入了全新世温暖期,组合中的木本花粉多为温带落叶阔叶树种,如桦、柳、榆、桤木等,暗示着该地区可能属于森林草原类型。此外,在LY4样品和大凌河自然沉积剖面上观察到了较多的环纹藻,这一现象可被视为暖湿气候的标志。然而,约5000 aB.P.以后,气候开始向干燥凉爽转变,这一变化在孢粉组合中得到了反映。具体来说,木质花粉明显减少,喜暖树种逐渐减少或消失,水龙骨的数量也有所减少[9]。李永化先生[10]研究了冀北围场地区属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泥炭样本,并进行了孢粉分析。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燕山山脉南北、内蒙古东南部以及长城一带,存在温暖湿润的针阔叶混交林。这一发现表明了当时的气候温暖,降水较多,对古土壤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三、红山文化人地关系研究
从环境考古角度来看,红山文化分布在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以及华北平原之间的三角地带,处于森林草原景观向草甸草原景观过渡的区域,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地带[11—15]。
“8.2 ka事件”之后,气候进入全新世大暖期 ,红山文化时期(6.5—5.0 ka B.P.)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最宜期末期。与最宜期相比,此时的气候呈凉爽干燥的态势,导致该地区湖泊地、沼泽地等湿地面积减小,而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则有所增加 。同时,科尔沁沙地经历了大规模的退缩,孕育了全新世最厚的古土壤[16]。此外,红山文化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这部分可以归功于前期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生产准备阶段[17]。可以说,温暖的气温和稳定的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人口数量得以稳步提升,促进了红山文化的稳定发展繁荣。
此外,“5.5 ka事件”的冷干化对红山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初,当地居民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迁移到其他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较偏北地区的居民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向南迁移到辽西地区。在有限的资源空间中,出现了对资源的争夺,战争开始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社会现象,这可以从随葬武器的广泛存在得到验证[18]。在经历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过程之后,许多以往不曾见过的社会复杂因素相继出现,产生了一些功能特殊、规模较大的聚落或祭祀遗址群,如牛河梁、东山嘴等。但是红山文化时期主要农作物为粟黍作物。这种农作物有缺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遇到干旱或低温气候,就会出现20年不结穗的奇特现象。所以气候转冷后的后期,粮食的供应远不敌资源的耗竭程度,原本已经成熟的农业经济体系彻底土崩瓦解了。因此,很有可能是5.5 ka B.P.的冷干事件导致了红山文化晚期的逐渐没落。
四、未来展望
考古工作的科学规范、材料的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多样化极大地拓宽了红山文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人们在对既往材料和研究的梳理、总结过程中也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都对未来的环境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目前发现的遗迹功能互补性差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似乎存在越向南年代越晚的特征。北部年代早,多为居住址,而南部年代晚,多为祭祀礼仪性遗存。遗存缺乏功能上的互补,寻找与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礼仪性遗存年代相同的生活居住址,有助于探讨红山文化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与牛河梁等大型宗教祭祀礼仪性遗址之间的关系。
(二)进行高分辨率古气候重建
大部分红山文化时期分布的遗址点并没有对剖面作相应环境指标的提取与分析以及高分辨率的精准测年,目前的古气候资料大多数来源于内蒙古地区,而辽宁地区则主要集中在牛河梁地层,研究区域较为单一。因此,在今后的环境考古工作中,应该进行分区讨论,加强对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周边遗址的环境指标提取,进行准确定年,提高定年精度。
(三)将微地貌和微环境变化对聚落形态及聚落变迁的影响纳入考察范围
由于所处地区河道改道频繁,开发人员在聚落选址时,除了考虑与水源的距离之外,还需要兼顾农业生产和邻近石器资源地点等多方面因素。
(四)与相关学科密切合作
结合科技考古的方法,从多学科的角度展开分析,以另一视角讨论人群的关系与互动、资源的获取与分配等问题,同时加强GIS等地理信息技术手段在环境考古学中的应用,促进红山文化人地关系的直观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