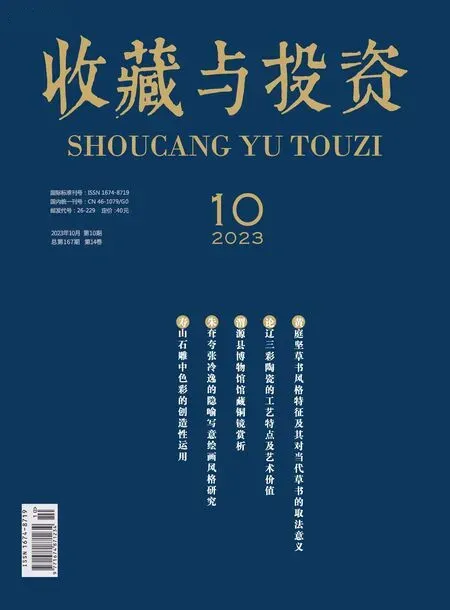清代西藏《御制“十全记”碑》考
黎竞飞(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一、碑碣概况
《御制“十全记”碑》,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立于布达拉宫雪老城南大门前侧,地处东经91°7′10.16″、北纬29°39′10.11″,坐北朝南。1965年因拉萨城建,碑与碑亭移置宗角禄康公园,1995年整体迁回原址。1996年《御制“十全记”碑》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
该碑通体石质,属中原地区纪功碑形制,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呈“神龟驮碑”状。碑文由汉文、满文、藏文、蒙古文四种文字镌刻,碑体两面中上部碑文清晰可见,但下部风化相较严重,尤以汉文部与藏文部为甚。碑首高134厘米、宽144厘米、厚46厘米[2],整体上色—以黄、白、青为主色调(原褪色部分现已修复),阴阳两面刻双龙戏珠浮雕,下部以白色祥云边饰为底。碑额镶于碑首中下部,呈扁方体状,额框篆刻纹路雷电纹,框周饰以卷草纹,碑额南面东侧竖刻汉文篆书“御制”二字,西侧竖刻八思巴文;碑额北面东侧竖刻回鹘式蒙古文,西侧竖刻正楷藏文,皆表“皇帝亲笔(御制)”之意。碑身高207厘米、宽132厘米、厚38厘米[2],两面四周边框饰以二龙戏珠图纹,碑身南面东侧竖刻汉文十九列,包括首端题记、末端印章、时间末署与立碑者名款,西侧竖刻满文十七列;碑身北面西侧横刻正楷藏文三十九行,东侧竖刻十七列蒙古文。碑座上顶横置垫台,长160厘米、宽58厘米、厚5厘米[2],起垫置碑身功用,垫台下部为赑屃底座(汉族神话传说中的龙九子之首,形似龟,好负重,为古代中原石碑底座制式典型[3]),呈椭圆状,首尾通长250厘米、身宽180厘米[2],四足缩壳,脖颈前伸,龟鳞刻以六棱圆角浮雕,纹理细腻,栩栩如生,彰显清代金石刻工精湛的雕刻技艺(今碑亭紧锁,透门间缝隙,以长管窥镜可辨石碑形制、雕刻实况与碑刻文字,但碑体尺寸毫厘难以实测,故引《拉萨史话》部分数据)。
此碑记载了乾隆帝在位五十七年间的“十全武功”,碑文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亲撰,由驻藏大臣和琳、驻藏帮办大臣成德以及参赞大臣惠龄主持刊立。
二、碑文考释
《御制“十全记”碑》所载碑文以《十全记》为底本,是清代唯一的以碑碣形式呈示《十全记》的物质载体。《十全记》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五十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浣”(1792年农历十月上旬)所撰,并编集成册,载于《御制文三集》,原贮北京重华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碑文的题记、序言、正文、时署从右至左分刻十七列,与立碑者名款并刻为十九列,“御制十全记”五字汉文题记刻于碑身南面右上角,《十全记》所钤“八徵耄念”“自强不息”压角章呈上下排列刻于碑身南面中下部,上章“八徵耄念”风化严重,字体漫漶;下章“自强不息”比较清晰,印章上方刻以时间末署,下方刻以立碑大臣名款—“和琳”名款与时间末署同为一列,“惠龄”与“成德”独成两列,分刻于印章左下部。

《御制“十全记”碑》碑亭 (图片来源:笔者自摄)
碑文所存可考著录见《卫藏通志》《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现当代刊行的文物普查专著《拉萨文物志》也对该碑文进行了收录,但四者所载与碑文实刻不尽相同[4—7]。碑文考释运用“』”标识碑文分列,以碑文实刻十九列汉文为基准,勘误补阙前人著录;结合碑文主旨与历史文献对专有名词与重点语句加以注释,根据现代汉语语法规则与标点符号用法,将碑文分段断句如下:
《御制“十全记”》』
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班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1),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2)。』
夫记者,志也。《虞书》(3)“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4)“掌邦国之志”,乃在事;《旅獒》(5)“志以道宁”,则兼心与(6)事而言之。然总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于』天,以冀承乎』贶,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么(7),弗』屑数也。
前己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8)等未宣我武,巴忠(9)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是以罪庸臣(10),选名将,励』众军,筹储饷。福康安(11)等深感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12)、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13),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14)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15)等前去,故不敢出也。
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犂庭,不遗一介,亦非所以(16)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策颉利(17)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18)廓尔喀非颉利之比』,番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
昔予记土尔扈特(19)之事,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至(致)(20)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21),《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22),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23),夫复何言』。
乾隆五十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浣,御笔。
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工部尚书镶白汉军世袭云骑尉臣和琳(24)』
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四川总督臣惠龄(25)』
钦差协理西藏事务赛尚阿巴图鲁副都统衔臣成德(26—27)
词句校注:
(1)《拉萨文物志》误“詩(诗)”为“词”①。
(2)《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录文缺失“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班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②”
(3)《虞书》:《虞书》是《尚书》的组成部分之一,记载了上古唐虞时代历史,反映了该时期社会发展与政治思想。“朕志先定”意为我的意志已经预先决定,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全句为“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4)《周礼·春官》:《周礼》作为中国古代职官政典,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春官以大宗伯为长官,掌理礼制、祭祀、历法等事。“掌邦国之志”意为掌管王国和王畿内诸侯国的史记,出自《周礼·春官·司巫/神仕》,全句为“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5)《旅獒》:《旅獒》是《尚书》的文章之一,当时西方部族献上一种大犬,太保做《旅獒》,以此劝诫武王不要沉湎于乐。“志以道宁”意为(自己)意志要依靠道来安定,出自《尚书·周书·旅獒》,原句为“志以道宁,言以道接”。
(6)《拉萨文物志》误“与”为“于”③。
(7)幺么:亦作“幺庅”,意为微不足道的。《鹖冠子·道端》:“无道之君,任用幺么。”
(8)鄂辉:碧鲁氏,满洲正白旗人,为第一次廓尔喀之役中清军将领,他和驻藏大臣巴忠等私自与廓尔喀签订“赔款赎地”条约,后受弹劾,逮赴前藏荷校示众[8]。
(9)巴忠:乾隆帝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钦差大臣之职赴藏主持用兵,翌年私自与廓尔喀签订赔款赎地条约,后畏罪投河自杀[5]。
(10)原碑文为“饱欲而归,是以罪庸臣”;《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录为“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藩,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④后者录文与《十全记》(乾隆手书本)相同,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廓尔喀的凶势。原碑文删去部分,似有意为之,或因有心隐匿战略目的,抑或出于建构清廷威权语境的需要。
(11)福康安:富察氏,字瑶林,号敬斋,满洲镶黄旗人,清乾隆年间名将。时任第二次抗击廓尔喀侵略战争中清军主帅[8]。
(12)索伦:清初把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北方少数民族各部统称为索伦部,索伦兵几乎参加过清代所有大规模战争,对维护清朝统治和守卫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9]。
(13)阳布:又作雅木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4)《拉萨文物志》误“所檄”为“新檄”⑤。
(15)丹津班珠尔:又称丹津班珠尔多仁,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出身西藏贵族世家,多仁班智达之子,康济鼐侄。因在抗击廓尔喀侵略战争中办事不力,战后免职解京[10]。
(16)《拉萨文物志》误“所以”为“新以”⑥;《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录文缺失“所以”⑦。
(17)颉利:原名阿史那咄苾,是东突厥汗国最后一任可汗。颉利在位十年,其间发动攻唐战争,后战败为唐朝所俘,唐太宗施以怀柔,义释颉利,并“全其部众”[11]。
(18)示之必克,其和乃固:意为应当充分展示武力和必胜决心,方能克敌制胜,使其求和归顺。此句是对《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所载唐太宗言论的凝练,原句为“朕将独出,以示轻知,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
(19)土尔扈特之事:土尔扈特部为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迁至额济勒河下游。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不堪沙皇俄国压迫,举族东返,历时半年,跋涉万里,终于到达伊犁河畔,回归祖国怀抱[12]。
(20)《卫藏通志》与《拉萨文物志》录“至”⑧;《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与《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录“致”⑨。原碑文此处漫漶不清,且“至”与“致”皆可与语义相契,因而两字是非难辨。
(21)知进知退:意为知晓得与失的关系,此句出自《易经·遁卦》,全句为“小忍则安,知进知退。”
(22)《卫藏通志》录文缺失“惟恐难承”⑩。
(23)全人:善于契合天道而又应合人为的全德之人。《吕氏春秋》:“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此处抑或代指“能继承乾隆帝‘十全功纪’的人”。
(24)和琳:钮祜禄氏,字希斋,满洲正红旗人,和珅胞弟。随福康安征廓尔喀,因功勋卓著,升都统衔,授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13]。
(25)惠龄:萨尔图克氏,字椿亭,蒙古正白旗人。以参赞大臣从征廓尔喀,督治粮运[8]。
(26)成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领队大臣从征廓尔喀。师还,任驻藏帮办大臣[8]。
(27)《卫藏通志》《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与《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录文均未录“和琳”“惠龄”“成德”立碑者名款⑪。
三、碑立始末
《御制“十全记”碑》以铭刻、记载、宣扬乾隆帝军事武功为立碑始因。乾隆年间,出于强化边疆控制,维护王朝统治的需要,清廷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战争,其中十场规模较大、意义卓著,分别为: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清缅战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安南之役、两次廓尔喀之战役,它们收录于《御制“十全记”碑》,作为碑文叙事主体和碑立历史根源而存在。
1747至1776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乾隆十二年(1747年),川西大金川地区土司莎罗奔劫掠邻近地区,同年清军进剿,莎罗奔不敌请降,清廷赦其罪,仍授土司,是谓第一次金川之战。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共谋叛乱,清军初期征讨受阻,遂以重兵合围敌军,叛首索诺木被迫出降,随即遭处死,是谓第二次金川之战[14]。战后,清廷在此常驻军队,废除土司制度,置设行政机构,推行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管理。
1755至1759年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趁蒙古准噶尔部落内乱之机,出兵伊犁,擒获首领达瓦齐,此为第一次平定准噶尔之战。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原归附清廷的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受沙俄挑唆,图谋反叛。清军分兵两路,进发伊犁,叛军不敌,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 ,次年毙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经清廷理藩院严正交涉,沙俄送还其尸 ,同年反叛残余得到肃清,准噶尔叛乱自此完全平定[15]。两场战争有力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遏制了沙俄的侵略企图,捍卫了国家尊严,巩固了清廷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
1757至1759年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新疆回部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与小和卓霍集占叛清,清廷发兵征讨,大小和卓兵败被杀,叛乱遂平[16]。经此一役,清廷实现了对南疆地区的完全控制,标志着清代中国统一战争的完成。
1762至1769年清缅战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缅甸贡榜王朝以中国西南土司拒绝纳贡为借口,出兵侵略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组织自卫还击。战争历经四场战役,以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清缅停战议和,缅甸称臣纳贡告终。此战宣扬了国威,巩固了清缅宗藩体制。
1786至1788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举兵抗清,起初势大,后清廷以福康安为将,驰援台湾,义军猝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庄大田被杀,林爽文被俘,磔刑于京师,起义失败。
1788至1789年安南之役:自明英宗以来,安南国(今越南)世代为黎氏家族统治,安南黎氏表贡不绝,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清廷为维护宗藩体制,出兵帮助黎氏复国,黎氏于年末复国后又遭阮氏偷袭,再度覆灭。阮氏随后多次上表乞降,向清廷俯首称臣,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得到清廷册封,清廷与阮氏安南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17]。
1788至1789年第一次廓尔喀之役:公元18世纪中叶,尼泊尔廓尔喀部势力壮大,在征服境内各部后野心膨胀,意图染指中国西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以贸易关税矛盾为借口,不宣而战,侵袭后藏。翌年初,部分西藏地方官员与驻藏大臣巴忠“迁就完事”,私与廓尔喀签订赔款赎地条约,并向清廷谎称廓尔喀乃“畏罪归降”[18]。此举虽使廓尔喀暂时退兵,但孳生了“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的祸根。
1791至1792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廓尔喀讨要“赎地款”未果,翌年夏,遂以“爽约”为由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战争之初,驻藏清军虽协力堵御,但寡不敌众,以致战事不利—济咙、宗喀、聂拉木、定日、萨迦等后藏要地相继沦陷,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驻锡地)亦遭廓尔喀军洗劫[18]。同年冬,乾隆帝得知廓尔喀再度入侵,“赫斯震怒”[4],令福康安率军冒雪援驰。清军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进抵后藏,五月即“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将廓尔喀侵略者驱逐出后藏地区。为永杜边衅,福康安乘胜追击,“深入敌境者七百余里,俘擒斩获凡三四千”[19],军锋益锐,势如破竹,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以致“廓酋举国慑怖哀恳乞降”[4]。乾隆帝认为“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且廓尔喀地处化外,与中原腹地相隔千里,即“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此外,清军跨境奔袭,还受到气候骤然转寒,冰雪行将封山,不习当地水土,粮草供应短缺,疾病瘟疫肆虐,兵士折损减员等因素影响[20](但《御制“十全记”碑》未予载录相关的不利客观条件),故而乾隆帝允许了廓尔喀投降纳和的乞求,令其立下“毋敢再犯藏界,永为不侵不叛之臣”[19]的誓约,战争遂平。抗击廓尔喀侵略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西南疆域,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廓尔喀归降,清军凯旋班师之际,乾隆帝深感自即位五十七年来,每用兵之际,无不“切深思、定于志”以求合乎道义,他认为克敌制胜得益于“承乎贶”,乃属“天予之”。为昭示其在位期间所立战功受之于天、孚之于民,乾隆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亲撰《十全记》,将“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并称为“十全武功”,令驻藏大臣和琳等按照《十全记》所述勒石刻碑于拉萨布达拉宫前《御制平定西藏碑》旁侧,并建盖碑亭[5],以冀昭假烈祖、俎豆千秋。这便是《御制“十全记”碑》勒石制碑的历史源委。
四、历史评介
(一)《御制“十全记”碑》是中国碑刻发展史上罕有的四文合璧碑碣瑰宝
碑刻历史悠久,整体风化较轻,保存完好;碑首、碑身、碑座形制规整,浮雕精致,纹刻细腻;刻以汉满藏蒙四文,阴镌篆刻,笔法苍劲,体现清代工匠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该碑是研究清代纪功碑制式、刻法的重要原始文献,更是研究中国藏事碑文历史背景与语言特征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御制“十全记”碑》是多维剖析乾隆帝的实体文献
碑文开篇《虞书》《周礼》等古籍典语即铺宏而出,亦借唐太宗谕论阐释清廷允许廓尔喀乞降原因,以及援引土尔扈特东归等体现出的贯古通今的叙论布局与大气磅礴的语言风格是研究乾隆帝文学素养和行文特征的重要参考;“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更体现乾隆帝修道而保法、备战而不黩武的用兵态度;而“十全武功”之中两征金川苦战数年却无胜绩,清缅战争中云贵总督明瑞被缅军围杀,镇压林爽文起义中屠杀无辜村民,平廓战争帕郎古之战清军轻敌冒进损失惨重等饰垢掩疵的部分也反映出乾隆帝讳败夸胜、好大喜功的心态。这彰显出该碑对研究乾隆帝武略战功、军政水平、文学思想、心理状态及特征的典型史料参考价值。
(三)《御制“十全记”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金石丰碑
“十全武功”巩固了中国西南、西北、东南疆域,奠定了清朝乃至今日中国的辽阔版图;有力打击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加强了民族团结,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深化边疆地区与中原的交流与联系—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思想文化、行政体制与社会治理模式进一步向西部推广普及,为其社会进步、经济开发与文明发展打下深厚基础;有力地抗击了外敌侵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对当今“疆独”“藏独”“台独”等国家民族分裂分子与外部反华势力起到警示与震慑作用。《御制“十全记”碑》作为清代乾隆时期军事战功的实体承载,不仅是研究清代军争史不可多得的实体文献,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反对民族分裂,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见证。
注释
①《拉萨文物志》第118 页第12 行见误处。
②《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第187 页第2 行与第3 行间应补遗。
③《拉萨文物志》第118 页第15 行见误处。
④《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第1018 页上半部第10 列至第12 列见录文。
⑤《拉萨文物志》第118 页第27 行见误处。
⑥《拉萨文物志》第118 页第29 行见误处。
⑦《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第1018 页下半部第4 列应补遗。
⑧《卫藏通志》卷首第32 页第13 列、《拉萨文物志》第118 页第37 行见录文“至”。
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第1018 页下半部第16 列、《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第187 页第14 行见录文“致”。
⑩《卫藏通志》卷首第32 页第18 列之间应补遗。
⑪《卫藏通志》卷首第32 页第20 列左侧、《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第1019 页上半部第6 列之间、《西藏奏疏(附〈西藏碑文〉)》第188 页第20 行下部应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