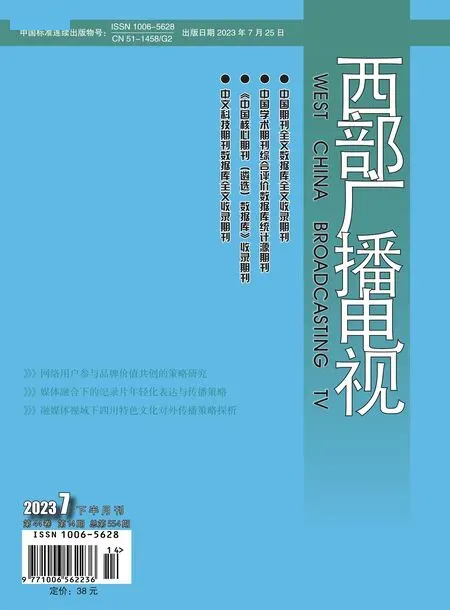镜像理论视域下《奇迹·笨小孩》的叙事解读
李僡伦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继《我不是药神》火爆银幕之后,青年导演文牧野再次推出现实主义力作《奇迹·笨小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片于2022 年春节上映,由易烊千玺、田雨、陈哈琳、齐溪等人出演。猫眼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10 月7 日累计票房13.79 亿。影片融合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类型片元素,记录了以景浩为代表的新时代普通人的创业历程。他们在大城市里沉浮,用努力创造奇迹,争取幸福。该片是中央宣传部国家电影局2021 年重点影片项目,入选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创作诉求和审美焦点,讲述了10 年前深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是打造新主流电影的重要范例。文牧野导演对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充满温情的人文关怀,使得这部电影在佳片如云的春节档收获了良好口碑。
1 观影心理的对镜建构
在观影者观看的早期阶段,观影者对银幕中的形象会产生自恋式的认同,将其视为与自己同一的存在[1],从而进入想象界,这被拉康称为一次同化。影片两分半的片头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主人公的家庭情况。导演通过轻快的音乐、温暖的色调、简短的对话、温情自然的动作,展现了景浩送妹妹上学的生活样貌,迅速将观影者代入导演所架构的故事情境当中。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构建自己。“他者”除了现实中的他人,还包括镜像中的“他者”,即在镜子、屏幕上出现的其他人。一方面,观影者会通过镜头,寻找片中角色与自己的共性,代入“他者”的表演中,从而产生情感共鸣。比如《奇迹·笨小孩》中拼命筹齐医疗费、无力偿还房租、房东催租的电话和纸条、投资过程中市场环境突变、求职时面对的冷脸和不公等细节,展示景浩也经历着普通人的经历,此时的观影者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
观影者在观看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并不存在于正在凝视的银幕上,意识到电影只是将虚构的故事搬上了银幕,从而进入理性的象征界。在观影过程中观影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干扰或因剧情的代入感不强导致缺席电影。景浩不顾伤痛,拼死赶到高铁站与赵振昌谈判,最终竟然顺利获得一次与老总谈话的机会,这一段紧张激烈的交叉蒙太奇配上积极向上的歌词与激情澎湃的编曲,勾勒出大城市打工人的奇迹故事。反观在场观影者,其并不能拥有片中景浩同样的勇气和振奋人心的机会,便会抽离于情节。但导演在视听层面的娴熟技法与叙事技巧的灵活运用,让观影者沉浸其中,满足内心期待,此时观影者又作为看与听的主体而在场,“缝隙”由此存在。
叙事的情感渗透、细节的刻画,再次将观影者代入电影中,并与其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幻想银幕中的“我们”即将发生的故事,此时裂缝被缝合。“观众在摄像机的连续调动下,不断调整自己去认同被设计和被组织后的形象,随后陷入到一种由双镜头所建造的虚构的陈述中,达到‘相信’影像内容真实的幻觉状态。”[2]
罗伯特·麦基在其著作《故事》中提到:“故事是生活的隐喻。”很多学业未完成就被迫谋生或者没有受过名校教育的观影者,都会自动代入这种身份,与影片中的角色共情,如同照镜子一般窥视自己在片中的表演行为,让观影者拥有两个人的视角。景浩在艰难困苦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取得了成功,为妹妹挣够了医疗费,还回到大学完成学业,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功镜像人物能帮助观影者完成“理想自我”的建构。
此时,观影者不是专注于镜头、角度、画面等,而是用他的主观幻觉填补了这些包含许多空间、叙述和意义的空白,观影者不再怀疑他所看到的东西的真实性,主体之间的“裂缝”得以“缝合”。
2 叙事话语的情感渗透
2.1 人物塑造:塑造草根形象的身份认同
电影凭借其直观的视觉、听觉传播优势,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造梦机制”的艺术,电影对观影者欣赏艺术与敏感度要求较低,更容易与观影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
相较于其他影视题材,草根人物在逆境中挣扎的故事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因为大多数观影者可以将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体验代入电影,并在银幕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尽管景浩这一角色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具体的人,但他却是现实中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化身。导演的意图就是以鲜明的情感表达方式调动观影者的代入感,电影与观影者的精神世界就变成了双向的情感交流。
法国心理学家拉康在1936 年首次提出“镜像”理论。他认为,人类心理学有三个领域,即“现实”“想象”和“象征”,与其相应的是“理念我”“镜像我”和“社会我”,从而置换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理论。他划分了人们逐渐能够与镜子中的形象合一的阶段,即人们逐渐形成“自我”[3],逐渐从“理念我”走向“镜像我”。
“镜像”理论后来在电影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孩子对镜子中自己的感知,与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面对明亮的银幕并最终离开电影院的观影者的情感体验和心理认知非常相似。“理念我”在观影时,会从电影中寻找“镜像我”,从电影所描绘的社会语境中理解“镜像我”和“理念我”的契合,进而变为“社会我”。
导演在人物塑造中并没有刻意渲染普通民众的辛酸苦楚。导演塑造的草根群体人物画像及其经历都具有典型性,如:景浩即便拿到质检合格的报告,也依旧无法与李平经理平等交谈;汪春梅勇敢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却遭到资本的反抗;梁叔夫妇热心善良,但还是需要看人眼色行事,只敢在深夜放居无定所的景浩兄妹进疗养院。他们的每一丝情感流露都被拥有类似经历的观影者准确捕捉,促使其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
几经坎坷,景浩终于获得成功。此时,典型的草根人物就不再是一群导演虚构的与观影者无关的人物,而是成为观影者的“镜像”。作为“理念我”的观影者和作为“镜像我”的角色在银幕上得到了统一,实现了情感交流。
2.2 主题强调: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认同
一部作品的灵魂是主题,它是作品内容的核心。《奇迹·笨小孩》的主要矛盾就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景彤必须在8 岁之前做手术才有治愈的可能,而此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跑路,只剩下还在读大学的哥哥景浩照顾她,并且景浩要在最后一年内独自筹集到30 万元手术费。从那以后,景浩的一切行动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人物的矛盾冲突,都是为了化解这个核心矛盾而展开的,虽说影片呈现的情节突出了金钱的重要性,但导演将景浩守护家人并找到一群异姓家人组成“奇迹小队”作为落脚点,将对金钱的追求替换成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主题。导演旨在用景浩的奋斗历程来阐释每个人都平等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奇迹·笨小孩》番外篇中提到,妹妹在1 岁多就查出得了家族性心脏病,父亲于是抛妻弃子,懂事的景浩和重病的母亲支撑着家庭的重担。景浩上大学后得知深圳互联网产业发达,有挣钱的机会,于是他才选择辍学到深圳打工。机缘巧合下景浩发现旧零件重新组装成新手机可以赚到钱,可没过多久,“打击翻新机”的政策相继出台,景浩事业遭遇重创。此时,距离妹妹的手术仅剩最后1 年,于是景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重新振作起来,通过努力争取到了大公司回收手机零件的机会,但却苦于没有定金。最终,景浩在梁叔的帮助下建立起电子元件厂,招收了形色各异的草根人物。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磨难、天灾人祸,但都被逐一化解,景浩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和超凡的品格。
“奇迹小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追求美好生活,最终电影展现出了一道群像弧光。身患残疾的钟伟创办了老年公寓,包括其本人在内的200 余位老人在此安居;“追风少年”张超和刘恒志联合创办了网咖,拥有7 家连锁店并承办多场电竞赛事;张龙豪与汪春梅结婚并创办了搏击俱乐部,建立流浪动物救助站;汪春梅还建立了“打工人帮扶中心”,服务了千名打工者。影片中每名成员都凭借自己的奋斗收获了成功与幸福,这无疑给在场的观影者打了一剂强心针,观影者为其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对追求美好生活产生情感认同。
2.3 情境建构:呈现深圳景象的地域认同
“城市意象”亦可称为“城市印象”,即一座城市在公众眼中的形态特征。影片中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背景,其还具备叙述者的功能,可以直接为电影的叙事作出贡献,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推动故事的走向,这就是城市作为一个场景的参与功能[4]。一部电影一旦在开头交代了地点信息,那么该地点就不再是“低介入”,而是“高介入”,因为城市因素会直接影响、改变甚至决定电影的线索或方向[5]。
2013 年的深圳被选为该剧的空间原型。彼时深圳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先进示范区”,是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特区。导演构建了2013 年观影者熟悉的深圳,观影者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也会调动近10 年的记忆,通过导演塑造的深圳的气候、深圳的高楼林立、深圳的拥挤破败等进行想象,进而达到镜像理论的一次同化,观影者仿佛置身其中,产生强烈的地域认同。
深圳承载着太多年轻人的希望。景浩来深圳拼搏,就是因为深圳本就是个奇迹之城,景浩希望妹妹的病也能像深圳一样通过他的努力赚钱可以奇迹般好转。景浩在高空擦玻璃时用水管浇自己,观影者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深圳天气的炎热,饿了就吃馒头,处处体现出打工人生活不易,这与玻璃窗里的人喝着红酒、吃着西餐谈生意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对比还有深圳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混乱的城中村。歌手陈楚生回忆自己在深圳打拼的那些日子,并创作了首歌,“那是高速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喘息角落,也是美妙梦想与残酷现实杂糅并存的驻足之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各种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有理想、有闯劲的青年都来到这个汇聚梦想的城市拼搏,个体命运与时代大趋势具有的天然联系,建构起观影者对于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地域认同。
2.4 意象表达:诠释影像创新的文化认同
真实且生动的细节是丰富故事情节、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增强艺术表现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创作者用来表情达意的有利方式。影片中景浩的背一直都是驼的,说明景浩每天都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例如,影片中有关于房东催房租的情节,第一次房东礼貌地在催租纸上用了个“请”字,第二次便直接写了“交租”,第三次房东更是用红笔写下“交租开门”四字,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可见景浩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片头中妹妹的分隔装药盒表明妹妹需要不断服药,但画面里却呈现出鲜艳的色调,如黄色的沙发、妹妹的黄色杯套、景浩的黄色T 恤衫。诸多意象的对比更加突出景浩兄妹面对不幸遭遇依旧不卑不亢、坚强乐观的态度:景浩带妹妹住进工厂里,早上吃稀饭的碗是买泡面送的;妹妹的衣服都是小女孩喜爱的漂亮的衣服,而景浩的基本都是老款Polo 衫(一种休闲服装);妹妹睡觉用的是厚厚的床垫,而景浩的就是薄薄的被褥。影片中还反复出现蚂蚁这个意象,一方面因为蚂蚁是群居动物,能够利用团结的力量挪动超越自己身体数倍的物体,是自然界的奇迹之一,这与“奇迹小队”互助互救相呼应;另一方面蚂蚁身处偌大的城市之中,虽然微不足道却顽强拼搏,这与景浩的性格很像,即勤奋执着充满力量,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遭到台风侵袭后,厂房坍塌,景浩低着头独自面对巨大的危机,此时镜头转向一只蚂蚁,它紧紧把住铁棚边缘不让自己掉落,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生存渴望,也是景浩内心的真实写照。之后厂里的员工都来了,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要承担接下来的拆解工作,同甘共苦的情谊在此刻得到凸显,强大的凝聚力感染着观影者,使其与片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山同样是影片的重要意象,“奇迹小队”创业的故事可以说是“愚公移山”的现代版本。旧手机第一次出场就堆成了一座山,这象征着当时压在景浩肩上的山,但在战友的通力合作下,这座山被“分解”了。其实,劳动人民的一大优点就是善于“愚公移山”,不畏艰辛,敢于挑战。无论是蚂蚁还是山,这些意象的恰当运用都更易使观影者产生文化认同。
3 结语
导演在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之外加入巧思,使得观影者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和内心情感的满足。对于讲述小人物励志成长故事的新主流电影,可以在镜像理论视域下分析其叙事策略,研究影片是如何通过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强调、情境的建构、意象的表达来给观影者呈现一面自我奋斗的镜像,进而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影片中的景浩作为观影者理想自我的投射,其行为及人格特征都对观影者的自我认知和建构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