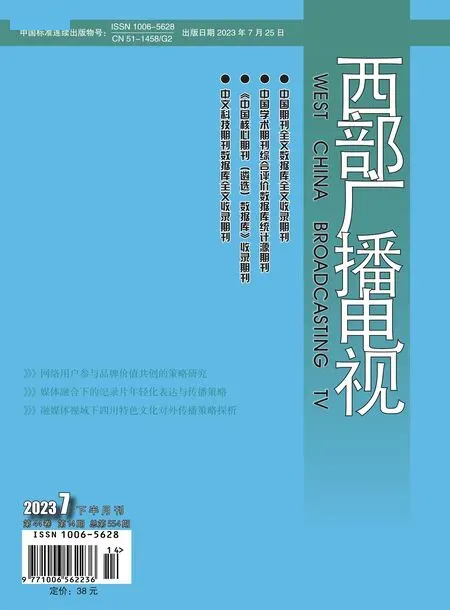转文化传播视域下真人秀综艺“出海”的破界分析
——以真人秀综艺节目《我们的歌》为例
吴佩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中国真人秀综艺节目发展20 多年,经历了分别以简单模仿、版权引进与原创发力为主的三个发展阶段,近年来更向海外不断推出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综艺节目模式。即使一些节目获得了国际制作与发行公司的青睐,签署了合作协议,却始终难以打通“出海”路径上最难的一道关卡——制作播出,从而真正实现“出海”模式的落地。在“转文化传播”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以《我们的歌》为例,剖析中国真人秀综艺节目得以实现“出海”的内在原因,探究如何孵化此类跨文化传播产品才能减少文化折扣,打破文化壁垒,实现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1 视域的转换: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它以传播学为核心,整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20 世纪90年代,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了“Transculurality”的概念,他认为“Interculturality”的概念试图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相互认同,实质上却把文化视作文化孤岛,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因此难以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Transculurality”则倾向于把文化视作多元的、复杂的、丰富的现象,强调了同一文化中不同的特点和各异的表征,而不同文化间是复杂的联系而非泾渭分明的区隔,其中有着许多关联、重叠、渗透、杂合。“今天的文化不再契合以往那种封闭、统一的民族文化观念。其特点是认同的多样性,具有跨越界线的特征”,可以归结为去边缘、去边界、去中心。针对“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学者Ting-Toomey 作出进一步的阐释:“跨文化交际者通过渐进式的学习过程,学会恰当、灵活地相互适应对方的行为……通过向对方发送我们愿意以文化敏感的方式调整自身行为的信号,我们表达了对对方文化参照系的尊重。”此概念被史安斌译为“转文化”。相比以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指向两个或更多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从而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与变化。在转文化传播的时代,要运用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作为“标签”来指认某种单个的文化现象变得极其困难。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赵月枝亦做了相似的表述,她对比分析了“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和“Transcultural”三个跨文化概念,发现“‘Transcultural’包含对前两者共享的文化概念本身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解的扬弃,这一理解强调本来就没有纯粹的、属于一个族群的文化,文化本身意味着混杂,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在群体和个体层面都是如此”。从实践来看,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就是要解决编码和解码的问题、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问题以及文化折扣问题。
其中,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应该关注电视的整体和结构,电视传播的生产环节即是编码/解码的过程,身处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传者和受众是不对称的,相应的编码、解码不构成直接的统一性。这种编码和解码之间的差异即是“编码、解码在构成单元一致的条件下包含不同的内容,而这种内容不是个人的、不可预计的,而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在不同社会文化结构下的不同养成”。按照霍尔的理论,结构化的信息生产过程和建构性的传播内容构成了一个卷入诸多要素、环环相扣、内部充满角力的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所以产生信息的“误读”并不是一种纯属意外的巧合,而是一种由编码解码的机制所导致的系统性后果[1]。
因此,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综艺节目,由于不同文化圈受众本身的文化背景、社会形态、语言体系等的差异,即使面对同样的故事也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必然面对“系统性扭曲的沟通”。转文化实践中需要考量如何达成传受双方的文化转化,不受限于任何一方的文化框架,形成文化杂糅[2]。
2 真人秀综艺转文化传播的破界现象
纵观中国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发展,按照制作来源的不同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模仿为主,如广东电视台的《生存大挑战》第一届、第二届分别借鉴了香港亚视与日本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波少年》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的《幸存者》,在角色设定、环节设置、规则流程等均进行了“移植”。该节目是中国“真人秀”综艺节目的雏形,引发国内各电视台竞相效仿,其中最为典型的节目是2004—2006 年的《超级女声》,2005 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全国收视率达到11.65%,成为中国综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的电视综艺。而《超级女声》的海选、民间造星等概念与创作理念直接来源于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的《美国偶像》。
第二阶段则更注重版权的引进。在《幸运52》《开心辞典》《舞动奇迹》等引入英美节目版权进行试水后,2010 年东方卫视从英国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 ITV)购买版权并制作《中国达人秀》,签署了节目制作保证忠于原版的协议,也打开了引入正规节目版权的新局面。2012 年,浙江卫视引入荷兰Talpa 公司《The Voice》的版权制作了《中国好声音》,大获成功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电视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其后《奔跑吧兄弟》等节目模式被相继引入制作并热播,这些节目以版权购买的方式得到了版权方全方位的指导,掌握了综艺节目制作的核心,原汁原味地呈现了节目效果,同时也避免了综艺节目因为模式、环节与国外节目的相似与重合陷入版权纠纷的风险。
第三阶段是与版权引进同步发展起来的原创勃兴。经过模仿、版权引入、联合制作等阶段后,我国综艺迎来了创新与突破的阶段,《中国好歌曲》《声临其境》《国家宝藏》等原创节目,就是基于中国语境与经验的自主创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综艺节目同质化严重、国外综艺节目版权引进难以避免的文化差异与冲突等问题,也由此开启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先河。中国电视人在法国戛纳春季电视主舞台上,第一次以“原创节目模式”推出了系列台网综艺《国家宝藏》《朗读者》《声临其境》《天籁之战》《跨界歌王》等。同年10 月,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出席了戛纳秋季电视节,《我就是演员》《这!就是灌篮》等原创综艺与海外公司签署了节目模式输出协议。这种逐渐规模化的“模式出海”推广,意味着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节目模式研发步入了正轨。
然而在后续实践中,较难真正实现反向输出。究其原因,主要是文化壁垒的存在:欧美电视生态环境有限制,而我国版权方又缺乏主动性去探究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共存的可能和机制等。可见意义共享是转文化传播的切入基准,有效融合则是手段。东方卫视《我们的歌》节目模式得以成功破界“出海”,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充分实践。
3 真人秀综艺转文化传播的破界逻辑
《我们的歌》是一档代际潮音竞演综艺节目,从2019 年于东方卫视开播第一季,至2022 年已是第四季,主要内容是由新生代歌手与曾叱咤华语乐坛的前辈歌手联合创作改编经典歌曲,现场演绎并进行评选。其首创的跨代际音乐合唱模式一推出即让人耳目一新,以下主要从内容、形式与新媒体赋能的角度,分析《我们的歌》节目模式得以真正落地欧美的深层原因。
首先,《我们的歌》的叙事符号主要借助诉诸听觉感知的音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文化背景和语言壁垒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的接受与理解障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经几代人传唱的本土经典歌曲,承载了记忆与情感,版权购买方可根据当地观众的关注点与兴趣点对本国新老歌手、经典歌曲进行替换,模式复制比较简单。其“代际传承”和“合作创新”的核心价值不受限于国籍与文化,而是属于全人类皆可体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基于这种共情,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淡化,人们共有的感情愈加凸显,并呈现出多元并存和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局面。节目中通过“音乐创新”角度、“盲选配对”形式和“代际竞演”模式等,设置容易引发共情的环节和内容,通过情感调动生理反应,实现人内传播,迅速拉近不同文化主体间的距离[3],让他们聚集起注意力资源,并且基于情感的一致性对所看到的信息内容进行同向解码,尽可能地减少文化折扣。
其次,东方卫视拟定了详尽的制作手册,记录下了从雏形设想到制作完成整个过程中的具体环节,比如分集主题的预先设定,人物性格的塑造和突显,真人秀与主舞台之间的配合,节目中的彩排,表演过程中的卡位等。手册内容还涵盖了协调人员进行节目生产的规则与注意事项,比如演员之间的关系调节、组合之间进行团战时的搭配原则,以及遇到演员档期出现冲突时的处理办法等,这些皆来源于版权方制作人员总结整理的《我们的歌》前三季的实践经验。在筹备与录制期间,中外团队亦进行了多轮细致周密的讨论与商榷,以便制作方通过标准化流程“复制”节目模式,保证节目形式与风格的一致性,提高制作效率,也有助于重现良好的节目效果与高收视率。
再次,东方卫视运用社交媒体为节目推广赋能,为制作方提供了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的可视化样本。现如今,国内的抖音、快手等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及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社交媒体已成为电视台综艺节目宣传、分发其信息与资讯的重要阵地。例如,东方卫视打造了全网亿级规模的“番茄新媒体矩阵”,以持续运营进行“快进式吸粉”,《我们的歌》通过节目与微博超话、微信公众号文章、微信朋友圈、网络短视频、网络图文海报相结合的“1+5”台网联动传播策略,实现了节目播出的前中后期与尽可能多的用户在不同终端的连接,完成了对节目的全面推广与宣传。
4 真人秀综艺转文化传播的破界效应及其启示意义
《我们的歌》从“迈出去”到“卖出去”的出海实践,既注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因,也与版权购买方的本国文化进行了深度交融,同时给了不同文化主体自主表达与意义阐释的权力空间,由此在相互构建、吸纳融合的过程中,“杂糅”出与当地文化习俗和观念相匹配的新形态与新模式。这种破界效应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即对外传播具有启示性意义。
首先要消解转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重点是着眼于人类共同价值层面的文化诉求和文化主张。爱德华·霍尔的“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二分法把文化折扣视为因语境文化差异引发的后果。“高语境文化”主要依靠语境来传递信息,将交流的内容施加于“上下文”或“内部”的过程,而不是通过对言语进行“加工”的过程,比如中国、日本等;“低语境文化”主要依靠信息编码进行意义传递,注重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对上下文的依赖程度偏低,比如欧美多数国家。在传递过程中,一方面,通常会忽略在情境中所包含的大部分隐含的意义,只有少数符号蕴含的意义被解读出来。另一方面,正如埃德兰·兰德研究结果显示的,人类的大脑能够提供缺失的信息,因此,“低语境文化”的接收者会依据自己的认知来补充传播者透过语境传递的信息,从而导致高语境下的象征意蕴被歪曲。正是由于这些在沟通中的信息失真和歪曲,导致了文化折扣产生。
从减少文化折扣的角度考虑,转文化传播的内容适宜选取受众熟悉度更高的叙事符号、更具普遍性的共同话题或母题,通过创作方式和叙事体系的设计,以共享情感建立起连接,引发情绪的共鸣[4]。比如《我们的歌》中关于“代际传承”的意义阐释,很容易引起外国观众的共同感知,这种共情“引起的社会性情感共鸣能够形成特定的记忆场域,延长记忆的时间,同时也能够参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这一长效的情感记忆能够形成一定的凝聚力,构建起特定的社会关系或圈层,从而形成持久的传播力”。
其次,中国对外的转文化传播应侧重于探究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共存的可能与架构。对于真人秀综艺节目来说,应考量当地目标受众的偏好,运用其青睐与习惯的传播符号、叙事形式和传播渠道,因地制宜地进行表达、沟通与认知构建。具体而言,传播者在编码时即对受众有一定的文化认知和背景理解,所以可以主动、及时地调整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在设计传播内容产品时,要把受众群体的偏好纳入其中,借助社交媒体等手段收集调取年龄、地域、职业、经济收入等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投其所好进行内容呈现方式与交互环节的设计,帮助受众在解码时尽可能地消解对异质文化的对抗性解读。例如,《我们的歌》以“借船出海”的方式与Grupo Ganga 制作公司、西班牙国家电视台RTVE 合作,制作方根据受众的惯常语感,将其名称改为D ú osincre í bles(《不可思议的二重唱》),邀请的歌手在本土化的同时也极具多样化,包括流行歌手、民族歌手、歌剧演员、网红歌手、情侣歌手等多种类型。为了显示节目的代际特色,迎合观众对于反差感的综艺欣赏需求,选拔参与者时年龄跨度也从20 岁至70 岁不等。这一系列本土化操作,使得大多数观众在观看体验中并未明显意识到节目的“中国身份”,而是专注于娱乐感受和情绪体验,节目信息的编码得以从“硬销”转为“软销”,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建了受众的认知[5]。
《我们的歌》节目模式“出海”的成功试水,既有利于归结可复制化渗透因素,以在后续进行更大规模、更多元化的对外传播,也警醒着应更长远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多重意蕴,挖掘其精神内核和创新呈现,让中国价值观得以从“表层文化”到“深层文化”持续输出,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