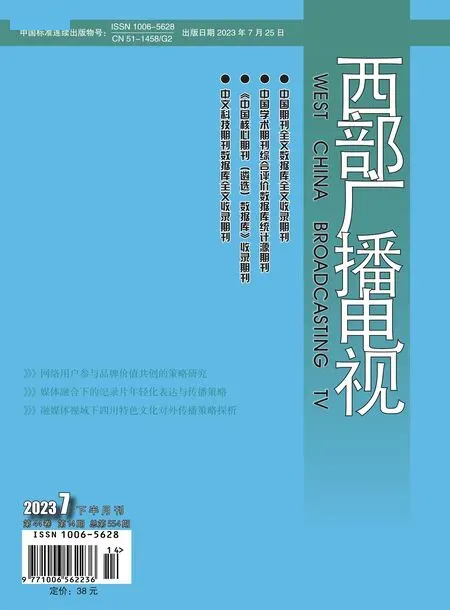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
——以影片《调音师》为例
丁 瑜
(作者单位:长春光华学院)
大多数的印度电影,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众人载歌载舞的场面,以此来营造喜庆、欢乐的氛围,而电影《调音师》摒弃了印度电影传统中的歌舞元素,用惊悚、悬疑等更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方式来表现故事。《调音师》又名《看不见的旋律》,是根据法国同名微电影改编而成,于2019年4月在我国上映。导演斯里兰姆·拉格万在微电影《调音师》的基础上,保留了原微电影的核心情节点——一桩不小心被撞破的意外谋杀案,在原故事的基础上丰富了情节,不仅延展了原短片的内容,更是给观众留下众多思考。整部影片通过男主角阿卡什的第一视角,对人性进行了深度剖析。
从创作形态上看,《调音师》是一部黑色悬疑喜剧,本质上塑造了“人性之恶”,剧中大量反转的黑色喜剧情节让各个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1]。《调音师》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开头阿卡什的那句“说来话长,咖啡?”开启了故事,结尾阿卡什又说了一次“说来话长,咖啡?”代表着故事的闭合,前后相互照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环。这种设计是在暗示观众,整个故事是阿卡什以自己的视角进行的一种回忆式讲述。阿卡什既给故事中的苏菲描绘了事发经过,也给故事外的观众讲述了故事的过程[2]。正因阿卡什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调音师》成了一部“耳听为虚,眼见不实”的电影,更深入地勾起了观众的探寻欲望。
1 不可靠叙述者的类型
“不可靠叙述者”属于显性叙述者的范畴,是叙事学中的常见概念之一。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先提出了叙述的可靠性问题,“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3]。
詹姆斯·费伦发展了韦恩·布斯的观点,提出不可靠性可以在三个轴上发生:两个是布斯提到过的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还有一个是布斯没有提到的知识/感知轴[4]。沿着这三大轴区分成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5]。
我国学者林咏认为,涉及不可靠叙述者的,可以从人格、智商和情感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学者尤达在此基础上,将不可靠叙述者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叙述者不由自主地受到人格、梦境、视角、智商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叙述不可靠,而后者指叙述者出于道德、想象等因素故意欺骗、隐瞒或误导观众[6]。
毫无疑问,在《调音师》这部电影中,阿卡什的叙述多数情况下都是主动不可靠叙述,不仅“以恶制恶”的价值观不可靠,其传递出的各种信息也不可靠,唯有苏菲参与的少数场景才是可靠叙述。但要想具体分析阿卡什哪些话是可靠叙述,哪些是不可靠叙述,还要结合电影本身,从“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和“知识/感知轴”这三个层面去分析。
2 不可靠叙述者阿卡什
电影《调音师》中的阿卡什,是一个善于隐藏自我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欲望,但并不是通过自我努力来获得成功,而是靠一个假性自我来完成——假扮盲人。为了让自己不露破绽,他白天戴隐形眼镜,晚上戴眼罩,而盲人音乐家的身份为他带来了很大便利:一是能够享受政府给残疾人提供的低租金住房;二是能让女人对才华横溢的他心生好感;三是能让别人对他放松警惕[7]。这是阿卡什用第一人称叙述在故事层面完成的“人物自我”的功能。而与苏菲在异国重逢使阿卡什从话语层面实现了“叙述自我”的功能,这直接影响了阿卡什叙述的可靠性。
阿卡什言语中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两者之间相互转化。为了让自己说的话听起来真实可信,阿卡什在不可靠的叙述中隐含了一些可靠信息。整部影片中,阿卡什明显是一个为了一己私欲就欺骗大众的主动的不可靠叙述者,他不断为自己辩护,甚至美化自己的行为。
2.1 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
阿卡什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都在两次去警察局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第一次阿卡什去公安局,其目的是报案,可意识到凶手就是警察局长,自己很可能会暴露后,他谎称自己是来求警察帮忙找走失的猫;第二次阿卡什作为普拉默一案的目击者出现,但他却做了伪证:这都是错误报道的表现。
不充分报道,被热奈特称为“少叙法”,是指叙述者讲述的内容少于他所知道的实情。阿卡什第一次去警局,他正要交代自己看到的全部凶杀过程,却在看到警察局长时戛然而止;第二次到警局他依然没有将知道的事实和盘托出,反而在虚假证词上签了字;甚至后来对普拉默的女儿也隐瞒了普拉默死亡的真相:这都是阿卡什对事实的不充分报道。
阿卡什作为叙述者,为了自保故意隐瞒真相,是符合逻辑的,能够得到观众的理解,但这选择破坏了他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性,在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叙述破坏了故事内在的叙述可靠性,说明他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8]。
2.2 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
警察局里,阿卡什在听到警察读假证词时,在自己的脑子里脑补了一场自己不畏强权、当着众人的面勇敢揭发警察局长和普拉默的妻子西米有奸情,两人合谋杀害普拉默的画面,把自己想象得英勇无比。这其实是他对自我在价值上的一个错误判断,是他在下意识地抹去自己不符合正确价值观的行为结果,是他对道德的反思[2]。在警察局做完伪证后,阿卡什已经偏离了他原本所站的看似正义的立场,价值观也逐渐开始扭曲,对整个故事的叙述产生了影响,凸显出他叙述的不可靠性。
2.3 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
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是指叙述者认为自己具备某些品质,而隐含作者却暗暗加以否定,这是叙述者因自身知识的局限对自己的性格进行的错误解读。
在影片结尾,阿卡什以盲人音乐家的身份与苏菲在欧洲偶遇,将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情娓娓道来。他告诉苏菲自己被开突突车的莫里、卖彩票的老妇人等同伴背叛,与西米被关在同一个仓库里,他一直在劝西米跟自己一起去警局自首,还着重强调自己在车里真诚忏悔,希望斯瓦米医生能放过西米。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当时医生听到西米不断撞击后备厢的声音后停车去处理,反被西米杀害。西米开车时,阿卡什表达了自己想放过西米的想法。为什么阿卡什和医生同行那么长时间都不说出这种想法,反倒等西米上车后才说呢?其中一种解读就是他凭自己的敏锐发现上车的人是西米而不是医生,帮西米说话不过是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通过阿卡什与苏菲分开后,他在夜色中准确地用拐杖打中易拉罐来看,他的眼睛已经复明,那么之前的叙述便全是不可靠的。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医生帮他移植了西米的眼角膜。阿卡什在自述中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而他的行为是对他叙述的否定,换句话说他对自己存在错误和不充分的解读。在他的认知中,这样的说法能够获得苏菲的同情,让她为自己感到惋惜,也能让他继续以盲人音乐家的身份生活下去。
显而易见,无论在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还是价值/判断轴上,阿卡什都做了不可靠叙述,无形中增加了影片的悬疑感。
3 不可靠叙述的作用
不可靠叙述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创作中,而不可靠叙述者的讲述让影片充满悬念,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3.1 营造独特的故事形式
悬疑影片的故事形式多采用“提出问题—展开问题—解决问题”的叙事模式,问题不仅供给叙述者去解决,而且要让影片中的参与者相信,让观众去猜测,从而推动故事发展。在影片《调音师》中,阿卡什的讲述逻辑严谨,一度骗过了片中人物,也骗过了观众,但很快不一致的言行就暴露了他的谎言。在阿卡什的讲述中,他是善良的,看到凶案也曾想揭发,只是不得不向现实屈服,这是他遇到的问题。前期他一直想办法躲避追杀,后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被追杀而不得不奋起反击的人,这个为了自保而“黑化”的理由博得了观众的同情与理解。观众跟随阿卡什的叙述,误认为他是个受害者,于是不自觉地被带入相应的情境中,每次他陷入危机观众都不自觉地为他捏一把汗,直到他用兔头拐杖精准打飞易拉罐,这一行为暗示他此时的志得意满,更说明他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包括他那被毒伤的眼睛。可他到底是何时开始说谎的,又是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恢复了视力,这些看似已经解决实际上悬而未决的问题,让故事又陷入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中,所有问题都留给观众去探究。
3.2 达到反讽效果
布斯在研究中着重关注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效果,这也是不可靠叙事在文本中最直接最显性的效果[9]28。在影片《调音师》中,阿卡什对许多信息的不充分报道和错误判断,让他这个形象充满了反讽意味,明明是个满口谎话的利己主义者,却偏要把自己形容成一个道德感较强、面对危险也不愿伤害他人的人。此外,《调音师》的反讽不仅是针对社会情境,也包括对叙述者的讽刺[8]。苏菲在影片中的出场并不多,仅有的几次出场也多是岁月静好的场面,对于阿卡什的凶险经历,她未曾参与,所了解的一切都来源于阿卡什的叙述。苏菲善良温柔,满足了阿卡什对爱情的幻想,也正是如此让她陷入了一种“眼见不实、耳听为虚”的窘境中。她对阿卡什欣赏挂画、准确拿爆米花的行为视而不见,却相信阿卡什与西米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并且认为这是阿卡什疏远自己的原因,因为这是她亲眼所见。前期她不给阿卡什辩解的机会,后期重逢时又轻易相信了阿卡什的叙述,甚至认为西米杀了那么多人,阿卡什就应该取她的眼角膜。自以为是的苏菲,外表美丽但内心狠毒的西米,邻居家贪财的小男孩班杜,唯利是图的莫里和卖彩票的老妇人……这些都是反映人性的典型人物。如果上文所提到的阿卡什与斯瓦米的确是合作关系,那么导演还想用这种看似荒诞的叙事抨击印度本土倒买倒卖器官的社会现实,以此凸显影片主题。
3.3 可根据影片进行多重解读
当悬疑片中隐含作者的意旨(情节的事实真相)有模棱两可之处,或放弃明确的指引时,逻辑线便需要观众自行推断出来,这就形成了多种解读的可能[9]29。而这一结果,离不开不可靠叙述者在影片中起到的作用。《调音师》能够引起关注,就在于阿卡什这个不可靠叙述者让故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真实的故事是怎样发展的,只能根据蛛丝马迹去自行想象。换句话说,影片中的故事内容可供观众从不同角度进行多重解读。影片通过运用阿卡什的不可靠叙述手法,让观众不断挖掘,只想梳理故事真正的发展脉络,从而看清阿卡什的为人。
印度虽然允许私人持枪,但需要经过层层筛选调查才能获得持枪资格。获得持枪的合格证后,还要学习枪支的使用方法,并且印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那些合法持枪的人进行审查。那么,普拉默被警察局长枪杀,就应该根据子弹确定枪支持有者,进而锁定嫌疑人,但关于该案件却一直没有下文;西米去阿卡什的家中试探他是否真盲,而单身的阿卡什却用情侣杯招待西米;苏菲敲门,西米明明可以不开门,假装家里没人,却披上床单假装她跟阿卡什有染……这些情节影片都以阿卡什的视角叙述出来,叙述中充满了破绽,却一直没被剧中人物所关注到,这设定也值得深思。
影片中除了阿卡什的视角外,还有苏菲的视角,她看到了阿卡什比较纯粹的一面,认为阿卡什是个很有才华的非常吸引人的盲人音乐家,她每天都笑意盈盈,沉浸在幸福中。苏菲作为参与者的这部分叙事是可靠的,而苏菲见过普拉默、西米和班杜,所以这三人是真实存在的。至于警察局长、莫里以及其他人,都只存在于阿卡什的叙述中,是否真有其人就很难考究了。
通过对各种细节的分析,发现对影片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即阿卡什与斯瓦米医生很早就合作了,两人辗转多地进行器官买卖。阿卡什用盲人身份首先博得女人的同情,然后靠自己的音乐才华和帅气脸庞骗取女性信任,之后再与斯瓦米联手贩卖女性肝脏等器官。阿卡什与西米早就认识,两人是情侣关系,是阿卡什与西米联手杀害了普拉默想要私吞财产,警察局长这个情夫根本就是阿卡什编造出来的角色。让这个犯罪团伙分崩离析的是,阿卡什遇到热情的苏菲并爱上了她,想要金盆洗手,可西米不愿意放弃他,于是他就杀了西米,卖了她的器官。这种解读不仅能够解释之前的几点疑惑,也与片头出现的那句“什么是生命?这取决于肝脏”相契合。
片中大量的不可靠叙述加上这些隐含叙述造成的不同角度的解读,留给观众多重解读的空间,并使其产生了对故事一探究竟的心理。
4 结语
《调音师》以阿卡什的第一视角回溯重构整个故事,这个不可靠叙述者的讲述增加了故事的悬念,有利于叙述形式多样化。而《调音师》开放式的结局拓展了画外空间,赋予影片更深刻的批判内涵,因此不可靠叙述者也成为近年来悬疑片的首选叙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