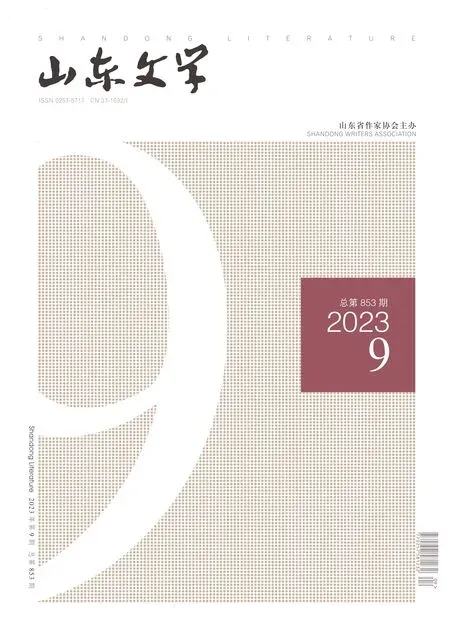美芹策、豪放词和四风闸村
柳 复
一
宋金之际,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东北三十余里处,有一处村庄,名唤四横牐,因附近一条河流上设有四个横拦河水的牐口而得名。由于方言口音之讹,四横牐演化为四风牐,而“牐”也被更方便地写为“闸”,遂有今天的四风闸之名。村西方向突兀一峰,是华不注山,李白称赞“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村的西南,有一座矮山,处于春秋时期属五霸之首齐桓公的重臣鲍叔牙封邑内,故名鲍山。鲍山向西偏南,就是甸柳庄,距离历城县衙便不远了。村北不远处,小清河逶迤流过,溯河而上可到一片水泊,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府城中趵突、芙蓉、黑虎、五龙潭等名泉清流汇集而成的大明湖。小清河之北,有一条更大的水系,是济水,济水之源在遥远的太行山南麓。济水流经河南、河北、山东许多地方,吸纳众多支流,在济南府城北经鹊山、华不注山之间,浩浩荡荡向着大海奔流,济南之名因此而得。村东远处,绣江河携带着明水湖的碧波向北流过,章丘百脉泉群的清流日夜补济着湖水,李清照常常记起的尽兴沉醉藕花深处美景而回舟太晚不知归路,就发生在明水湖岸外某处溪亭附近的日暮时分。村南更远处的绵绵群山,峰峦如聚,河川相连,是岱岳余脉,藏有开元、兴国、灵岩等宝刹。四风闸村就在这样的山河之间,拥有方圆十数里一马平川的土地,勤劳的村民耕作陇亩,曾经过着物阜人康的生活。
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 年)五月十一日,一个男婴降生在四风闸村一处药栏围绕、数株梧桐冠盖的庭院,门前有石泉流过,院里房屋装饰陈设都是北宋官宦风格。时值入卯,月潜日出,梧桐树下初成荫,满庭清昼的时空已经错位十五个年头。从华北到中原,北宋的大片土地被移入金朝版图,四风闸就是变动版图中被裏挟的一个斑点。婴儿的诞辰其实应该用另一种纪元:金熙宗天眷三年。婴儿的祖父为他命名弃疾,借鉴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大名,期冀他成年之后能像霍氏一样驱逐外虏,剜弃家国之疾,恢复宋朝在华北和山东的广袤河山。弱冠之后为他取字“坦夫”,希望他成为坦荡如砥、博学多才的大丈夫。
这个婴儿姓辛,祖父是辛赞。他的父亲辛文郁,在他三岁时不幸病逝。四风闸村,就是辛弃疾的家乡,他二十二岁前的生活与此地紧密关联。
“药栏围竹屿,石泉逗山脚。风流不可攀,谁结一丘壑。斜阳甸柳庄,长歌自深酌。”清代德州籍诗人田雯造访四风闸,凭吊辛弃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彼时田雯眼中的四风闸是否实写,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六句诗有三句源出辛弃疾词《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一丘壑,老子风流占却。茅檐上、松月桂云,脉脉石泉逗山脚。寻思前事错。恼杀晨猿夜鹤。终须是、邓禹辈人,锦绣麻霞坐黄阁。长歌自深酌。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词句所写是辛弃疾被贬官退居瓢泉意象,田雯诗中三句出于此词,面对四风闸辛氏故村的变幻,写实的可能性应该较小。遍寻典籍,南宋以降,文人造访四风闸村的诗文记载可能唯此一首,少得可怜。究其原因,四风闸旧居在辛弃疾的诗词中几乎没有出现,而远在赣南上饶的带湖稼轩、铅山县瓢泉的居所在辛词中频繁出现,更为文人士子所熟知,几乎被认作他的故乡。
经过九百年风雨淘洗,四风闸村还在,村里却没有了辛姓人家。村外辛弃疾旧居纪念馆已经建成多年,我二十多年前曾经造访,而今再来,大门紧闭,据说前期闭馆后就未曾开放,我不得入,甚为遗憾。可能是因远在城郊的缘故,这处旧居远不如济南城里大明湖景区的辛稼轩纪念祠更招游客抬爱。
二
辛弃疾生活的历城县有讲究气节的乡风民俗。清代乾隆年间所修《历城县志》载:历城男子多务农桑,勤俭持家,贵礼尚义,推崇读书,劲勇顽强。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说“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是他基于历城乡俗扩而大之对山东民风的认知。辛弃疾受乡风影响,少年时代就习武学剑,练就英勇本领。辛赞在金朝历任沂州、海州、宿州等州吏和亳县知县、开封知事等职,但气节不馁,自认宋朝遗民,“被污为官”,一直“思投衅而起”,期盼回归赵宋。辛赞在迁徙为官中,精心抚育幼年丧父的辛弃疾,延请名师严加教诲。辛赞的思想和行为,对辛弃疾的影响极其深刻。乡风的浸濡,祖父的引导,使辛弃疾苦练本领,铸就“一世英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英雄品格。
辛弃疾“以气节自负”的品格,在求学时期就呈现出来。辛赞任亳州谯县知县时觅得名师刘瞻,将辛弃疾送其门下受教。刘瞻是当时闻名的田园诗人,对儒学教义精研深究,辛弃疾在其一众弟子中虽然年龄最小,但学业拔萃,深得器重。辛弃疾受业刘瞻七八载,期间与年长七岁的泰安人党怀英交好,成为刘瞻最得意的两个弟子,时称“辛党”。其间辛赞升任开封府知事,辛弃疾与党怀英同到开封,游览北宋宫殿凝碧池遗迹,看着破败的旧朝宫阙,党怀英深以为胜王败寇,而辛弃疾感受的却是金兵残暴,“管弦凝碧池上,记当时风月愁侬。翠华远,但江南草木,烟锁春宫”,发出唐代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般的兴亡之叹,砥砺意志,思谋恢复旧时东京繁华。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二人志向不同更加明显。传说刘瞻令二人用蓍草占卜前程,辛弃疾得“离”卦,象征火,南方属火,意味将来南渡,党怀英得“坎”卦,象征水,指北方,预示将北赴金朝为官。从此两人志趣越发迥异,多有争执。后来同游灵岩寺,辛弃疾设想在此布阵,定能重创南下的金兵,而党怀英则认为即使布阵重创也不能阻止金朝铁骑的步伐。辛弃疾登上一座小山,指石为馔,捋风为酒,对党怀英说“吾友安此,余将从此逝矣”,遂假酌而去,从此绝交。从辛党绝交中可以看到,辛弃疾时刻以雪仇复土为念,对党怀英即使师出同门仍毫不犹豫断绝来往。
辛弃疾青年勇武的历史记载,体现于杀、擒两个叛徒的英雄行为。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 年),金朝皇帝完颜亮亲率大军南下,兵临长江采石矶,目标直指建康城。此时二十二岁的辛弃疾在四风闸“鸠众二千”投衅而起,在济南南部山区试图阻挡金兵。两千人的队伍面对几十万虎狼之师,虽劲勇敢创,也只能伤其皮毛。辛弃疾权衡之后率众加入济南人耿京为首、规模多达二十五万人并已攻克泰安、莱芜等城的起义军队伍,任掌书记。在耿京军中,辛弃疾单枪匹马追杀叛徒义端。义端本是僧人,与辛弃疾友善,因寺庙所属土地被金朝的屯田军侵占而聚众起义,在辛弃疾劝说下加入耿京队伍,义端像辛弃疾一样被耿京重用,但浮言贪财的本性使其不能如愿,愤懑不已,趁夜盗出耿京帅印投奔金兵欲讨封赏。耿京次日一早发现帅印被盗,迁怒之下欲斩辛弃疾。辛弃疾请求说:“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辛弃疾只用一日就将义端追杀,携其头颅掷于耿京帐前。耿京看辛弃疾勇武有谋,更加信任,军中大事多与商讨。
耿京起义军队伍勇武不惧,英猛善战,攻下山东西路东平府所在的郓州城,以北宋曾驻扎于此的天平军自号。但粮草接济不足,耿京担忧早晚被金兵所败,辛弃疾建议联络南宋官军,相为呼应,一旦危难不支就南渡归宋。耿京深以为然,遂派辛弃疾等人到江南联络。辛弃疾奉耿京表章南渡建康,正在建康巡幸的宋高宗大喜过望,就势将耿京队伍正式命名为天平军,对大小将领二百余人大加封赏,并派枢密院两位官员随辛弃疾赴北宣诰。北返途中得知叛将张安国杀害耿京,被政变上台的又一个金朝皇帝完颜雍赏官济州知州。辛弃疾对叛徒张安国切齿痛恨,与宋将王世隆率五十骑突袭济州金兵大营,设计将正在帐中宴饮的张安国骗出,缚置马上,急速押回建康,张安国被斩首于临安市井。洪迈在《稼轩记》中述说:“余谓侯本以中州隽人,抱忠仗义,彰显于南邦。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深简知。”长途奔袭,深入敌营,智取叛徒,又千里押送,宋高宗由此深知辛弃疾的英雄胆略和强悍战能,任命其为江阴签判。从此,辛弃疾在江南辗转为官,其间起起贬贬,再没有机会亲看一眼四风闸村的故居庭院,只能在他的诗词里惦念了。
辛弃疾的英武,在这两次追杀、智擒行动中得以淋漓表现。追杀义端时,史载义端跪地求饶:“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青兕”一喻,出自和尚之口,为辛弃疾膂力过人的形象涂上神秘的先天色彩,虽有传奇成分,仍足见其英伟勇猛的武将本色。后来,多位南宋名士描述辛弃疾形象的用词与“青兕”一说呼应。陈亮说辛弃疾“眼光有棱,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背负有胛,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刘过说“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青眼”。
三
独骑杀义端、智擒张安国,只是牛刀小试,辛弃疾更大抱负“驱除金兵,恢复中原”始终萦绕心怀。与持剑杀敌的勇武相比,辛弃疾的北伐韬略《美芹十论》和《上虞雍公九议》同样令人佩服。
《美芹十论》是乾道元年(公元1165 年)辛弃疾二十七岁时越职进呈宋孝宗的一部奏疏,陈述北伐复土方略,分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和详战等十篇,“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态度坚定,目标明确,策略具体,措施有力,是南宋在强悍的金朝军事恫吓下符合双方实情的持久战之论。《美芹十论》原名《御戎十论》,呈奏宋孝宗时辛弃疾任广德军通判,官阶低下,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但“爱主之诚可取”,图复中原的豪志使他“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借用“野人美芹”的典故呈奏。次年辛弃疾改任建康府通判,被宋孝宗召至延和殿对论抗金对策,又呈送《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陈述淮南东、西两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提出为北伐经营两淮的策略,尽早变更优化战场布置,措施更加具体可行。
乾道六年(公元1170 年),辛弃疾又向当时主战宰相虞允文进献《九议》,内容与《十论》相似,以坚定虞氏北伐必胜、恢复必成的信心。在《九议》引论中,辛弃疾明确表示:“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铁骨铮铮,敢作敢当,言语之中不给自己留一丝后路,体现着对《美芹十论》和《九议》所提策略对战胜金兵的高度信心。
《美芹十论》及《九议》两部雄文得以产生,除了辛弃疾天才般的军事战略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他青少年时代与其祖父辛赞共同对金朝上下的观察和分析。
家在四风闸的二十余年里,辛弃疾随辛赞历官求学、两次到燕京参加金朝科举,在辛赞的指引下观察、搜集金朝的“形”与“势”,多年累积,为投衅而起做准备。辛弃疾在《美芹十论》札子中自述:“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为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河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从这些自述可见,辛弃疾从小受祖父影响,对侦察被金朝侵占二十多年后山东等地的地形、军事部署、社情民意,工于心计,下了很多功夫,积累起方方面面的情报资讯,逐渐形成明晰的策略判断。对金朝多年多地乃至以科考为名两次深入燕京的观察,是辛弃疾得以写出《美芹十论》的基础。没有辛赞引导下的“登高望远、指画河山”,没有“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就不可能有“审势”“察情”“观衅”篇中的分析和研判。《美芹十论》及《九议》,是建立在辛赞、辛弃疾祖孙俩“历宿、亳,涉沂、海”以及辛赞任金朝开封府知事十余年“调研”基础上的结论。辛弃疾所言“谋未及遂”中的“谋”,应是与辛赞共同的谋划。辛弃疾强烈的北伐愿望,与辛赞的引导和教诲不可分,《美芹十论》和《九议》凝结着辛赞的贡献。可惜没等到谋划全部完成,辛赞辞世。假设辛赞不过早辞世,仍在金朝的开封知事任上,他会不会像范邦彦“率豪杰开蔡城以迎王师”一样“尽室而南”?虽未可设想,但以辛赞“思投衅而起”的作为,想来大概率是会的。《美芹十论》和《九议》之平戎大策,就人而论,无论辛赞是否过早下世,融含着其心血确属无疑;就地而论,与辛氏祖孙所生活的四风闸村密不可分。
从《美芹十论》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的内容上看,也凝结着辛赞的认知和心血。这三篇策论对金朝的弱点做了详尽深刻的分析。
首先,金朝看起来地广、财丰、兵多,其实有三不足虑。其疆域“虽名为广,其实易分”;其财赋“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其兵力“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况且金朝内部官员互相猜忌,皇族派系残杀迭出,必将自取灭亡。
其次,金朝当时和战两难。辛弃疾认为金朝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三不敢必战:完颜亮调动金朝几乎全部兵力南侵,完颜雍发动辽阳政变进入燕京取而代之,完颜亮在采石矶被虞允文大败后又孤注一掷,仓促间在扬州再次进攻江南欲取临安,被部将所杀兵败身亡,完颜雍不会重蹈覆辙,很难再次发兵南下;海、泗、唐、邓四州被宋军收复已经三年,金兵未能夺回,契丹旧部在金朝后方侧目而视,中原士民扼腕相向,有可能起而反金,完颜雍顾虑重重。二必欲尝试:金朝怕得不到南宋的岁币,会不间断出兵进行威胁;金朝心存侥幸,认为虚张声势出兵,可能会从南宋获取额外好处。
再次,辛弃疾认识到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中原士民心向宋朝,金朝统治下北宋故土百姓倍受欺凌,“有常产者困窭,无置锥者冻馁”“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大大小小的起义此起彼伏。他们经过多年战乱,已经适应战争,并且能攻善守,盼望南宋王师北上,复归宋朝的愿望强烈而坚定。
辛弃疾分析金朝的这些弱点,得出南宋其实是可以战胜金国的结论。辛弃疾这一判断,不是到南宋以后凭空得出,而是建立于在山东生活时期与辛赞共同观察基础上,是祖孙俩人调查研究的结果。而研究,应是许多时候在四风闸的家中进行的。由是而言,美芹策出四风闸,并非妄说,实乃其来有自。
《美芹十论》是辛弃疾以四风闸村为圆心的早年生活经历砥砺而出的恢复宋朝北方故土志向、气节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文字结晶,是他一生北伐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北伐策略的基础表达,此后重要论兵奏疏都反复体现着《美芹十论》的基本主张,《九议》承续《美芹十论》,是《美芹十论》别版。在这两份奏疏中,辛弃疾特别强调,备战首先要“自治”,分清大是大非,必须在思想上破除“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于争衡中原”的畏战谬论,树立北伐必胜的信心。辛弃疾主张北伐是南宋的国家大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长期作战,多方准备。要从长远出发,不可为战而战,要为胜而战,反复提出“无欲速”“审先后”,宜“久任”,要“致勇”,能“任败”。辛弃疾提出“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要“详战”,详细研究所战之地,否则就是“浪战”。在详战策略中,辛弃疾提出“地有险易,有轻重,先其易者险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轻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非山东莫属,他屡番在美芹、守淮、九议等奏疏、呈文中主张要先出兵山东地区,“使兵出沭阳(海州属县),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北伐大计就可告成,而且详细阐明先出兵山东而后北定中原的进军线路和具体步骤。整个南宋时期,主和派在朝廷占据上风,不敢出兵北伐,也有主战派占上风的时候,发动“隆兴北伐”“开禧北伐”。但两次出兵,均采取从河南贸然进军,意图先收复汴梁故京,以长志气,而未从战略考虑采用辛弃疾主张先出兵山东的合理策略,结果丢盔弃甲大败而返,落得屡次纳币进帛的下场。
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历史记载他治理经济有所作为,把北宋经济繁荣的景象部分地延续到了南宋,他也有心北伐,期望恢复中原故土,多次召集群臣答对,但在战与和的争论中犹豫不决,每次结果都是“议不行”。即使岳飞率军北伐即将大功告成,在金朝的反间和秦桧等投降派的蛊惑下,宋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岳飞召回,断送大好机会。绍兴辛巳年(公元1161 年),宋高宗曾满腔壮志部署迎战完颜亮军兵,当时力主宋高宗亲征的宰相陈康伯拟好了一份《绍兴辛巳亲征诏草》。隐藏心底的“恐金症”使宋高宗再次陷入首鼠两端,最终未敢颁布。三十三年后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 年),已经六十五岁的辛弃疾首次看到这份未颁发的诏书草稿时,写下了《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
“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俱存也,悲夫!”
据山东师范大学薛祥生教授考证,这是两宋时期文人士子写就的最短跋文,全文如生铁铸就,短小精悍,神完气足。辛弃疾仅用三句四十六字,说明“此诏”之“行”不“行”对有宋一朝关系重大。因其未“行”,才使宋高宗赵构蒙受“事仇之大耻”,使此诏拟就第二年接任皇位的宋孝宗赵眘浪得抗金虚名。辛弃疾写下这区区数十言跋文的时候,“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一个“悲”字,如一腔郁结之气喷薄而发,把辛弃疾悲诏、悲国、悲时、悲己的复杂感情集中、极尽呈现出来。
将跋文中的“此诏”换作《美芹十论》,不亦宜乎?
宋孝宗登位之初也有壮心,但隆兴二年的仓促北伐,因用人不当、调度失机而大败,被金朝加码勒索不得不再次纳币贡帛,使他从此与宋高宗一样患上了恐金症的巨大心理阴影。对辛弃疾呈奏的《美芹十论》,阅后虽然很激动,“帝锐意恢复”,但最终不是从所提策略可行与不回做出决断,而是“以讲和方定,议不行”。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里说:“呜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度外哉。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余读此书而深悲焉。”刘克庄的“深悲”与辛弃疾的“悲夫”,同出一辙,而辛弃疾的悲更加痛彻心扉。“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平戎大计不得行,辛弃疾徒奈其何!写下这篇跋文时,距离辛弃疾辞世仅剩四个年头,岁月蹉跎人老去,北伐雄心仍未酬,他只能再次发出三十六年前登建康赏心亭时的悲愤,“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宋孝宗赵眘不行《美芹十论》之大策,犹如宋高宗赵构不行《绍兴辛巳亲征诏》,都是南宋一朝的悲哀,也是辛弃疾一生的悲痛、悲怆、悲壮、悲豪!
四
在《美芹十论》及《九议》中畅述的御戎大策,承载着辛弃疾实现恢复北宋故土的政治抱负和膺惩家仇国恨的生命重任,他一生执着于此。可惜的是,南渡之后,宋孝宗不敢起用辛弃疾出掌北伐兵权,让南宋一朝有气节的文人士子和后世有识之士徒叹辛弃疾虽负管仲、乐毅之才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使辛弃疾自己不断感叹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至死仍在高喊“杀贼、杀贼”!
有杀贼的勇武,有北伐的雄心,有能战而胜之的韬略,却不能率军将兵走向北伐战场恢复故土,是辛弃疾南渡后持续四十多年的巨痛,同时掺杂着对北方家乡的思念之苦。痛上加痛、苦中又苦的沉郁在三起三贬的仕途中没有缓解途径和机会,他只能以文人意气在赋词写诗中来舒展了,而正是表达这种双重痛苦的种种意象为造就辛词的豪放风格增添了重墨异彩,成就了他“词中之龙”的赞誉。这个赞誉是至高的,就豪放词论,后世评家往往将“苏辛”并列,而“词中之龙”的评价,使辛弃疾更胜苏东坡一着,可谓是前无古人可溯,后无来者可追。
面对金朝虚张声势打打谈谈的策略,南宋朝廷唯诺胆怯得不敢一战。辛弃疾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首渴望率兵北伐的豪放词作。夜半北风潇潇响起,睡梦中的他以为是北伐战场中金戈铁马的厮杀而自己正身居其中,“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北风起,听铮铮铁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司空见惯的江南寻常风景,辛弃疾也能映照出图复中原的梦想不能实现而带来的苦笑长叹,“过眼溪山,怪都是、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身居三国时期东吴旧地,他感叹当年孙权尚能屡次发兵北向图谋,而自己却等得白发尽生,仍不能将兵北进,“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软毫写下似乎看破尘世“西风吹尽,了无尘迹”的放下之语,笔峰展现的却是岳飞式“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满纸愤慨。“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已白”,让岳、辛两首《满江红》呼应起来,造就他们不同文字却同出一辙的悲切。夜深人静独宿寺庵,辛弃疾不能入眠,周遭是“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雨急,破纸窗间自语”,而他想到的却是“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无论白日行走还是夜晚独眠,无论醒来还是梦中,辛弃疾想到的都是还未恢复的中原故土万里江山,都是南渡后盼北归而不得的悲切悲叹。
如果说辛弃疾这些梦里梦外、白天黑夜的悲叹将他收复故土的豪放词格表现得还不够极致的话,那他用“补天”“洗胡沙”“整顿乾坤”等来比喻收复故土的昂扬壮志和斗争精神的词句,则将豪放词格推向顶峰。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汗血宝马本应与勇武战将一同驰骋疆场,如今却被用来拖拉盐车至死,令人空悲骏骨。辛弃疾就是南宋的一匹汗血宝马,却被用在对江西茶寇、湖南乡社的剿杀中,他仍然壮心如铁不曾改变,一直期望有机会收复中原,将大宋裂开的天空补全,胜利归来在长江边谈笑,看一江碧波在美丽的大地上缓缓流淌,光彩夺目。“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碧澄,佳丽地。”辛弃疾多次用“补天”这样的雄词表达北伐壮志,他有这样的气度,也有这样的能力。辛弃疾不仅要向上“补天裂”,还要飞车入云,问天借雨,向下“洗胡沙”,将胡虏践踏过的土地洗刷一新,“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补天洗地已经是壮举,在辛弃疾的词中那也只是补缺掸尘,他不满足,还要将整个乾坤进行整顿,“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在辛弃疾眼里,即使整顿乾坤,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只是为长者贺寿的礼物,“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补天”“整顿乾坤”,是辛弃疾一贯主战意志的豪迈表达,与《美芹十论》里的主张一脉相承。但这只能在他的词里,在他的想像与梦境里。现实中辛弃疾无用武之地,只好借回忆在故乡山东的战斗经历来表达对率兵北伐的向往和信心,“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射金仆姑。”他多么渴望率领五十名骑兵深入金兵营帐智擒张安国的战斗场景再现于自己身上,可惜南宋朝廷始终不让他如愿,他眼看着那些胸无点墨的败军之将浪费战机徒叹奈何,“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如果给他统军北伐的机遇,他一定会像擒拿张安国那样俘获金军将领,再沿扬州道路押到临安交付朝廷,“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峰火扬州路”。现实里辛弃疾得不到率军北伐的机会,即使曾经的壮举也是昙花一现,他只能借酒消愁、借梦扬志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酒消梦醒之后,现实依然没有改变,他只好再次像岳飞一样叹息空悲切、白了少年头,“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的豪放壮词,不是为写词而写,不是为写眼前的景物而写,写的是他胸中的北伐大计,写的是他收复故土的情操和理想。郭开受辛弃疾之托辑订稼轩词,在《稼轩词序》里直言:“公一世之豪……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说得十分直白,辛弃疾写作豪放词作,就是把词作为工具,抒发“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北伐壮志,“意不在作词,而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辛弃疾把赋词作为陶写工具,表达的还是《美芹十论》《九议》中的北伐情怀。辛弃疾以词作篇什传达的慷慨沉郁理念和盘旋激荡意境,穿透而论还是源自山东时期与祖父辛赞的共同生活经历,还是源自四风闸这个生养他的村庄。当然,辛弃疾的词作篇什能够比他的奏疏文章流传更广,与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博洽学识、磅礴才气也有莫大关系。而他的学识和才气,也是赖依在山东生活时期刻苦研读所奠定。
一旦南渡,归来无期,辛弃疾思念家乡,思念四风闸村的庭院旧居。在写思念家乡的词句中,辛弃疾也要把收复故土的情怀和意志渗透进来,使本属婉约色彩的思绪染上豪迈之风。在隆兴二年春天写下一曲《满江红》,抒发北望之情。“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秋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层楼,平芜碧。”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辛弃疾写词,始于南渡之初,将自己的字由“坦夫”改为“幼安”,也在此际。这首词是辛弃疾最早的词作,表达的是登上长江岸边的赏心亭,北望山东,思念家乡。这首词起句说“家住江南”,其实是倍思家乡。在词人的思乡情绪里,清明过后,四风闸的庭院里桐树应该花尽落,叶渐密,荫蔽堂前。但此刻的辛弃疾,虽然改字幼安,但家书无处寄,来信无踪迹,心岂能安?让辛弃疾心不能安的仍是故土未复,有家不能回,期望北伐复土的意志充盈心间。
“桐荫清昼”是辛弃疾对家乡四风闸村里自家庭院情景的记忆。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弹劾罢官,退居上饶带湖。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字南涧)致仕后寓居上饶,二人都有北伐雄心,惺惺相惜,过从甚密。淳熙十一年,韩元吉六十七岁寿辰,辛弃疾为他赋词贺寿,写下《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其下阕曰:“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坠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乾坤整顿了,为先生寿。”辛弃疾生日与韩元吉寿辰只隔一天,作词时自然想到自己出生时节的景象,所以“桐荫清昼”不期然而至。在为人祝寿的词作中,辛弃疾想到祖父辛赞曾经给他讲述自己出生时的四风闸故园的情景,不仅借贺词回想自己平生风云奔走,壮志难酬,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北伐复土,“整顿乾坤”。
清人赵翼的诗句“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辛弃疾南渡后的词作得到典型验证。辛弃疾一生写词六百二十余首,体现豪放词格的有一半之多,而展现豪放意象的词作均与北伐壮志不得酬紧密关联。郭沬若题写的联句“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更是把有宋一代豪放词的两位杰出代表苏轼、辛弃疾的词风和词意简赅道出,尤其“美芹悲黍”,用两个历史典故把辛弃疾的终生悲壮一囊尽括。辛弃疾南渡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北伐壮志,而南宋朝廷不仅对他不加重用,反而始终不让他到前线统兵,甚至两次将他贬到无官无职,致使他在上饶和铅山闲居十数年,这对辛弃疾而言实在是人生的大悲哀,也是南宋朝廷的大不幸。辛弃疾个人的悲哀和南宋朝廷的不幸,让他把博洽学识和磅礴才气用到赋词中,赋出果毅之资、刚大之气,赋出沧桑,赋到词句的高峰,成就后人称他为词坛巨擘、词中之龙的评价。
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两宋最盛,形成文人赋词的高峰。两宋词作,大致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风格,有些词人只擅一种,有些词人两者兼具。在众多词人中,又首推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苏轼将婉约、豪放两种风格集于一身,极难把他径归一派,生年又早,可谓两宋词作仰为观止的高峰。李清照、辛弃疾也是将两种风格集身,与苏轼相比,就集于一体而言,李、辛难以企及。将两种风格分别而论,将婉约推到高峰的应是李清照,将豪放推到高峰的则是辛弃疾。长期生活在济南的清代新城(今桓台县)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说:“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假如能将二安词风叠加,应胜苏轼一筹。李易安、辛幼安并称济南二安,二安的家乡旧居相距甚近,李清照家乡在章丘明水湖岸的义仓村,百脉泉水经绣江河滋润了四风闸周边的土地。易安、幼安前后相继,婉约、豪放两峰称宗曰首,实乃济南璀璨人文的耀眼明珠。
五
南宋半朝一直对北伐争论不休、犹豫不决,让《美芹十论》和《九议》中的宏韬大略在朝廷官员和文人士子中广为传诵,被赞为“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辛弃疾矢志北伐复土的声名传遍宋金两边,南宋主战派盼望起用辛弃疾掌兵,而主和派则百般阻挠,一代铁血文人将军就在这争论的岁月中蹉跎着,南宋懦弱的统治者在金朝无休止的侵扰、蹂躏下一再低头纳贡。
历史按照它自身的步骤随日月转动而行进着,万字雄文《美芹十论》和孕育它的四风闸村,基于《美芹十论》的数百首豪放壮迈的词作,在岁月漫漫的烟尘里洗尽铅华,呈献给后世一位怀有不遇之虞、闲置之痛因而浸染浓郁悲壮色彩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这位生长于济南,生长于四风闸的历史英雄,一生未能遂愿到战场上一展雄风,将勇杀义端和智擒张安国般的英勇行为进行到底,这是他的悲切和不幸。他在数百首词作和美芹良策的文字中将英雄情怀淋漓尽致地遗赠后世,让人景行仰止,这又是他的荣光和幸运。慷慨激荡的豪放词作,英伟磊落的雄文美策,激励着一代代后人,让这位文才与武略兼具的四风闸村走出的历史人物,始终绽放着他应有的光芒。辛弃疾为朱熹所写的铿锵诔言,也正是定格他自己生命的写照: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谁谓公死,凛凛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