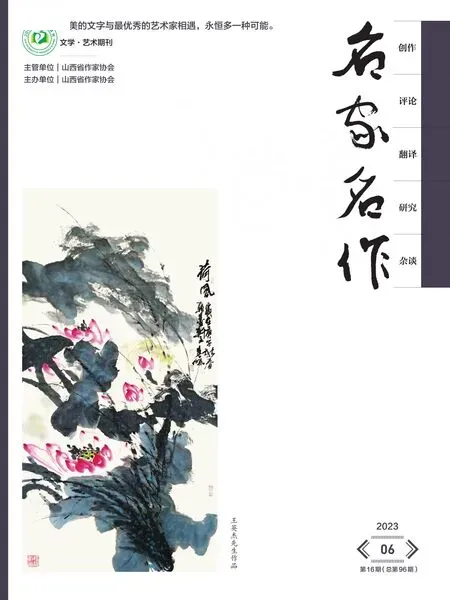含泪的微笑
——王祯和《嫁妆一牛车》中的黑色幽默
陈胤竹
《嫁妆一牛车》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王祯和的成名之作。该文悲喜并置,运用大量丑陋的意象、滑稽逆转的结构手法、杂化的叙事语言,从一个滑稽戏谑的叙事者的单一视角出发,书写以万发为代表的小人物的愚昧、低俗与落后,表达了作者对小人物命运的悲悯与同情。诙谐的语言、轻松的叙述、巧妙的情节、幽默讽刺甚至玩世不恭的语调,夸张、嘲讽、双关等手法的运用,都让读者忍俊不禁,这是《嫁妆一牛车》中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含泪”又具有悲剧内涵,轻松的文字背后是内心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作品揭示了20 世纪70年代社会民众的悲惨处境,表现了小人物在残酷的社会中承受心灵的创伤,并寄予他们深深的同情。
一、贯穿全文的黑色意象——耳聋
纵观全文,万发的耳聋“似乎”是其悲剧命运的源头。他在战乱中耳朵进了污水,被一位妇科医生胡乱医治,最后落得一个八分聋的下场。万发的耳聋,使他不能及时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村里人如是谈论道:“是个臭耳郎(聋子)咧!不怕他。他要能听见,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啦!”
(一)耳聋带来的孤独与歧视
自从万发耳聋后,街坊们嫌弃他重听得太厉害,同他说话如同吵架似的吼,便逐渐孤立万发。生活的贫穷以及街坊的孤立,万发只得把家搬到公墓边上的“鬼屋”,靠白天给别人拉牛车挣一点稀粥钱。“聋子”听不见,仿佛给了街坊一个肆意嚼舌根的许可,他们不仅在背后讥笑万发,甚至当着他的面也毫不收敛,不畏万发恼忿。万发的耳聋同样导致了他自卑,他反复拒绝阿好提出的看望新邻居的建议,担心自己的耳聋丑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二)耳聋带来的信息差
当万发听到街坊议论自己的妻子与姓简的外乡人好上了的时候,一个半月的工夫早溜了去。万发的耳聋让他即使与他俩同在一个屋檐下,也不得听见他俩的谋划,“烟里雾里,阿好和简姓的鹿港人比手兼划脚,嘴开复嘴合,不知情道什么说什么来?仿若睇听一对鬼男女心毗邻着心交谈,用着另一天地的语法和词汇,一个字也不懂,万发走不进他们的世界!”我们可怜的男主万发,总是在关键时刻错过应该听到的信息,却总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候听见街坊对自己的谩骂与侮辱。当他质问阿好为什么摘取衣服上原有的锁扣时,他的耳朵怎么也听不进去,像临阵脱逃的兵。当他将阿好与姓简的捉奸在床的时候,只能看见他俩商议着如何编谎话,“眼珠霍然光亮起来、阿好向简不知吩咐了什么,就一步两步向那暗角落蹙去,两手摇醒着眠在那里的人,推摇得很力。”缺乏第一人称的直接在场论述,万发听到的绝大多数关于简和阿好的传闻都来自阿好这部传声器的“转述”,期间省略了多少事情的真相,歪曲了多少又无从得知了……
(三)耳聋的象征意味
王祯和在《嫁妆一牛车》中将现实生活中的丑集中提高到刺目的地步。无论是万发的耳聋还是简的狐臭,抑或是阿好的嗜赌,无一不指向肮脏落后的乡村。与那些讴歌自然风情、歌颂淳朴乡亲,洋溢着温馨美好氛围的乡土文学作品不同,《嫁妆一牛车》里有的是一幅幅令人窒息的地狱画卷——街坊的孤立与辱骂、妻子的不忠、墓地旁边的小屋、满屋的红头苍蝇。这些意象映射出当时下层小人物的经济困顿、生活的无奈和挣扎的痛苦,呈现出关怀社会、直面人生的基本特点,描摹出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当代生活图画,对社会客观存在的不公、黑暗与落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万发是否是真正的耳聋?如若是,又为何总是选择性耳聋?“刀锐的、有腐蚀性的一语半言仍还能穿进他坚防固御的耳膜里去。”万发曾与阿好提及自己不是聋子“莫再啰唆啦,我又不是聋子,听不见”。万发与阿好的日常沟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作者鲜有笔墨提及阿好故意提高嗓门。但为何阿好与简先生的沟通万发总是听不见?万发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听不到别人说话,例如阿好与简先生在努力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万发为何总是听不见?“啊?这耳朵——这耳朵——这耳朵应该听进去,避不听闻,临阵脱逃的兵。”20 世纪70 年代乡土文学受鲁迅乡土文学影响颇深,耳聋这一缺点是否又可以看作是阿发的挡箭牌,又抑或是阿发精神麻木的外在具象表现?或许阿发并非是真正的耳聋,他只是想以耳聋为借口,进而逃避街坊对他的谩骂或者充当回绝某事的借口。
(四)耳聋对万发悲剧的戏谑性表现
从情节上看,万发的“抗争”和失败本该是悲凉的,但这样的悲凉却似被作者王祯和调侃了一番。万发的敌人是简姓“鹿港仔”,他要从“简的”那里夺回自己作为阿好丈夫的尊严。似乎照着文本来读,万发并不是输给了“简的”,而是输给了饥饿与命运,这确实是“甚至连修伯特都会有无声以对”的时候。其实,对于贫困落魄的万发而言,阿好和几个孩子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仅剩的尊严。当阿好和“简的”月下偷欢被抓现行后,万发决心要抗争。但“二十四小时不到,两汉子就不战而和啦。几乎都如此地,每当万发气忿走出来……翻出纸票正倒着数……离顶台牛车还距远一大截,多少容纵姓简的一点!”每每想到生存危机,想想被奉作生存理想的“牛车”,万发便让步一点,直到“简的”住进了他家,直到他“盛情难却”地接受了“简的”给他的牛车,他便十分自觉而知趣地盘桓到深夜才回家,最终竟有了几分麻痹的满足了。作家把万发的悲惨命运轻松归结于他的耳聋而不是捉弄人的造化,以轻写重,以戏谑的手法更深刻地体现了万发的不幸与社会的黑暗。
二、滑稽逆转的剧情
在黑色幽默作品中,常常还会使用到滑稽逆转这一叙事技巧。滑稽逆转主要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使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逆转结构来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叙事手段,让观众的情感得到瞬间感染与宣泄。
(一)功亏一篑的万发攒钱买牛车之旅
得到一辆属于自己的牛车是万发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贯穿全文的行文线索。万发省吃俭用,当牛做马,甚至默许“简的”占有他的老婆,但当他积蓄越来越多,眼瞅着离买牛车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先是经历了车主的解雇以及简先生的离开(阿五被解雇),一度回到了过往饥寒交迫的日子。而后以前的牛车主又找他拖车去,眼看着日子要朝着正轨走去,可万发上岗不到一周便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万发拖着的牛车,因为牛突然发野,撞碎了一个三岁小孩的头,他因此坐了很久的牢。万发此次坐牢,不仅断了靠自己攒钱买牛车的念想,更是直接丧失了对妻子阿好的监管。果然,阿好在探监时告诉他“多亏了简的照应着一家”。万发攒钱买牛车的念想至此宣告完全破灭,这也象征着他与命运进行搏斗的抗争永远败下阵来。
(二)万发得知妻子被抢占后对“简的”的态度变化
作为“二男争一女”故事的核心人物,万发和他的情敌“简的”之间的态度变化也同样值得探讨。其中,当万发第一次听说简和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好似180 度大转弯。惑慌→奇异的惊喜→憎恨→杀气腾腾→困惑→质疑自己听错了→平息怒火,仅仅不再去简的房子。这一段心理描写,细腻生动地写出了万发在得知自己的妻子被简占有后,是如何一步步愤怒,而又最终说服自己复归平静的。“之后,心中有一种奇异的惊喜泛滥着,总谩嗟阿好丑得不便再丑,垮陋了他一生的命;居然现在还有人与她暗暗交好——而且是比她年少的,到底阿好还是丑得不简单咧!”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可是万发居然第一反应是兴奋与惊喜。这畸形变态的心态后面折射出的是万发长期被他人鄙夷下的落寞,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贬低,他需要通过别人抢占他妻子来证明自己的眼光与价值,这是何等的可悲。除此之外,自卑所带来的不自信一直贯穿万发对这件事的始终。他听见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惑慌,作者将之归因为“也难怪,以前就没有机缘碰上这样——这样——的事!”和那些传统落后的旧社会中国男性一样,万发把妻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由于万发的自我价值认同感极低,他自然也把妻子阿好放到了与自己一样的位置,以至于得知居然有人看上阿好而感到意料之外、无比困惑。尽管后续这种困惑被对简的怨气以及男人间的胜负欲所压制,但是并未消失。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甚至拔高到意识流的高度,于是万发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思念,都一一披露出来。这样一段看似嘲弄戏谑的叙事口吻,来冲淡故事本身的悲苦,进而避免像万发典妻这样悲苦的故事滑入感伤的滥调中,减弱了读者的反思力度。
三、杂化与戏谑的特色语言
对于现代派小说而言,语言文字的创新求变意识,具体体现为两种有些极端的语言实践:一方面是中文的纯化(纯洁化、纯粹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语言的杂化实践。《嫁妆一牛车》的作者王祯和走的是语言杂化的道路。纵观《嫁妆一牛车》全文,罕有充满复古味与梦幻感的文字,完全看不见追求语言纯化的作家们所提出的那一套“回环往复连绵不绝的氤氲效果、富有音乐性的语言以及古典诗化浪漫意境”。相反,王祯和用漫画化、戏剧化的语言戏谑嘲弄后殖民情景中失落民族尊严的杂化群体:一群落后愚昧、丑态百出、自我奴化的小人物,在杂语喧哗的丑剧情景里不断自我消解、自我矮化。
(一)错位的词组内部结构
王祯和曾在《永恒的追求》一文中谈到自己创作的《嫁妆一牛车》时,为了表达一种自己预想中“怪诞、荒谬、悲凉又好笑”的意思,他不惜细心琢磨,“试着把动词、虚词调换位置,把句子扭过来倒过去,七歪八扭的”。这种语言策略制造了一种极不和谐的杂烩丑剧场景,它非驴非马、非东非西,它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自我贬损的降格的语音语义。王祯和把成语颠倒运用,把主词摆在后面,大量运用方言,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加真实、尖锐、有力,并富于嘲弄性。如:
一生莫曾口福得这等(一生莫曾得这等口福)
缩矮得多么(多么缩矮)
阿好竟兴狂得那么地(阿好竟那么地兴狂)
万发把朴重的笑意很费力地在口角最当眼的地方高挂上(万发把朴重的笑意很费力地高挂在口角最当眼的地方)
嘴牵成斜线一杠(嘴牵成一杠斜线)
投合得多么的(多么的投合)
到地瓜挖掘空一了(到地瓜挖掘一空了)
姓简的鹿港人终究来归了(姓简的鹿港人终究归来了)
如果说精神上的“混乱”症候在文本中获得颠覆性意义而成为文学上的“混乱”,那么这种“混乱”在文学语言层面平行的表达所指向的也必然是一种具有逆反、否定与颠覆作用的修辞。《嫁妆一牛车》中这些与正常语序词序相颠倒的话语,可以视其为在语言修辞层面对权威意义的延宕性否定与解构。它暗示着一个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文本世界,表达的是对理性主体深刻的怀疑。
(二)方言与俗语的大量杂糅
传统本文强调遣词造句之美,或为清新自然之美,或为雕润密丽之美,但罕见低俗杂糅之美。日常方言中裹挟着文化习俗的民间趣味和满溢着人性原生态的丰富语调给他带来灵感,尤其是双关语的生动谐趣,那是书斋里难以想象的也是他格外钟情的。真切的民间趣味使王祯和的叙述姿态与多数现代派作家划开了一条明显的界限,也成为他一向被史家认定为乡土小说家的重要原因,民族语言的粗、俗、辣、鲜活和俏皮形成了他的语言实验的一种醒目色调。如
呷顿崭的(吃顿好的)
料理店的头家(老板)
干(语气词,表达不屑轻蔑的态度)
臭耳郎(聋子)
你爸(生气语,如“老子我”)
骗肖(混账)
干伊娘,干伊祖公(骂人语)
《嫁妆一牛车》中这些“低俗不入流”的语言的运用,体现了作者对广大生存处境悲惨的小人物的关注与同情。原本这群从事着低等粗重工作的人,贫穷、卑微、文化程度低、受人歧视,但作者却有意放大他们那微弱的声音,书写那真实、自然、清新、紧贴着脚下土地,充满抗争意识和尊严感的声音。同时,这些杂化语体如同一面哈哈镜,以扭曲夸张的修辞折射出社会病体的真相。貌似喜剧,其实却是一场闹剧。正是在这样一种戏化与杂化的嬉笑怒骂中,我们感受到作者深切的文化受挫感与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定志愿。同样的,这种百音嘈杂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嘲弄了文化杂乱无章的本质,“也加强了小说本身反抗‘正统小说’所依持之‘单音’系统的力量。”这个肯定着重于强调该小说反正统单音叙述的文类突破行为,也看到了小说语言修辞策略的嘲弄功能。
《嫁妆一牛车》是一部包裹着喜剧外壳的悲剧。万发与现实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最后被迫“典妻”的结局,构成了悲剧的基本内容。万发虽然落后、愚昧、蠢笨,但他身上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抗争精神,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攒钱只为买一辆属于自己的牛车的万发却因为生活中的种种突发状况变卖了理想与妻子,真切地揭示生活中的罪恶,社会的黑暗以及民众的苦难,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含泪的微笑,既能够防止读者过分陷入感伤的泥沼,又能通过反衬的效果强化突出了作品的悲剧色彩与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