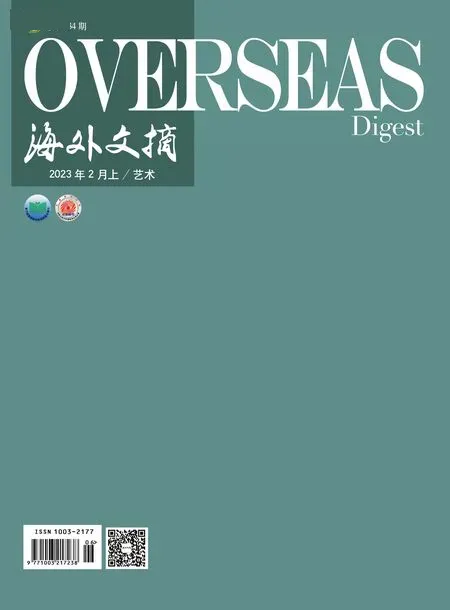“离散”到“新离散”:国家电影下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中的族群想象
□胡盼鹤/文
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以下简称马华电影)长期处于排他的电影文化氛围之下。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马来西亚的电影文化逐渐民主化,马华电影开始崛起并与马华国家电影在电影文化领域里平分秋色,马华电影的崛起与发展除了与科技与市场因素相关联以外,也和马华电影构建的在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所处电影文化场域特殊状态所适配的族群想象息息相关。针对上述内容,本文先对马来中心国家电影下马华电影的处境现状进行了大致的说明,接着重点分析马华电影在与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博弈中所构建的三种不同形式的族群想象,最后探讨这种作为方法论的族群想象的构建对于马华电影的启示和进一步发展的意义。
1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马华电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语言概念,而成为一个广泛的跨国、跨区域的文化概念,实际上包括对各种文化、政治、制片和观众等因素的考虑。为寻求华人自主的电影论述,新马华人在独立建国后创造了马华电影这个新词,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只要是华人导演拍的电影、华人扮演、面向华人放映的片子都可以称作马华电影[1]。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重要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文化及发展逐渐得到国内学术研究界的关注,马华电影呈现的多元文化景观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学术研究的方向。电影作为一种表征形式和再现机制,其叙事和生产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但其本质是更深层意义上对身份认同的表达和族群想象的建构,而马华电影在反抗马来西亚国族电影的过程中,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族群想象空间,实现了国族电影围堵之下的突围。本文旨在研究马华电影在与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博弈中如何构建不同形式的族群想象以实现围堵中的突围,并将其作为方法一以贯之,这对在电影工业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其他族群电影具有重要的启示,是具有反霸权意味的。
2 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马华电影的现状
国家电影简单定义便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电影,“国家电影的发展是为了确保马华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被马来裔掌控的必要措施”[2]。实际上,马来西亚国家电影的定义和官方所建构的国家电影话语,是种族政治下所产生的马来中心化的电影话语。
20世纪70年代,马来当局颁布了《国家文化政策》,规定要以马来土著文化为马来西亚电影中的文化基础,并将马来电影20%的娱乐税退还给电影制作公司,这些规定推动着马来西亚电影的马来化[3]。同时,根据国家电影发展机构的法规规定,马来西亚生产的电影中马来语言占七成以上的影片才能称得上是马来西亚电影,这个法规实际上就等于把马华电影和马来西亚语电影直接画上等号[4]。此时,在马来中心化的电影文化场域中,作为“非马来”的马华电影不可避免地处于离散状态,而其电影中构建的族群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离散”特性的影响,都表现在作为“他者”的电影导演对中国性的探寻,其特征为一种在地化的反离散的实践。之后,在全球化电影文化场域中,伴随着数码影像技术的加持,马来西亚一大批独立华语电影导演开始崭露头角,马华电影逐渐进入一种反离散的状态,而其电影中构建的族群想象也实现了国族性与跨国性的接合。李添兴、陈翠梅、刘城达等电影导演生产的大部分马华电影都采用或借鉴着各种外国和跨国技巧,另辟蹊径地实现了马华电影的突围[5]。这些马华独立电影导演及其作品对马来西亚的电影工业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当局政府关注到马华电影并放松对其的管制,规定“只要一部电影的50% 以上是在马来西亚拍摄的,并且电影公司50% 的股份由一名马来西亚人拥有,那么这些电影都可以被称为本地电影[3],只要附上马来语字幕,对话的语言就变得无关紧要。”这一转变是马华电影本土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原有的边缘化的“他者”“离散”处境逐渐被扭转,大部分商业电影崛起,开始在新离散的状态下构建起新的族群想象。
3 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马华电影的族群想象
在与马来西亚国家电影的纠葛下,马华电影实际上经历了离散、反离散再到新离散的处境状态。马华导演不同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经历使他们的身份复杂化。在马华电影所处的特殊环境下,马华导演的族群认同和族群想象实际上也处于多重认同的复杂状态。“身份是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认识我们的方式,是由看和被看的辩证法构成的”[3],马华导演身份的建构不仅是一个人如何定义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还涉及到马来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如何看待和定义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所以马华电影导演擅长在电影内外构建不同特性的族群想象来表现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族群认同。
3.1 离散状态:作为“他者”的华人与“在地化”的身份书写
“离散”来自古希腊语diasperien,原指离开故土、漂泊在外、四处流散的犹太人生存状态。随着当前全球化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发展,离散脱离对特定人群的指代,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对移民、跨国在内的人群流动等文化实践研究当中,多用来指代一种异质文化空间里的生存状态,常与“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文化属性”等概念关联[6]。在东南亚,尽管华人对本土化有着强烈而持久的渴望,但“中国性”永远是外来的、离散的、不被认同的“侨民”[7],所以华人在马来西亚文化身份上永远属于“他者”,而华语电影在本质上存在着“中国性”的内涵,也永远处于边缘化的“离散”状态而不被认可。由于其不能被归入马来西亚的“国家电影”,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华语电影似乎都挑战着马来的国家民族主义[7],与其说马来西亚华人渴望一种族群认同,不如说他们在表现一种族群认同更为准确,他们假装臣服于国家电影的民族寓言,“承认它的力量,但以讽刺的扭曲来回应它”[6]。所以在离散状态下,这种族群想象主要通过在文化张力之间的抵抗性实践所构建,表现为一种在地化身份的书写,其典型代表便是作为“他者”的华人音乐导演黄明志和其音乐电影《Nasi Lemak 2.0》(《椰子饭 2.0》)进行的在地化身份建构。
作为马华导演的黄明志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文化场域间穿梭,虽然扎根在马来西亚,但“不完全”等同于马来人,也不被马来土著人民接纳为正式的公民,所以他在马来西亚通过音乐和电影等文化形式进行着“在地化”身份的书写,以对抗马来中心化的文化张力。《椰子饭 2.0》是由黄明志导演的电影,它直面中马关系,使用混杂食物椰子饭,体现华族文化在马来西亚本地化的流动性,同时去建构起自己的族群想象和身份认同[8]。由马来西亚三个主要民族烹饪而成的椰子饭,是马来西亚本土化的象征,正如黄明志在采访中解释的那样,椰子米并不是纯粹的马来食品,它融合了来自不同地方烹饪传统的原料,它的烹饪方法来自印度人,而食材来自巴巴娘惹(Baba-Nyonya),在电影中体现为华裔主人公在制作椰子饭时主动拜访巴巴娘惹和印度大师,实际上体现马来西亚本地化的椰子饭是由中国、印度和马来的饮食原料混合而成的。这里,黄明志通过食物的混杂,加强马来西亚华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也表达对建构“一个马来西亚”的族群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话语。另外,黄明志电影中所表现的“一个马来西亚”是一种“文化适应”的理想,体现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可以互动和融合,但与民族同化保持绝对的边界。在他的电影中,不同语言并没有形成政治对立,而是形成一种“汉语治理”[9],他把华语作为一种文化媒介来管理各种政治关系,而不是把华语作为抵制其他语言的政治谈判筹码。他的成功表明马来西亚华人可以在不放弃自己的“中国性”内涵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种族的文化互动完成“在地化”身份的书写与建构。
总之,在马华中心主义的氛围下处于离散状态且被认为是“外国电影”的马华电影需要通过强调自身“华人-马来西亚”的特性,通过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完成“在地化”身份的书写,以便获得族群身份认同,构建起“一个马来西亚”的族群想象。但随着全球化以及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大批马华独立电影导演诞生,大量优秀的马华电影传播海外,马华电影开始作为马来西亚的国族电影进行生产传播,之前的离散状态被打破,开始在“反离散”“新离散”的文化场域下诉说着新的族群想象。
3.2 反离散:马华电影的世界性与跨界化的身份言说
马来西亚国家电影的主导地位导致华语电影的长期处于离散的边缘位置,然而这样的两极分化随着独立电影的发展被逐渐打破,新一代的数字电影导演生产的跨越语言、角色和国族边界的华语电影逐渐出圈,在马华电影的发展逐渐进入“反离散”的状态[10]。这里的“反离散”实际上是指马华电影在马来中心电影的围堵中突围,改变在马来西亚电影工业中所处的边缘尴尬位置,而其主要策略便是马华电影挖掘世界性、普适性内涵以实现国际化发行的跨界电影的生产格局。
马来西亚民族中心主义的背景注定了许多华裔导演及其独立电影只能游走于制度和体制的边缘,因此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华裔电影导演以国际渠道作为电影放映的主要渠道。就像李添兴导演在采访时所说:“我的电影能否在本地上映,对我来说并不是关键的问题,如果在电影院上映便会有票房的压力,所以我只会寻求别的途径来放映电影。[11]”许多马来西亚独立华裔导演直接跳过本地电影院,以国际电影节为目标去生产发行电影,他们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频繁放映。国际路线在给予马华电影导演及其电影更多可能性的同时,实际上也给他们的电影话语设置了前提,要求挖掘电影中跨越国族性的世界性、普适性内涵,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起去国族化的、泛华人化的族群想象。华裔导演李添兴的影视作品便是不拘束于特定民族身份的表达,也没有表达强烈的身份认同意念,而是通过镜头语言构建现代都市华人男女的心理疏离而实现跨国界传播,呈现出的是一个泛华人化的族群想象空间。
李添兴反对别人称自己为“华人电影制作者”,也“并不以电影去表达马来西亚华人的声音”为电影制作的宗旨[12]。他说:“代表华人去生产电影的这种表述令我感到别扭,我并不认为呈现马来西亚或者华人是我生产电影的职责。”所以他在电影生产中跳出国族性的桎梏,挖掘电影中更深层次的世界性内涵,构建一种“去国族化”“泛华人化”的族群想象[11]。李添兴的电影里没有带有地域特征的符号,电影中的空间被公寓、办公室、洗手间、狭窄小巷等封闭局促的场景所统一化,这样的场景与任何一个城市空间都是类似的,其实是一种共同的当代华人共通的生存境遇,构建的是一种泛华人化的想象。正如李添兴曾说:“我的电影可以是发生在有中国人生存的任何地方。这不是故意的,由于我和我的父母都没有国外学习的经历,我很大程度上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看待问题,是一种非常本土化的华人思维方式[11]。”这里的华人化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国族化的华人思维方式。《美丽洗衣机》是李添兴在2004年拍摄的马华独立电影,整部影片场景冰冷亮洁,角色面无表情宛如行尸走肉,在冷漠的影片氛围中神秘女子成为男性凝视对象,影片在光怪陆离之中展现都市人际的疏离,人物之间的交流被锁定自封闭的房间、冰冷的办公室以及嘈杂的超市等私人场景、公共场景以及消费场景中。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评论家将《美丽洗衣机》解读为,资本主义的物质消费文化造成了亚洲家庭的崩溃和解体,可以看出非马来西亚的国际化观众也能够从这部电影中解读出意义。由此可见,李添兴电影的生产传播格局不再仅以马来西亚公民为观众,而是置身全球视野,针对的是国际性的观众,在国际性的语境里分享人类共通的人道主义价值和主题,这实际上为马华电影导演以及华语电影的生产创造了以国际性消费者为主要对象的共享交际空间[7]。其中通过“去国族化”的表达方式所构建的“泛华人化”的身份想象,似乎也更能在国际影像空间中得到更多华人的共鸣和认可[8]。
3.3 新离散:马华电影的全民性与身份的共同塑造
随着数码影像技术的发展和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推动,马华电影开始发展壮大,其不再作为外地电影,而是以马来西亚本土电影的姿态进行电影的生产和传播。在这样新的形势和背景下,马华电影进入了新离散的状态,开始通过国族身份的共同塑造构建着全民性的族群想象。
其中华裔导演周青元的作品相较于之前离散叙事突出的创伤体验、政治对峙和身份政治色彩,展现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全民性族群想象的共同塑造。周青元,马来西亚华人导演,祖籍福建泉州永春,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正如居维宁学者所说:“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可以有多重认同,比如,在政治上偏向于认同和效忠马来西亚,而在民族和文化上认同华族和华族文化。这种多重认同现象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在东南亚华人当中极为常见。[13]”周青元本人是具有文化跨界性的,加上马来西亚混杂的文化圈层,也形成了他杂交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意识,他在新离散的状态下进行文化实践,在真实与想象之间进行着文化身份的追寻以及全民化族群想象的建构。周青元导演在2006年拍摄的《辉煌年代》呈现出更开放、更平等、更和谐的文化互动空间,具有明显的全民化特征。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马来西亚足球队故事的体育类型片,讲述的是一个种族、阶层和文化杂糅的足球队,克服一次又一次的磨难,通过个人艰苦、团队矛盾的考验,锻炼出过人的毅力,培养出团队的默契,最终取得决赛胜利的故事。电影的主题相较于早期的离散电影,明显已经超越了个体情感、族群情感和阶级情感,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整体情感层面,在电影中各族群共同塑造了一个全民性的族群想象,呈现出这种重构的族群想象展现出来的集体精神和爱国情怀对国家命运的意义。正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明确指出的那样:“各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会给国家带来问题,而且只要把不同族群的文化融汇贯通,也能塑造一个象征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14]”这部影视作品实际上给予了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及其族群文化一个新的想象空间,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正是多族群文化长期互动融合形成的,各种族有着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和特殊身份,大部分族群电影人创作的作品亦体现其族裔文化,而周青元在《辉煌年代》这部影片中却模糊了族群文化之间的差异,让各种代表族群的小人物相互合作创造国家荣耀,通过这种集体记忆和族群身份共同塑造的方式,让族群中的普通人感受到自我价值和民族自豪感。导演用想象共同体的利益模糊了个体、族群和阶层之间的冲突,构建了一种全民化的马来西亚族群想象,最终《辉煌年代》在马来西亚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服饰、配乐等特别奖项。
4 结语:作为电影方法论的马华电影族群想象构建
马华电影三种主要的族群想象构建形式,不仅适应了马来国家电影中心主义氛围下马华电影不同的发展形态,而且助力马华电影在马来国家电影围堵中实现突围。以马华电影族群想象建构为方法,其本质上来说就是尝试在族群与国家维度上构建一个规律性的电影文化概念,将在同一时间或时期内活动的不同国家的族群电影现象纳入该规范中予以关照,转变以往仅参考简单的种族围堵考察华语电影叙事的思路,推动华语电影在地化的发展,挖掘出华语电影文化中的民族性、跨界性和全民性。
起初,马华电影在边缘位置进行着文化实践,其通过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实现在地化身份的书写,以获得族群身份认同,构建起“一个马来西亚”的族群想象;之后通过跨国生产传播另辟蹊径,并逐步弱化电影的国族性,挖掘其世界性和普适性的内涵,增强电影的世界影响力,华语电影与世界其他各国间的电影交流更趋普遍化、国际化。此外,李安曾用“民族寓言”来诠释马华电影,认为电影中的欲望、象征和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表达,是与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相关联并作出的回应,这也就意味着马华电影语言表层之下是必须正视的国族身份诉求,即使用华语语言构建既独立又融合的国族身份。其实,电影都有意识形态立场,影片可以用各群体共同的意义或价值去放大族群认同这一概念,通过简单的叙事结构让任何受众都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它,同时建构起一种全民性的族群想象。未来华语电影的发展也可以围绕这三个维度,构建与其所处状态相适配的族群想象,从而使华语电影永葆生机。■
引用
[1] 鲁晓鹏,许维贤.华语电影概念的起源、发展和讨论——鲁晓鹏教授访谈录[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3):60-71.
[2] Khan, H.A.The Malay Cinema[M].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1997.
[3] Shih S.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4] 曾一洲.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电影市场,2020(8):57-62.
[5] 易莲媛,彭雨晴.国族电影与跨界电影:马来西亚电影中的香港遗产[J].当代电影,2018(6):79-84.
[6] Martin,M & Yaquinto,M.Diasporic cinema[J].Schirmer encyclopedia of film,2006,57-58.
[7] Shih S.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M]//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Brill,2010:29-48.
[8] Kevin, Taylor, Anderson.An Accented Cinema: Exilic and Diasporic Filmmaking[J].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Europe,2002.
[9] Donald, Stephanie, Hemelryk.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Shu-mei Shih[J].The China Journal, 2008, 60:216-217.
[10] 许维贤.反离散的华语语系——以陈翠梅和刘城达的大荒电影为例[J].文艺争鸣,2016(6):31-40.
[11] 居维宁.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A].陈文寿.华侨华人新论[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90-91.
[12] 章旭清.跨界型的全才——解读马来西亚新浪潮导演李添兴[J].当代电影,2013(7):156-160.
[13] 王昌松.马来西亚多语种电影产业语境下国族电影的挣扎[J].电影评介,2017(22):6-9.
[14] 王昌松.作为方法的东南亚电影[J].电影艺术,2019(4):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