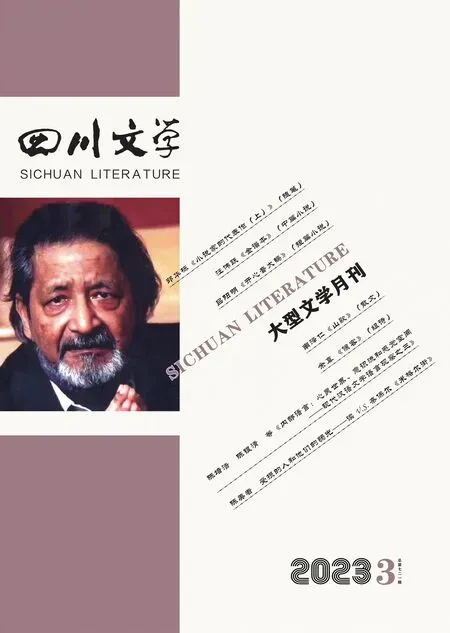候客(组诗)
□文/余真
躁动
昼夜的转场只换来,湖水在岸上交替
探寻底线。雨在夜晚下得那么动情
月亮站在湖水的身上。想象着流动的
一夜。湖水的响声如此隐忍,在蝴蝶兰的
体香中,感受着力量成为具象
女人看着月亮,以自身确定了湖水的中心
湖水幽幽发蓝,充满波折的细节
夜晚在夜晚中陈列,潮水在潮水中鱼贯
月亮在雨夜下得那么动情,落在每一个湖心
它遭遇了黄昏的无尽焚烧,到达你的手中
紧握着月亮,这唯一的核心
花朵立在幸福的湖面,绝望的水波
从云端排出。你的雨,席卷大地
你的月亮,独霸一方。面对着善变的湖水
像我这样爱你那样,全身心地投入
讯息之三
行李箱能送我更久,空气更能给我安静
大数据知道我的喜好,推销商在我的需求区
投石问路,扫码电子秤清楚我几斤几两
诈骗电话比你更了解我。这多让人感到悲哀
当我收拾好所有行装路过高山和湖泊,快乐
屹然挺立仿佛从未和悲伤交手。当我站在
你的面前,一言不发,用我只能看到你的眼睛
专注地看你。而你毫不知晓这目光的深意
而你毫不明白,你就是我还爱生活的缘由
候客
你要用什么理由来到这里?
像孩子不知所措地躲在门后
我站在你淌水的眼里
你时年百岁,满头雾水
有许多问题亟须解答
你的衬衫很破很旧,行李很脏
你不知道明天爱慕什么人
今晚应该几点入眠
你亟须解答。而故事们支支吾吾
总是讲不清楚自己的来意
候客之二
雷雨时的飓风如同藏獒
我把门窗关紧,闭上眼睛
念祷。回想过去的生活
我怎样侥幸地爱上你,阳光
怎样在我身上活泼地降落
没有苦难在我身上降生
也没有流言使我变得狰狞
鲜花开在我的房前屋后
时间是永不结尾的环形
我的生活处在对你的等待中
勤勉地维系着它的安静
夜饮
我不需要有人劝我早睡,我需要人
助我入眠。夜饮持续多日,天气啊
大病一场。速食、纸巾、一次性快餐盒
堆满了桌面。无聊就给花浇水,花
它快被淹死啦,我还在哀叹,等一支
未熄的烟重生。黑夜的长梯,我不止
一次在上面绊倒。那硌手的幸福,
在你的发后。我的心永远无法触到。
你那双不带侵略的眼睛,横跨对岸。
即兴的恋人,已不再令我仰慕。叹息
像艰难的一次长跑那样持续吞吐。
我听着你安心闭目,浅鼾四浮,想到
我们将永远如此在一张床上经历时差,
如两个国度。你将永远错过每个夜晚
那个我的低沉。爱总是有心人的误会,
漫长事后仓促。我看到波浪燃烧如沸腾的
铁水。我看到爱的隐喻在我和母亲之间
接力。我看到故事总像回文的诗歌。
亲密关系总被距离的弹簧约束。
服饰
她鲜亮的蓝色长裙在限量唯一的
她身上只展示了十万销量的之一
往上是什么,细脖颈像即将扭断的兰花
天空这反复冲洗的照片带走了她
流光溢彩的年纪。在窗边我看着
她的秀发火焰一样燃烧,如盘桓的日落
打开视频网站,依据我喜好的数据
向我投食,通知栏上全是广告与商品
朋友圈的微商一个个告知我美丽的优势
和丑陋的坏处,年轻的优越、衰老的式微
如同扼制一朵野花,要它洗掉坚韧的习性
要它从自由这最大的花盆,移居到我的室内
羊绒或者涤纶、绸缎或者锦绣,那条
二十包邮,在你亲手的编织下复活了我
一场春意的流苏围巾。流行来回打转
过时永远在复辟,时尚只是我们不忍的错觉
头顶白云无奈地涌动,今天与昨日的雷同
人类从未停止消极,对美丽的追求与摧残
永远贪得无厌。到底是一种无奈重复
还是一种对过去的深深依恋……
午后
躺在人工驯养的草上
阳光透过我的手指
和湖水一样未受污染
一个整洁的人在水边净手
他把阳光当作一条擦拭的毛巾
水边竖着禁止戏水的标识
一些午睡的人在长凳上
一些在野餐后的桌布上
条件好的带着帐篷
我们空空的手造成了两极分化
这样是有罪的
梧桐出色的舞姿衣袂翻飞
一只风筝飞进眼睛的高空
风随意动,云卷云舒
我想这儿是一只大鲲
沉睡的背部
断章之六
白云的浮沫在青山上,青山上的青杉挂着
青衫。语言有时候就是这样无聊地解谜
人类的生活有时候胜似语言游戏
我永远不能摘下这具身体,获得我灵魂
那早已失实的面容。生活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我稍感不耐烦的提问,回应的只有
远如星野的静默。吃饭睡觉也劳神费力
我远远想到他的那句“今我不乐,岁月如驰”
感到我发出的叹息,并不是我的叹息
月季
它有群星中的月亮,夺目地绽放,香气深刻而
销魂
也能暂避锋芒,壮美地凋零,泫然欲泣
形成果实这绝望与希望的集合。最终被随手采下
站在瓶中,看着抚摸花瓣的手,有着和它一样
的面孔
想到过去它深深惊愕于自身,幻想这一生,如
何告一段落
母亲叫美
方言真是十分的有意思。
过年我们用闹热,而不是热闹。
倾慕一个人,用欢喜,而不是喜欢。
任何走在路上的人,不管职业
贵贱,我们都称他为老师。
在我的家乡。母亲叫美。
我喜欢父亲称呼我的祖母,
让我发觉美可以发生得那样简单。
工作叫活路。棺材叫长生。(后
遗憾发现“长生”这一说法通用
略微感到遗憾)一个人不学无术,
可以叫他杂皮。年轻时
我只想爱这样的少年人。农忙劳作
闲时打牌掷骰。生命的河流半点波澜
也无。无数平静像干柴一样燃烧和熄灭。
火星静静给食物保持着微温。
另一个半球的人们集会或者倡议,
电缆上一些鸟从不惧死,山谷里
大片大片的荻花,让人觉得虚幻
产生埋骨于此的妄想。我想吃祖母烤的
麦团,她用南瓜叶包着。有时
是芭蕉叶。让我觉得树叶除了衬花
还有无数种美丽面纱。可惜我
并不想做母亲,我的厨艺无法使他
期待早上、中午、晚上的来临。
我的爱意并不能在他的白天与夜晚
充足地发挥。我去楼顶收回被风
烘干的裙子。楼梯下站着的父亲五十岁
他有蜡像一样刻板的脸,但他也还
可以轻柔地管我快八十岁的祖母叫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