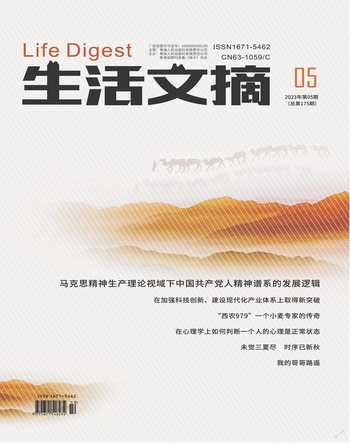从《禹贡》看中华文明的特性
《禹贡》的问世标志着中华先民首次对九州大地进行完整且理性的认知,通过对九州之间山脉河流及其走向、流域等方面详尽描述,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地理观念和社会结构。《禹贡》提出的五服贡纳制度,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建立了秩序化和制度化的关系,形成了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基础。《禹贡》开创了后代人文化地理研究的先河,展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体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萌芽。
前言
距今4000多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集团汇集、融合而成的核心——华夏集团。它与周围各集团进行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使得华夏集团最早具备了文明条件,并率先进入了尧舜禹时代的中华早期文明时代。[1]距今约3800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夏王朝以禹为核心人物。《禹贡》是先秦经典著作《尚书》中的一篇,全文分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部分,记载了大禹治水及各地向冀州交纳贡赋的情形。《禹贡》的成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应该是在最初蓝本形成后,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增添了新内容,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痕迹,最终成书于战国时期。
《禹贡》开创了后代人文化地理研究的先河,展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体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萌芽。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王朝,中华早期文明经历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宗族制度向宗法制度转变、部落酋长制向王国政治结构转变等演进过程。同时,以人文地理为基础构建社会结构,以贡赋制为基本形式构建国家政治体系,这些都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大禹治水: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早期,神权与王权始终没有完全分离。禹作为传说人物,既是一个人又被赋予了神性。他被视为鲧的儿子、颛顼之后,排入了大一统的帝王世系中。这种人神杂糅的背景下,禹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传说人物。
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早期文本叙述中,主要强调大禹降土和敷土的功绩。例如,《天问》中提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诗经》“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中也描述了大禹敷下土方、开辟新国家领域等伟绩。当洪水来临时,人们不得不寻找高地或山川避难,敷土成了人们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紧迫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文献中强调大禹降土和敷土方面的功绩。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特别是战国时期,人们开始探索解决洪水的方法。大禹治水传说便逐渐加入,并成为主要叙述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学派兴起,将大禹视为贤能之君,通过治理洪水泛滥展现了圣王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因此,在文献中对大禹治水事迹的描述逐渐增多,并且被人们广泛传颂。
大禹治水传说不仅是一个英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勇敢面对困难、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禹的英雄事迹和统治九州时展现出无私无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质,让九州各地区团结协作。从降土到治水,这一转变彰显了社会对于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生存安全的追求。《禹贡》记录了大禹治水及各地向冀州交纳贡赋的情形,通过对不同区域土壤、经济状况和物产的考察,人们确定了赋税等级和贡物品类,并通过疏通水道来实现治水避灾以保障民生,同时也确保了贡赋运输的畅通。禹将九州万邦协和为一体,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部落,这也为四方朝服纳贡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推行“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禹的功绩更是中华文明形成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禹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构建
在古代,由于江河水道处于自然状态且容易堵塞,洪水泛滥成为常见现象。禹可能在一定区域内协调各邻邦疏通水道以实现泄洪导水的目标,随着大禹成功治理了洪涝灾害,他接受了邻邦的物产作为馈谢之礼。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初步的“禹贡图”和《禹贡》。
到了西周时期,尽管天下未能完全一统,但周天子通过封邦建国和分封诸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天下共主。为了明晰疆域、掌握山川形胜、划分区域以及征缴贡赋等的需要,周人对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图文进行了梳理和扩展,并将其绘制为反映西周时期地理物产的图录。由于周人对夏禹时期的“禹贡图”和《禹贡》进行承袭与发展,符合统治合理性和尊夏心理要求。商代以河洛为中心的区域内大小邦国约有两千,而周初诸侯至少也有八百。因此,在万国林立的夏禹时代,以《禹贡》所载之规模,要求各地出产物品进贡至冀州或其他一地并不现实,但这并不能割裂《禹贡图》与禹、夏之间内在关联。[2]《禹贡》所描述的夏禹时代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着许多大小邦国,这些邦国之间相互封闭,缺乏交流和合作。然而,中华文明的形成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不同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融合,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夏禹时期已经孕育出“协和万邦”的理念,并产生了推动各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宏大政治构想的萌芽。
《禹贡》是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文献之一,它标志着九州地理划分观念的形成,并肇始了中国天下九州一统的观念。《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对各地区的文化类型和文化习俗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揭示了中华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新发展以及《禹贡》对后代人文地理的影响。
三、九州:中华文化的中心观
九州作为构建中国古代格局的一種视野,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禹贡》,大禹在平定洪水后,根据各地土地和资源的情况划分了九州。许多文献都提到了禹划九州的观念。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开九州,通九道。”《左传·襄公四年》也提到了:“芒芒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而屈原在《天问》中对禹划九州表示疑问。这些记载表明,“禹序九州”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九州包括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关于九州起源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九州来源于战国时期以前,是对古代部落征服和领土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区域概念。[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九州是基于三代历史事实而形成,并成为战国时期诸雄分野的重要依据。[4]不论是哪种观点,九州的存在与变迁都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九州的划分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密切相关。根据《禹贡》,每个九州都有独特的土质和自然地貌,这些因素决定了各地区物产、民风、民俗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在《禹贡》中,冀州被标注为“正中”,冀州被视为九州之首,是天下之中心。这一观念逐渐发展为中央王朝中心观和中原文化中心观的基础,主导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
《禹贡》不仅对各州的山脉河流进行了记述,还对全国范围内的山脉走向和河流流域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这标志着中华先民首次对九州大地的土地、山脉和河流进行了完整且理性的认知。通过以高山大河来划分界域,形成了九州的地域观和区域观。
《禹贡》揭示了九州与中华文明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禹贡》中记述的各州的土地山川构成了各州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各州通过开垦土地、种植农作物、养蚕桑、修建水利设施、发展交通道路等人文活动,提高了人文生态环境的质量。这些活动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化,并保证了国家贡赋制度的顺利实施。这种理性认知是围绕着“九州攸同”“四海会同”的国家中心观展开的。人们将商人来往于九州之间看作是常态,将周人所居住之处视为王土,表达出中华文明中心观念的延续与发展。从神秘观念世界和宗教世界中解脱出来,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大自然(山川土地),展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理性认知,也展现了以人为主体的天人关系和人地关系时代观念。这正是《禹贡》问世的历史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早期文明的主要特征所在。
四、五服制: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禹贡》首次提出了五服制,包括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五个层次。五服制构建了夏代早期中原地区与四夷的关系图,形成了内圈甸服、中圈侯服和绥服、外圈要服和荒服的分布格局。通过不同层级关系和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格局来反映了王室与周边部族、方国之间的关系。而“服”的含义是指对天子的服侍义务,不同“服”之间界线模糊,真正清晰鲜明的界线发生在华夏与荒服之间。
夏王朝采取了近似分封的制度,承认已存在的部族、方国政权,并推广中原文化保卫中央和诸侯国的安全。五服制试图在地理空间上构建一种公共秩序,以区分华夏族群与夷夏两个群体,并确立了对天子的服务义务。这些思想和制度体现了华夏族群对于社会秩序和地域划分的努力与设想,这一思想体系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构建了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金字塔式文化思想体系。通过五服制度,地方与中央之间建立了秩序化和制度化的关系,形成了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基础。这一思维定式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古代中国社会,并成为古代中国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个体系使得中央王朝既成为政治上的核心,又成为文教上的核心。它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说,五服制已经成为古代中国最基本的思维定式,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
五、结语
夏代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展现了历史连续性和由中原向周围辐射的延伸性。《禹贡》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展现了人文地理观念和文明中心观念的经典,对于探索中华早期文明具有极大的价值。《禹贡》的成书,虽然历时较长,存在后人掺入与润色,但仍是我们了解中华早期文明某些特征的宝贵资料。
中华文明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范围内展开,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形成。中国的文明发展和形成是在广大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融合,中华文明才孕育出“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产生推动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周人通过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体,这个政体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5]
从《禹贡》,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部落联盟酋长逐渐演变为国王与群巫之长,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二为一,宗族制度逐渐发展为宗法制度。部落酋长更迭制被王位禅让制取代,家天下成为新的政治形式。人文地理行政区划构成了社会结构,贡赋制成为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形式。赐土和姓氏分封诸侯建立了官僚制度,构成了王国政治结构。而天人同构和人地同构则构成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宇宙观。这些早期文明形态和特征决定性地影响着古代中国文明史的发展道路。
《禹贡》的问世标志着中华先民首次对九州大地进行完整且理性的认知,通过对九州之间山脉河流及其走向、流域等方面详尽描述,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地理观念和社会结构。《禹贡》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和中华早期文明特征的作品,展现了中华文明中心观念的延续与发展,中华文明以多元一体的方式构建起来,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它孕育了“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并通过政治措施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愿景。
参考文献:
[1]张碧波.人文地理学与文明中心观之始原——读《尚书·禹贡》[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1.
[2]徐新强.“禹贡图”与中国早期贸易中的水道交通[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11(006).
[3]史念海.論《禹贡》的著作年代[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
[4]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1989.4.
[5]李新伟.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孕育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N].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2020-09-23.
本文为2023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一般单列项目《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及其时代价值》(项目编号:2023DL03)成果
作者简介:
谢羽(1980—),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历史学博士,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