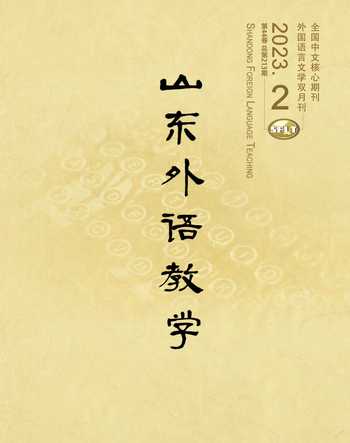奴隶贸易、黄热病与大西洋流散共同体的覆灭
陈豪 乔雪笛
[摘要]本文以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代表作《老水手行》中的政治隐喻为切入点,将诗歌置于18至19世纪之交英国殖民策略调整期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梳理诗中信天翁之死和老水手赎罪情节的现实指涉。诗人用信天翁之死的情节隐射奴隶贸易中大西洋流散共同体犯下的残暴行径,揭示出该共同体已成为英国民众心中不可摆脱的道德包袱和历史罪责。本文同时阐述诗人如何借黄热病的象征意象表现老水手赎罪行为的徒劳,暗指英帝国的政治转型将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柯尔律治;《老水手行》;流散共同体;黄热病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1002-2643(2023)02-0078-10
SlaveTrade,YellowFeverandtheFalloftheAtlanticDiasporicCommunity:PoliticalMetaphorsin“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
CHENHaoQIAOXuedi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BysituatingColeridges“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withinthehistoricalcontextofBritainsinitiativetoadjustitscolonialiststrategyaroundtheturnofthe18thcentury,thispaperaimstoexplorethepoliticalmetaphorsandhistoricalreferencesinthepoemstreatmentofthealbatrosssdeathandthemarinersmoralredemption.Thepoettapsintothescenarioofthealbatrossbeingkilledtoalludetotheatrocitiesperpetuatedbythediasporiccommunitythatemergedinthetransatlanticslavetrade,anticipatingthefactthattheBritishpeoplehavetoenduretheconstanthauntingspecterofguilt.ThepaperalsodiscusseshowthesymbolicyellowfeverisusedtoimplythefutilityofthemarinersrepentanceandthedoomedfiascoofBritishempirespolitical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leridge;“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diasporiccommunity;yellowfever
1.引言
《老水手行》是柯尔律治(S.T.Coleridge,1772-1834)所有诗作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首,以奇幻情节、瑰丽想象和深刻立意著称。两百多年间,评论家们运用神学、美学、伦理学和心理分析等视角对该诗进行了各种解读,却似乎未对作品的现实关照予以足够重视,更少探究其中暗藏的政治隐喻。该诗的创作时期——18世纪末是西方历史上的变革年代: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民主思想和人权观念的普及,所有这些都涤荡着旧有统治模式。在英国,第一帝国悄然瓦解,废奴呼声日益高涨,大西洋上以奴隶贸易维系的流散共同体难以为继,一场政治变革箭在弦上。作为一名对时局高度敏感的作家,柯尔律治不仅参与现实政治,更擅长以诗为传声筒表达政治主张。这首诗晦涩难懂,反倒为政治视角的解读创造了更多可能。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老水手行》的政治书写主要聚焦奴隶贸易批判。英国学者艾巴特森(J.R.Ebbatson)的论文《柯尔律治的水手与人的权利》通过史料挖掘与互文分析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论证。但该研究在两处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第一,信天翁之死与贩奴船罪行之间有着怎样的象征关系;第二,船上水手暴亡背后是否另有隐情,他们的死与奴隶贸易是否有关。在此基础上,李(DebbieLee)的论文《黄热病与奴隶贸易:柯尔律治的〈老水手行〉》选择以黄热病大流行事件为切入点,解开了水手集体死亡之谜,发掘出黃热病隐喻的历史批判功能。美中不足的是,该作者尽管在文末提及黄热病隐喻对帝国政治的指涉,却未予展开。在笔者看来,此隐喻把老水手的罪与罚关联起来,不仅深化了对奴隶贸易的批判,更暗示了作为其依附的流散共同体的覆灭。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试图揭开隐蔽在诗歌非自然叙事之下的历史呈现与现实关切,考察诗人对殖民政治的反思。
2.信天翁之死: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老水手行》是一首象征意味极强的诗歌,却也有其现实一面。该诗完整记述了一次从英国出发、跨越两大洋的航行,不禁让人想起英国作为海洋帝国的发迹史。尤其对当时读者而言,他们很难不联系现实政治,而纯粹将诗中描绘的航海活动视为某种抽象事件的表征。以燕卜荪(WilliamEmpson)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此诗映射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奴隶贸易,指出诗人的关切在于揭露帝国“海上扩张的可怕故事”(1993:167)。艾巴特森更挖掘出诸多证据,有力支持了上述论断:“这首伟大诗作讲述了欧洲人的罪行和对赎罪的迫切需求”(Ebbatson,1972:206)。沿着这两位学者开辟的路径,我们发现仅把信天翁被杀视为人类原罪的表征似有文过饰非之嫌,所以有必要联系英国大西洋殖民史,重新考察该事件所承载的罪恶往事和梦魇记忆。
诗歌中,老水手与人分享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Beebe,1966:213)。航海途中,他射杀一只信天翁后引发一连串天谴:先是遭遇严酷的自然环境,后是同伴离奇死亡;他独自海上漂泊,承受着死亡威胁和精神煎熬。在柯尔律治笔下,那只信天翁极富灵性,不仅被视为基督使徒,而且也与水手们相处融洽:“冰海上空/一只信天翁/穿云破雾飞过来;/我们像见了基督的使徒,/止不住向它喝彩”(柯尔律治,2001:311)。①当鸟儿被杀的情节出现时,诗人在旁注里作了谴责:“老水手极为冷酷地杀死了这只虔诚的,预告吉兆的鸟儿”(Coleridge,2018:450)。从愤懑的文字看,作者将信天翁刻画成无辜弱者形象,意在指涉现实。
该诗发表一年后,柯尔律治写下政治诗《孤独中的忧思》(“FearsinSolitude”)。诗中,他公开批评英国政府的无道统治,揭开了信天翁之死的历史影射:
是呵!令人痛心地,我们犯下了
极其残暴的罪孽。从东方到西方,
受苦的黎民在指斥我们;他们,
不计其数的、怒火如焚的群众,
都是上帝的子孙,我们的兄弟!
……我们曾汹汹出动,
把奴役和苦难带给远方的部族;
更其凶险的,我们的污毒腐恶
就像软刀子慢条斯理地杀人,
把躯体和灵魂一齐摧毁!(395)
从引文看,柯尔律治采纳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建议插入信天翁情节,很可能是为暗示英国在海洋帝国崛起过程中对他族犯下的累累罪行。他创作《老水手行》时身处布里斯托(Bristol),完整见证了这段历史。他在当地举办专题讲座,痛斥奴隶贸易之恶。诗歌的创作背景与布里斯托的黑历史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英国人同远方部族的接触始于大西洋民间航海活动,其开端可追溯至15世纪后半叶“由布里斯托人领头的贸易与探险等早期殖民活动”(姜守明,2019:113)。诗歌标题中的“ancientmariner”一语双关,既指年长水手,也可引申为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代代水手集体形象的化身。随着拓殖活动深入,水手们长期孤身海外,抱团取暖,产生了强烈的身份和职业认同,一个与帝国殖民事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流散共同体在远离故土的茫茫大洋上形成。
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认为“作为边界共同体的流散群体可通过多样的文化形式、亲缘和商业关系维系流散者的内部联结”(曾艳钰,2022:128-129)。显然,大西洋流散共同体的壮大亦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起先,水手的职业属性要求他们精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海上风险。后来,布里斯托民间对海洋与财富的原始兴趣唤起英国官方海外拓殖的野心。奴隶贩子的加入扩充了共同体的势力范围,赋予了它更为明确的经济意图。此时,奴隶贸易也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关注。特立尼达多巴哥国父、历史学家威廉斯(EricWilliams)指出:“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发展贡献巨大,产出的利润滋养整个国家的生产体系”(Williams,1944:105)。诗中老水手的船在启程时受到欢呼,欢呼的人群或许在为水手们送别,更可能是在向帝国的摇钱树——远洋船喝彩。至此,活跃于大西洋上的这个共同体已成为帝国海外利益的保证,其兴衰成了帝国成败的晴雨表。“共同体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怀旧。”(王卫新,2022:86)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共同体原初的精神诉求必然被淡忘,共同体随即蜕变为伪共同体,而信天翁之死乃是该共同体走向覆灭的象征。
美国学者迈库西克(J.C.McKusick)把信天翁视为“欧洲对外征服史上所有被害的无辜生命的标志性形象”(1998:684)。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创作之初,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曾就诗的功能达成共识,即诗歌除了创造新颖的想象客体,还“具有一种激发读者同情心的力量”(Coleridge,1817:145)。顯然,迈库西克的解读不仅呼应了诗人废奴主义的政治立场,更彰显了他诗歌创作的艺术宗旨。《老水手行》中蕴含的共情结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天翁之死联接着诗人同胞对奴隶贸易中受难者的怜悯;二是老水手的噩梦反映了共同体成员对这段黑历史的焦虑,进而预示其必然崩溃的命运。就第一点来说,柯尔律治的同时代读者或许会想起贩奴船上奴隶们的命运。当时已有消息渠道披露他们在海上的悲惨境遇。据统计,“在从非洲到加勒比海和美洲的大部分旅途中,人员流失率约为百分之五十”(沙玛,2020:180)。当然,英国人贩子不会在意奴隶死活,如同诗中老水手受同伴指责不是因为杀害信天翁,而是厄运由他而起。但在英国国内,废奴呼声已经形成,“宗号”船上的杀戮事件让大西洋上的英国船队声名狼藉。
1781年11月29日,船长柯林伍德(LukeCollingwood)以淡水储备告急为由决定对船上黑奴实施肉体消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宗号”惨案(TheZongMassacre)。《老水手行》中,柯尔律治也关注海上的饮水短缺问题:“水呀,水呀,处处都是水,泡得船板都起皱;水呀,水呀,处处都是水,一滴也不能入口”(314)。面对困境,白人船长想到的不是同舟共济,而是大开杀戒。屠杀持续三天,第一批黑奴被扔下船时甚至来不及挣扎。如此惨烈一幕在诗中也曾上演,只不过诗人把奴隶换为水手:“两百个水手,一个不留,/(竟没有一声哼叫)/扑通扑通,一叠连声,/木头般一一栽倒。/魂魄飞出了他们的皮囊——/飞向天国或阴间!”(319-320)此时,老水手似乎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的独白不免让读者想起那些葬身大海的冤魂:“这么多一表堂堂的汉子/都死了,木然僵卧;/成千上万条黏滑的爬虫/却活了下来,还有我”(320-321)。字里行间流露的除了同情还有愤怒,表明道德意识与身份认同发生了强烈冲突,共同体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
然而,历史上惨案的始作俑者与同谋都未受到起诉,审理此案的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Mansfield)甚至认为柯林伍德的行为跟把马匹扔海里并无二致(Krikler,2007:36)。诚如柯尔律治所言,“奴隶制的存在违背了基督教精神,因为它把人颠倒为畜生”(Coleridge,1853:222)。正义未得到伸张,但该事件已触及良知底线。诗中,柯尔律治唤醒英国人良知的做法是赋予动物与人类同等的生命尊严与权利。借巴特勒(JudithButler)所创的概念表述就是,动物在诗里成了“可哀悼的生命”(grievablelife)(2009:38),而现实中的贩奴活动则把人贬为“不可被哀悼”的商品,两相反差揭露出帝国经济赖以生存的大西洋流散共同体实则是一部杀戮机器,其运作方式完全违背西方人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信天翁之死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老水手的讲述亦营造出心有余悸的氛围,反映了英国民众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负罪感。诗歌第三部分出没的幽灵船既是对大西洋上贩奴船的生动再现,也是共同体成员暗恐的客观关联物。在诗人笔下,幽灵船与贩奴船颇为神似:“直直的栅栏把太阳挡住,/(愿天国的圣母带来恩赐!)/仿佛透过地牢的格栅,瞥见/太阳滚烫的大脸”(Coleridge,2018:453)。这段描写选取舱内视角,老水手化身为贩运途中的黑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废奴主义者里兰(JohnRiland)同样用“地牢”一词来形容贩奴船的内部环境(Rediker,2007:68)。据他描述,“地牢”空间局促,空气污浊,光照不足,当清晨的阳光穿过格栅时,奴隶们会像幽灵一样躲闪。随着英国海外贸易越做越大,一座座流动的人间地狱在海上漂浮,展示着英国人引以为傲的造船技术,更诉说着水手与奴隶贩子相勾结所制造的苦难。
“宗号”事件后,英国朝野上下再也掩盖不了奴隶贸易中的罪恶行径,废奴立法刻不容缓,大英帝国极欲与其背后的共同体进行政治切割。在献给柯尔律治好友、著名废奴运动领袖克拉克森(ThomasClarkson)的诗里,华兹华斯描绘了萦绕于他们那代良知未泯者内心的不安:“听到了控诉的声音,不断地反复,/那是你心中的神谕在召唤,催你奋起”(1852:258)。在1796年的一场讲座中,柯尔律治也有相似之语:“神的信仰者会相信上帝爱其子民就如同父母爱其子女。敬神畏神的人怎会干出压迫上帝孩子的事情?让千千万万的孩子沦为奴隶,受尽折磨,惨遭杀害!”(Coleridge,1990:136)诗人一定觉得他的同胞犯了渎神的重罪,重到已无法得到救赎。无独有偶,骚塞(RobertSouthey)在题为《从事奴隶贸易的水手》(“TheSailor,WhoHadServedintheSlaveTrade”)的诗里借当事人之口也表达了相似心境:“‘哦,该死!干的那些该死的事啊!/可怜人答道,/‘无论白昼夜晚,置身何处/那些做的孽总是在眼前重现”(Southey,1837:63)。
文学是社会心理的晴雨表。老水手喃喃自语式的痛苦忏悔并非孤例,相似的表达在不同语境中重现,表明因奴隶贸易结成的流散共同体已成为帝国形象的负累。老水手在讲述信天翁之死及其后果时难以启齿又不吐不快,揭示出英国人面对贩奴船的故事既欲遮掩又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国家的颜面和国民身上的“文明人”标签需要维护;另一方面,民众出于道德本能或宗教感化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并希望通过赎罪来缓解。这种矛盾心理作用于创作便产生了该诗中的艺术难题,作用于现实则让海外殖民群体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然而,柯尔律治在诗中对黄热病疫情设法化用,为难题解决找到出路,更在无意中预见了英国殖民策略的重大调整。
3.黄热病之患与帝国的“悔罪书”
诗歌中,作为杀戮者的老水手痛改前非,并在上岸后向人布道,宣传众生平等观念。他的这种转变当然有助于表现罪与罚的主题,但如何使转变自然发生?这成了摆在诗人面前的一道艺术难题。
要探究柯尔律治的解决之策,需要先考察信天翁被杀后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整个旅程中让老水手最无法释怀的是共同体瓦解后其成员的非正常死亡,他的悔罪和反思皆源于此,所以破解他们的死因成了关键。表面看,他们死于天谴,即死于幽灵船上两个精魅的生死赌局,但超自然的情节背后是否存在现实指涉,就如幽灵船与贩奴船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约关联?从诗的第二章起,柯尔律治陆续为读者留下了蛛丝马迹,如黏稠的海面、枯萎的舌头、血红的太阳、滚烫猩红的海水等。这些意象让人联想起某些疾病的症状。据李推测,整船人员可能都感染了黄热病。该病症状主要有呕吐、高热、黄疸、头痛、口渴(Lee,1998:677),以及“眼、口、鼻部发红”(基普尔,2007:988)。不难发现,部分症状与上述意象之间存在视觉上的对应关系。诗里反复提及老水手焦黄的肤色也似乎在暗示此病病愈后留下的黄疸后遗症,加之叙述中出现的各种亦真亦幻的情节亦符合病程中时有发生的幻觉症状。进一步考察历史,可以发现黄热病传播与奴隶贸易关系密切。
关于此病的起源地,学界目前有两种看法:一说是西印度群岛,另一说是西非。两处地点恰好都位于奴隶贸易三角区上。17世纪奴隶贸易升温,极有可能“这些运送奴隶的船只运送黑奴身上的病毒的同时也运送了隐藏在水桶中的蚊子”(基普尔,2007:989),而黄热病病毒的宿主就是埃及斑蚊(AedesAegypti)。在非洲,黄热病具有选择性传染的特点。当地人对它似乎是免疫的,而欧洲人属于易感人群。历史学家查克拉巴提(PratikChakrabarti)的研究表明历史上该疫病的三次大爆发“都标志着大西洋地区帝国史的独特阶段”(2019:169)。1790年代的首次爆发与《老水手行》的历史语境最接近。1793至1798年,“在马提尼克等西印度群岛岛屿,约五万名英国士兵和水手死于黄热病”(同上:170)。此次爆发对奴隶贸易扩张提出了警告。诗里,船板和大海之所以被形容为“腐烂发霉的”(321),是因为贩奴船充当起了病毒洲际传播的媒介。殖民者到非洲和美洲掠夺、杀戮的同时还在当地打开了疾病的魔盒。从此,臭名昭著的“中间通道”(TheMiddlePassage)不仅是黑奴们的死亡通道,也成了白人水手们的梦魇旅程。
黄热病让奴隶和水手都沦为帝国殖民行动的牺牲品,诗中老水手对船上尸体的种种幻想构成了他悔罪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尸体“活”了过来并在沉默中用眼神控诉:“孤儿的诅咒可以把亡魂/从天堂拖下地府;/而死者眼中发出的诅咒/却更加可惊可怖!”(321-322)在此,我们无从辨别亡灵身份。按理它们应该来自那些染病而死的水手,但无声的诅咒更很符合屈辱中死去的黑奴形象。当然,也可能是诗人故意模糊了亡灵身份。此时,水手与黑奴有了相似的命运。对两者而言,生死就像精魅掷出的骰子充满“随意性”(Miall,1984:645)。共同的恐懼淡化了主奴身份差异,让共情有机会建立起来,也一定程度恢复了黑奴的主体性地位。老水手为水蛇祈福时的心理活动体现了这种观念转变:“美妙的生灵!它们的姿容/怎能用口舌描述!/爱的泉水涌出我心头,/我不禁为它们祝福;/准是慈悲的天神可怜我,/我动了真情祷祝”(323)。不少学者将此段视为他救赎成功的标志,隐喻着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解”(Stokes,2011:9)。结合历史语境还可以对上述结论稍作延申:老水手的祈祷表达了殖民者在遭受黄热病天谴后产生的一种试图与被殖民者和解的救赎心理。如果说从观念上撕去黑奴身上“神圣人”的标签是和解的前提,那么1804年英国立法取缔奴隶贸易则成为和解的结果。
祈祷显灵后,信天翁的尸体从水手脖子掉下,赎罪之旅取得标志性进展。令人意外的是,随后的返航格外顺利。除神灵一路护佑,每次忏悔也都有响应,种种迹象显示老水手身后有一股强大势力在支援其赎罪。细数回家之旅中的护佑者,按出场先后顺序分别为天使精灵团、南极神怪的同伴魔魅、水下神怪和林中隐士。这些仙灵等级分明、目标明确,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俨然一个有序运作的组织。至此,救赎成功与否已不只是老水手个人之事,个体背后的体制力量也迫不及待地介入其中。宏观看,殖民者的行为维系着帝国的形象和利益,他们的焦虑与诉求折射出帝国统治的积重难返。无论是贩奴船惨案还是黄热病爆发都让旧的殖民体系备受质疑,老水手的自我救赎成了帝国政治自救的一次预演。
十八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独立终结了英国第一帝国时代。第一帝国奉行重商主义原则,推动国家走向了“自给自足”的“贸易帝国”(郭家宏,2019:42)。在这个循环体系中,殖民地蕴含着丰厚的剩余价值,导致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实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就像老水手无视信天翁的生命权,殖民者为追求经济利益肆意践踏人权,两者的尖锐矛盾是第一帝国瓦解的重要原因。18世纪末,黄热病频发又让殖民者吞下自酿的苦果。此外,工业革命初见成效,帝国迫切需要重塑自身形象,以挽回美国独立一事上丢掉的颜面,同时也为建立新的殖民体系做准备。总之,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奴隶贸易都已成为第一帝国留下的负面遗产。
对奴隶贸易的自我检讨开启了英帝国的形象重塑工程。1789年5月12日,废奴运动领袖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在国会演说,历数奴隶制罪状,他言辞之恳切与老水手回国后对林中隐士做的忏悔如出一辙。演说过后,“他获得了诸如皮特(WilliamPitt)、福克斯(CharlesJamesFox)和柏克(EdmundBurke)等政治领袖的支持”(Sonoi,2006:28)。这次演说拉开了帝国集体反思的序幕,此后历经18年漫长等待,政府最终颁布了带有“悔罪书”意味的奴隶贸易禁令。在此过程中,威尔伯福斯所属的福音派贡献巨大。但在其后岁月里,该派宣扬的人道主义理念被帝国的意识型态机器吸收,用于弥补野蛮统治造成的形象受损。值得注意的是,该诗传递出的宗教精神亦处处留有福音派的思想印迹。例如,它的两个核心教义“皈依主义”(conversionism)和“积极主义”(activism)都在老水手的救赎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魔魅的预言“‘此人虽有罪,已受了惩罚,/惩罚将延续不休。”(329)指向了“永恒惩罚”的信条。福音派一贯认为罪与罚有其积极意义,指出“要让有罪之人独自承受苦难,并通过这种赎罪方式驱使他们向信仰基督的目标迈进”(Forsythe,1987:10)。照此逻辑,黄热病意象架起了罪与罚之间联通的桥梁。借此,老水手实现了从杀戮者到赎罪者的自然过渡,重归上帝怀抱。如果说为水蛇祈祷是老水手的一次精神自救,那么废奴运动就是帝国在宗教精神启示下的一场政治自救。
然而,这种自救并不彻底。诗人把流散共同体当作替罪羊,就不可能把反思深入至帝国政治的骨髓,这成了浮于表面的表演式救赎。诗中,老水手从未就杀戮事件深刻反省,以至于杀戮背后的心理动机始终是谜。他说:“对人类也爱,对鸟兽也爱,/祷告才不是徒劳”(339)。这话意味着爱不是目的,而是讨好上帝的手段。当然,讨好上帝也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摆脱天谴的噩梦。就这样,老水手愈要回避恐惧,恐惧就愈形影相随,最终陷入赎罪的死循环。行文至此,可以发现诗中黄热病的意象又有了新的寓意。瘟疫爆发时,老水手眼里永远只有作为表象的症状,这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都意在消除症状,而非根治疾病。现实中,帝国的自救何尝不是如此。不同于第一帝国粗暴的统治,第二帝国试图展示亲善,措施包括“向殖民地推广在国内已普及的社会制度与宗教”(Brady,1950:585),终极目标是“通过改善(原住民)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来消除普遍的不平等”(Lester,2014:5)。但诚如英国历史学家贝莱(C.A.Bayly)所指出,第二帝国新政的实质是向外界标榜英国人的“民族优越性”(1989:108),其目的是为维持殖民统治寻找合理性根据。就像老水手强行拦下行人说教,所谓“良政”不过是在粉饰强权。若没有对奴隶制背后殖民思维的彻底反思,种族平等就是空话,帝国的救赎和改良仅仅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
第二帝国的政治困境不禁让人想起1793年的“汉基”号(Hankey)事件。这艘载着殖民者的商船从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出发,沿着三角航线驶向几内亚比绍的博拉马群岛,开启了一场赎罪之旅。船上殖民者对奴隶贸易深恶痛绝,他们尝试在非洲建立一个理想的自由殖民地,走一条雇佣而非奴役、开发而非掠夺的新路。悲剧的是,赎罪之旅非但没有成功,航船还成了传播黄热病病毒的移动温床。诚然,黄热病肆虐弱化了英国人对非洲奴隶作为商品的印象,却让后者开始作为“被贱斥者”出现在前者头脑中,成为某种“既非客体又非主体”(Kristeva,1982:1)的存在。怀着怜悯与恐惧并存的复杂心理,殖民者表现出对非洲原住民的理解无能。《死亡之船》一书作者、历史学家史密斯(BillyG.Smith)一语中的:“那些幼稚的殖民者不乏善意,却无比傲慢,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文化优势极度自信,认为完全可按自身形象来改造世界。于是,他们几乎无视西非特有的社会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2013:155)。
除了信天翁尸体,水手亡灵也是被贱斥者的絕佳形象表征。它们本来和老水手一起承受上天惩罚,却在接近返航终点时被后者无情抛弃,甚至连一起乘坐的船只也沦为了贱斥的对象。贱斥行为本质上可概括为转移和掩饰,即把自身肮脏投射至与自我相关联的他者身上并予以排斥,目的是制造自身洁净的幻象。作为结果,老水手陷入了忏悔无能的困境。就帝国而言,上述两种无能指向同一种统治危机。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和流散共同体仿佛是其体内的毒瘤,仅仅将它们切除而对其病灶置之不理,终究治标不治本。第一帝国的问题没有因第二帝国的崛起而根除,瓦解的种子在它开创之初就已埋下,而这一预见已通过这部作品中的政治寓言暗示给了诗人同时代的读者们。
4.結语
1840年,皇家艺术学院展出英国画家特纳(J.M.W.Turner)的油画新作《贩奴船》,引发舆论关注。其时距奴隶制废除已逾6年,距奴隶贸易禁令颁布更过去了33年。这幅画以“宗号”惨案为背景,捕捉了黑奴被抛下船的悲惨瞬间。特纳描绘出了咆哮的怒浪和逆光中贩奴船的朦胧轮廓,而构图的关键——奴隶在海中挣扎的身影却被画面下方若隐若现的几只人手代替。从柯尔律治的诗到特纳的画,受害者形象愈来愈模糊,贩奴船却在大海和红日的映衬下平添了几分崇高。“奴隶贸易制造的恐怖已转化为愉悦观众的审美客体,并在恐怖和鉴赏者之间建立起某种隐秘的共谋关系”(Frost,2010:380)。继柯尔律治的诗作之后,特纳的画作再次暴露了帝国既欲赎罪又欲盖弥彰的矛盾心态,却始终逃避检视殖民主义的根本罪恶。当具体罪状被抽象为神学意义上的普遍原罪,或被供奉为美学意义上的非实体性恐惧,对历史的反思也就只能止步于形而上的冥想,而无法落实为现实中行动力量。
注释:
①引自《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参考文献
[1]Bayly,C.A.TheBritishEmpireandtheWorld:1780-1830[M].London:LongmanGroup,1989.
[2]Beebe,M.&L.A.Field.RobertPennWarrensAlltheKingsMen:ACriticalHandbook[M].Belmont: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1966.
[3]Brady,R.A.CrisisinBritain:PlansandAchievementsoftheLabourGovernment[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50.
[4]Butler,J.FramesofLife:WhenIsLifeGrievable[M].London:Verso,2009.
[5]Coleridge,S.T.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A].InS.Greenblatt(ed.).TheNortonAnthologyofEnglishLiterature.Vol.D,TheRomanticPeriod[C].NewYork:W.W.Norton&Company,2018.448-464.
[6]Coleridge,S.T.BiographiaLiteraria[M].London:BellandDaldy,1817.
[7]Coleridge,S.T.Notes,Theological,PoliticalandMiscellaneous[M].London:EdwardMoxon,1853.
[8]Coleridge,S.T.TheCollectedWorksofSamuelTaylorColeridge:TheWatchman[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
[9]Ebbatson,J.R.ColeridgesMarinerandtheRightsofMan[J].StudiesinRomanticism,1972,11(3):171-206.
[10]Empson,W.&J.Haffenden,TheAncientMariner:AnAnswertoWarren[J].TheKenyonReview,1993,15(1):155-177.
[11]Forsythe,W.J.TheReformofPrisoners,1830-1900[M].London:CroomHelm,1987.
[12]Frost,M.“TheGuiltyShip”:Ruskin,Turner,andDabydeen[J].TheJournalofCommonwealthLiterature,2010,45(3):371-388.
[13]Krikler,J.TheZongandtheLordChiefJustice[J].HistoryWorkshopJournal,2007,64:29-47.
[14]Kristeva,J.PowersofHorror:AnEssayonAbjection[M].LeonsR.Roudiez(tran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2.
[15]Lee,D.YellowFeverandtheSlaveTrade:Coleridges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J].ELH,1998,65(3):675-700.
[16]Lester,A.&F.Dussart.ColonizationandtheOriginsofHumanitarianGovernanceProtectingAboriginesacrosstheNineteenth-CenturyBritishEmpir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
[17]McKusick,J.C.“ThatSilentSea”:Coleridge,LeeBoo,andtheExplorationoftheSouthPacific[J].TheWordsworthCircle,1993,24(2):102-106.
[18]Miall,D.S.GuiltandDeath:ThePredicamentof“TheAncientMariner”[J].StudiesinEnglishLiterature,1500-1900,1984,24(4):633-653.
[19]Rediker,M.TheSlaveShip:AHumanHistory[M].NewYork:Viking,2007.
[20]Sonoi,C.ColeridgeandtheBritishSlaveTrade[J].TheColeridgeBulletin,2006,26:27-37.
[21]Smith,B.G.ShipofDeath:AVoyageThatChangedtheAtlanticWorld[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13.
[22]Southey,R.ThePoeticalWorksofRobertSoutheyVol.II[M].London:Longman,1837.
[23]Stokes,C.“MySoulinAgony”:IrrationalityandChristianityin“TheRimeoftheAncientMariner”[J].StudiesinRomanticism,2011,50(1):3-28.
[24]Williams,E.CapitalismandSlavery[M].ChapelHill: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44.
[25]Wordsworth,W.TheCompletePoeticalWorksofWilliamWordsworth[M].Philadelphia:Troutman&Hayes,1852.
[26]查克拉巴提.醫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M].李尚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7]郭家宏.英帝国史(第四卷)[M].钱乘旦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28]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主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29]姜守明.英帝国史(第一卷)[M].钱乘旦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30]梅申友.隐秘的自况——《老水手行》旁注者身份探析[J].国外文学.2002,(2):96-107.
[31]沙玛.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M].李鹏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32]王卫新.苏格兰的神话:伊恩·麦克莱伦小说中的乡村共同体[J].山东外语教学.2022,(5):78-87.
[33]曾艳钰.流散、共同体的演变与新世纪流散文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2022,(1):127-134.
(责任编辑:翟乃海)
收稿日期:2022-11-01;修改稿,2023-03-10;本刊修订,2023-04-1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27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维多利亚小说疾病与医学书写的现代性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1YJC752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豪,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textbook_5@126.com。
乔雪笛,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qiaoxuedi@foxmail.com。
引用信息:陈豪,乔雪笛.奴隶贸易、黄热病与大西洋流散共同体的覆灭——《老水手行》的政治隐喻[J].山东外语教学,2023,(2):78-87.
DOI:10.16482/j.sdwy37-1026.2023-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