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白成势
——董其昌山水画布白艺术初探
文_梁松林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从多个角度探讨董其昌山水画的布白艺术处理手法,研究其成就与价值,指出董其昌的布白艺术处理在艺术理念及相关联的山水画图式上的独到之处,对后世影响巨大。研究董其昌,不得不研究他的布白艺术。
本文论及的“布白”,是指对不着笔墨的空白部分的安排。“白”就是指画面中的留空的部分。
在传为晋代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中即有“分间布白,上下齐平”[1]31之论。这里的“布白”,其义是指笔画之间的空白分布。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的论述,可见黑与白互为作用的辩证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扎根,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后来有“计白当黑”的说法,如清代包世臣所著《艺舟双楫》记载清代邓石如有“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1]641之说,表明了布白艺术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艺术有书画同源之说,布白艺术也在中国画艺术中得以发展。
自五代荆浩《笔法记》提出“有笔有墨”的笔墨要求后,山水画至宋代达到高度成熟,技巧完备,尤重渲染,通常空虚部分(如天空、云水、地面)均落墨渲染,即所谓“染天染地”,画面可以说无有不落墨之处。这也可视为宋代山水画特点。到元代,直接留空不着一墨的布白手法开始在山水画中出现,如赵孟的《秀石疏林图》《水村图》以及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作品。此后,山水画的这种布白处理开始变得越来越常见。到明代,山水画追求“简、淡、虚、空”之风盛行,作品中的留白便极为普遍了,而其中值得研究者,当首推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松江人。明代“华亭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董其昌作为书画艺术皆通晓的大家,在他的山水画中,天空、地面、云水、山石、树木、亭台桥榭等造型元素,皆可体现其布白艺术处理的手段,“计白当黑”可谓无处不在,达到一个前人未有的高度。本文拟从以下几点来展开探讨。
一、布白成势
势,据《辞源》有“态势、趋势”[2]之意。董其昌于画论中有云:“今人从碎处积为大山,此最是病。古人运大轴,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虽其中细碎处甚多,要之取势为主。”[3]70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造型都简洁,崇尚单纯的形式趣味,尤其是提出“取势”的关键作用。董其昌作品中的布白艺术处理,同样讲究以“势”来形成简洁的形式关系。他的作品,因“势”而生动,尤其着眼于计白当黑,使作品气机流动,浑然一体。下面通过具体作品说明。
如《婉娈草堂图》(图1)中,画面中几道显眼的留白串成一个反写的“S”形(红笔标处),构成画面的暗藏脉络。又如《仿古山水册之一》(图2),画面最上方位置居中一团云的留白如空中皓月,其他小空白犹如众星拱月般错落散布,耐人寻味。再观《秋兴八景图之一》(图3),横亘画面一团云雾,不着一墨,但是在山的衬托下,显得响亮、浑厚,且与画面中隔断近景与中景的水的布白呼应成势。

图1 董其昌 婉娈草堂图111.3cm×68.8cm藏地不详
如果进一步分析董其昌作品中的布白的形势,会发现其往往呈现丰富多样的连绵的“W”形或“Z”形等富于动感的形态,如《婉娈草堂图》《仿古山水册之一》《秋兴八景图之一》《山水图册之一》(图4)、《关山雪霁图》(图5),无不具有一种强烈的、迂回的运动感,使得画面富有董氏独特的形式感,而这与他主张的“势”是密不可分的。

图5 董其昌 关山雪霁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兹以《关山雪霁图》做更为详尽一些的分析。这是他晚年的一幅作品,布白的处理可谓登峰造极了。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面积的这种留白,充满动感,与用墨部分互为作用,忽明忽暗,时强时弱。交替出现的“W”“Z”与“C”等富于动感之形,与长卷形式的画面结合,迂回、曲折地展开,犹如音乐中的变奏曲;同时与画面中笔墨构成的富于变化的点与线等形式互相配合,一虚一实,宛如华丽的交响乐。
董其昌尤其善于“虚实互用”[3]72,往往于物象造型的阴阳两面来施展他布白的手段。如《栖霞寺诗意图》(图6),如果说山之阳面留白是常理,而山之阴面留白则不符合常理。董其昌作品中的山石之阴面和阳面往往皆由留空所形成的“白”贯通,从山脚到山巅、山左到山右,当留则留,当通则通,布白无所拘束。这于前人作品绝无仅有。这种贯通无碍而又迂回反复的留白,在画面中与各种造型元素互相呼应、互相联系,形成气脉相连之势,构成独特的形式美感。显然,在这幅作品中,形式趣味才是画面表现中最重要的,对物象刻画不做遵循常理乃至近乎匠气的描绘。他主张作画要“一超直入如来地”[3]76,而这种别具一格的巧妙布白,是他通往这一境界的不可或缺的要津。可以说,这也是董其昌超越宋元绘画的透脱之处。

图6 董其昌 栖霞寺诗意图(局部)133.1cm×52.5cm上海博物馆藏
二、布白地位升为主角之势
在董其昌之前的山水作品中,画面中的空白部分通常是配角,起辅助的作用,而董其昌则将其提高到具有主角意味的地位。
如《山水图册之一》(图4)及《山水册之一》(图7)中的云,留空不染一墨,但地位显赫、突出、集中,而常常是主角的山石的地位则被弱化。前者,主体山形简单处理成类似符号的“山”形,最为靠前的一组树也仅有半截树干,姿态也处理得简单。相反地,云的形态婀娜多姿,虽不着一墨,却响亮、夺目,构成画面主体的几朵白云犹如在空中追逐嬉戏的精灵,别有情致。

图7 董其昌 山水册之一25.8cm×18.5cm上海博物馆藏
尤其是后者中的云与水,无论面积还是位置都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且形态生动,可见其地位之高,非主角莫属。如果仅仅是停留在看山与树这类实形,则难以品味画中蕴藏的妙处,而当将审美点放在这些空和虚的布白手法处理上,则会豁然开朗,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这种空白的处理,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三、光感之势
如果说阴阳的处理具有中国艺术的特点,那么,董其昌在作品中通过对布白的处理,表现出光感,则是具有突破性的。在《仿古山水图册之一》(图8)、《山水册之四》(图9)中,主体山中的留白,看似云烟,然而更有光的感觉,可以说耀眼夺目。他在画论中提到“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3]100,强调通过对“暗”的处理来表现含蓄和丰富的意蕴,实则这“暗”也绝离不开这白的映衬。反之,这光亮的白,则是通过画面中最黑的“暗”来加以映衬,因而显得特别亮,亮得夺目,亮得有凝聚力,亮得纯粹。黑与白,可谓相反相成,缺一不可,构成浑然一体的整体。布白与布黑(指画面的落墨处)在他的作品中犹如八卦图中的黑白关系一般,是互动互生、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实现高度的统一,构成中国艺术特有的形式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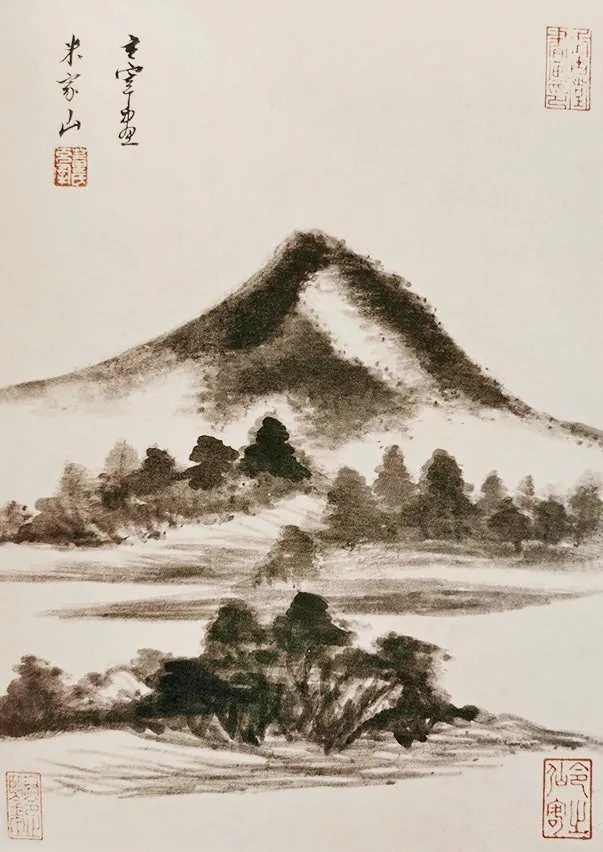
图9 董其昌 山水册之四27.1cm×19.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笔墨中进行光的表现,可以说董其昌探索得相当早,前人似难以有比肩者。当代著名山水画家贾又福先生以“墨明境清、光华照人”[4]42来形容董其昌的艺术,可谓的论。后来的龚贤、黄宾虹、李可染、贾又福等人于此方面不断探索和发扬壮大。可以说,董其昌是用光感进行布白的开拓者。
四、以书入画之势
董其昌以“士人”画为高标,尤重以书入画:“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3]73
他的布白也如书法用笔般充满激荡回旋意味,恍惚可以追寻到草书及篆书的高古气息。其作品中留白而成的云的形状,往往一波三折,有书法般含蓄、圆浑的意蕴。尤其有趣的是,行书作品中重心向右倾斜的董其昌标签式的“势”,在董其昌山水作品的地平线上也往往可见。如《仿古山水图册之一》(图10)中的大面积布白之形也是以极为夸张的势向上倾斜的,这更是颠覆了前人作品中地平线千篇一律水平方向的图式。《仿古山水画合册之一》(图11)中,画面主体山石中留出多道向上倾斜、长短不一的布白之形,有力地将画面的“势”向上引,而溪涧形成曲折的“Z”字形状,富有“欲左先右,欲下先上”之书法笔意,更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向上之势的意蕴。可以说以书入画的理念充分地融入“布白成势”之形式意味中。

图11 董其昌 仿古山水画合册之一26.3cm×25.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以禅喻画之势
董其昌有“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3]72之论,认为笔墨具有超然于真山水之外的独立审美价值,此论明确了笔墨语言在中国画中的本体地位,而作为笔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布白更是成为反映他禅宗思想的绝妙场所,使他的山水画境界进一步迈向空灵通达,直达“心源”。
董其昌主张作画须“一超直入如来地”,推崇禅宗顿悟式的画学理念,“以禅喻画”。而参禅须悟“空”(读音为第一声),禅宗对“空”是有特别要求的。提出画分南北宗的董其昌当知此理,故而他作品中布白而成的“空”,无疑是内蕴丰富的。有意思的是,董其昌别号“思白”,而“虚”和“白”在中国哲学里往往具有特别含义,“虚白”意指空明纯净的心灵境界。《庄子·人间世》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5]之语,体现的是人类对虚空宽广、纯净祥和的心灵宇宙的探求之道。这一“白”字,更具有人生哲学层面的意蕴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董其昌“以禅喻画”的重要内涵,即以画养生之道:“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3]79他认为明代画家仇实父“其术亦近苦”[3]76的画法,不可习,故他的画多追求简化、简淡之美,布白则是通往简而空的禅意境界的必由之径。
董其昌画面中如此大量、集中且具有独特趣味的布白处理手法,为他之前画家作品所未见。不难推断,如果没有他的自觉追求,难以达到如此境界。可见,“布白”对董其昌而言,不是单纯的画面空间的安排了,而是具有独特精神境界的高层面美学追求,融入了艺术家的特殊精神力量。引用布莱克·贝尔的说法,可谓“有意味的形式”。
综上所述,董其昌绘画作品的布白艺术是综合了绘画、书法、审美、哲学乃至宗教学等诸方面因素的,可用“集其大成,自出机轴”[3]74来总结。他的许多作品的布白处理称得上典范,具有承前启后意义。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开拓性的,是有突破的。他的山水画艺术也被后人称为“千古不朽”[4]44。因此,研究董其昌,不得不对他的布白艺术加以重视,否则必定是我们认识董其昌艺术的重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