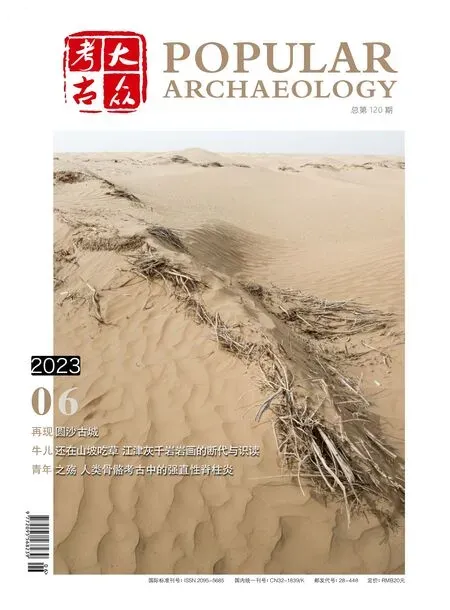南京九峰山路汉墓出土蚩尤持兵带钩
文 图/高浩

九峰山路汉墓出土蚩尤持兵带钩
九 峰山路汉墓位于南京浦口区星甸街道环保产业园内。2020—2022 年,为了配合基建工作,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这一带进行了考古勘探及发掘,清理出201 座古墓葬和2 处遗址,其中汉墓M18 出土一枚铜带钩,钩体铸有一神怪,四肢和嘴分别持有5 种类型兵器(简称神怪持兵),形象刻画复杂,精美细腻。
出土
M18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置一椁一棺,出土有陶器、带钩、铜镜、铜钱、铁剑等,根据随葬品推测该墓具体年代应为新莽—东汉早期。带钩置于棺内,青铜质地,长9.4 厘米,宽3.6厘米,高1.8 厘米,由钩首、钩体及钩钮三部分组成。
钩首呈螭首状,双目无珠,鼻孔微小,折曲延伸至钩体。钩体为神怪正视像,蹲坐姿。头部似熊,两侧有前凸双耳,宽大扁圆。面部天庭饱满,双目凸起圆瞪,鼻头宽大,嘴部龇牙衔戟形饰。头部两侧有鬓发,长至披肩。下身有短尾,穿鱼鳞纹铠甲,四肢手足部执4 种不同类型武器,其中左右手各执盾牌和短剑,左右足各执钺和短刀。钩钮呈圆形,位于钩体北部,钮柱相连,素面,微残。
神怪持兵带钩
类似可考的神怪持兵样式带钩出土较少,从已发表的考古简报、报告以及馆藏中寻找仅寥寥几件,年代均为汉代。这些神怪持兵带钩根据钩首与钩体的相对位置可分为居中型和侧首型。
居中型
1965 年石家庄东岗村东汉晚期砖石墓出土一枚铜带钩,长14.8 厘米,宽5.1 厘米,钩身为神怪图像,手持剑盾,足握刀钺,神人四周铸有四神,但因资料年代久远,仅有拓片,不甚清晰。2008 年辽阳苗圃墓群西汉砖石墓M20出土一枚铜带钩,从大小、图案构造对比来看,应与石家庄东岗村出土一致。这两枚带钩神怪头部非熊形且有角,嘴部未衔武器。2021 年杭州余杭径山古墓葬出土一枚熊形带钩,与M18带钩形象一致。
侧首型
这一类型国内未见出土,见于国外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枚汉代神怪持兵铜带钩,神怪持兵非蹲坐姿,而是呈进攻姿势,巧妙地将神怪手持的盾用作钩首。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也藏有一枚类似汉代铜带钩,镶有绿松石。这两枚带钩神怪并不相同,一为具象的熊形,一为头部有角神怪样式。

石家庄东岗村东汉墓出土带钩

辽阳苗圃墓群西汉砖石墓M20 出土带钩
以上5 枚神怪持兵带钩不论居中型还是侧首型,神怪均持五兵或四兵,武器种类上仅有细微差别,但神怪主体图像存在较大差别,根据其头部是熊耳或角的特征,可将神怪分为熊形和有角形。
汉画像石中多见类似神怪持兵图案,形态各有不同,但同样持五兵,熊形神怪居多(头部多见熊耳)。
神怪持兵形象思辨
对神怪持兵图像识读目前有不同的观点,主流认为是蚩尤形象,部分学者认为是方相氏。
蚩尤说
西周时期祭祀军法,先祭黄帝或蚩尤,《周礼·春官·肆师》曰:“祭表貉,则为位……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秦汉时期,祭祀蚩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其神化为兵主,《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尊蚩尤为八神兵主,并设专门制度祭祀之,“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祝官。四时祭祀蚩尤”。《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起义时在沛县祭蚩尤,“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史记·郊祀志》记载汉朝官方也设祠祭之,“今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蚩尤作五兵,神怪也持五兵或四兵。《世本·作篇》:“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管子·地数篇》:“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又曰:“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 、戟”。《太平御览》卷339 引《周礼》:“五兵者,戈、殳、戟、矛、牟夷。”不同文献对五兵的解释不尽相同,神怪所持兵器种类也与文献记载有所差异。武器或发展或改弃,根据不同时域的需要,神怪所持武器种类、数量有些许差别。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汉代神怪持兵铜带钩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汉代神怪持兵铜带钩

汉画像石中的神怪持兵图案
史料中对蚩尤的造型描述与有角形神怪相像。《太平御览》卷七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述异记》:“蚩尤能作云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从文献上看,蚩尤兽身人语、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的特点,与有角形神怪十分相像。
虽然蚩尤说得到了主流的认可,但却难以解释有的神怪无角且为熊形的特点,这就牵扯出第二种说法。
方相氏说
方相氏,早期傩仪的主体,与葬俗联系紧密,早见于《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这里方相氏是一种祭祀官,大丧时,率领百人作傩仪,用来驱鬼。
方相氏有熊的模样且持兵器。方相氏“掌蒙熊皮……执戈扬盾”不仅见于《周礼》,《后汉书·礼仪志》中也有相同记叙,《东京赋》也有写到“方相秉钺”的特点。
武氏祠汉画像石所描述的内容,有学者将其辨认为方相氏主持傩仪的情形,里面熊形持兵器者为方相氏。
此类观点似乎能很好地解释神怪熊形问题,但存在更大的问题:第一,五兵是受蚩尤影响,方相氏为何持五兵?第二,方相氏在汉代仅为祭祀人物,出现在带钩上神化进程过快,且寓意不明。方相氏作为傩仪的祭祀主导,他蒙熊皮应只是中间概念,所扮演的形象原型才是关键。那么方相氏蒙熊皮的原型是谁?关于此点,陈多先生在《古傩略考》中有考辨,方相氏扮演的应是蚩尤。
如此看来,方相氏说似乎也指向了蚩尤,但存在一个问题,蚩尤有熊的形象么?孙作云先生在《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戏图》一文中有解释傩戏的含义,指出方相氏披熊皮与黄帝有关。自古先族有熊的崇拜,传黄帝氏族便以熊为图腾。《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蚩尤与黄帝有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黄帝与蚩尤为宿敌,不过在最新发表的清华简《五纪》中我们知道了新的关系:“黄帝又子曰寺蚘,既长成人,乃作为五兵。”表明蚩尤是黄帝之子,而熊又是黄帝一族观复博物馆藏图腾,蚩尤可以有熊的特征似乎说通了。

观复博物馆藏汉代熊形龙首金带钩
但需要注意一点,不应将熊笼统看作单一意义的图像,有些熊图像仅是象征意义,没有蚩尤或方相氏一说。汉代不乏此类带钩,如观复博物馆藏汉代熊形龙首金带钩。自古中华民族就有崇熊习俗,熊不能完全等同于黄帝、蚩尤或某个具体人物,《太平御览》引《孝经援神契》:“赤熊见奸佞自远”,《诗·小雅·斯干》也有写道:“维熊维罴,男子之祥”,《山海经·中次九经》有云:“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这些文献将熊看作祥瑞的象征,所以把熊等同于蚩尤还要配合其持五兵的特点来考虑。
国内出土的这4 枚居中型神怪持兵带钩,不论角形还是熊形,应均为蚩尤题材。蚩尤辟兵,盖因蚩尤为兵主,百兵不敢挡之于前,有消灾之意,应是此类蚩尤带钩的寓意。
为什么汉代蚩尤有熊形,也有带角形呢?从出土区域来看,有角形蚩尤带钩出自石家庄和辽阳,而熊形神怪带钩,包括汉画像中的此类图像均在两地以南地区,推测应是蚩尤形象在不同地域上的差异。南梁《述异记》中提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觝”,记载当时冀州流行蚩尤戏,而戏中蚩尤便带牛角,此书虽非汉书,但有一定启示意义,石家庄和辽阳均在或靠近冀州之地。不过目前由于出土资料过少,难以完全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