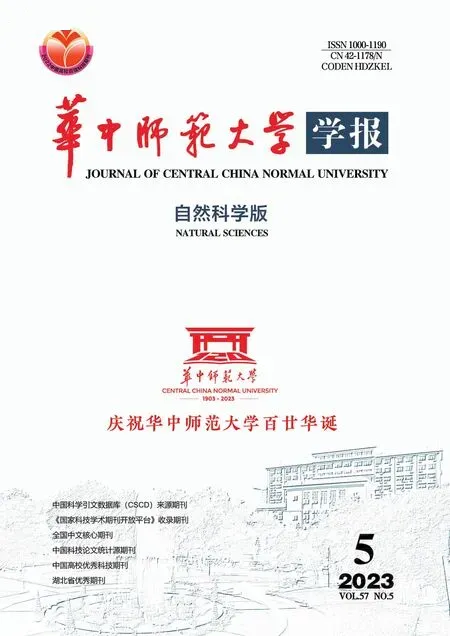江南地区自北宋时期近千年来的疫灾地理研究
王晓伟,龚胜生,张 涛,李孜沫,石国宁,梅佳琪
(1.山东女子学院旅游学院, 济南 250300; 2.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9;3.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32; 4.聊城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疫灾是瘟疫流行所致的灾害[1],对人类社会造成很大影响.江南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文化繁荣.历史时期引发江南地区疫灾流行的传染病较多,如疟疾、痢疾、天花、伤寒、霍乱、鼠疫等[2-6].学界对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的研究,有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的断代研究[7-9],也有从医疗史、生态史、环境史、社会史视角的断代研究[10-15],但长时段的历史医学地理学研究成果不多.鉴于此,本文从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出发,对北宋至清代近千年来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应对重大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决策支持和借鉴.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1.1.1 疫灾史料数据 全部采自龚胜生编著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16].该汇编是迄今为止国内最详备的疫灾资料,整体性较好,以全样本为统计对象能够满足研究需要.从汇编中提取北宋至清代江南地区所有疫灾事件的疫情信息制成“江南地区近千年疫灾数据集”,作为本文疫灾分析的数据基础.
1.1.2 研究区域 江南地区本文是指清代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镇江、江宁(今南京)、杭州、嘉兴、湖州8府、太仓1州之地[17].地形南高北低,北部地势平坦,以平原、丘陵为主,南部有天目山、莫干山等山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域内河湖棋布,有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太湖为全国第三大淡水湖.近千年来,江南地区行政区划变化较大,清末行政区域趋于稳定,为便于比较,以1900年为标准年代,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18]《清代政区沿革综表》[19]绘制江南地区府州及其辖县行政区划图作为空间分析的底图.
1.2 研究方法
本文以“江南地区近千年疫灾数据集”为基础,选取重心法、疫灾强度、近邻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不同研究模型(表1),对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疫灾的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均衡性、空间分布变化等进行探讨.

表1 研究方法与地理意义解释
2 江南地区近千年疫灾的时间变化过程
2.1 年际变化
2.1.1 朝代变化 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包括宋、元、明、清时期,共历时952年.据统计,此间江南地区共有疫灾之年300个,疫灾频度为31.51%,基本上是三年一遇.
宋元时期(960—1367年)战事较多,疫灾多由兵事、旱歉及其引起的饥馑所致.疫灾之年72个,疫灾频度为17.65%.其中,北宋时期疫灾约8.79年一遇,哲宗朝(1086—1100年)、神宗朝(1068—1085年)疫灾频度较高,分别为33.33%、22.22%;除英宗朝(1064—1067年)、钦宗朝(1126年)江南地区未发生疫灾外,太祖朝(960—976年)、真宗朝(998—1022年)、仁宗朝(1023—1063年)疫灾频度最低,分别为5.88%、4.00%、2.44%(图1a).南宋时期疫灾约四年一遇,恭宗朝(1275—1276年)两年都有疫灾发生,疫灾频度为100%;孝宗朝(1163—1189年)、宁宗朝(1195—1224年)各有10年疫灾发生,疫灾频度分别为37.04%、33.33%;度宗朝(1265—1274年)、理宗朝(1225—1264年)、疫灾频度较低,分别为10.00%、7.50%;端宗朝(1277—1278年)无疫灾发生.元朝时期的疫灾约5.9年一遇,文宗朝(1329—1332年)连年有疫灾发生,武宗朝(1308—1311年)有疫灾之年2个,惠宗朝(1333—1367年)有疫灾之年7个,世祖朝(1279—1294年)、仁宗朝(1312—1320年)、英宗朝(1321—1323年)、泰定帝(1324—1328年)江南地区均未见有疫灾发生的记载.
明代时期(1368—1644年)有疫灾之年72个,疫灾频度达25.99%,约3.85年一遇.明代江南地区疫灾主要与水旱灾害有关,疫灾频发期集中在景泰朝(1450—1457年)、崇祯朝(1628—1644年)、正德朝(1506—1521年)、万历朝(1573—1620年)和嘉靖朝(1522—1566年),疫灾频度分别为50.00%、47.06%、43.75%、41.67%和37.78%,万历、嘉靖、崇祯3朝共有45个疫灾之年,占整个明代江南地区疫灾之年的62.50%.其余建文朝(1399—1402年)、洪熙朝(1425年)、天顺朝(1458—1464年)、泰昌朝(1620年)江南地区未见疫灾发生.
清代时期(1645—1911年)江南地区水旱灾害多发,疫灾广泛流行,共有156个疫灾之年,疫灾频度高达58.43%,约1.71年一遇,是明代江南地区疫灾频度的2.25倍(图1b).其中,光绪朝(1875—1908年)、宣统朝(1909—1911年)年年都有疫灾发生,疫灾频度达100%;咸丰朝(1851—1861年)、道光朝(1821—1850年)、雍正朝(1723—1735年)、同治朝(1862—1874年)的疫灾频度也不低,分别达到72.73%、66.67%、61.54%和61.54%,顺治朝(1645—1661年)、康熙朝(1662—1722年)江南地区疫灾相对稀少,但疫灾频度仍然高达41.18%和44.26%.

图1 江南地区近千年疫灾频度的帝纪变化(a)、朝代变化(b)和世纪变化(c)Fig.1 Changes of frequency of epidemics in emperor periods(a), dynasities(b) and centuries(c)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in Jiangnan area
2.1.2 世纪变化 考虑到世纪分布的完整性,选取10~19世纪为研究时段,10世纪上溯至唐代、五代十国时期,涉及2个疫灾年份(944年、954年).在10~19世纪,江南地区疫灾的世纪分布并不均衡,疫灾频度低至6%,高至71%,呈螺旋式波动上升,整个过程可分为2个400 a左右的周期波动,第二波周期波高比第一波周期高,说明江南地区疫灾越来越频繁(图1c).10~12世纪,江南地区疫灾频度逐步上升,12世纪后迅速下降,形成一个长达3世纪的低谷;15世纪以后,疫灾频度又迅速上升.13世纪的“中世纪暖期”,18世纪的“相对温暖期”[25],疫灾频度均处于相对低谷期;15~17世纪全球气候处于“小冰期”,疫灾频度形成高峰期,证实气候寒冷时期疫灾相对多发,气候温暖时期疫灾相对少发.
2.1.3 长期趋势 截取960—1909年时间段计算江南地区的“十年疫灾年数指数”、“十年疫灾县数指数”和“十年疫灾等级指数”,建立10年尺度的疫灾时间序列,然后据以分析其长期趋势.图2是近千年来江南地区疫灾十年指数变化图,如图所示,三种十年疫灾指数都呈波动上升趋势(线性斜率均为正值),多项式趋势线具有非常近似的波动周期规律.

图2 江南地区近千年疫灾长期趋势Fig.2 Long-term changes of the epidemics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in Jiangnan area
2.2 年内变化
2.2.1 季节变化 季节性是疫灾年内变化的季节分量,疫灾作为一种生物灾害季节变化特征明显.统计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中的300个疫灾之年的季节频数,春季102个,占23.29%;夏季148个,占33.79%;秋季135个,占30.82%;冬季53个,占12.10%.由此可见,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在夏、秋季节流行,春季次之,冬季最少.以上疫灾季节频数的统计,无法体现疫灾季节范围的差异,进一步统计江南地区过去千年来历次疫灾波及的范围,发现疫灾累计波及2 615县次,其中春季600县次,占22.94%;夏季1 018县次,占38.93%;秋季828县次,占31.66%;冬季169县次,占6.46%.很显然,夏、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春季次之,冬季最少,同样说明夏秋季节是江南地区疫灾最严重的季节.
2.2.2 月际变化 月际变化也是疫灾年内变化的基本分量,是疫灾季节性的细化体现.统计过去千年来江南地区300个疫灾之年的疫灾月数,总体上无月不有疫灾发生,其中六月(15.51%)、七月(15.33%)、八月(10.84%)疫灾发生最多,累计223次,合占41.68%;十二月(3.36%)、十一月(3.74%)、正月(3.93%)疫灾发生最少,累计59次,合占11.03%,其余月份发生疫灾的频数介于上述月份之间.总体来看,除了夏秋季节诸月份疫灾多发外,季节转换之际的月份疫灾也相对较多,如六、七月为季夏孟秋之交,江南地区气候暑湿炎蒸,利于各种细菌等病原体和蚊虫等疫病媒介的繁殖,疫灾最为频繁;九、十月为季秋、孟冬之交,江南地区天气变化无常,疫灾发生的频率也比较高.
3 江南地区疫灾空间变化过程
3.1 江南地区疫灾空间分布整体特征
3.1.1 空间分布的形态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地理事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距离越近关联越密切.地理学常用近邻指数法来分析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形态.文中采用欧几里得距离定义要素间距离[26],再利用近邻指数(公式(1))计算得到江南地区各县级城市间的平均观测距离(13.55 km)、理论平均距离(16.32 km)和近邻指数R,R=0.83(p<0.01),R<1,说明在县域尺度上,江南地区的疫灾分布为集聚型.
3.1.2 空间分布均衡性 地理集中指数是反映地理事物整体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集中指数(公式2)计算出江南地区疫灾县的地理集中指数G=36.46,高于平均状态下地理集中指数G=33.33,表明在县域尺度上,过去千年来江南地区的疫灾分布较集中.不平衡指数反映不同区域中研究对象分布的均衡程度[27],根据不平衡指数(公式(3))可计算出江南地区县域尺度上疫灾分布的不平衡指数S=0.27>0,说明其疫灾分布是不平衡的,事实上,仅苏州、松江、杭州3府的疫灾县数就占了整个江南地区累计疫灾县次数的51.51%.
3.1.3 空间分布关联性 利用ArcGIS软件中优化的热点分析工具测度各地区局部空间关联性,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江南地区各县疫灾分布分成5级区域,绘制疫灾分布的冷热点图,结果如图3 a所示.不难看出,江南地区疫灾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东西向梯度差异.热点区为太湖腹地的吴县、长洲、元和、太湖厅以及三角洲前缘的上海、华亭、奉贤、南汇、川沙厅等县域,这些地方疫灾频发与太湖水患、滨海风潮、商贾往来、人口丁盛有关.冷点区是苏南的溧水县以及天目山区的安吉、武康、孝丰、临安、昌化、於潜、新城等县,这些地方疫灾稀少,主要是地形崎岖、位置偏僻、人烟较少、交通不便的缘故.
3.2 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区域差异
3.2.1 疫灾的地区差异 区域差异是地理空间格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考虑省级单元区划、人口地形等因素,将江南地区分为苏南区和浙北区,苏南区包括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江宁和镇江6府州;浙北区包括杭州、嘉兴和湖州3府.据统计,过去千年来,苏南区42个疫灾县的疫灾厚度平均为38.90层,相当于在这一千年里被疫灾席卷了近39次;浙北区23个疫灾县的疫灾厚度平均为27.75层,相当于在这一千年里被疫灾席卷了近28次.很显然,苏南区的疫灾比浙北区频繁.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江南地区的疫灾分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各朝代疫灾分布重心的变化,可以观察疫灾空间分布的变化.以县治为县域质心,据重心法(公式(4))计算宋、元、明、清各朝的疫灾重心,结果如图3b所示.图上显示,过去一千年来,江南地区的疫灾分布重心稳定在太湖之中,先向南移,后向北、向东迁移.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重心在太湖东部地区,南宋时期疫灾重心南迁,移至太湖南畔的归安县境内,这是因为,南宋时期行都(杭州)多疫、杭嘉湖一带水旱之余,亦多疫灾.元朝时期,疫灾重心北移至太湖厅的东北境,明代疫灾重心继续北移东迁,清代疫灾重心与明代疫灾重心十分接近,都在太湖东岸的吴县境内[7-8].元明清时期疫灾重心偏向东北迁移,这与太湖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太湖东部的松江府开发相对较晚,元代之前仅华亭1个县级政区,明清两代由于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政区多次析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华亭县分立上海县,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四月分华亭、上海二县地置青浦县,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析华亭县地置娄县,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析华亭县地置奉贤县,析娄县地置金山县,析上海县地置南汇县,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月析上海、南汇二县地置川沙厅;至此,松江府增加到8个县级政区.
3.2.2 疫灾的府域差异 如前所述,江南地区在清代包括8府1州共9个府域单元,其疫灾分布在府域尺度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根据疫灾强度(公式(5))计算各府域的疫灾强度,采用自然断裂点法进行分级,结果如图3 d所示.图上显示,江南地区疫灾强度呈现由东向西北、西南递减的分布特征,松江府疫灾强度(0.89)最高,镇江府(0.27)疫灾强度最低.疫灾强度的这种府域差异,与松江府所辖上海县经常成为疫灾发源地有很大关系.上海县在清代康熙年间设立海关,乾隆、嘉庆朝逐渐成为全国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号称“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鸦片战争后更成为中、西交流的前哨,因而常常成为疫情的发源地,如嘉道之际江南地区的霍乱大流行,上海县就是最先出现疫情的发源地[8].疫灾强度的府域差异还受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江宁府(今南京)长期作为省会城市,人口众多(1820年为525.2万人[28]),且地处交通要冲,人口流动性强,因而疫灾也相当频繁,疫灾强度也较高.其他如杭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府也是如此.
3.2.3 疫灾的海陆差异 以长江、钱塘江入海口的城市连线(常州-杭州连线)将江南地区分为东部滨海区和西部腹地区.滨海区共有41个疫灾县,占全部疫灾县的63.08%,占千年累计疫灾县次的76.59%;与之相比,腹地区共有24个疫灾县,占全部疫灾县的36.92%,占千年累计疫灾县次的23.41%.显然,滨海区疫灾甚于腹地区,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滨海区地处长江三角洲顶部,地势低平、水系密集,水源含盐量高,水质偏碱,适于病原体繁殖,尤其利于霍乱弧菌的生存与繁殖.
4 结论
本文基于历史疫灾史料数据,运用历史疫灾指标和地理模型综合分析了自北宋时期近千年来江南地区疫灾的时空变迁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 过去近千年来,江南地区的疫灾频度为31.51%,基本上是3年一遇.朝代变化上,宋、元、明、清的疫灾越来越频繁;世纪尺度上,疫灾频度螺旋式波动上升,可分为2个400 a左右的波动周期;长期趋势上,三种疫灾十年指数都呈波动上升趋势,反映出疫灾发生的频度越来越高,疫灾危害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2) 过去近千年来,江南地区的疫灾大多在夏、秋季节发生,夏秋季节疫灾波及的范围也最广泛;全年十二个月都可发生疫灾,但季夏、孟秋的夏秋之际,季秋、孟冬的秋冬之际,季节转换之月份疫灾更容易流行.
3) 过去近千年来,江南地区整体的疫灾分布形态为集聚型,苏州、松江、杭州3府疫灾县次数占江南地区疫灾总县次数的51.51%,太湖腹地与三角洲前缘为疫灾热点区,浙西北山地丘陵区为疫灾冷点区.
4) 过去近千年来,江南地区疫灾危害的区域差异明显.在地区差异上,苏南区甚于浙北区,呈北多南少特征,但在朝代尺度上,疫灾分布的重心有由西南向东北迁移的趋势;在府域差异上,疫灾强度总体上是东部大于西部,拥有国际口岸城市上海的松江府疫灾强度最高;在海陆差异上,杭州-常州一线以东的滨海区疫灾频度和强度都远远高于该线以西的腹地区.
5 讨论
以上研究结论,与我们以往研究各历史阶段全国疫灾时空规律所取得的结论是一致的[1,20-21,23],如疫灾越来越频繁,疫灾多发生于夏秋季节,疫灾分布具有空间集聚性,疫灾以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性大的交通沿线地区为重灾区,等等,这些在江南地区都有很好的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过去近千年来,江南地区都是全国经济水平最高、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其实也是全国疫灾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地区.总之,生存环境是疫灾流行的基础,地理环境因子对疫灾流行具有综合作用,地理环境格局和人类活动格局制约着疫灾流行的空间格局.历史观照现实,未来长三角地区将始终处于我国重大疫情防控的最前线,不仅要严格机场、海港口岸的检疫,外防疫情的输入,而且要加强特大城市疫情的精准防控和应急储备,内防疫情的蔓延,切实保障民生.
——入侵植物响应人为扰动的适应性进化方向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