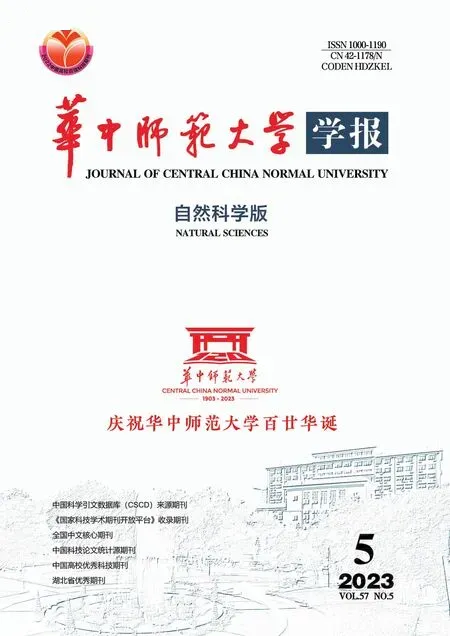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特征及鼠疫流行
龚胜生, 肖永芝, 李孜沫, 张 涛, 谢海超, 石国宁, 陈发虎
(1.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9;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3.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32;4.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5.邯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6;6.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 北京 100101)
最新研究表明,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541年,由查士丁尼瘟疫(541—544年)开始,直到750年,持续2个多世纪.人类基因考古学[1]和现代传染病模型模拟[2]都证明,查士丁尼瘟疫是由腺鼠疫引起的.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时期,在中国处于南北朝(420—589年)后期到隋唐(581—907年)中期,此间中国的瘟疫流行状况如何?有没有鼠疫流行的迹象与可能?如果有,与欧洲鼠疫的流行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假使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只有一个疫源地,考虑到鼠疫在相距遥远的中国与欧洲之间传播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里以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时期为核心,将研究期向前向后延伸,从整个6-8世纪的300年时间来观察.
1 6—8世纪中国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
1.1 6—8世纪中国疫灾的简略年表
根据龚胜生对“疫灾之年”的定义[3]及其《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4]所载6-8世纪的疫灾史料和最新修订,将6-8世纪各疫灾之年的疫灾状况编成简要年表,胪列如次.
(1) 501年.正月,萧衍率军围攻郢州城(今湖北武汉).七月,郢州城破,疾疫流肿,城中男女十万人,死者十七八,积尸比屋皆满.九月,萧衍顺江东下,围攻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十二月,建康城被攻破,城中瘟疫流行.按:造成此次瘟疫的病种系498年南齐与北魏在南阳打仗时,由北魏军队传给南齐军队,进而由南齐军队带到郢州城的,史书称“流肿”,医籍称“虏疮”,后文考证即腺鼠疫.
(2) 502年.春,建康城疫疠流行.
(3) 503年.南梁(主要是都城建康地区)是夏多疫疠.
(4) 504年.南梁(主要是都城建康地区)是岁多疾疫.北魏都城洛阳六月地震,大旱,疾疫.按:501年十二月,萧衍军队将“流肿”从郢州城带入建康城,导致建康城502—504年连续大疫.陶弘景《真诰》卷六描述了这次瘟疫之惨烈:“且顷以来,杀气蔽天,恶烟弥景,邪魔横起,百疾杂臻.或风寒关结,或流肿种痾,不期而祸湊,意外而病生者,比目而来集也.”
(5) 510年.北魏禽昌、襄陵二县(今山西临汾)大疫,自正月至四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6) 515年.夏四月,在钟离郡(今安徽凤阳)修建浮山堰的军民大疾疫,死者相枕.
(7) 529年.六月,南梁都城(即建康)疫甚.
(8) 547年.南梁都城(即建康)旱疫.
(9) 548年.十月,南梁都城(即建康)内已有疾疫流行.十一月,侯景军队来围城.十二月,建康城中粮绝,“稍行肿满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
(10) 549年.三月,侯景攻入建康城.史称:自侯景围攻建业之后,城中多有肿病,死者相继.闭城之日,城中有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余人,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最后剩下不满四千人.
(11) 551年.四月,侯景攻巴陵(今湖南岳阳),久攻不克,五月,军中疾疫,死者大半.按:548年以来的瘟疫流行都与侯景军队有关,“肿病”之疾(即腺鼠疫)一直驻存于其军士之中,军队行进到哪里,肿病就流行到哪里,因而死亡率甚高,“死者大半”甚至“死者什八九”.
(12) 563年.二月,北周境内(主要是关中地区)风雨僭时,疾疠屡起.
(13) 565年.是岁,河南大疫,死者十四五.
(14) 566年.二月,南陈疹患淹时,亢阳累月,大赦天下.按:561—562年中国西北连年大旱,随后引发大疫.563年,瘟疫在今陕西、甘肃的北周境内流行,周武帝在都城长安(今西安)下诏罪己.565年,瘟疫向东传到北齐境内,导致河南大疫,死者十四五.566年,瘟疫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下游的南陈境内,陈文帝在都城建康(今南京)下诏罪己.导致这次疫灾的病种为“疹患”,皮肤出疹是许多疫病的表征,如天花、伤寒、鼠疫等,但从瘟疫起于西北大旱之背景看,这里可能是指鼠疫.清代余师愚《疫疹一得》中的“疫疹”就是指腺鼠疫,甚至直到晚清民国,仍有以“疹”特指腺鼠疫的.
(15) 573年.十月,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发生围城战争,“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什六七”.
(16) 574年.四月,战争胁迫下,朐山、黄郭一带饥馑疾疫.
(17) 583年.四月,隋军北伐突厥,突厥士兵“饥不得食,又多灾疫,死者极众”,或曰“饥疫死亡,人畜过半”.
(18) 589年.岷州(今甘肃岷县)疫.
(19) 592年.都城长安疾疫.
(20) 598年.二月,隋朝集结30万大军挥师高丽.六月,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次辽水,军队“大遭疾疫”.至九月撤军时,军士“死者十八九”.
(21) 610年.二月,隋攻流求(今台湾岛),“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
(22) 612年.正月,隋朝集结一百一十三万大军进军高丽,七月大败而归,“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史称“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23) 614年.隋第三次征讨高丽,军中“复多疾疫,自黄龙以东,骸骨相属,止泊之处,军人皆积尸以御风雨,死者十八九”.按:598—614年间,隋朝军队的大疫均与军事行动有关,其瘟疫或是之前从突厥军队传入,以“死者十八九”的死亡率来看,或是腺鼠疫流行.
(24) 617年.九月,关中疠疫,死人如积,不可胜计.
(25) 618年.关中骨蒸病大流行.按:据《旧唐书》卷191《许胤宗传》和《新唐书》卷204《许胤宗传》载,骨蒸病“递相传染” “得之必死”“得者皆死”.医史学家认为,“骨蒸病”即今之肺结核,但死亡率如此之高,不排除是具有“结核”表征(淋巴结肿大)的腺鼠疫.
(26) 621年.二月,秦王李世民围王世充于洛阳宫城中,至三月,城中乏食,民病身肿脚弱,死者十之八九.围城之初,洛阳宫城之民凡三万家,疫后死剩不足三千家.按:此次瘟疫表征为“身肿脚弱”,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应该是被称为“流肿”或“风毒脚气”的腺鼠疫所致.
(27) 627年.九月,大兵之余,疫疠方作.十二月,西突厥地区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疫,长城之南,暴骨如丘.
(28) 629年.正月,长安城疾疫.
(29) 636年.关内、河东大疫.
(30) 641年.三月,泽州疫.
(31) 642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
(32) 643年.夏,泽、濠、庐三州大疫.
(33) 644年.庐、濠、巴、普、郴五州疫.
(34) 648年.九月,邠州大疫,诏医疗之.
(35) 653年.“虏疮”从西域东流,遍于海中.按:627—636年大疫的源自突厥,是导致其“暴骨如丘”的腺鼠疫,其中653年“从西域东流,遍于海中”的瘟疫明确是“虏疮”(腺鼠疫)流行.
(36) 655年.三月,楚州大疫.
(37) 681年.三月,突厥阿史那伏念部士卒多疾疫.
(38) 682年.关中三月旱蝗,四月饥馑,六月疾疫,自陕(今三门峡市)至洛(今洛阳市),死者不可胜数.冬十月,长安地震,人相食,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按:681年唐朝出兵反击突厥,突厥部队因疾疫流行引发内讧,其首领被押送至唐都长安城处死,瘟疫也随之带入长安,导致682年长安和洛阳两京之间的瘟疫大流行.
(39) 707年.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旱,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按:唐中宗在位(705—710年)的六年间,“水旱不调,疾疫屡起”,“自剑南尽河、陇,山东由青、徐、曹、汴,河北举沧、瀛、赵、鄚,或困水旱,或顿兵疫,死亡流离略尽”,是年是瘟疫流行最猛烈的一年.
(40) 711年.京师疫疠相仍.
(41) 751年.四月,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兵八万讨伐南诏国,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结果大败,士卒瘴疫,死者六万人.
(42) 754年.六月,七万唐军攻南诏太和城(今大理),结果“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死者十八”,“涉海,瘴死者相属于路……死者十八九”.按:751年和754年唐朝两次发兵攻打南诏,战争均由外戚杨国忠发动,史称其在751年鲜于仲通大败之后“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或曰:“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用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两次战争失败,均与“瘴疫”有关,每次瘟疫死亡,都在六万人左右.云南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和恶性疟疾流行地,这里的“瘴疫”除恶性疟疾外,也不排除腺鼠疫的发生.
(43) 762年.秋大疫,流行范围极广,北自淮沂,达于海隅.其中,江东大疫,死者过半.三吴尤甚,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浙江杭、越间疫疾颇甚,户有死绝,十月,唐代宗令州县瘗民疫死不能葬者.按:医史学家麦格劳(Roderick E. McGraw)据此认为中国的腺鼠疫是8世纪从地中海由海道传入的,并称762年中国沿海省份流行剧重的高死亡率的腺鼠疫[5].
(44) 783年.洛阳大乱,谷贵大疫.
(45) 784年.四月,吐蕃军在武功(今陕西武功)一带大疫.十月,疫疠荐至,水旱相乘.
(46) 787年.三月,吐蕃军队春疫大兴,羊马多死,人马疾疫.
(47) 790年.夏,淮南、浙东、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人暍且疫,死者甚众.
(48) 799年.夏,吐蕃麦不熟,疫疠仍兴.
1.2 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间特征
根据上述疫灾简略年表,将6-8世纪各次疫灾发生的年份、季节和疫灾等级制成表1,表中疫灾等级的划分着眼于中国三千年疫灾流行的整体情况,主要根据疫灾流行县数和死亡人数分为7个等级,其中Ⅳ级以上疫灾统称为“大瘟疫”,6-8世纪大瘟疫之年17个,占48个疫灾之年总数的35.42%(表2).概括起来,6-8世纪中国疫灾流行的时间变化特征有以下三点.

表1 中国6-8世纪疫灾发生的年份、季节及其等级

表2 中国三千年疫灾严重程度的等级划分
1) 疫灾主要在春夏季节流行.季节性是瘟疫流行的最主要的特征.6—8世纪,中国疫灾发生在春季的12次,夏季的14次,秋季的5次,冬季的6次,全年都有流行或者季节不详的11次,总体而言,疫灾多在春、夏季节流行,但“大瘟疫”多发生于夏、秋、冬三季.据研究,中国北方腺鼠疫主要在秋冬季流行,南方地区腺鼠疫主要在春夏季流行[6],6—8世纪中国疫灾流行的这些季节特点,可能与当时有较多鼠疫发生有关系.
2) 疫灾流行频度总体趋于下降.从整个中国三千年疫灾史看,6-8世纪处于魏晋南北朝疫灾高峰期的后期和唐代疫灾低谷期的前期,总体上属于疫灾偏少的时期,3个世纪里只有48个疫灾之年,其中6世纪20个,7世纪18个,8世纪10个,在世纪尺度上,疫灾频度总体趋于下降.在十年尺度上,无论是疫灾频数指数还是疫灾等级指数,波动特征十分明显,其中7世纪10年代和40年代的疫灾频度最高,8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疫灾频度最低,六阶多项式趋势线呈“W”型波动,线性趋势线下降特征明显(图1).

注:虚直线为线性趋势线,虚曲线为六阶多项式趋势线,细实线为10年指数波动线,粗线为50年滑动平均线.图1 中国6-8世纪疫灾十年指数的变化Fig.1 Changes of the decade epidemic index in China from the 6th to 8th century
3)疫灾流行具有显著的周期性.中国三千年疫灾变化具有多种波动周期[3],6—8世纪是其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时期,对其十年疫灾频度指数和疫灾等级指数序列分别进行小波分析,发现十年疫灾频度指数存在280 a、100 a、50 a三个波动周期,十年疫灾等级指数存在210 a、280 a、100 a、50 a四个波动周期,二者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且接近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11.2 a)的倍数,说明疫灾流行的周期性可能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性有关,这一特点与整个历史时期长时段的疫灾流行规律相一致[3,7].
1.3 6—8世纪中国疫灾的空间特征
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其间的疫灾也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中原区域,以及与中亚相通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图2).概括起来,6—8世纪中国疫灾流行的空间特征有以下三点.
1) 京畿地区疫灾频繁,疫灾多发区随都城变迁而迁移.6—8世纪中国的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先后有建康(今南京)、长安(今西安)、洛阳等几处重要都城,这些城市作为都城时,其周边地区无一不是疫灾的多发区.这是因为,都城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人烟辐辏,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而且也是割据战争、农民战争、甚至民族战争的攻伐攘夺之地,一旦发生战争和灾荒,都城还是难民、灾民、流民麇集之地,故而疫灾极易流行.例如,建康(今南京)作为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是当时中国南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也是6—8世纪中国南方地区疫灾最频繁的地区;长安(今西安)、洛阳作为北朝时期的都城,特别是大一统王朝隋、唐时期的都城,是当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疫灾尤为多发,以致从长安到洛阳之间的地区,成为6—8世纪疫灾之年最密集的地区.
2) 疫灾地域空前扩展,西部边疆地区的疫灾显著增多.与之前的魏晋时期相比,6—8世纪的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境内的疫灾流行的频度并不十分频繁,但疫灾分布范围却大大扩展,远迈前朝.图2显示,西自西域、突厥、吐蕃、大理,中连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关中平原、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东北至辽东,东南至流求(今台湾),均有过疫灾的流行.6—8世纪疫灾地域之所以空前扩展,原因有二:一是开拓边疆的战争.如隋朝征流求(今台湾)、高丽(今朝鲜半岛)、突厥(今蒙古高原中西部以西迄中亚一带),唐朝征南诏(今云南)、吐蕃(今青藏高原)、突厥(今蒙古高原以西迄中亚一带),据统计,6—8世纪总共48个疫灾之年中,至少有11个是由隋唐王朝与吐蕃、南诏、突厥、高丽、流求等的战争所致.二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中亚联系的加强.自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西域、中亚与中国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隋唐一统之后,丝绸之路更是得以畅通,西域、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背景下,作为贸易通道的丝绸之路也就成为了疫病传播的通道,如653年,号称“虏疮”的鼠疫“从西域东流,遍于海中”.研究表明,中亚地区和中国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北部、云南高原西部都存在有鼠疫自然疫源地,在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与中亚地区持续的贸易往来,诱发和传播鼠疫的风险是极大的.

注:基于审图号为GS(2019)1822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2 6-8世纪中国的疫灾和鼠疫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epidemics and plagues in China from the 6th to 8th century
3) 疫灾分布格局巨变,开启南方疫灾重于北方的千年转换.以现代县级政区为单元计算6—8世
纪中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发生疫灾的县数之比,6—8世纪为1.26(324/256),其中6世纪为2.50(55/22),7世纪为6.24(337/54),8世纪为0.51(144/282),也就是说,6—8世纪中国的疫灾总体是北方重于南方,但8世纪以后,南方疫灾重于北方.这种转换,是千年的巨变,因为自此之后,中国的疫灾重心就一直分布在南方地区了.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对疫灾分布具有基础性影响,是疫灾流行的“启动器”.人口流动是疫病流行的主要传播途径,也是疫灾流行的“加速器”,历史上的疫灾蔓延基本上都是通过人口流动来实现的[3],因此,人口分布是疫灾分布的牵引器,人口格局的转变必然导致疫灾格局的转变.8世纪后期,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由盛而衰,中国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迁移,受其牵引,疫灾重心也由北方迁移到了南方.
2 6—8世纪中国腺鼠疫流行的可能性
鼠疫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鼠疫菌早在5 000万年以前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成[8].欧洲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鼠疫流行,中国何时出现鼠疫,学术界有不同看法.20世纪40年代,医史学家陈方之(1884—1969年)认为,东汉末公元217年发生的“大疫”十分惨烈,曹植《说疫气》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是“我国鼠疫纪录之嚆矢”[9].现代医史学家冼维逊采信之,并据此认为《后汉书》记载的东汉时期的其他十次大疫也很可能是鼠疫[5].最近,中医史家符友丰更是认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黄帝内经》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鼠疫的流行,甚至中医所谓的“医源于疫”,这里的疫指的就是鼠疫[10],8世纪以前的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肘后方》《诸病源候总论》《千金要方》,等等,都有鼠疫的记载,它们记载的“热病”“恶核”“流肿”“阴阳毒”“风毒脚气”,等等,都是对鼠疫的描述[11].这些观点,也许有些偏颇,但中国很早就有鼠疫流行,应该是可以采信的,因为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杆菌一旦在合适的生境建立地方性,鼠疫自然疫源地就十分稳固地存在,只要人类在自然疫源地区域的活动达到某种程度,就有可能引发鼠疫的流行.现代研究表明,中国南方、北方存在10类鼠疫自然疫源地[12],它们应该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因此,中国早在雅典大瘟疫时期(前430—前427年)就已有鼠疫流行,应该是可信的,更不用说在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541—750年)发生过鼠疫.
2.1 中国在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的鼠类异常活动
人间鼠疫发生前,一般都有鼠间鼠疫发生,或有老鼠的异常活动.6-8世纪中国有多次老鼠异常活动,有的疑似就是鼠疫的发生.
1) “鼠为灾”.508年八月,甘肃泾川县一带“黄鼠为灾”(《魏书》卷112《灵征志》).526年,陕西宝鸡邻近地区“田鼠为灾”(《北齐书》卷23《魏蘭根传》).“鼠为灾”,是指老鼠给人类造成的灾害.老鼠造成的灾害,无外乎二:一是损毁庄稼,二是引发鼠疫.如果只是损毁庄稼,史书一般会称“鼠害稼”,但是,这两年明确记载是“鼠为灾”,极有可能是黄鼠和田鼠引发了人间鼠疫.甘肃泾州和陕西宝鸡位于关中平原西北部,不仅是中国通往中亚的必经之地,而且是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区域,在这里发生鼠疫是十分可能的.
2) “鼠害稼”.639年,福建建瓯“鼠害稼”.647年,重庆城区一带“鼠害稼”(《新唐书》卷34《五行志》),奉节一带“旱,鼠害秋稼”,四川省渠县一带“蝗,鼠害秋稼”.648年,四川宜宾一带“鼠伤稼”(《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707年,陕西延川一带“鼠害稼”.714年,广东韶关一带“鼠害稼,千万为群”(《新唐书》卷34《五行志》)等.四川、重庆不是自然疫源地区域,发生在那里的“鼠害稼”事件可能不会引发鼠疫,但发生在陕西、广东、福建的“鼠害稼”事件,都有可能引发过鼠疫,因为这些地方都有鼠疫自然疫源地存在.
3) “鼠渡江”.据观察,人间鼠疫发生之前,一般都有鼠间鼠疫的发生,而鼠间鼠疫发生时,因为高热烦渴,老鼠大都死于河流和池塘的水边.明末崇祯年间鼠疫大流行期间,黄土高原的宁夏、陕西、甘肃都有老鼠的异常活动,而长江中游的湖北、下游的江苏,都有老鼠渡江事件的发生.如1639年,湖北黄州“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绝”,1642年,“群鼠渡江,昼夜不绝”(《绥寇纪略》卷12《物异》).这样的事件在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也发生过,如588年四月,“有群鼠无数,自蔡洲岸入石头渡淮,至于青塘两岸,数日自死,随流出江”(《南史》卷10《陈本纪下》).这次老鼠的异常活动,与鼠间鼠疫极为相似.长三角地区现在不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地区,但在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的明朝末年,这里是有过大范围鼠疫流行的.
4) “掘鼠食”.528年,农民军领袖葛荣(鲜卑人)被北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打败被杀,其部众流入并州(治今太原)、肆州(治今忻州)者二十余万人,号称“降户”.此后直到530年,“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北齐书》卷1《帝纪一》).黄鼠是黄土高原鼠疫传播的介体,山西北部也是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明朝末年中国的鼠疫大流行就始于其附近的长治.还有,548年十月至549年三月,围攻建康城(今南京)的侯景军队因为粮食匮乏,“军士熏鼠捕鸽而食,数月之后,殿鼠鸽皆尽”(《封氏闻见记》卷7《蜀无兔鸽》).此次捕鼠而食之后,该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不过,建康城之大疫,可能与侯景军队熏鼠而食关系不大,而是与“虏疮”或“流肿”一直存在其鲜卑兵士中有关.
2.2 中国在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对腺鼠疫症状的描述
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已经证实是腺鼠疫大流行,中国历史文献很少记载染疫者的临床表现,但也留下了这个时期腺鼠疫流行的蛛丝马迹,当时记载的“恶核”“虏疮”“流肿”“疹疫”“暍疫”“瘴疫”,甚至“骨蒸”“苦头痛”都有部分可能包括鼠疫在内.
1) 恶核病.首次指出中医典籍中的“恶核病”就是腺鼠疫的人是鼠疫专家伍连德(1879—1960),后此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据日本人丹波康赖(912—995年)《医心方》(卷16《肿物部•治恶核肿方第九》)称,东汉医家张仲景(约150—约219年)所著医方(《张仲景方》)中有“治消核肿”的“黄耆贴方”[13],并将其与治疗恶核病的药方放到一起,但“核肿”是否就是“恶核病”,有待考证.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最早记述恶核病的医著是东晋葛洪(约283—约363年)的《肘后救卒方》(又名《葛氏方》,成书于306—317年间[14]),后南朝陶弘景(456—536年)修订《肘后救卒方》,于500年(庚辰年)撰成《肘后百一方》(简称《肘后方》),至于金代,杨用道增修《肘后方》(1101—1110年),又揉入北宋唐慎微(1056—1093年)《证类本草》(1082年成书)的有关内容,名曰《附广肘后方》,但到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始刻印流传.今本《肘后备急方》为明代嘉靖中襄阳知府吕颙所刻,该刻本中“凡杨氏所增皆别题‘附方’二字列之于后,而葛、陶二家之方则不加分析,无可辨别”(四库全书《肘后备急方提要》).其实,吕颙所刻《肘后备急方》还揉入了唐代张文仲(620—700年)所著《随身备急方》的有关内容,正因为如此《肘后方》才有了《肘后备急方》之名.因此,今本《肘后备急方》中的文字未必都是葛洪《肘后救卒方》的原文,不过其中有关“恶核”的记载,医史学者认为都是葛洪的原文,其方有“若恶核肿结不肯散者”,“疗恶肉、恶脉、恶核、瘰疬、风结肿、气痛”,“疗恶肉、恶核、瘰疬、风结诸脉肿”,“疗时行温疫、诸脚气、毒恶核、金疮等”,其被指为是腺鼠疫描述的为如下文字:“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如梅李,小者如豆粒,皮中惨痛,左右走身中,壮热,恶寒是也.此病卒然如起,有毒入腹,杀人.南方多有此患.”(卷5《治痈疽妬乳诸肿毒方》)这段文字描述了“恶核病”之三大表征:一是恶核大小如梅李核或豆粒;二是恶核长在皮下,可以游动;三是发病急猝,疼痛异常,高热恶寒.这三个表征与腺鼠疫淋巴结肿大的特征十分一致.关于恶核病的分布,葛洪说是“南方多有此患”.葛洪是句容人(今江苏句容),后隐居罗浮山(今广东博罗),其言“南方”应该是葛洪家乡以南的岭南地区.岭南地区分布着鼠疫自然疫源地,世界第二次、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腺鼠疫在中国的流行就被称为“核瘟”或“核疫”.据此,中国至迟在4世纪初就已有了腺鼠疫流行的记载.
东晋葛洪之后,南朝刘涓子、陈延之、僧深等也记载了恶核病,说明腺鼠疫已是南朝时期常见的疾病了.刘涓子(约370—450年)是东晋、刘宋间京口(今江苏镇江)人,他在东晋义熙六年(410年)随刘裕北征,专治被创者,并于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撰成《鬼遗方》(又名《痈疽方》),南齐永元元年(499年)经龚庆宣重编后,得名《刘涓子鬼遗方》,书中载有“治恶核肿毒汤方”[13],可惜原书已佚一半,未见恶核病症描述.陈延之是刘宋、萧齐间人,生卒不详,著有《经品小方》(简称《小品方》),其书成书于454—473年间,其云:“有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累如梅李核状,小者如豆粒,皮肉中瘆痛,左右走人身中,壮热,畏寒是也,与诸疮痕(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痕(根)瘰疬,要因疮而生,是缓疾,无毒;其恶核病,卒然而起,有毒,不治,入腹烦闷则杀人.南方多有此疾,皆是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冷相搏,气结成此毒也.”这段文字与《肘后方》所言颇相似,或即采自《肘后方》,但又有进一步阐发,一是将恶核与疮根瘰疬加以区分,二是阐释了恶核的病因和流行季节.南方地区恶核病主要在春夏季节流行,这与近现代观察到的南方地区鼠疫流行的时间一致.僧深为“宋、齐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太平御揽》卷724),著有《僧深药方》,亦称《僧深集方》,简称《僧深方》《深师方》.据考证,僧深实为梁、陈、隋三朝人,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扬州一带,其《僧深方》成书于540—610年间[15],其云:“凡得恶肿皆暴卒,初始大如半梅桃,或有核或无核,或痛或不痛,其长甚速,须臾如鸡鸭[子]大,即不(不即)治之,肿热为进,烦闷拘挛,肿毒内侵,填塞血气,气息不通,再宿便杀人.”[13]这里的“恶肿”中之有核者即恶核病,其核初起时约半个梅桃大,不久就会长到鸡鸭蛋大,核肿与发烧不断加重,一两天就会死人,其症状与腺鼠疫颇相符合.
至于隋朝,巢元方(550—630年)对“恶核病”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巢元方在隋大业中任太医令,奉诏于610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该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大成之著,今称《诸病源候论》,简称《病源论》,其云:“恶核者,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桃李,小(有)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人)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测测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也).”又云:“恶核者,是风热毒气与血气相搏结成,核生颈边,又遇风寒所折,遂不消不溃,名为恶核也.”(《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31《恶核肿候》)上述病症,与《肘后方》《小品方》的描述基本一致,恶核的“卒然而起”,“生颈边”,能“左右走人身中”,患者“烦闷恶寒”,这些都是腺鼠疫的典型症状.
唐朝以后,人们对于恶核病就不再陌生.如甄立言(545—约638年)《古今录验方》(简称《录验方》)载有“治恶核肿毒入腹五香汤方”[13].孙思邈(约581—682年)《备急千金要方》载:“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累如梅李核,小者如豆粒,皮肉瘆痛,壮热索恶寒是也,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是缓无毒.恶核病卒然而起,有毒,若不治入腹,烦闷则杀人.皆由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凡恶核初似被射工毒,无常定处,多恻恻然痛,或时不痛.人不痛者便不忧,不忧则救迟,迟治即杀人,是以宜早防之……其疾初如粟米,或似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疱,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臾即短气……恶核……多起岭表,中土鲜有.”[16]其《千金翼方》也有类似的记载,不再赘引.上述描述,与《肘后方》《小品方》《病源论》等一脉相承,但亦略有发展,一是恶核病有隐然不痛者,容易被人忽视,一旦发病后再治就来不及了;二是恶核病主要在“岭表”流行,明确《肘后方》等所指“南方”特指岭南地区.
2) 虏疮.“虏疮”也有腺鼠疫之症状,其名始见于5世纪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东晋葛洪《肘后卒救方》不仅首次记载了被视为腺鼠疫的“恶核病”,而且也首次记载了被视为天花病的“斑疮”,其曰:“比岁有病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剧者数日必死,此恶毒之气也”[17].这里的“比岁”,是葛洪撰《肘后卒救方》的附近几年,即306—317年间.这段文字被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天花流行记载.今本《肘后备急方》对“斑疮”的记载文字如下:“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乃)呼为虏疮” (卷2《治伤寒时期温病方》).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已非葛洪原文,大体而言,“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云云,为陶弘景增补文字,其所云“仍发疮”乃是对比葛洪原文而言,其所云“仍呼为虏疮”乃是“乃呼为虏疮”之讹,其所谓“比岁”乃是500年陶弘景撰成《肘后百一方》的近岁.而“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一句,乃是张文仲《随身备急方》中的文字,王焘《外台秘要》引其原文为:“永徽四年,此疮从西域东流于海内,但煮葵菜、蒜齑啖之则止,鲜羊血如口亦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很显然,陶弘景所言“虏疮”与葛洪所言“斑疮”病症虽然相似,但其实不是同一种病,“虏疮”更可能是腺鼠疫.“白浆”的皮肤症状一般认为是天花患者特有,其实不然,腺鼠疫患者也有这样的皮肤症状.如第二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期间,清代桂馥(1736—1805年)先后在云南永平、邓川、顺宁(今凤庆)诸县为官九年(1796—1805年),他在邓川县见到的腺鼠疫患者的症状是“其疾皮肤起泡,割之有白浆,或成羊毛”(《札朴》卷10《滇游续笔》).更有论者,在中国历史语境里,“虏”一般指西北方的游牧部落,如汉代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等.“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是指建武年间(494—498年)南齐军队在河南南阳一带抵御北魏军队侵略的事件.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被自称继承正统的南齐称为“魏虏”(《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虏疮”一词,陶弘景在这里其实隐约地告诉我们,腺鼠疫是从北方草原民族鲜卑族输入中原的.497年,北魏侵占南齐南阳地区;498年,北魏十万骑兵突袭襄阳城,南齐军队大败.正是在这次战争中,北魏军队把“虏疮”传染给南齐军队,又由南齐军士带到郢州(今武汉)、建康(今南京)等城市,导致501—504年南齐境内的大瘟疫.至于隋唐时期,中国人称突厥人为“虏”,与突厥人活动有关的大疫,都可能是腺鼠疫流行.583年,突厥军队与隋朝军队在蒙古草原交战,突厥大疫而败,此次大疫人畜共患,死亡率在50%以上,鼠疫的可能性很大.不但如此,突厥军队可能还将鼠疫传染给了隋朝军队,以致此后隋军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伴随着大疫发生,死亡率之高,唯鼠疫可当.如,598年隋军征讨高丽,30万军士疾疫“死者十八九”;612年隋军再征高丽,30.5万军士因疾疫死剩2 700人,军士撤回关内又引起山东、河南大疫,导致“死者数十万”.627年冬,突厥地区大疫,大疫传入中国内地,629—653年间,黄河流域有多次大疫发生.681年,突厥再次与唐朝交战,大败,首领被押送长安处死,结果又引发682—711年陕西、河南地区大疫.这些大疫,都可能是腺鼠疫流行.
3) 流肿.“流肿”之名,始见于西汉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的《春秋繁露》卷13《五行逆顺》.其后,魏晋南北朝多有“流肿”记载.231年,吴国孙权欲亲征辽东“乐浪公”,因为海上远征,“善生流肿,转相污染,凡行海者稀无此患”而作罢(《三国志•吴志》卷8《薛综传》).253年,吴国军队围攻魏国的新城(今安徽合肥),城中魏军和城外吴军“泄下流肿”,“死者大半”(《宋书》卷34《五行志》).“流肿”是什么病?中医史家符友丰认为就是腺鼠疫[11].如前所述,498年北魏军队将“虏疮”传给萧衍军队,501年萧衍军队将“虏疮”带到郢州城(今武汉).同一个疫病,医著称“虏疮”,而正史称“流肿”,《南史》记载该年郢州城的大疫时说:“郢城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南史》卷6《梁本纪》).顾名思义,“流”是流动的意思,“肿”是肿块的意思,“流肿”就是可游动的肿块,即“左右走身中”的“恶核病”,从“死者十七八”的描述看,也与腺鼠疫70%以上的死亡率相符,因此,“流肿”也是腺鼠疫的一种称谓.可以肯定,中国501—504年的大瘟疫就是腺鼠疫流行,较欧洲查士丁尼大鼠疫的发生早约40年.之后,在第一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期间,中国还有多次大疫由“流肿”引起,如“侯景之乱”期间(547—551年)的大疫.侯景(503—552年)原是北魏后裔,鲜卑人,一说是羯族人,曾跟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镇压葛荣农民军,此后,“流肿”之病就一直驻存在侯景的军队中,其军队流动到哪里,“流肿”就流行到哪里,如548—549年侯景军队在建康(今南京)时发生的大疫,551年侯景军队在巴陵(今岳阳)时发生的大疫,有“肿满”“肿病”“身肿气急”“羸喘”之症,这些都是腺鼠疫的典型呼吸系统症状,而“死者大半”“死者什八九”的高死亡率,与腺鼠疫的死亡率也相符合.侯景之乱后,573年发生在安徽寿县城中的疫疠也以“肿”为主要特征,“死者十六七”,腺鼠疫特征也很明显.
至于隋唐时期,“流肿”已成为医书必载疾病.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成书于610年)多处载有“流肿”病.关于流肿形成的原因,其曰:“人阴阳俱虚,湿毒气与风热相搏则荣卫涩,荣卫涩则血气不散,血气不散则邪热致雍(臃),随其经络所生而流肿也”(卷8《伤寒毒•流肿候》).关于流肿的类型,其曰:“流肿凡有两候,有热有冷.冷肿者,其痛隐隐然,沉身着臂膊,在背上则肿起,凭凭然而急痛,若手按及针灸之即肿起是也;热肿者,四肢热如火炙之状,移无常处,或如手或如盘着背腹是,剧则背热如火,遍身熠熠然,五心烦热,唇口干燥,如注之状.此皆风邪搏血气所生,以其移无常处,故谓流肿”(卷31《肿病诸候•流肿候》).其中的“热肿”,颇似腺鼠疫的症状.唐代成书于652年的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成书于752年的王焘的《外台秘要方》都记载有多个治疗“流肿”的药方.史志对战争中发生的流肿也多所记载,成书于718—726年间的《唐开元占经》就有“枉矢黑,军士不用,疾流肿”的星占(《唐开元占经》卷86《枉矢》).敦煌出土的唐代《发病书》也有“病者连流肿而脚寒热”[18]的记载.621年春,洛阳城大疫流行,“死者十之八九”,其病症也是“身肿脚弱”.可见隋唐时期腺鼠疫的流行也不少,不过同样主要是在军队中流行.
4) 暍疫.“暍”,一般认为是中暑,《黄帝内经》多所记载.从《医心方》所引《葛氏方》《小品方》《病源论》《千金方》来看,“暍”病确实主要是指高温中暑,如《病源论》曰:“夏月炎热,人冒涉途路,热毒入内,与五脏相并,客邪炽盛,郁瘀不宣散,至阴气卒绝,阳气暴壅,经络不通,故奄然闷绝,谓之暍也.”[13]不过,据中医史家符友丰考证,张仲景《伤寒论》(成书于129年)所记载的“湿热病”和“暍病”都是鼠疫,暍就是指鼠疫的发热现象.790年夏,淮南、浙东、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竭,人暍且疫”,“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显然,这里的“暍”具有传染性,导致死者甚众,非一般中暑可比.我们认为,这次大范围的暍疫,很可能也是鼠疫流行.据南梁顾野王(519—581)《玉篇》(成书于543年)解释,“暍”就是“中热”,与“流肿”患者五心烦热、唇口干燥、烦渴多饮的腺鼠疫症状一样.如前所述,鼠间鼠疫发生时,疫鼠因为热渴难耐,大都死于水滨.
5) 其他.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瘴”主要是指恶性疟疾,但“瘴疠”“瘴疫”有时也可能指鼠疫.6-8世纪,有两次大疫的病症被描述为“瘴疠”:一次是610年隋朝军队发兵台湾时遇到的大疫,当时2万兵士,在台湾“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一次是754年,唐朝军队攻打云南时遇到的大疫,当时7万兵士,在大理城“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台湾和云南地处亚热带或热带,为恶性疟疾流行区,但云南分布着鼠疫自然疫源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鼠疫记载的地方,台湾在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也经常有鼠疫发生,从死亡率高达70%~90%来看,这两次疫灾也有可能是鼠疫流行,因为恶性疟疾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还有“苦头痛”,这里的“苦”做“病”解,即头痛病.敦煌、吐鲁番发掘的唐代《发病书》记载了唐代河西走廊一带最常见的流行病,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年、月、日所患之疾病,最多的是“苦头痛”.据记载,这种头痛病伴随有高热、烦闷、气逆、狂语、面黑等症状,而且有极强的传染性和很高的死亡率,故曰“吊丧问病,凶”,“若得病者,十死一生”[18].所有这些,都是腺鼠疫典型症状的描述,说明鼠疫是当时河西走廊及中亚一带常见的流行病.
根据瘟疫期间病症的特征,可以肯定,历史记载中描述的“恶核”“虏疮”“流肿”“暍病”“苦头痛”等称谓,都是对腺鼠疫某个方面症状的描述,其间中国境内肯定是有腺鼠疫流行的.在6—8世纪站有48个疫灾年中,除515年、574年、642年、643年、644年、648年、655年、711年、783年、784年等10个年份无法判定为鼠疫外,其余38个年份均有可能是腺鼠疫流行.
3 6-8世纪中国、中亚与欧洲鼠疫互传的可能性
3.1 世界范围内鼠疫的发生具有多源性
鼠疫是自然疫源性非常强的一种环境生物性疾病,啮齿类动物生境的自然变化可能导致不同鼠疫自然疫源地的鼠疫同时爆发,形成多个鼠疫发源地.据研究,鼠疫流行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在中国,第二次(1331—1650s)、第三次(1854—1940s)鼠疫大流行,都处于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第一次鼠疫大流行(541—750年)早期,气候也是相当的寒冷[19].在中国北方,寒冷气候往往伴随着干旱的发生,旱灾导致人类活动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扰动加剧,比如捕猎旱獭,掘食鼠粮,从而增加鼠疫的风险.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在中国北方的山西地区,和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地区,几乎同时进入鼠疫活跃期,两地相距遥远,并不能找到彼此传播的证据.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激发了鼠疫在不同地方的同时发生,形成鼠疫发生的“多源性”.
关于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发源地,直到现在,学界并没有取得共识,有人认为源自非洲,有人认为来自中亚.关于非洲起源说,主要是基于古老的0.PE鼠疫菌株“安哥拉”和历史学家Evagrius Scholasticus说“鼠疫始于埃塞俄比亚”.关于亚洲起源说,一种可能是鼠疫通过红海和印度洋从海路传入,因为印度和早期拜占庭帝国有着良好的海上交通;另一种可能是鼠疫从欧亚草原经伊朗从陆路传入红海,再从红海传到埃及[1].但是,这些观点都没有取得共识.我们认为,鼠疫流行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具有发生学上的多源性,因为生态环境的激发,它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发生,并不需要彼此之间的传播途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时,非洲和亚洲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都有可能是被当时全球性寒冷气候激活的.
如上所述,中国远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的《黄帝内经》就有了鼠疫症状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有了“流肿”记载,公元4世纪有了“斑疮”记载,公元5世纪有了“虏疮”记载,这些疾病虽然并非专指腺鼠疫,但都可能隐含腺鼠疫在内.也就是说,中国在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有了腺鼠疫的流行,这是确凿无疑的.那么,中国的鼠疫发源地在哪里?我们认为,就是包括现在中国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在内的中亚地区,毋庸讳言,中国也是鼠疫的发源地之一.
现有基因考古数据表明,中亚是导致第一次大流行的鼠疫杆菌基因的大多数分支发散点[20],所有已知的基因树分支在中国新疆地区[21]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22]都能采到样本;还有,在新疆天山山脉的一个2-3世纪的鼠疫杆菌里,也分离出了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所有基因组[20].据此,有人认为,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欧洲的鼠疫是中国的匈奴人引入的,但是匈奴人的活动是在3世纪,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发生在6世纪,其间存在3个多世纪的空白时间,令人费解[1].其实,如果欧洲鼠疫真是由中国的匈奴人传入的,这并不难解释,一是鼠疫在空间上的传播需要时间,从疫源地到暴发地的距离越遥远,传播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二是鼠疫杆菌的致病力和传染力需要一定的气候、人口条件,当气候、人口条件不适宜其繁殖和扩张时,其致病力和传染力就弱,鼠疫只是散在性发生,只有气候、人口条件适宜其繁殖与扩张时,其致病力和传染力才会大为增强,鼠疫才会大规模流行.更何况,3-6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中国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时期,疫灾的流行相当频繁,而且如上所引,其间许多疫灾事件可以指实为是腺鼠疫的流行.
3.2 6—8世纪中国的鼠疫来自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是世界核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生活在这片地区游牧民族是天然的鼠疫杆菌携带者,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已经被证实是由蒙古军队带到卡法城并进而蔓延整个欧洲的.其实,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鼠疫种子,也极有可能是由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传播的,比如匈奴、鲜卑、突厥等.如前所述,有人怀疑欧洲的鼠疫是3世纪时由匈奴人传入的,我们认为这种怀疑是有依据的,因为匈奴人活动的地域是中亚鼠疫自然疫源地,而他们的生活方式极易将鼠疫杆菌从啮齿类动物身上带到人间,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畜牧和狩猎,几乎成天与草原动物打交道.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他们以野生鼠、兔为食,而这些啮齿类动物正是鼠疫杆菌的宿主,这使得他们的部落和军队很容易成为鼠疫的传播者,以致他们的军队行动到哪里,瘟疫就会流行到哪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游牧民族剥食染疫旱獭和野鼠导致鼠疫流行的例子.
中亚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前164—前114年)就打通了中国汉帝国通往欧洲罗马帝国的贸易通道,到6-8世纪时,中亚地区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中亚大国为吐火罗(Tokharoi),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北魏时期就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至于隋唐时期,吐火罗为突厥人统治,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不少吐火罗人甚至在唐朝政府做官.629年,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到达吐火罗,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描述吐火罗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气序既温,疾疫亦众……其国风土并多温疾”[23],说明“温疾”是其国家的地方性疾病.这里的“温疾”,就是发热之病,即中医典籍和史志文献所言的“暍疫”,是腺鼠疫的发热、头痛之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吐火罗是在突厥人的统治之下,隋唐之际,突厥人经常入侵中国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并把瘟疫带到这些地区.这说明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中国与中亚联系十分密切,鼠疫从中亚传到中国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唐朝张文仲(620—700年)的《随身备急方》就明确记载,653年,“虏疮”是“从西域东流,遍于海内”的,这说明鼠疫是从中亚一带向东传播到中国境内的.
如图3所示,中亚地区(含中国西北地区)位于中国腹地和地中海的中间位置,匈奴、突厥等军队循贸易通道向西进入欧洲和向东进入中国,都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从6—8世纪中国鼠疫发生的情况来看,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中亚地区不仅是中国鼠疫的来源地,而且也是欧洲鼠疫的来源地,中亚地区的鼠疫传到地中海和欧洲和传到中国西北及内地,两者的空间距离差不多.

注:基于审图号为GS(2016)1667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图3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541-750年)中国和欧洲的鼠疫分布示意图Fig.3 Distribution of plagues in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first plague pandemic time 541-750 C.E.
总之,我们相信,中亚地区是一个古老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无论哪个民族占领这片地区,他们就获得了传播鼠疫的地理条件.在中国,秦汉时期的鼠疫主要由匈奴人通过战争传播;南北朝时的鼠疫主要由鲜卑人通过战争传播;隋唐时期的鼠疫主要是通过突厥人的战争传播.
4 结语
尽管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时代距今久远,当时的历史记载也相当简约,但我们还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搜集到不少指向腺鼠疫流行的线索.中医史家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黄帝内经》时代,中国就有了鼠疫的记载.经过考证,我们认为,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541—750年),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恶核”“虏疮”“流肿”“暍疫”,甚至“疹疫”“瘴疫”“苦头痛”等等称谓,都包含有腺鼠疫症状的描述,其导致的瘟疫流行,患者的死亡率(即病死率)高达70%~90%,也都有可能是腺鼠疫的流行.因此,可以肯定的是,6—8世纪中国境内有过多次腺鼠疫的流行,其中17个Ⅳ级以上的“大瘟疫”,基本上都是鼠疫的流行.
鼠疫是一种具有地方性的自然疫源性和环境生物性疾病,鼠疫杆菌及其宿主受自然生态规律的制约,一旦某个区域的自然生境适合它们的生息繁衍,它们就在那里建立地方性,那里就会成为稳固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当全球气候环境变迁适宜于鼠疫杆菌的繁殖和扩张时,就会同时激活不同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杆菌的致病力和传播力,导致鼠疫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因此,鼠疫流行具有多源性.
中亚地区是古老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鼠疫从中亚向中国和欧洲的传播没有任何障碍,欧洲和中国的鼠疫主要由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通过战争和贸易输入与传播,6-8世纪,中国与中亚国家联系密切,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国西北地区是鼠疫流行最频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