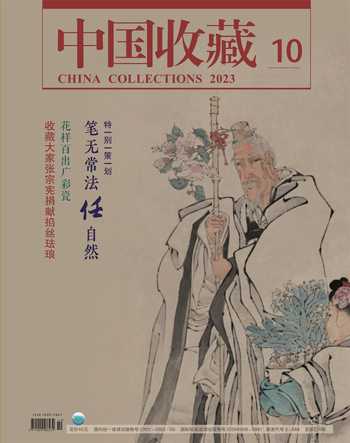花样百出广彩瓷
邓玉梅

“廣彩”是清代以来广州地区釉上彩瓷的简称,是应海外市场之需出现的外销瓷品种,其创烧于康熙晚期至雍正时期,盛于乾隆、嘉庆时期,历300年窑火不绝。它以“广州”命名,发展历程及工艺特征凝聚着广州这座口岸城市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以及瓷商、瓷匠们融会贯通、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
新世纪以来,广州博物馆作为口岸城市的综合性博物馆,循昔日广彩传播之路,开展相关文物征集和研究工作2 0余载,陆续汇集曾外销世界各地的广彩瓷器1500余件(套),藏品年代序列完整、品类丰富、时代风貌鲜明,可清晰展现广彩创烧历史、工艺发展轨迹和文化价值。
2023年9月,广州博物馆甄选其中150余件(套)代表性藏品,举办“广东彩 世界风”广彩主题展览,讲述广州彩瓷不断融合中西制瓷工艺并创新发展,随各国商船遍及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明的历程。广彩因其外销特征而兼容中西文化的内涵,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交流的载体,尤其是在18世纪,即清代康熙晚期至乾隆、嘉庆朝,广彩瓷器生产和销售处于早、中期的创烧和多元实践阶段,其产品工艺及品类极为丰富,中西兼备的图像纹样和丰富多变的器型种类,成就了世人对广彩“式多奇巧,岁无定样”的赞誉。

开炉烘染 应需而生
广彩瓷器的出现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及中外贸易发展有直接关系。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684年至1686年),清廷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其后80%以上的外国商船泊靠广州港,成为中西方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中国瓷器既可作为返航西洋商船的压舱货,更能带来可观利润。为顺应欧洲市场需求,准确传达客户订单、缩短定制周期、降低运输损耗和制作成本,广州瓷商开始将景德镇白瓷运至广州,根据外商要求彩绘后二次烧制再销往海外,广彩瓷器应需而生。
康熙中晚期至雍正时期应是广彩的初创阶段,产品风格尚不鲜明,以个性化定制为主,产量不大。各类彩料、技术、特殊纹样及器型随外国商船被引入广州,并迅速运用到广彩生产中。目前国内收藏及公布的早期阶段实物很少,广州博物馆收藏的初期广彩产品颇具规模,藏品实物可为探讨早期广彩产品实践创烧轨迹提供佐证。
早期广彩使用的颜料,融合了明代三彩、五彩的传统颜料与外国珐琅彩料。纹样绘制风格往往受欧洲巴洛克风格影响,整体庄重磅礴,线条干练大胆,这恰恰与同时期即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的瓷器造型偏硬朗大气的风格相得益彰(图1)。
此时的广彩产品主要为特殊定制的外销瓷类型,采用中国传统折枝花卉与个性化纹章图案相结合的纹章瓷占据主流,这也体现了广彩应欧洲市场需求而出现的特质。有些私人定制瓷器上的边饰图案被多次效仿,并发展成为早期广彩瓷器的普通装饰纹样而广泛流传,如1712年英国沃克(Walker)家族定制的纹章瓷中采用的欧洲风格的卷叶纹边饰,在短短几年后便出现在普通外销瓷产品中(图2)。

从总体风貌看,早期广彩产品大多品质精良、绘工细腻,按定制需求绘制的纹样如私人纹章图案绘制极为精准,展现了同时代尤其是雍正时期瓷器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用彩构图上也明显呈现出受同时期铜胎画珐琅工艺影响的痕迹。如1730年前后出现一种以蓝、砖红或金彩绘制人字锦地纹的产品,此类底纹一般铺满整器,仅留多个如意形开窗,内绘中式花鸟纹(图3)。画珐琅的装饰工艺进一步运用到广彩绘制中,除了人字锦地纹外、龟缩锦纹、八角锦纹、三线金线锦纹等均出现,私人定制瓷器大量采用珐琅工艺常见的各类锦地纹与中国传统折枝花卉纹相结合(图 4),折枝花卉以工笔绘就,展现出雍正时期工整、雅致、细腻的瓷绘风格。

18世纪初生产的广彩餐具器型较为简单,仅包括少量的套装盘和碟,且大盘的数量较多,绘制精细工整。对西方人而言,绘制精美的瓷盘除了基本的实用功能外,展示陈设也是主要功能之一。尤其是在18世纪上半叶,中国外销西方市场的瓷盘常常被放置在餐边柜或陈列柜内作陈设器。有些绘制中国传统纹样的瓷盘规格偏大,显然陈设功能大于实用功能,应是广州瓷器店铺专为欧洲商人准备的现货类型。此类中国传统纹样充满东方情调,迎合了18世纪上半叶欧洲盛行的“中国风”时尚(图5)。

岁无定样 多元实践
乾隆时期,尤其是1757年至1842年间,广州作为对欧美航海国家开放贸易的唯一口岸,迎来了“广州贸易体制”的繁荣时代。中西瓷器贸易快速增长,广彩生产迅速适应海外市场多元化需求,脱离景德镇影响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外销品种。对于任何可能引发市场反响的新造型、新图样、新技法,广彩匠师都大胆尝试。这一时期西红、麻色、干大红、茄色等暖色调彩料被广泛使用,绘制技法中西结合,工意并用。纯粹的西洋题材大量出现,器型随市场需求和审美时尚变化迅速更替演变,既反映了欧洲社会生活变革,也部分融入了欧洲本土新兴的瓷器烧造艺术,开创了广彩产品国际化新气象。
16世纪以来,欧洲饮食方式經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瓷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到了18世纪,欧洲市场对仿西方造型的广彩瓷器需求越来越大,最常定制的广彩器型一般都是实用器皿,包括碟、盘、杯、壶、罐、碗、盐托、烛台、汤窝等,成套的咖啡具、茶具及餐具也是外商定制的主要品种,还有特别定制的器型,如剃须盘、水罐和水盘、冷酒器、表座、调味瓶套件、甜品碟等,种类较18世纪初大为丰富。
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外商到广州定制瓷器的需求重点从器型满足功用转向更符合欧洲审美的纹样。欧洲版画、藏书签、文件、钱币、纺织品,甚至是专门设计的纹样作为瓷绘样板被带到广州供广彩匠人临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元素和潮流风尚被广彩匠人吸收融合后,形成了广彩瓷器有别于内销产品的多元化、国际化风貌。仿德国迈森瓷器风格的产品大量出现(图6),宗教和神话主题纹饰风行一时,纯粹西式的纹样种类丰富。希腊神话故事“帕里斯的审判”便是18世纪中叶广彩瓷最常见的神话主题纹饰,纹饰展现的是帕里斯将苹果递给阿芙罗狄忒时的场景。

广彩瓷器中花卉纹样的绘制风格,在整个18 世纪经历了中国风格到西方风格再回归中国风格的大致过程。18世纪中叶,广彩产品中出现了纯粹的西式花卉,如完全模仿迈森产品中的“ 德式花卉”(Deut sche Blumen),这种欧式花卉图案是以多种不同花卉组成的,多以成束花卉形式出现,绘制略带写意但更注重描绘花卉的自然状态。“德式花卉”主题纹饰除了在大宗贸易的广彩瓷中出现外,也会根据客户需求添加个人纹章图案,并搭配不同的边饰后销往不同的国家。
1775年前后,一种被称作“ 满大人”(Mandarin)式样的广彩瓷器出现,这种绘有清代富裕阶层生活场景的清装人物图瓷,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直接媒介,激发了欧洲社会对“ 东方生活”的无限想象。“满大人”纹大量采用西红和干大红等红色调,用色华丽,有时也与釉下青花的开光形式相结合。有些产品也融合同时代的德国迈森瓷厂产品风格,如边饰中的茄色菱形地纹和双钩线小开光的装饰手法均来自迈森(图7)。
就中国人物主题纹饰而言,到了1 8世纪末,中国传统人物故事纹再度流行,这也是广州瓷商为了保住外销订单,强化产品地域特点,明显提升产品品质的表现。这种人物故事纹被称作“官人图”(Mandarin design),但与18世纪后期的“满大人”纹不同,绘制的主题人物并非出自清代生活,而是清以前广为流传的文学名著和戏剧故事。其中,以《西厢记》中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生进京赶考的别离场景最为常见,在大宗外销广彩瓷和私人定制的纹章瓷中均有大量出现(图8)。

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中国购买大宗瓷器,英国本土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也征收高于10 0 %的税点,只有少数真正喜好东方瓷器并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买家,才会到广州定制瓷器,私人贸易者定购的瓷器品质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一种被后人称作“宫廷瓷”(Pa lace ware)的新样式便是少数私人贸易者定制的品质极高的广彩品种(图9)。“ 宫廷瓷”之称源自其华丽的描金边饰和精细绘工,特征在于中部圆形开窗内绘制精美的宫廷人物建筑或乡野景观,用干大红、黑彩绘制的菱形锦地内沿和大面积的鎏金卷草纹外沿,口沿中散布绘工细腻的麻色开光风景。美国知名实业家、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约翰·洛克菲勒也曾收藏过一套“宫廷瓷”餐具,因此也有人将此类广彩称作“洛克菲勒”瓷。
19世纪到来之际,受欧洲瓷业崛起、主要市场转变、烧制材料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广彩的种类、风格和工艺特点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形成构图饱满、色彩绚丽、堆金织玉的典型风格,并传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