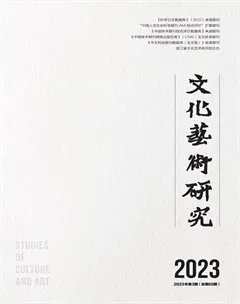阿多诺论艺术创作中社会素材的利用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4)
艺术作品的社会性体现在艺术作品的社会素材方面。如果没有社会素材,艺术作品就会非常空洞。那么,艺术作品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社会素材呢?阿多诺反对直接把社会素材运用到艺术作品中。他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特征来看待艺术作品处理素材的方式,又通过分析艺术作品处理社会素材之方式来进一步说明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性题材的去社会化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社会性的题材。如何利用社会性的题材显示出艺术作品的水准?阿多诺反对直接利用社会题材,因为直接利用社会题材就缺乏反思层面,而当艺术作品缺乏反思层面的时候,题材在艺术作品中的作用就显得模棱两可。阿多诺把这种艺术倾向说成资产阶级的唯名论。正因此,阿多诺认为,题材是最表面、最具欺骗性的。也就是说,如果直接利用社会题材,那么这种题材就会具有欺骗性。比如,法国古典主义艺术家埃米尔·穆尼尔(Émile Munier)的煤矿工人的雕像就是明显具有社会性的题材。从表面上看,这一题材是要赞扬煤矿工人的,但是赞扬煤矿工人的宣传画恰恰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东西,激励煤矿工人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幅绘画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色彩明亮光鲜,人物造型俊美动人,结构关系和明暗处理严谨。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契合的。从埃米尔·穆尼尔对理想的矿工的塑造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些无产阶级也具有完美的人性和高尚的品质。但这些做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内曾有一幅画作反映上山下乡时期城市女青年和乡下农民结婚的场景。从城市女青年角度来说,这或许是苦难,而从乡下农民的角度来说,这是幸福。所以,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直接以现实中的东西为题材,那么这种题材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正如反对理论上的实证主义一样,阿多诺也反对艺术中的唯名论倾向。
与资产阶级唯名论相反的是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这种自然主义倾向从表面上看是与资产阶级唯名论相反的,但实质却是一致的。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作品应纯粹客观地描述自然,艺术也应该是自然的流露。如果说现实主义会表现出明显的现实倾向和主张,甚至直接为政治和社会服务,那么自然主义则反对艺术直接为政治和社会目的服务。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自然主义从表面上看来是中立的,但这种中立的自然主义与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唯名论)思路是一样的。他认为,左拉那种毫不掩饰的自然主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性格特征的表现,表现为一种压抑性的快乐。用弗洛伊德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肛门快感。这种快感是在控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从它所排斥的东西的痛苦和污秽中获得。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就是如此,既要获得自然的满足,又疯狂地排斥和压制自然。正是这样一种被压抑的满足,体现了法西斯主义对自然的态度,既压制自然又要满足自然。他们从他们所排斥的大屠杀中获得快感。法西斯主义所说的那种自然主义,它所高呼的“血与土”的口号,与左拉的自然主义如出一辙。[1]230
由此可见,在题材的层面上,人们都是用昭告式的、直白的语言来描述现实,或者自然地流露自己的倾向。在这里,攻击性和顺从性是无法区分的。这些处理题材的做法缺乏反思的要求。从某个角度来说,浪漫主义就比这种现实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多了反思的层面。而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艺术作品中包含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其中,现实与自然或者被简单地排斥了,或者被简单地接受了,甚至排斥和顺从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启蒙的辩证法。在这里,阿多诺还列举了20 世纪30 年代失业者那种煽动性的合唱《失业者进行曲》(类似于20 世纪80 年代在我国流行的《一无所有》),这种合唱被人们要求以一种“丑陋”的方式进行表演。[1]230这种表演形式发挥了一种政治的功能。而这种表演究竟是排斥某种社会现象还是迎合某种社会现象呢?其实并不清楚。这个事实也表明,直接把社会中的事实作为题材,并不能真正地用来否定社会的事实。
阿多诺赞赏卡夫卡的做法。这种艺术方法中包含了反思,甚至比浪漫主义更高层次的反思。比如,卡夫卡的作品也会涉及垄断资本主义,但他不直接叙述垄断资本主义。他不是直接用小说的形式来描述工业托拉斯,而是叙述在总体社会的魔力之下,人民成为这个被全面控制的世界的残余,成为被碾压了的碎片。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都表现了这个被全面控制的社会,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小人物——他把被压制的人们作为题材。[2]阿多诺认为,卡夫卡的这种做法更加准确、更加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卡夫卡的做法表明,形式是内容的真正所在地。这两部小说所说的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纯粹形式的东西,但是这些虚构的事实却表现了一种客观的东西,即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揭露了一个被全面控制的社会。在这里,读者总是会面对一个矛盾: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客观性与虚构的故事的矛盾。这种虚构性表现为,一种准现实主义的描述把一种不可能的东西变成日益逼近我们的东西。在这里,虚构的好像是现实的,而现实的好像是虚构的。在他的作品中,虚构是不言自明的,而这种虚构变成现实也是不言自明的。虚构和现实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转换。这成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形式脱离现实,而又对现实进行批判。卡夫卡对题材的这种处理方式,使它能够真正批判资本主义,而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从这里可以看出,艺术产品不是直接讨论社会的,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其“社会意义上是沉默的”。虽然它不直接讨论社会,却把如此这般处理过的材料回流到作品之中,从而达到类似讨论社会的目的。在这里,艺术作品好像进行了一种新陈代谢,并把这种新陈代谢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反思,这种反思也成为艺术的荣耀。[1]231当艺术创作者处理艺术材料的时候,会在艺术作品中抵抗社会的影响,抵抗社会大多数所产生的影响,并把这种抵抗作为艺术真理的标准。与此同时,艺术创造者在抵抗外部影响的时候也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直接体验作为艺术的材料。相反,艺术家把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引入自己的直接体验中,这时,又遵循了社会的普遍性。在艺术家通过这种矛盾的方式处理艺术作品时,艺术作品内部存在着一种矛盾,即个别和一般之间的矛盾。
当这个深层的结构被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时候,艺术参与实践,影响社会。这个形式化的、更深层次的矛盾结构本身并没有直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是沉默的。这个沉默的东西好像有一个实践的轮廓,而这个实践的轮廓虽然没有真正地参与实践,但也不是与真正的实践毫无关系。它满足了一种艺术的需要,表现了艺术本身的行为方式。在这种行为方式中,艺术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它没有能力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也不需要为它不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而道歉。即使艺术在这里产生了社会影响,其影响也是不确定的。[1]232
二、净化与升华:艺术作品处理现实的特殊方式
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艺术作品总是要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题材。那么,艺术作品究竟如何来处理这些题材呢?
在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中,阿多诺强调,自律的艺术之中必定包含了他律的东西。因此,当艺术努力从社会中摆脱出来,争取艺术上的自律的时候,也回过头来走向他律。比如“我们”会被纳入客观化的作品中,而这个艺术作品中的“我们”与外在于艺术作品中的“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的呼声也在发挥作用。所以,阿多诺说:“集体的呼声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原始罪孽,而且是它们的形式法则中所蕴含的东西。”[1]238艺术作品必定会把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呼声包含在其中。既然艺术作品不可能排除这种他律的东西,那么我们也不能局限于从艺术作品内在性的角度来看待艺术,而要关注艺术作品的审美效果。在这里,阿多诺强调,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关注艺术作品的审美效果。比如,对于柏拉图来说,一件艺术品的好坏与它是否与共同体的品性相一致有关。而亚里斯多德则试图克服柏拉图思想的缺陷。他在《诗学》中提出了“净化”(Catharsis)的概念。[3]这个概念就是要清洗掉情感的作用。他借助这一点,反对艺术直接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艺术又借助于审美幻象给人们提供某种满足,而这种满足不同于大众的肉体满足。这就是被人们所称颂的所谓“艺术的升华”。当然,把升华理解为一种替代性满足,也就剥夺了艺术升华中那种尊严的要素。比如,悲剧能够给予人一种精神的力量。但是,这种升华作用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却被理解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阿多诺认为,这种替代性的满足,这种所谓的升华在清洗掉情感要素时其实同时是一种压制。这就如同一个社会,本来是可以满足人们的感性需求的,却用一种精神的东西来满足人,剥夺了人们的感性需求。这就是通过颂扬人们否定自身感性需求的做法来剥夺人的感性需求。
阿多诺对艺术中的这种升华进行了反思。如果艺术作品被理解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那么这种升华观念其实就为后来出现的文化工业铺平了道路。文化工业从精神上满足人,其实也是剥夺人们感性上的需求。这就是用一种虚假的、替代的东西来满足人,让人沉迷在审美的幻象之中。如果一个社会剥夺了人们的物质满足,那么它就把物质的追求当成一种粗俗的东西,要借助于升华的作用否定人们的物质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也不能完全排斥粗俗的东西。问题在于艺术如何来处理那些粗俗的东西。
在阿多诺看来,如果艺术不是用一种高傲的态度来吸收粗俗的要素,那就意味着,人们承认粗俗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那么艺术就有真正的分量。反之,如果用一种高傲的态度来对待粗俗的东西,那么就要满足一种根深蒂固的扭曲文化,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扭曲,亦即既排斥甚至痛恨自己的自然需要,又试图满足这种自然需要,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所以,阿多诺说,如果艺术通过一种傲慢的态度,尤其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对抗粗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诉诸一种扭曲的意识,并且肯定这种扭曲的意识。[1]239如果艺术在精神上满足大众这种扭曲的意识,那么,实则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控制。阿多诺认为,如果从大众中得到的那些东西,那些可以重新返回大众中的东西,可以被归咎于他们自身的丑恶欲望,那么这种艺术适用于控制。如果大众的欲望被理解为丑恶的欲望,那么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文化控制人们对这种欲望的需求。这就好比说,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的德国人不愿意参战,法西斯主义分子就会说,这是受到丑恶的欲望的支配,好像人害怕死亡是丑恶的事情一样。如果他们参与战争,那么他们就是“高尚”的,这是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是否定了他们的欲望之后再满足他们的欲望,这就是对他们的控制,是在物质欲望被否定之后的一种自我憎恨。
艺术作品如何才是真正地尊重大众呢?艺术作品应该把自身作为它们所可能成为的样子呈现给大众,而不是让自身去适应大众的堕落状况。比如说,在生活中,某个人被人们发现做了某个不雅的动作,如果有人故意在这个人面前模仿这种动作,那么显然就是在侮辱这个人,挖苦这个人。在艺术上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故意把某些人身上粗俗的东西客观地再生产出来,那么就是在故意羞辱这些人。
可是,这些被羞辱的人为什么竟然会喜欢羞辱他们的东西呢?阿多诺的解释是,在生活中,大众被无奈地取消了一些东西,面对这些被取消的东西,大众反过来会欣赏这种取消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利用被取消了的东西所留下来的位置。[1]240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羞辱大众的东西恰恰为大众所欢迎了。例如,大众被取消了去高档饭店吃饭的资格,那么,被用来填补这个位置的是欣赏这种挖苦“装阔”的艺术作品。“装阔”是他们被排除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外后所导致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变成了他们欣赏的对象。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人心灵的扭曲。一些吃不起高档饭店的人会挖苦那些去高档饭店消费的人——这是“装阔”。于是,“装阔”就成为他们的欣赏对象。这就是用一种扭曲的心态来满足自己被压抑的需求,是一种被掩盖了的嫉妒心理。在这里,人们所喜欢的不是真理、正义,而是丑恶、愚昧。阿多诺指出,这种低档的艺术(娱乐)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被合法化,并且是自明的。[1]240挖苦穷人、丑化穷人在这里变成一种合理化的东西,变成自明的不受怀疑的东西。因此,阿多诺说,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表达了到处都出现的压制。审美中的粗俗性就如同广告中的儿童好像有一种罪过那样,闭着眼睛吃巧克力。被压制的东西返回到这种粗俗的艺术中,携带着压制的痕迹。[1]240
另外,本研究加入舒适度指数这以综合性气象条件进行研究,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考虑为舒适度指数是用于衡量人体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的人体感觉的指标,惠州地区四季气象条件不明显变化不大,舒适度指数基本位于“舒适”范围(50~75)。舒适度在气象条件的研究中可能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本来是要把生活中的东西升华,而艺术中粗俗的东西却说明了这种升华的失败。什么样的艺术品显示了升华的失败呢?如果艺术作品模仿被压制的东西,把被压制的东西直接表现出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升华的失败。
当穷人因没有钱到高档饭店吃饭而被排斥时,如果挖苦穷人,把穷人作为取乐的对象,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野蛮的。穷人是社会压制的产物。如果艺术作品能够成功地升华,比如,对这种野蛮行为进行批判,或者,如果艺术作品能促使人们反思为什么穷人被迫“装阔”,并批判迫使穷人“装阔”的文化,那么,这就达到一种升华。
为什么艺术会导致这种升华的失败呢?艺术本来应该羞辱野蛮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野蛮的东西已经在文化中沉淀下来,文化不再需要羞辱野蛮的东西,因为文化通过习惯来强化它们就已经足够了。艺术中粗俗的东西就是文化传统的延伸,是文化压制中的一个要素。艺术中粗俗的东西模仿了社会压制,模仿了社会中堕落的东西。
艺术中粗俗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形式——赞美自身的高雅。在这里,艺术中的高雅代表了某种不存在的东西,而这种不存在的东西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把这种形象的东西直接转换为它的反面,并污蔑这种东西。比如说,某个美丽的模特在广告中总是赞美自己洁白的牙齿,宣传某个品牌的牙膏。而一旦人们认为其宣传的东西是虚假的,就会批判这种东西,诋毁这种东西。艺术要坚持高雅,但绝不是把高雅、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我欣赏。高雅是在抵抗粗俗中出现的。如果高雅把自身作为赞美的对象,那么高雅就会变成虚假和粗俗。如果一个高雅的人总是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的高雅,那么这种高雅就直接变成了粗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直接就是高雅的。高雅和粗俗如果完全对立起来,就会走向各自的对立面。
总之,艺术的升华是要达到高雅,但艺术的升华不能被用来满足扭曲的需求。因此,高雅不是直接否定粗俗的需求,不是把高雅和粗俗对立起来,而是既承认粗俗的需求,又对它进行提升。只有当高雅和粗俗处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和解的关系中时,艺术作品才真正具有升华的效果。
三、题材的运用:意识形态与真理性之间的相互转换
按照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采用工具理性的方法来控制自然,包括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这就需要用同一性的思维方法来把各种不同的对象进行归类、整理,从而有效地控制对象。这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而在这样控制对象的活动中,人所得到的只是有效知识,而不是真正地把握对象,不是获得关于对象的真理。而当人们获得有效知识的时候,会把这种有效知识当成“真理”。这是生存斗争中的必要幻象。阿多诺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必要的幻象。而这种必要的幻象其实是一种扭曲形式的真理。艺术本来是要把握不能用概念表达的东西,把握非同一的东西,但是非同一的东西必须借助于概念才能显示出来。所以,真理必定以幻象的形式出现。艺术作品也是如此。艺术作品是精神性的,但是必须借助于质料才能出现。艺术作品陷入一种拜物教的幻象之中。其实艺术作品中也有概念,也必须包含概念,如果没有概念,艺术作品表达非同一的努力就不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艺术作品都必定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必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个意识形态恰恰以扭曲的形式表达了真理。在这里,人们必然会说,既然意识形态是必要的,是扭曲形式的真理,而真理本身又是不可能直接显示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只能满足于意识形态了。在阿多诺看来,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可能就会满足于这种意识形态,而审美意识区别于日常意识的特点就在于,审美意识反思艺术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如果艺术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包含了社会批判的要素,那么审美意识也要反思这种社会批判要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种社会批判要素。
在阿多诺看来,奥地利作家阿达尔贝特·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就是故意用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表达真理的内涵。他以保守主义的方法来选择素材,并提供一种寓言式的教诲,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不仅如此,其作品的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客观主义做法,比如温馨的微观世界、有意义的正确生活等,也明显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但就是在这个温馨的世界中,斯蒂夫特把和解的要素非常夸张地凸显出来。这就表明,他所客观地描述的那个温馨世界原来是充满矛盾的,是矛盾着的东西的和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行的和解。于是,这个客观的描述就固化为一种掩饰,而他所描述的生活就变成一种辩护性的仪式。温馨的世界不过是勉强地压制矛盾而表现出来的表面世界。在温馨的生活中所闪现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被掩藏起来的和被否定了的痛苦,是异化了的主体和不和谐生活的痛苦。那些洒在他的成熟作品上的光彩暗淡了下来,变得死气沉沉。他好像对色彩斑斓的东西特别反感。他的散文好像变成一种素描。生活中的那些不正常的东西,那些恼人的东西都被视为与诗歌形式不契合的东西、与诗人的伟大理想不同的东西。凡是与史诗般的宏伟壮阔的理想不同的东西都被排除到现实生活之中。散文和诗歌的绚丽变成了对平淡生活的描述,变成了生活中的痛苦的装饰品。与散文和诗歌作者的本人意愿相反,这里所暴露出来的是诗歌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他的表现形式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被极度夸张了的意识形态,多姿多彩、夸张优美的散文、诗歌与压抑性的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就表达了非意识形态性的真理内容。客观的描述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所隐藏的是痛苦。优美的诗歌淡化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客观描述。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这里表露无遗。而恰恰就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真理的内容被表达出来了。在斯蒂夫特的作品中,诗歌的形式、作品中所直接表达出来的意义恰恰被否定了,夸张的表达反而变成了客观的内容。从这样一种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内容变成了对他所表达的意义的否定,然而,他的作品如果没有故意地表达意义,那么内容也不可能存在。但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意义恰恰被作品自身的复合性外表所改变,甚至被取消。作品自身试图表达意义,却又消解了要表达的意义,从而使作品的真理内容显现出来。所以阿多诺说:“在斯蒂夫特的作品中,肯定变成了绝望的密码,而内容的最纯粹否定却包含了肯定的颗粒。”[1]233
从阿多诺对于斯蒂夫特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不是来自作品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描述。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恰恰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现实的反映,而阿多诺对于这种直接反映持否定的态度。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来自艺术作品的自身矛盾,来自艺术作品自身的意识形态特点。离开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离开了艺术作品的自我否定,那么艺术中的真理是不可能的。阿多诺对于艺术作品的这种审美理解与他对于哲学真理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哲学中,我们要通过概念来否定概念,从而走向真理。在艺术中,情况也是如此,艺术需要走向自身的反面,艺术作品必须在它自身的否定中走向真理。比如,斯蒂夫特在表达意义的企图中走向了对意义的否定。
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作品禁止一切肯定性,但是从艺术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斑斓色彩却又是不可消除的肯定性的显现,像是某种曾经存在过而现在不存在的东西那样显现出来。对于这种东西存在的许诺好像是在审美的幻象之中闪烁,不存在的东西借助这种显现而被作为存在的东西得到承认。在这里,存在和不存在的东西构成了一种星丛,这种星丛就是艺术的乌托邦形象。艺术中所出现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肯定性是艺术作品内在发展的结果。在这种内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着的肯定性,不能被视为它们对社会现实态度的一种外在结果。艺术作品中矛盾着的肯定性,是艺术作品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概念——自我发展的内在矛盾一样。艺术作品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并非对外在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结果。这种矛盾着的肯定的东西是在艺术作品内部发展起来的,是朦胧地存在于艺术作品本身之中的。
艺术作品中存在着这种朦胧的具有肯定性的东西。如果人们把这种肯定的东西固化,那么艺术作品就偷偷摸摸地通过这种固化了的肯定获得了美。所以,阿多诺说,美无法逃避“它究竟是不是美的”这样一个问题。实用艺术就是把这种具有肯定性的东西固化,并变成一种“美”的东西。这种美的东西其实就是艺术作品的要素之一,没有这种肯定性的要素,艺术作品的美也无从表现。但是,艺术讨厌实用艺术。那么,艺术作为总体时为什么会讨厌实用艺术呢?因为这种实用艺术总是让艺术从每一个乐声中,或从每一种色彩中意识到艺术自身所包含的肯定性东西,而艺术又试图掩盖这种肯定性的东西,并将其置于模棱两可之中。所以,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对于实用艺术的反感从间接的方面来看,是艺术作为总体而显示出来的坏良心。[1]234本来,人都喜欢美的东西,但是它却遏制美的东西,表面上肯定,其实是要否定这种肯定。艺术在总体上所显示出来的这种坏良心只能从艺术作品的内部得到理解,而不是从外部来进行分析。例如,电视小品《主角与配角》就表现了主角和配角由肯定走向否定的特点。
在艺术作品中,真理和意识形态是无法区分开来的。二者的相互作用会诱惑人们误用意识形态的特征。这种误用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或者把它变成一种实用艺术,或者以艺术中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否定艺术,强调艺术的终结。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真理如果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意识形态和真理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很容易使艺术走向意识形态。在阿多诺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作品很容易多走一步。[1]234他说,社会越是厚颜无耻地变成一个总体,艺术就越是变成这个总体中的一部分,就会失去其自律性。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作品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或者艺术作品变成社会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艺术作品直接抵抗这种意识形态。而在阿多诺看来,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这两种极端中,艺术好像要么只能是纯粹意识形态,要么只能纯粹是不受束缚的“真理”。阿多诺认为,如果艺术作品变成对意识形态或者对社会的绝对反抗,那么艺术就限制了自身,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艺术是依赖于社会存在的,极端地抗拒社会的艺术无法在社会中存在。而如果把艺术作品极端化为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艺术作品就变得极端浅薄,变成社会现实的简单复制品,成为现实的贫乏的、武断的复制品。[1]234
四、第二层次的反思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作品在利用社会素材的时候都会对社会素材进行加工和处理。甚至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都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而是加入了一定的反思要素。不过阿多诺认为,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在处理材料的时候多了一个层次上的反思。我们知道,席勒把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素朴的诗,一类是感伤的诗。素朴的诗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基于自然和现实的感受而产生的一种自然流露。而感伤的诗把素朴的诗所迷恋的现实与理想加以比较,更多地凸显了对理想的追求。与素朴的诗相比,感伤的诗多了一个反思的层面。现代艺术是在这个反思层面上进行的第二次反思。在这第二层次的反思中,艺术所表达的既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也不是对于某种理想的期待,艺术的真理内容超出了作家有意表述的东西。所以,阿多诺说,第二层次的反思是达到新东西的发动机,通过它能达到传统艺术所达不到的真理内容。
在第二次反思中,艺术要化解第一次反思中所表达的意义。如果我们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来模仿席勒的区分,那么,现实主义类似素朴的诗,而浪漫主义类似感伤的诗。其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包含了第一层意义上的反思。现实主义描述了现实或揭露了现实,而浪漫主义则包含了对于未来的设想。它们都有所指涉,并借助这种指涉表达意义。而第二次反思则剔除了第一次反思中所表达的意义,仿佛要回到素朴的诗的水平上。它具有质朴的特点,却又远远超出了素朴的诗的意义表达。它消解了意义,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了社会的基本关系。我们可以说,它以朴素的形式返回到“现实主义”。这是在扬弃浪漫主义的反思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反思,通过这个反思而返回现实。这是更本质的现实。
在这里,阿多诺以贝克特的作品为例来说明现代艺术的这个特点。在阿多诺看来,贝克特之所以拒绝解释自己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因为他主观上讨厌这种解释,还因为随着反思层次的提升,它的力量和范围也不断地提升。在提升反思的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其所表达的意义也越来越不清晰。在这里,贝克特恰恰是完全意识到他的技术方法,他的戏剧素材和语言素材所意味的东西。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技术方法来消解其中的意思,不是要引导人们去理解他自己的意图,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的这种第二次反思是要促使其他人去思考,而不是要代替别人思考。这就是说,虽然贝克特拒绝解释,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的。其中当然有可解释的东西,但是人们不能满足于这种解释。在这里,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可能是最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作品期待人们的解释,并且期待人们的不断解释。艺术的真理内容又离不开这种解释。如果满足于这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断言。比如,布莱希特的作品就陷入这种困境之中。他让他的艺术作品发挥教育功能,而艺术作品要发挥教育功能必须依赖人们所具有的反思能力。可是如果人们有反思能力,就不需要他的艺术作品来进行教育了。所以,阿多诺曾经嘲笑布莱希特,他是向获救者布道。
第二次反思在化解第一次反思所要表达的意义的时候,又在一定的意义上返回第一次反思,即返回到反思与内容之间的天然联系。这表明,第二次反思和第一次反思一样,也对现实表示不满。如果说第一次反思表现了作品对超越现实的浪漫幻想,那么第二次反思虽然也针对现实,也把“现实”作为艺术作品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已经被转换了,已经被形式化了。在第一次的反思中,现实被进行了理性化的处理,浪漫主义的精神不满足于这种现实。其实,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浪漫主义就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它要把精神所不能控制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之中。在这里,被内化在艺术作品中的现实内容是被理性化的内容。而在第二次反思中,艺术作品与第一次反思一样面对这种内容。但是第二次反思的内容并不是与理性一致,而是批判理性。按照阿多诺对贝克特作品的分析,他是借助于抽象来反抗抽象,借助于理性来反抗理性。正因为如此,阿多诺说:“内容变成了对无所不能的理性的批判。”[1]27现代艺术中的内容不能再按照传统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理解。如果从处理社会素材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次反思“把握住技术方法,即更广泛意义上的艺术语言,但是它的目标是达到盲目性”[1]27。“荒谬”所表达的就是这种盲目性。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艺术语言消解了第一层次的方式所表达的意义。从第一层次的视角来看,这是荒谬的。
当艺术作品用理性来反抗理性的时候,艺术作品的意义就不是传统理性模式所理解的意义。当“荒谬”的艺术用理性来反抗理性,用抽象来反抗抽象的时候,艺术作品的意义也变得不确定了。如果艺术作品没有确定的意义,那么艺术作品就是一个谜,是没有谜底的谜。[1]118如果艺术作品包含了真理性内容,那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就是要不断地解谜。既然艺术作品中包含了真理性的内容,那么这又是确定的;但是其真理性内容并非同一的东西,于是这个真理性的内容又是不确定的。这里存在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作品总是未完成的。艺术作品对于社会材料的运用不是直接告诉人们某种意义,而是要促使人们思考。在这里,社会素材的利用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它比现实主义更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它不是停留在现实的表面现象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远远脱离了现实主义,是纯粹的幻象。现代主义在处理社会素材方面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趋势。
如果从阿多诺处理艺术作品的素材方式来说明艺术作品和社会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阿多诺艺术作品强调的是自律性,虽然其中包含了社会性,但它是去社会的社会性,是扬弃了社会的社会性。当然,在这里,阿多诺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思考艺术作品的,对于他来说,艺术作品应该被用来提升人的反思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某种确定的意义。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