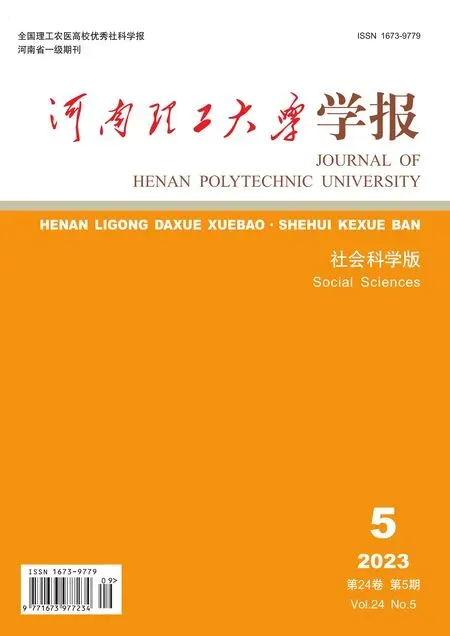焦作市公众的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及影响因素研究
陈 昊,高晓兰,孔娜娜
(河南理工大学 应急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长期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和威胁,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2021年全球自然灾害评估报告》显示:我国自然灾害死亡人口在全球处于较低位置,但洪涝灾害损失的排名高于其他灾害,且在全球洪灾损失中有较大占比[1]。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2016年长江洪灾、2020年7月份长江淮河流域特大暴雨洪涝灾害、2021年7月中下旬河南特大暴雨灾害等,这些洪涝灾害呈现频繁性、突发性、持续性、范围广、致灾性、损失大、季节性等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发展。为此,如何预防、应对洪涝灾害并尽快消除其影响,最大限度地减轻洪涝灾害损失,成为我国政府亟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应对日趋频繁、复杂和严重的洪涝灾害过程中,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局限性逐渐凸显。灾区公众既是灾害受害者,也是参与灾害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探究公众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及影响因素,对于提高公众灾害风险感知水平,促进政府与公众间有效风险沟通,增强应对洪涝灾害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20世纪末期以来,风险感知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然而在集中研究地震、台风、公共卫生事件等灾害,针对洪涝灾害风险感知的研究比较贫乏。王志强等学者在景德镇对719名随机抽样的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2]。通过量化分析得出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洪水经历、洪水知识教育、防洪责任和对政府的信任等因素与洪水风险感知密切相关。刘羿滢等学者对居民的灾害风险感知能力从可控度、熟悉度两个方面进行测评,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得出不同个体特征社区居民的风险感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3]。赵岑等学者,在有限理性视角下,以南宫山景区游客作为研究对象,对游客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进行测评,并提出完善暴雨预警系统、制定应急预案等对策[4]。
通过整合国内外关于洪涝灾害的研究成果发现,学者对于洪涝灾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机理、发生规律、灾后评估、对策建议等方面,关注政府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参与能力的现状较多。在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研究中,鲜有学者从公众个体的角度出发,根据公共危机治理的需要,对公众个体的风险感知展开研究。公众个体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参与能力、参与意识、参与水平等都与其风险感知水平紧密相关。而且目前国内外针对洪涝灾害风险感知专项研究较少,对地震、台风等灾害的相关研究较多。因此,研究公众对洪涝灾害这一灾种的风险感知水平及影响因素具有特殊意义,有利于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完善风险评估体系,更好的减轻灾害损失。
对于风险感知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Gregory和Mendelsohn指出灾害发生的紧迫性、灾害的破坏程度以及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等会影响个人的灾害风险感知水平[5]。Covello和Merkhofer等认为灾害发生可能性、公众对灾害的认知程度、公众的无助和恐惧感等可能对风险感知产生调节影响[6]。周忻等认为个体特征、风险沟通、风险的性质和知识结构是风险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7]。贾宁将影响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分为个体和社会两层面,个体层面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种族等,社会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组织信任、群体心态等内容[8]。薛莹莹提出居民受教育程度、受灾次数、防灾技能掌握程度等都对内涝灾害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9]。
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也会不同[10]。比较流行的风险感知理论视角有心理测量范式[11]、社会文化理论[12]及社会放大风险理论[13]等。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对公众心理、性格等个体层面因素更感兴趣;社会文化理论则将个人与团体结合起来进行风险感知,并认为个人的风险认知程度受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放大风险理论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包括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14],该理论指出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在对国内外有关灾害风险感知因素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公众的灾害风险认知受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综合影响。
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公众的灾害风险感知影响因素主要概括为个体和社会两方面,个体层面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灾害经历、防灾技能掌握能力等,社会层面因素主要包括灾害可控性、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等。为此,提出以下假设,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假设

表2 问卷设计题目
二、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设计
焦作市地处河南省西北,北靠太行山,南靠黄河,是华北富水区,地表水资源丰富,河川众多[15],其复杂的地理位置导致焦作气候多变,时有干旱、暴雨、大风、雷电、冰雹等自然灾害发生[16]。2021年7月中旬,河南省遭遇遭受特大暴雨洪涝灾害,郑州、焦作、新乡、洛阳、许昌、平顶山等地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其中焦作市同样遭受连降暴雨、大暴雨,防汛Ⅱ级响应、Ⅰ级响应,让全市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交叉口黑河水涨、道路严重积水、桥梁涵洞阻断、部分山体出现滑坡落石,这一系列的危害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甚至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焦作市人民政府在加快灾后重建工作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次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导致全市11个县(市)区、110个乡镇共74.45万人受灾[17]。焦作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暴雨洪涝灾害,且其自然地理禀赋在三、四线城市具有代表性,因此论文选取焦作市作为此次研究问卷调查区域样本。
(一)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由3大部分组成。一是问卷填写说明。二是公众个体层面的基本情况调查,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受灾经历、防灾技能掌握能力等方面。三是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社会层面因素测量,主要包括灾害可控性、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等方面。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受灾经历等调查问题主要采用单选形式,防灾技能掌握能力、灾害可控性、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等方面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将回答选项从1到5赋予5等级,如:很不符合为1分、不大符合为2分、一般为3分、比较符合为4分、非常符合为5分。
在2022年5月15日至30日,笔者通过微信、微博、QQ等平台,向在焦作市长期居住的社会公众发放线上问卷220份,收回216份,有效问卷200份,回收率98.19%,有效问卷的个人基本信息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样本数据基本情况
(二)问卷信效度分析
Cronbach’s Alpha系数信度检验是评估问卷内部稳定性指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来说,Cronbach’s α系数为0.700~0.799时,表示量表信度佳;大于0.800时,表示信度甚佳[19]。通过对问卷量表进行检验(表4)。本研究各测量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数值均在0.900以上,表明调查问卷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4 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
效度分析通常指问卷量表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即分析问卷题目的设计是否合理。在效度检验中,若样本数据可进行因子分析,则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20]如表5所示。“风险感知测评”“灾害可控性”“防灾技能掌握能力”“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KMO值均大于0.600,通过检验。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P值均为0.000,(P<0.05),表明水平上呈现显著性,拒绝原假设,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因子分析有效。为此,该量表的建构效度良好。

表5 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结果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一)风险感知整体水平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本文将运用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个体和社会两个难度对上文提出的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公众较高的风险感知易引发非理性决策和从众行为[21]。风险感知过低会使其对灾害风险警惕性不足,引发消极应对行为。如表6所示,焦作市公众对洪涝灾害整体风险感知水平的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1,平均值为3.287。公众对洪灾的总体风险感知在中位数3.000以上,说明公众的认知水平中等偏高,这与近几年焦作市出现一些严重的洪涝灾害相关。公众在经历过洪涝灾害后,对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技能、居住地抗洪减灾设施建设、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及新闻媒介权威性等了解加深,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及危机意识。

表6 公众风险感知水平测评题目得分情况
(二)个体层面相关假设验证
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受灾经历6个因素主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防灾减灾技能因素主要通过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
1.性别因素
根据定类变量“性别”对定量变量进行分组,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在统计学中,根据显著性检验得到P值,一般以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P<0.01为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如表7所示,不同性别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P值为0.844,大于0.05,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不同性别在“对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对生命安全的影响程度”“对物资财产的影响程度”“对正常学习和工作的影响程度”“对基础设施及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的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不同性别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上分析结果一致。为此,我们可以得到,性别因素对洪涝灾害的风险感知并无显著差异。

表7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的P值
2.年龄因素
如表7所示,不同年龄阶段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P值小于0.01,且在“对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等5个维度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1,存在显著差异,即年龄不同的公众对洪涝灾害的风险感知水平不同。
进一步分析可得,年龄较大或较小的公众风险感知较高,年龄阶段居于中间范围的公众风险感知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好。如表8所示,31~40岁及41~50岁两个年龄阶段公众的风险感知均值较低,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公众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较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抗干扰能力较强;18岁以下及18~30岁年龄阶段的风险感知均值相等且最高,其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公众年龄较小且经济基础薄弱、生活阅历较少,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经验不够充分、抗干扰能力最弱;51~60岁及60岁以上两个年龄阶段,同样呈现出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其原因可能是当公众年龄逐渐步入老年年龄区间,对身体以及生命安全将赋予更多的关注,且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公众生活阅历丰富,大多经历过洪涝灾害事件,风险感知呈现较高水平。

表8 不同年龄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对比(平均值)
3.学历因素
由表7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历的公众在“对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等4个维度上的方差分析结果P值均小于0.01,存在显著差异,与受教育程度不同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上的分析结果一致。即学历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学历较低的公众风险感知明显高于学历较高的公众。但学历不同在“对正常学习和工作的影响程度”P值为0.059,大于0.05,无显著差异。可见,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公众正常的学习生活。如表9所示,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公众风险感知水平最低,均值为2.687。其原因可能是该学历阶段的公众,大多接受过系统的公共危机教育,掌握较多获取知识的渠道,能全面了解有关防灾减灾技能知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公众风险感知均值为3.604,风险感知水平最高,其原因可能是该学历的公众大多为18~30岁及50岁以上的公众,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公众风险感知水平本身偏高,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观接受洪涝灾害风险的能力较差。

表9 不同学历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对比(平均值)
4.职业因素
由表7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职业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P值小于0.01,且在“对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等5个维度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1,存在显著差异,即职业因素与感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职业的公众感知水平不同。
如表10所示,公司企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公众风险感知均值分别为2.750、2.815、3.058,风险感知水平较低,究其原因,由于职业因素,这些公众受到系统宣传教育机会较多,社会责任感较强,社会满意度较高,因此抗干扰能力最强;学生、离退休人员的公众风险感知均值分别为3.972、3.889,风险感知水平较高,可能是因为这些职业分类的公众大多为18~30岁及60岁以上的公众,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公众风险感知水平本身偏高,且易受外界环境影响,主观上接受洪涝灾害风险的能力较差,因此风险感知水平较高。其中学生风险感知水平最高,其原因可能是学生大多居于群体环境,易受他人影响,且生活阅历较少,对灾害的认知薄弱,很多知识技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真正面对洪涝灾害时,抗风险能力较差。

表10 不同职业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对比(平均值)
5.经济状况因素
由表7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经济状况不同的公众在“对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等5个维度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1,与经济状况不同的公众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上的分析结果一致,可见经济状况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经济状况越好的公众风险感知越低,抗风险能力越高。
如表11所示,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公众,风险感知最低,均值为1.933,其原因可能是该收入范围的公众经济基础较好,且这一类的公众大多接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受到的系统宣传教育较多,因此抗干扰能力最强;月收入在3 000元以下的公众风险感知均值为3.939,风险感知水平最高,主要是因为该收入范围的公众经济基础较差,洪涝灾害发生后会严重影响公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因此,经济基础较差的公众在风险来临时会手足无措,抗干扰能力较差,从而风险感知水平较高。同时,月收入在3 000元以下的公众大多为学生、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这些职业分类的公众受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抗干扰能力较差。

表11 不同经济状况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对比(平均值)
6.受灾经历因素
由表7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受灾经历的公众在“对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等5个维度上的方差分析结果P值均为0.000<0.010,存在显著差异,与经济状况不同的公众在“风险感知整体水平”上的分析结果一致,可见受灾经历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有过洪涝灾害经历的风险感知明显高于没有风险感知经历的公众。从统计数据可得,没有经历过洪涝灾害的公众风险感知最低,均值为2.300。其原因可能是没有经历过洪涝灾害的公众对洪涝灾害的认知较少,对其破坏程度了解度不够,因此抗干扰能力较强,风险感知水平较低;经历过洪涝灾害的公众风险感知均值为3.671,风险感知水平最高,主要是因为有过受灾经历的公众在灾害发生后,会留下一定的心理创伤,对洪涝灾害的关注度也会提高,从而风险感知处于较高水平。
7.防灾减灾技能因素
对公众防灾技能掌握能力平均值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034 9(表12),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公众的防灾减灾技能越好,对洪涝灾害越了解,风险感知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

表12 防灾技能掌握能力与风险感知水平的相关性
如表13所示,公众对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技能了解程度一般偏高。其中公众对“洪涝灾害形成原因及规律”“应急技能”了解程度较高,对“预警机制及预防对策”“次生灾害及破坏程度”的了解程度一般、对洪涝灾害“防灾减灾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为此,在提高公众风险感知水平、增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过程中,要注意重视公共危机教育,提高公众对洪涝灾害等各类灾害的了解程度。

表13 防灾减灾技能因素不同指标对比(平均值)
(三)社会层面相关假设验证
社会层面的灾害可控性、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3个因素,主要通过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下面将社会层面的3个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量化关系进行验证:
1.灾害可控性因素
对灾害可控性平均值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164(表14),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公众认为灾害的可控性越高,风险感知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

表14 灾害可控性与风险感知水平的相关性
如表15所示,公众认为洪涝灾害整体可控性居于中等偏高状态。其中公众认为“控制准确预报”“控制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高,“控制伤亡情况”“控制经济损失”“控制公众心理恐慌”的可能性一般。为此,在提高公众风险感知水平、增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努力提高洪涝灾害的可控水平,尤其提高控制公众心理恐慌的能力,拓宽公众获取灾害信息的渠道,加强对各类新闻媒介渠道的监管力度,从而有效降低公众的经济损失,减少灾害对工作、身心健康的影响程度。

表15 灾害可控制性因素不同指标对比表(平均值)
2.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因素
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平均值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349(表16),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政府危机治理能力越强,公众的满意度越高,风险感知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

表16 政府危机治理能力与风险感知水平的相关性
如表17所示,公众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满意度较高,居于中等偏高状态。其中公众对“灾害预警情况”“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政府灾后安置工作”的满意度较高;相对平均值,公众对“防洪减灾工程完备情况”“社会组织作用”满意度较低。为此,要注重提升危机治理的应对能力和工作效率、注重灾后救援与补助工作,强化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及时发布灾害相关信息等工作,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

表17 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因素不同指标对比(平均值)
3.周边环境影响
对周边环境影响平均值和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598(表18),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公众越容易受周边环境影响,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表18 周边环境影响与风险感知水平的相关性
如表19所示,公众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一般,尤其容易受到周边认识人伤亡情况的影响。相对平均值,“周边朋友的恐慌”“应急物资抢购现象”“周边停工停课现象”对公众影响的平均值较低。由此可见,公众在新冠肺炎、洪涝灾害等大环境背景下对灾害的相关信息具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且洪涝灾害预警情况、报道情况较为官方权威,从而公众受周边环境影响的程度相对较低。为此,在提高公众风险感知水平、增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过程中,要注意从新闻媒介、公共危机教育、社会组织宣传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提升公众对洪涝灾害等公共危机的熟悉度,提高公众对各种危机情况的辨别能力,从而将公众对灾害的风险感知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

表19 周边环境因素不同指标对比表(平均值)
(四)回归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用来研究一个自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否给因变量造成了显著差异和变动。相关分析则是用来表明现象是否相关、相关方向和密切程度,不能指出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而回归分析可以通过一个数学模型来表现变量之间相关的具体形式。因此,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回归分析。根据所选定的数据指标,最终将风险感知整体水平确定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灾害经历、灾害可控性、防灾技能掌握能力、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分别为自变量X1、X2、X3、X4、X5、X6、X7、X8、X9、X10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变量Y与X的线性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
线性回归满足条件:
(1)本研究调整后R2达到63.4%(表20),说明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变化的63.4%都可以由参与本次研究的自变量所解释。由德宾检验得到数值为1.660,接近于2,各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满足相互独立条件。

表20 模型摘要表
(2)通过绘制样本数据观测量累积概率P-P图,如图1所示,从左下到右上的样本数据所呈现的散点基本呈直线趋势,由此可以认定样本分布基本上服从正态分布。
(3)由标准化残差图可得(图2),残差基本在0的上下绝对值距离为3的范围内波动,且上下随机分布,没有规律,无异常值,满足条件。

图2 标准化残差图
数据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条件,以进入值为0.10,踢出值为0.15展开逐步线性回归。从以下的ANOVA表(表21)中可以清晰看出,P=0.000<0.05,说明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只要有一个就能够显著影响因变量洪涝灾害整体感知情况。那么为了进一步判断具体是那几个自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因变量,还需要继续分析表22。

表21 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

表22 回归模型系数表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回归系数表22,表中主要呈现出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检验数据,同时通过该表得出模型中5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4.229、0.292、-0.103、0.140、0.041,将其分别代入线性回归模型,即可得到回归方程:
Y=4.229+0.041X4-0.103X5+1.033X6+0.140X8+0.292X10
从建立的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都为0时,常数项系数即整体感知情况为4.229,且月收入与因变量为负相关,灾害经历、周边环境、灾害可控性、职业与因变量为正相关。其中,灾害经历与周边环境的P值为0,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547、0.310,影响较大,其他因素影响次之。
综上分析,将个体层面的7个因素及社会层面的3个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量化关系验证结果进行总结(表23)。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可以证明假设2~9均成立;另外,在相关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回归模型,可以证明,在假设1~10综合作用时,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假设4、5、6、8、10。
四、结论与建议
(1)通过对焦作市公众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及影响因素探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个体层面。性别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并无显著性差异;年龄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年龄较高或较低的公众风险感知较高,年龄阶段居于中间范围的公众风险感知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好;学历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学历较低的公众风险感知明显高于学历较高的公众;职业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职业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不同;经济状况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较好的风险感知较低,抗风险能力更好,反之则风险感知较高,易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受灾经历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过洪涝灾害经历的风险感知明显高于没有风险感知经历的公众;防灾减灾技能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公众的防灾减灾能力越好,风险感知水平越低。第二,社会层面。灾害可控性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具有相关性,公众认为灾害的可控性越高,风险感知水平越低;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具有相关性,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越强,公众的满意度越高,风险感知水平越低;周边环境影响因素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之间具有相关性,公众越容易受周边环境影响,风险感知水平越高。
(2)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包括难以控制的个体特征因素以及防灾减灾技能、危机治理能力、周边环境影响等可控制因素。这些因素并非单一产生影响,而是相互作用。为此,需要注重从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等多元主体着手,采取系统性、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进行应急宣传教育,要根据不同群体和特征差异,开展信息传播和风险沟通,从而有效提高公众对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的科学认知及应急技能。第二,公众对洪涝灾害治理工作的满意度反映出其对政府的信赖,是衡量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公众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为此,不断提升政府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和工作效率、加强社会保障工作也至关重要。第三,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一方面,要注重增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既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也可以保护弱势群体,开展慈善活动等。另一方面,应积极发挥官方媒体以及应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公众容易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官方媒体和应急专家学者的正确宣传与引导至关重要,可有效预防不良舆论的发生和蔓延,推动全社会合力应对洪涝灾害。第四,做好灾前预警、防范工作。灾害的可控性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以及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我国的应急管理能力逐渐提高,对洪涝灾害等灾害事件的控制能力也不断增强,但还存在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如不断加强防洪减灾工程的规划建设、提高灾害预警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