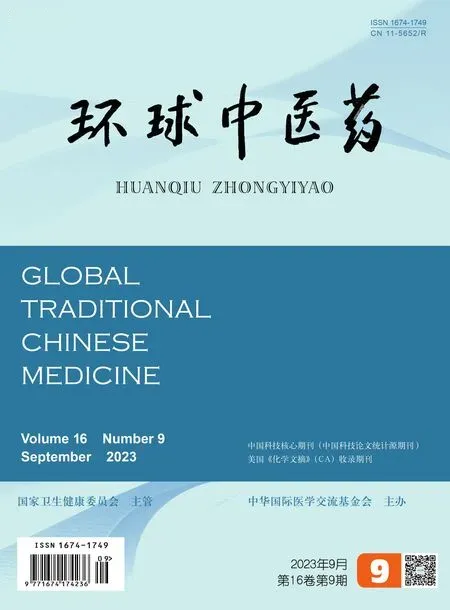从《医宗必读》《里中医案》探析李中梓治喘学术特色
刘颖儒 林伟兰 叶玲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其一生重视中医理论研究,兼取众家之长,论述医理多能深入浅出,著书颇多,且多通俗易懂,在中医学的普及方面作出较大贡献。《医宗必读》为李中梓所著综合性医书,全书共10卷,集理、法、方、药于一体,是其代表作之一;《里中医案》为记载李中梓医案的著作,共收医案50多则,不分门类,大多为内科杂病疑难治案。
喘病是肺系常见疾病之一,由外感或内伤等因素致肺失宣降而肺气上逆或气无所主而肾失摄纳,以喘促短气、呼吸困难为主要特点。西医学中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炎、肺源性心脏病、心源性哮喘属于本病范畴,可参照本病辨证论治[1]。喘证涉及疾病众多,病因病机复杂,而中医的独特辨治体系,因证施治,治病求本的理念在喘病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与可观的疗效。明末医家李中梓以博采众长,立论平正为特点,其治病灵活不拘古法,治学严谨且著书颇多,其著述常多考诸家观点,结合自身经验加以合变,多给人以新的启发。在喘证的治疗中,李中梓亦有其独到见解,今笔者引用《医宗必读》及《里中医案》中治喘相关的论述及其治喘数例医案并总结其涉及方剂与治法(见表1),试探析李中梓治喘学术特色,以求为喘病的临证治疗扩充思路。

表1 《医宗必读》《里中医案》喘证医案整理
1 李中梓治喘辨证特点
1.1 辨喘尤急,首辨虚实
在《医宗必读》中,李中梓指出其时医家治喘之弊端:时医一见喘,多以实证论治而纯行破气,见喘止喘。李中梓认为喘家“究不越于火逆上而气不降也”,病机虽总属肺气不降,但病因繁多,证机复杂,非止实喘一证,现代研究亦表明喘病证型分布并不单一[2-3]。而针对时人见喘咳上气者而以“气有余”作论攻实破气的现象,李中梓借王海藏语“肺气果盛,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皆以火烁真气,气衰而喘,所谓盛者,非肺气也,肺中之火也”表明此之“气有余”非肺气之有余,而指邪气盛实,肺气亏损,当属脏腑元气不足的“少气”虚喘证,指出治喘辨明虚实的重要性。
《素问·调经论篇》云:“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概括出喘证分为虚实两类。东汉张仲景亦在《金匮要略》“上气”篇中将喘分虚实论述。至元代《丹溪心法·喘》[4]中亦记载:“六淫七情之所感伤,饱食动作,脏气不和,呼吸之息,不得宣畅而为喘急。亦有脾肾俱虚,体弱之人,皆能发喘”,总结出辨喘当分虚实两端。明末医家张景岳[5]指出气喘之病“欲辨之者,亦惟二证而已。所谓二证者,一曰实喘,一曰虚喘也”,首次明确指出虚实为辨喘之总纲并沿用至今。李中梓沿用辨喘虚实之总纲,并补充道“辨证不可不急,辨喘证尤为急也”,认为喘病病因复杂,虚实难辨,治失其要易贻误病机甚至发为喘脱,故临床辨证需迅速而准确。
1.2 治病求本,重视脾肾
李中梓认为“病不辨则无以治,治不辨则无以痊”,强调审查病机的重要性。此外,李中梓传承李东垣以脾胃立论的思想,著“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强调调补脾肾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如《里中医案》有一案:相国杨文若,病痰喘苦楚伴有善饥而不能食,服用清气化痰丸病情未减。李中梓诊后示病患形体肥胖,善饥而不能食是其胃强而脾弱,以六君子汤加苍术、南星、姜汁健脾益气消痰,从脾治喘,服数剂后脾健痰消气行则喘止。就脾胃之病,李东垣言“脾胃具旺,能食而肥;脾胃具虚,不能食而瘦”“不能食皆作虚论”,李中梓之论脾胃多遵从李东垣之法。本案杨文若患痰喘而不能食,虽经服清气化痰却病未向愈,可见本证不能单以实邪痰喘作论。脾为生痰之源,脾弱不能胜湿故出现痰喘,故李中梓以六君子汤健运脾气、除湿消痰,从疾病本源入手以使病瘥。再有《医宗必读》中医案:朱宁宇,多痰喘急,可坐可俯不可仰,李中梓诊其两尺独大而软,遂以地黄丸一两,佐以桔梗、枳壳、甘草、半夏,煎汤送下,不数剂而安。《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记载:“左右尺脉沉取无力为肾虚”,李中梓诊其脉两尺大而软,结合其多痰喘急的表现,辨为肾虚于下,痰阻于上的上实下虚证,遂以地黄丸补肾治本,兼施以枳壳行气除满、半夏燥湿化痰、甘草补脾和中、桔梗载诸药上行以达病所,共奏上下同治之功而使病愈。
综上,李中梓治喘强调辨证求因,治病求本,同其他诸多医家一般重视脏腑辨证的运用,不单以肺病论治——如李东垣认为喘病可因脾胃气虚,阴火上冲犯肺而喘,并善于运用中土五行思想从脾胃治喘[6]。清代医家叶天士治喘多用温法,结合脏腑辨证,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就喘病治法提出温肺、温胃、温肾等法[7]。近代医家张锡纯治喘主张不滥用止咳平喘之套药,注意纳肾气、降胃气、疏肝气,深究喘之本因,以求标本兼治[8]。而李中梓脏腑辨证思想根源于易水学派,尤其重视脾肾作用[9],明确提出“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认为脾肾有相赞之功并在喘病的证治中贯彻这一理念。王雨等整理分析《里中医案》中李中梓遣方用药规律得出其用药具有偏于补益,脾肾双补的特点[10]。笔者认为,李中梓在喘证治疗中所求之“本”不仅是致病之本源,还包括人的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正如其在《医宗必读》中记道:“独举脾、肾者,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随着现今人们起居失常、饮食失宜情况日益普遍,人之先后二天多有受累,李中梓治喘重视脾肾先后天的理念对如今临证辨治具有重要意义。
2 李中梓治喘施治特点
2.1 实喘攻邪,兼顾正气
对于实喘证的治疗,李中梓多在祛邪之余兼有补益,以固护正气或防止药伤。如《医宗必读》中医案:张饮光发热干咳,呼吸喘急,先后服用苏子降气及八味丸未效,喘反益急。李中梓观其两颊俱赤,诊其六脉数大,遂以肝肺蕴热,木火刑金治之,运用逍遥散加牡丹皮、薏苡仁、佩兰等清肝利肺。此外,李中梓还以麦味地黄丸与龟胶等滋阴之品,益肺之源以生肾水,防止肝肺火蕴日久伤阴[11]。然金元医家张从正认为:“治病有先后,不可乱投,邪未去时,慎不可投补”[12],只恐补而留邪反而耗损正气,而李中梓祛邪同时兼有补益的思想似有别于张从正理念。对此,李中梓于《医宗必读》言:“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但著书立言则不及耳”,指出张从正亦非纯用攻伐。对于实邪致喘,李中梓少佐补益以防祛邪伤正的做法亦正合叶天士“先安未受邪之地”的理念。针对实喘有邪,现多以温宣、清泄、化痰、降气等法[1],但祛邪之余恐伤正气,实邪易祛虚体难补,故临床治喘以祛邪利气之余可考虑少佐补益以防伤正。
再有文学顾明华一案:喘嗽十年之久,百药无功,李中梓诊其脉见两寸数而涩,法当纯攻其邪却遍治无功。李中梓指出应该以吐下之法祛邪外出,但需要补养月余以助患者正气,以达扶正祛邪之功。半年期间,行吐下十次而补剂已服百余,病乃愈,后期更已补中益气丸加减经年服用,不再复发。《素问·刺法论篇》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并由此而衍生出“扶正祛邪”的治则,广泛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活动[13]。此案中顾明华病十年之久,痰凝必是根深蒂固,当须行吐下之法给顽邪以出路,然病程迁延正气必有所伤,故李中梓先于吐下扶助正气,再施吐下以除痰饮窠囊。
针对虚实夹杂证候,李中梓更加注重正气的固护,正如《张氏医通》中提到:“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于害……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也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笔者认为,临床治疗实邪致喘之时祛邪之余需注意正气是否虚损或峻药是否伤正,应了解到正、邪的发展情况,何以祛邪而不伤正,何以扶正而不敛邪,都需要临床细细体会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2.2 虚喘补益,勿求速成
对于虚喘证的治疗,李中梓善用补法,且往往予以较长疗程以使病瘥。如在《里中医案》王征明一案中,病患喘咳吐血十余年,求诊李中梓,诊断其喘咳日久肺脏亏虚又外感风邪,予其薄荷、苏子外散表邪兼以定喘,人参、麦冬以补肺润肺,降肺中伏火以止咳血,再以橘红、茯苓、甘草等培补后天之本,患者服药长达三月而除病根。再有医案:王邃初患哮喘二十年,李中梓先后予丹溪治哮丸与六君子汤,患者连服经年才得以痊愈。
关于虚喘证的治疗,李中梓言:“治实者,攻之即效,无所难也。治虚者,补之未必即效,需转折进退,良非易也。”观其医案亦可见李中梓认为虚喘患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今医者关于虚喘证治疗亦同于此理念,认为虚喘为气失摄纳,根本不顾,补之未必即效,且易感邪而致反复发作,致使病情迁延难愈,故对虚喘应持之以恒地调治[1]。笔者认为,不论在疾病治疗还是科研设计中,治疗周期的合理与否往往关乎着最终的效果。冯超男等[14]指出中成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临床研究存在着方法学问题,而目前没有相关标准来界定中药治疗喘证的疗程设计合理与否。李中梓在虚喘证治疗中采取较长治疗周期以使正气充养的学术思想可对当今喘证的治疗及相关临床研究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3 重视本元,多用温补
从天地元气入手,李中梓在《古今元气不同论》中运用邵雍的元会运世说,从大周期的角度阐释历代医家用药的变化,认为伴随着元会运世大周期的推移,天地气化渐薄,人们所能接受到的元气也愈来愈弱[15],故主张多事调养而专防克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如在《医宗必读》医案:宋敬夫令爱,其人中气素虚,仲春忽然喘急,后出现昏不知人,病情危急。李中梓辨其证属气虚之极,须施以大温大补治之。遂以人参一两、干姜三钱、熟附子三钱、白术五钱,一服即苏。后服人参七斤余、姜附各二斤,全愈不复发。社友孙芳其令爱案:久嗽而喘,一日喘甚烦躁,视其目则胀出,鼻则鼓搧,脉则浮而且大,李中梓言肺胀无疑,以越婢加半夏汤投之,一剂而减,再剂而愈。嘱以参、术补元,助养金气,竟因循月许,终不调补,再发而不可救药。再有《里中医案》医案:邑宰夏仪仲太夫人,发热头痛,医以伤寒治之,后出现气高而喘。李中梓辨其中虚作喘,用人参、黄芪、附子等补气助阳,后总计用参二斤而安。
以上医案李中梓均予大剂人参以补养元气,并强调病后调补对疾病最终转归的影响。李中梓顾元气、多温补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金元之后,时医多用苦寒滋阴之品,为纠时弊,逐渐形成了固本培元的新安学派及以温养补虚为旨的温补学派。刘珍珍等[16]发现两派均以善用甘温之品补虚为临证特色,均重视元气、脾肾、命门的作用。李中梓继承并发展温补学派,于《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中提到:“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强调了阳气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的重要性。陈瑞杰等[17]通过总结李中梓内科疾病用药规律亦发现其用药多温补的特点。吴凯文[18]通过研究士材学派医家养生思想,指出士材学派医家重视病后调摄,在疾病后期,症状缓解之后,注重继续用药调理,使正气得复,达到病后防复的目的。综上,李中梓治喘病好以参、术等温补药物调养,注重病后调摄,重视本元,认为“元气不足者,须以甘温之剂补之,如阳春一至,生机勃勃也”,反对“惟知尽剂不顾本元”的做法。
2.4 临证炮药,服法考究
李中梓认为临证用药不该照本宣科,感叹“用药之难,非顺用之难,逆用之难也。非逆用之难,逆用而与病情恰当之难也”。临床治病过程中,若辨证准确却用药无功,或许可从用药用法方面寻找突破。如《里中医案》中:周洱如,伤于拂郁,胀满喘嗽,左寸大而滑,右关弱而沉,李中梓诊其病机属脾虚阳亏,法当参、附,然曾服参、附后病情加重。对此,李中梓同样施以参、附,但以寒凉之品秋石、黄连、薄荷佐制人参、附子、橘红温燥之性,用行气之功的白蔻制白术以防中满,并加入行气利络之沉香、通草等,服后转效。此案中李中梓便是通过炮制药物的方法解决了补益药在喘闭证中助壅的弊端。姚静等[19]指出通过中药临方炮制可以减少或者消除药物的不良反应并一定程度上改变药物药性,抑制方中主药对人体的不良反应并突出临床所需要的治疗效果,同时提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殷桃花[20]亦指出使用经正确炮制的药物进行治疗能够有效减轻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
再有《医宗必读》医案:给练黄健庵,中气大虚,发热自汗,喘急。李中梓诊之脉大而数,按之如无,辨其内有真寒,外有假热,法当温阳散寒,遂予理中汤冷饮以达病所。此案中李中梓通过改变服药方式以达到防止药物格拒的效果。中药的服法始终是历代医家治疗疾病的切入点之一,如清代医家徐灵胎,其治疗上盛下虚之痰喘,因恐人参增上焦气壅之弊,故人参切块吞服,以达到使药力缓发以扶助下焦之气的效果[21]。中药服法贯穿于中医药传承过程,诸如服桂枝汤需啜热稀粥,参苓白术散需用枣汤调服,失笑散要用黄酒或醋冲服,止嗽散需以生姜汤调下等等都体现历代医家对中药服法的考究。正如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所言:“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
李中梓注重药物的炮制及服药的方法,在其所著的《内经知要》中记道:“服药有徐疾,根梢有升降,气味有缓急,药剂有汤丸膏散,各须其法,无越其度也。”然而在现代临床工作中,中药服用方法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这一中药特色和优势,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张立双等[22]亦指出目前中药汤剂在临床使用较为随意,缺少相应的规范及标准。笔者认为,中药的临证炮制以及服药方法均是需要传承并发展的中医药特色之一,应重视中药临证炮制思想与中药传统服法的传承与创新,临证结合中医辨证论治,做到合理用药以提高临床疗效。
3 结语
李中梓论治喘,唯精通医理,辨证思变,举一反三方不愧为明通。其在喘病辨证时,强调辨喘尤急,当首分虚实;审查病机应严谨以求治病求本,同时重视脾肾二脏。在喘病的施治中,李中梓认为治实喘祛邪之余要固护正气,治虚喘施以补益应予足疗程勿求速成;治喘重视人之本元,多以温补药物调摄病后虚体;用药应考究,重视服药方法及药物临阵炮制以达更佳疗效。李中梓淹通众家之长而不偏倚,著书颇多,临证经验丰富,然对于喘病的证治着墨不多,故笔者撰文分章析句以试述其意,以求抛砖引玉,望诸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