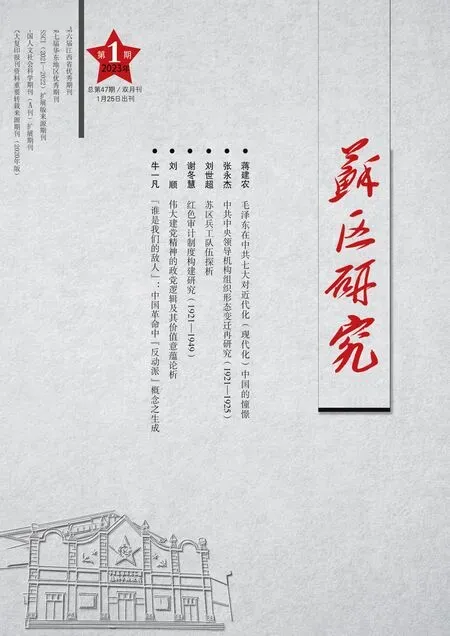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形态变迁再研究(1921—1925)
提要:作为中共组织体系的大脑,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形态的变迁反映了时局变动与中共组织的调适。从中共组织建设进程来看,1921—1925年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名称和结构上,呈现为从中央局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单层继替、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的组织合体到三层复合结构;在性质上,呈现为从临时性到正式性、特指性到泛指性、单层性到多层性的变迁轨迹;在成员构成上,呈现为由知识分子为主体向工人为主体的变动,且成员南方化趋向明显;在驻地上,呈现为以上海为中心,北迁南往的特点,且驻所主要分布租界内或租界与华界交界地带。这既反映了“作始也简”的初创形态,也因承了近代革命群体和革命重心偏南方的轨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多次更名、调整、改组、发展,渐趋科学、合理。学界关于早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1)相关研究成果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王健英的《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朱泽春的《中共一大会议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再考证》(《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占善钦的《中共一大到六大对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伍小涛的《中共“一大”前党员的知识谱系学考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易凤林的《中共的革命指向与知识分子的革命自觉(1921—1927)》(《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等。主要聚焦于党的代表大会、机构名称及人员构成等方面。为更好探究其组织形态变迁的内在理路,需对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释: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局还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如何由特指转换为泛指?临时性的中央局如何向正式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过渡?中共二大前后的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如何?中央局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如何合体?中央领导机构驻地与成员构成有何变化?等等。笔者利用已出版的中共组织史资料,并结合相关档案文献,试图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的临时性与特指性
(一)中央领导机构的单一性与临时性
关于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长期以来众说不一。有学者提出选举的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2)王健英提出,大会选出的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与张国焘、李达会合后,组成党中央常设机构——中央局,由于执行委员会只有三人,因此同时兼中央局委员,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局。,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央局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3)朱泽春:《中共一大会议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再考证》,《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132页。两种观点虽均主张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弱化了中央局的地位。在名称上,与前述观点不同,来自苏联的一份档案记载是第一届中央委员会。(4)李蓉:《中共一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页。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提出,“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此观点的显著变化在于,中央局为中共一大设立的中央领导机构,但性质上又是临时性的。甚至有资料提出,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便成立了临时中央局,(6)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较前者提前了近一年。综合现有资料来看,笔者认为中共一大选举的临时性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局。但关于中央局成员构成,一般认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即“三人说”。此说虽渐成公论,然争议仍索绕其间。不乏有“四人说”“五人说”“六人说”“九人说”等,概言之,不外乎“正式委员说”和“候补委员说”。其中,“三人说”和“四人说”属前者范畴,“五人说”“六人说”和“九人说”属于两者组合范畴。还须说明的是,不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档案资料,其对中央领导机构的称谓有时是(临时)中央委员会,有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时是中央局,没有统一名称。(7)从部分报告和回忆来看,中央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混用,使用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较多,共产国际、联共(布)一般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临时性领导机构,中央局具有特指性,这要与中共五大前后的泛指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加以厘清。
(二)中央领导机构的特指性
中央局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雏形,具有特指性。1921年11月,中共就以中央局名义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8)《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1921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7页。是时,中央的通告或指示多是以中央局或中局的名义下发的,如1923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登的《中局报告》和1924年6月1日出版的该报第四号刊登的《中央局报告》。(9)《中局报告》(1923年11月)、《中央局报告》(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86—188,251—255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亦效仿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临时中央局,派代表施存统参加中共二大。可见,中央局成为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主要领导机构。
在中共早期,有3个特指性的中央局,分别是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局(1921.7—1922.7)、中共三大产生的中央局(1923.6—1925.1)和中共四大产生的中央局(1925.1—1927.5)。中共四大时,中央局逐步发展成为中央三层领导机构的中间层;至中共五大时,中央领导机构全面调整,中央局的角色和职能为政治局所取代,性质上由特指性转变为泛指性,数量上由一变多,它也结束了中央机构的使命,发展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
(三)中央局成员南方化、知识分子化倾向明显
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形态不仅体现在名称、性质和结构层次上,还体现在成员的学缘、地缘、业缘等方面。中共一大时党员和大会代表总体呈现知识分子化和南方化,继而塑型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58人,南方地区49人,占比达84.5%。(10)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从大会代表和中央局成员的籍贯或出生地来看,13名代表中,除王尽美为山东人,其余全部来自南方地区,占比高达92.3%。在两个基数之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成员3人,均为南方地区。具体来看,陈独秀1901年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6年创办《青年杂志》,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总司令”,(11)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第53—55页。在学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李达是教授身份,也有留日背景,从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与宣传,被誉为“红色教授”“理论界的鲁迅”。(12)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第70页。而张国焘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总体来看,中央局成员是由有一定年龄差、来自南方地区、从事理论宣传和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组成,理论化色彩较浓。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革命思想接受最为自觉,响应最为热烈,成为建党创始人和地方组织的开创者,并在中共组织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13)易凤林:《中共的革命指向与知识分子的革命自觉(1921—1927)》,《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第69—70页。中共一大时,党员总数和大会代表中,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占比分别达到92%和100%,(14)《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锋和主体创建和起步的。
随着中共组织发展和革命情势变化,临时性的中央局向正式性的领导机构转变成为必然。但这种转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另一个临时性机构的短暂衔接过渡,虽然衔接过渡的痕迹不是很明显,但仍是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形态变迁的重要环节。
二、中共二大前两个临时性领导机构的短暂过渡
中央局未转变为中央派出机构前,经历多次调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从中央局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单层继替。作为临时中央领导机构,待条件具备后,中央局必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过渡。而过渡的基本条件是党员人数达到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进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数量达到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
(一)中共一大党纲关于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与组织发展
俄文译稿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1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如果说党员超过30人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应然条件,那么,“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16)《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页。就成了必然条件。与俄文译稿相比,英文译稿除个别译法的差异,在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是一致的。(17)陈公博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127页。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各共产主义小组及旅法、旅日小组党员有58人(18)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人数,长期以来有多种说法,大致有53人说、56人说、57人说、58人说、59人说等,本文采用58人说。,达不到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甚至党员人数最多的北京也仅有16人,当时上海14人、武汉8人、长沙6人、广州4人、济南3人、旅法5人、旅日2人,(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29—30页。远未达到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按照中共一大党纲规定,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和旅法小组具备了成立地方委员会的人数标准,但还不具备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名义发出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20)《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1921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7页。。
经过半年多的发展,到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到,党员人数共计195人,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21)《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此时,陈独秀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报告的。这引出了前后接续的两个问题,即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是何时达到的,又是何时成立的?进而又诱发出另外两个问题,既然中共二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么,中共二大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存在与否、性质如何?
(二)各地党组织的对标转型
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从考察各地党组织转型着手。中共一大后,在没有达到成立地方委员会或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条件下,地方支部成为最初组织形态。各省区从设立支部、地方委员会到成立地方和区执行委员会,存在时空差。1920年10月,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年底成立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27—28页。翌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刚结束,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有委员3名、候补委员2名,范鸿劼任委员长。(2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93页。武汉支部成立于1920年9、10月间,包惠僧任支部书记,(24)《回忆党的创立时期》,《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1921年秋成立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翌年初夏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1921年8月成立的广东支部隶属中央局,谭平山任书记,到1922年6月,有党员32名,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约于6月间,建立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又称粤区执委)。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有党员10余名,到年底,发展到20多名。(2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560—582、374页。1922年5月底,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党员发展到30多人。(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济南地区党组织发展相对较晚,1923年改为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2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195页。而旅莫支部方面,到1925年1月,改为中共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2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696—697页。
中共最早组织(29)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等名称都有,陈潭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中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在上海。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3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8月,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定名为共产党,同月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1月,又创办《共产党》月刊、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31)《中共上海党志》编委会编:《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1921年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3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直属中央局领导。上海早期党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负责筹备中共一大的具体工作。中共成立后,中共中央长期驻扎上海,且与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密切关联,有地利、人和之便,呈互融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央局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升级版,且中央也曾委托上海地方委员会代行区执行委员会的职权,(33)《中共上海党志》,第97页。所以上海早期党组织相较于其他地区,有前沿性和先行性的特点。1922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有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徐梅坤任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34)《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39页。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没有建立支部,而是直接建立上海地方委员会,然后发展到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
(三)制度设计层面的组织标准再调整
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可从制度设计和实践执行两个层面探究。在制度设计层面,建立地方委员会的标准是党员5至30人,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是超过30人,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是党员超过500人或者成立5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35)《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译稿)》(19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而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名义发出的通告,恰好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中共二大召开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假定限于特定时空条件,按照党员发展标准和速度,短时间内党员较难突破500人,且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势在必行,而组织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又是短时间可以达到的。但通告没有要求成立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而是成立5个区执行委员会。与之相矛盾的是,中共一大党纲只规定了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而没有规定成立区执行委员会的标准。由此推断,区执行委员会是中共一大后新提出的一级组织,陈独秀此时要么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与区执行委员会的标准等同,亦或将地方执行委员会标准的升格为区执行委员会的标准,两者标准尚比较模糊。
中共二大党章对此给出了答案,其规定党员入党“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36)《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而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是一个地方有2个以上支部,组织区执行委员会的标准是各区有2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37)《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7页。相较于中共一大党纲,中共组织体系更加明晰、建立标准更加具体。由此进一步推断,成立区执行委员会的想法应产生在中共一大结束后,成型于中共二大召开前,定制于中共二大。
(四)实践执行层面的临时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短暂过渡
在实践执行层面,中共一大时不论在党员数量还是在地方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数量上,都未达到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条件。1922年5月,有上海、湖南两地党组织改组为地方执行委员会,广东在6月改组为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在中共二大刚结束就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而武汉在1921年秋成立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是最早成立地方执行委员的党组织,进而在1922年初夏又成立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换言之,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后,有武汉、上海、湖南、广东、北京等五个地方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或区执行委员会,在地方执行委员会数量上基本达到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标准,为中共二大选举正式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奠定了基础。但陈独秀在1922年6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和6月30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均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可以推断,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局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在1922年5月底至6月间。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共二大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临时性的还是正式性的。中共一大党纲规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38)《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俄文译稿)》(1921年),《“一大”前后》(一),第8页。。陈独秀在中央局通告中也指出,“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39)《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1921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7页。。由此可知,陈独秀寄望于中共二大时成立正式中央委员会,在会议召开前,尚不能完全具备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条件,但根据党纲规定,应(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可以推定,中共二大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是按照中共一大党纲规定,在尚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雏形。
三、中共二大实现中央领导机构从临时性到正式性的单层继替
如前所述,如果说中央局和中共二大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均具有“临时性”特点,那么,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则完成了从“临时性”向“正式性”的转换。
(一)正式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单层继替与正式候补组合结构的形成
中共二大党章将党的组织体系分为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四级,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5人组织,并选举候补委员3人。(40)《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中央领导机构不仅如期实现首次转换,还形成了由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组合结构。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为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张国焘和蔡和森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4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1页。与中共一大相比,除了名称变化,人员实现了变更和增加。李达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其负责的宣传工作由蔡和森负责。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五人名单,有多份材料述及,但具体人员略有差异。陈独秀说是“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42)《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张国焘说“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和组织职务”(43)李蓉:《中共二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马林记载的是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44)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蔡和森在报告中说是“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45)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1926年),《“二大”和“三大”》,第489页。,瞿秋白在报告中说是“独秀、和森、国焘、仲夏、君宇”(46)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节录)》(1929年),《“二大”和“三大”》,第519页。。有争议之处在于李大钊和邓中夏的正式委员身份。尽管多人的报告和回忆,没有提及李大钊的正式委员身份,但也有资料提出相佐意见。有资料提出其虽未出席会议,但当选为中央委员。(47)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页。也有人提出其是正式委员,邓中夏是候补委员。(48)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与陈独秀被誉为“南陈北李”,其思想和地位影响毋庸多言。然就组织内身份而言,其思想要先于组织。中共一大时,“由于领导北京教职员的索薪斗争”(49)《李大钊年谱长编》,第352页。,其未能出席一大,也未当选中央局成员。中共二大时,李大钊是否参加和当选?从目前资料来看,笔者认为,李大钊未参加中共二大,但当选了候补委员。这一论断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中共二大召开前两天,其出席北京教育会召开的临时评议会,因故未出席中共二大。(50)《李大钊年谱长编》,第373页。张国焘也讲到,大会闭幕后不久,马林回到上海,李大钊这个时候也到达上海,中央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二大,马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51)张国焘:《我的回忆(节录)》(1971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50页。其二,马林、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都没有提到李大钊是正式委员;在西湖会议上,马林曾主张增加李汉俊和李大钊为中央委员;(5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1926年),《“二大”和“三大”》,第489页。中共三大时,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进一步佐证了其当选候补委员的可能性。而且,中共三大前夕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在杭州会议上“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53)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42页。,“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开滦]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指出实际上“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待在一起”(54)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46页。。其中的邓同志,即邓中夏。陈独秀稍早把邓中夏作为中央委员,后又把李大钊当作中央委员。这种差别,很可能与时间远近和交往疏密程度有关。陈独秀不提中央执行委员会,而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报告,一方面,可能受到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共同影响。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文件多用中央委员会,(55)《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80页。维经斯基等在信函中也曾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6)《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17页。;另一方面,在党际交往方面,用中央委员会便于对等统一,且中央执行委员最终被中央委员会替代。
关于候补委员,有人认为是李大钊、向警予、张太雷,有人认为是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有人认为是李大钊、向警予、李达,也有人认为李大钊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李达为候补委员,还有人认为没有选举候补委员。(57)转引自《中共二大轶事》,第160页。综合来看,笔者认为,除了李大钊外,还有向警予和李汉俊。一方面,妇女工作重要性越加显现,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决定中共在尽快时期内设立妇女部,在机关报中设妇女专栏,(58)《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4页。妇女工作明显加强,急需女性干部;另一方面,李汉俊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曾负责上海党组织工作,中共二大召集他到会,他未到会,但写了一封意见书,(59)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1926年),《“二大”和“三大”》,第488页。且中共三大时,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6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5页。这增加了其当选的可能性。
(二)中央领导机构的“北迁南往”与成员构成的“微调”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驻地问题一直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间的争论点。在中共早期,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北京、广州为两翼的“北迁南往”变迁轨迹。1922年5月,利金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报告,提议把工作重心迁往广州。(61)《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95页。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必须把地址迁到广州。西湖会议后,马林提出“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62)《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93页。。10月,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北京。京汉大罢工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后迁到广州。中共三大后,陈独秀、毛泽东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表示将中央执委会搬到上海,同年9月,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中央领导机构进驻上海期间,其驻所的地理分布反映了“一城四界”的城市格局。如果说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两省或多省交界处,那么,早期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在上海的驻所则主要集中在租界内或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的交汇地带。比如,中共四大在华界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其附近宝源路209弄(原宝兴里)成为中共四大后中央局机关旧址。(63)苏智良、姚菲:《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华界与租界虽一路之隔,但安全环境大相径庭。相对来说,租界或四界交汇地带为组织活动提供了城市地理缝隙。再比如,1927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为保证安全,实行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分隔,即中央机关一般设在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江苏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团中央则在法租界,相当多的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64)《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第481页。
而在成员构成上,这一时期仍体现了知识分子化和南方化趋向,但出现了“微调”。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195人,上海、长沙、广东、湖北、四川等南方地区有135人,占党员总数的69.2%,北京、山东和郑州等北方地区有37人,旅外党员有23人,分别占党员总数的19%、11.8%。(65)《中共二大轶事》,第8页。中共组织重心虽仍在南方,但有明显北扩趋势,中共中央也曾一度北迁,但时局的变化,使组织时有伸缩。中共二大代表中,除1人身份不定,其余11人中,南方8人,占72.7%;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5人,南方地区4人,占80%。(6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加,但仍以南方地区为主。而党员中,工人、知识分子及其他的比重分别为19%和81%,(67)《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90页。工人占比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从临时性到正式性的过渡转换后,中央领导机构框架渐成。但随着时局变化和组织的发展壮大,扁平化的单层的结构逐步向立体结构转型,并在中共三大后,衍生出多个中央工作机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结构日趋完善。
四、中共三大到四大前后的组织合体与三层结构生成
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中央领导机构仍是单层,成员少,且不能经常在一起。中共一大党纲规定“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68)《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译稿)》(1921年),《“一大”前后》(一),第11页。,中共二大虽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没有制定具体章程。中共三大时,党员人数增加,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实现组织合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央领导机构设置走向制度化。
(一)中央局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合体
新修订的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局和中央特派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由5人增加到9人,候补委员由3人增加到5人。(69)《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二大”和“三大”》,第190页。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7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4—25页。其中,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共中央局,后加入王荷波。(7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5页。于是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两层结构,中央局成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常设机构。从中央领导机构的纵向变革来看,中共三大实际上是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的组织合体。
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72)《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68页。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任会计,并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每四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73)《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69页。但实际上三届一次会议于1923年11月24日召开,且中共三大到四大期间,共召开了两次全会和一次扩大会议,故中央局应在三大时或稍后选举产生。
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初设时,未设专门工作机构,由委员分管各项工作。中共三大时,各地党组织有所增加,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委员长、秘书、会计,但仍未设立专门工作机构。直到1923年10月设立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1月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1924年5月设立组织秘书部、宣传报刊部、工农部和出版部等,(7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41页。中央工作部门在三大以后逐步衍生和完善。
按照党章规定,中央通告文件须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署才能产生效力。1923年7月2日,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以后的情况,9月6日毛泽东和陈独秀曾共同签署了中共中央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75)李蓉、叶成林:《中共三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9月10日,中央通告指出,“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76)《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中央局迁沪后更动》(1923年9月10日),《“二大”和“三大”》,第219页。此时的落款签发人为“委员长T.S.Chen”和“秘书D.I.Lo”,即陈独秀和罗章龙。10月的《中央通告第九号》落款署名“委员长T.S.Chen”和“秘书Leo D.”(77)《中共通告第十九号——开展承认苏俄运动》(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9页。,12月的《中央通告第十一号》与《中央通告第十三号》(78)《中央通告第十一号——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1923年12月)、《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9、212页。也是由陈、罗联合署名。由此可知,毛泽东在赴湘筹建国民党党部期间,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中央通告文件签发人由陈独秀、毛泽东变为陈独秀、罗章龙。直到1924年2月中旬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继续担任中央局秘书。4月19日,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署名发文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79)李蓉、叶成林:《中共三大轶事》,第197页。第十五号、第十七号、第二十一号中央通告均为陈独秀、毛泽东联合署名。(80)《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1924年7月21日)、《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1924年9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1924年11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104、107、164页。后面的中央通告多署名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钟英或不署名。
(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党上海党部的“组织合体”
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开一次全体会议,但原定于1923年10月20日召开,因与劳动大会冲突,改在11月15日,后又因为等待驻粤委员,延期到11月24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中,4人派驻地方,谭平山驻粤,李大钊驻北京,项英驻汉口,朱少连驻湖南,毛泽东作为中央局委员因事赴湘,因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局委员4人,驻京驻鄂委员各1人,S,Y.代表1人,特别招待同志1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8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24日—25日),《“二大”和“三大”》,第232页。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员占四分之一,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杨鲍安为秘书,冯菊坡任工人部秘书,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澎湃任秘书。(82)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同时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建立三个执行部,其中,毛泽东担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罗章龙任组织指导干事,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施存统和沈泽民任宣传指导干事,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邓中夏任调查干事,王荷波任办事员,向警予任青年妇女部助理。(83)《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9页。而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为中央局成员,毛泽东同时担任中央局秘书和组织部主任,罗章龙担任会计和宣传报刊部主任,王荷波担任工农部主任,邓中夏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换言之,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实现组织合体不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和国民党上海党部实现了组织合体。但1924年2月底,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把国民革命运动归于国民党,把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去解决,党的工作因此陷入半停顿状态,党的组织发展出现了徘徊。(8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3页。
(三)三层结构的生成与再调整
为摆脱停滞状态、加快组织发展,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工农部内设工会运动委员会,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第一次提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特别设一个编辑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4人必须在中央所在地。(85)《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1924年5月10日—15日),《“二大”和“三大”》,第275、279、280页。中央领导机构的层次也发生变化,1924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维经斯基。(86)《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5页。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中央政治局三层结构,中央局成为中间层。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委员长”称谓改为“总书记”或“书记”,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负责指导地方党组织,(8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6页。而中央领导机构仍维系着三层结构。
(四)成员构成上的“此消彼长”与比例“倒挂”
中共三大时有党员420人,从目前已发现材料来看,虽很难精确党员地域分布,但也可通过现有资料管窥其大致分布情况。中共二大到三大之间新加入200人,其中工人130人,分布在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长辛店、唐山、济南、浦口,杭州、汉口、莫斯科等,(88)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节录)》(1929年),《“二大”和“三大”》,第516页。南北方城市数量大致相等,且是时北方工人运动发展较快。中共三大到四大期间,党员人数增加一倍有余,达到994人。从地区分布来看,国共合作渐兴,组织发展重心复归于南,南方地区占比重较大,且呈较快发展趋势。据李逸回忆,中共四大时党员达千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湖南—特别是安源以及武汉(89)李逸:《中共四大会议琐忆》(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中共四大后,党员人数倍增,到1925年10月,达到3470人,仅江浙地区就有1080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90)李蓉、叶成林:《中共四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中共三大代表中,已知身份的代表35人,南方地区28人,占80%;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南方地区8人,占88.9%,(91)《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第8页。中央局成员5人,均出自南方地区。(9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5页。中共四大代表20人,南方地区19人,占比达95%,而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南方地区8人,占88.9%,候补委员5人,全部为南方地区。(93)《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第11、12页。无论从党员总数、代表人数,还是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构成,组织发展的南方化态势明显,这一定程度上因承了近代革命群体和革命重心偏南方化的轨迹。
在党员总数和大会代表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比重呈现“此长彼消”的态势。尽管三大时两者比重为25%和75%、0和100%,但到中共四大时,两者比重调整为35%和54%、10%和80%,至中共五大时进一步调整为65%和15%、33%和57%。(94)《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90页。工人在党员总数中占三分之二强,在大会代表中占三分之一左右,而知识分子在党员总数和大会代表中的占比却出现“倒挂”现象。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中共基层组织的成员以工人为主,中高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两者的变化,体现了中共组织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向以工人为主体转变,“工人阶级化”倾向愈加明显。
结语
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共组织体系的大脑和根脉,其组织形态的变革趋向决定着各级组织和各项事业的走向。本文虽然探讨到中共四大,但中央领导机构仍处于变动中。中共五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五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领导机构的三层结构维系不变,但名称发生较大变化,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中央局退出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调整为中间层,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最高层,基本塑型了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结构,且影响至今,而中央局则成为中央派出机构,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淡出中共组织体系。
中共组织形态的变迁是时局情势的“晴雨表”。总体来说,中共组织此时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党员人数与党组织数量稳步增加,中央领导机构由临时性、不稳定性、单层性到正式性、稳定性、多层性,结构不断优化,名称不断变更,机构不断健全,成员不断调整,制度不断完善,日益从扁平化向立体化转变。这一时期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形态变迁还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央领导机构呈现年度周期性继替。中共早期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年会制,使得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形态变更周期较短,加之时局的变动不居,成员流动性明显。二是中共组织处于第一次大规模转型中。从中共组织发展进程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机构处于从知识分子为主向以工人为主的转型中,这是中共成立后,为顺应国内革命形势和共产国际要求,在成员构成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转型。三是中共对组织建设的认知成熟度不断提高,机构设置不断完善,推动了以中央领导机构为大脑和主脉的组织体系建设。中共日益走进革命救亡运动的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磁场,团结和吸纳了各种进步力量和积极因素,其根本上得益于中央领导机构变革完善。中央领导机构逐步完善、定型,进而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