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之外的奥本海默
杨雯

1943年的圣诞派对,是电影《奥本海默》里为数不多的欢愉场景。穿着长大衣的玻尔作为“圣诞礼物”现身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小镇,使“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备受鼓舞。欢声笑语之后,他对奥本海默说要谈谈“之后的事”。
在1945年7月16日的晨曦中,当“三位一体”试验的巨大蘑菇云升腾而起,等同于2.5万吨TNT(三硝基甲苯)的能量在顷刻间释放,奥本海默终于理解了玻尔在那一夜诉说的担忧:“这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一个新的世界。”
奥本海默的挣扎
看过电影《奥本海默》的观众,都会对原子弹爆炸的一幕难以忘怀,刺痛视觉的白光瞬间降临,长达25秒的静默之后,轰鸣和风沙才将银幕内外的人拽回真实世界。该片导演诺兰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此处时表示,确实是一种充满隐喻的处理——人们率先看到的火光象征着神圣的美感,而后的声音才预示着真正危险的到来。
奥本海默对危险的知觉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降临了。1945年10月,他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领导职务,拒绝继续研制氢弹,称原子弹是“一种恐怖至极的武器”。而仅仅在几个月前,当美国政府决定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以结束战争时,155名“曼哈顿计划”科学家请愿反对,奥本海默却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
9年后,在麦卡锡主义阴影的笼罩下,奥本海默走上了令他备受屈辱的听证会。
电影中,在面对委员会诘问为何起初不反对向日本投放核武器、后来又阻止核武器继续军用时,8年前新墨西哥州沙漠里天地为之失色的那一瞬再次出现在奥本海默的眼前。视野被白光逐渐湮灭,耳边轰鸣声回荡不绝,奥本海默就自己看似“前后矛盾”的行为解释说:“我意识到,人类的确会使用所拥有的任何武器。”

科学家的这种矛盾性,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看来,并不难理解,这是科学研究无法规避的困境,即探索本身与前景的未知和不确定。
“从科学进步的角度而言,科学家一定是希望研究成功的。”曹则贤观察到了“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发过程中流露出的种种不确定,对能否成功爆炸的忐忑、对爆炸规模有多大的怀疑。“电影中,他们在试爆的前一天晚上还在打赌能否成功。事实上,很多科学研究到底能带来什么结果,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很难预料。”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是中文版《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以下简称《奥本海默传》)一书的审校,这本书曾获美国普利策奖,也是电影的灵感来源。他认为,今天的人们在了解核武器危害的全知视角下去讨论当时科学研究的道德伦理,是失之偏颇的。“任何时代的认识都是阶段性的,这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的特点,而作为科学家,一定会有追求真理的冲动。”
方在庆记得奥本海默的一句名言:“科学中深层的内容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被发现,它们被发现是因为它们可能被发现。这是一个深刻而必然的真理。”
一个令曹则贤印象深刻的电影画面是,爆炸成功后,两名美国士兵对奥本海默说“我们将接管这里”,而后奥本海默看着另外两颗原子弹被军方装车运走,露出不安的神情。“当这项研究成功以后,他发现威力超过他的想象,开始后怕,并出现内心的挣扎。”曹则贤说。
这令他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弗里茨·哈伯。当他扬言化学武器是“尽快结束战争的人道武器”时,同为化学博士的他的妻子克拉克难以忍受良心的谴责,拿起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兵凶战危,兵器从来都是凶器。”曹则贤说,“奥本海默的挣扎是真实的,这不仅反映的是他的个体,也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一直都处在这种挣扎和矛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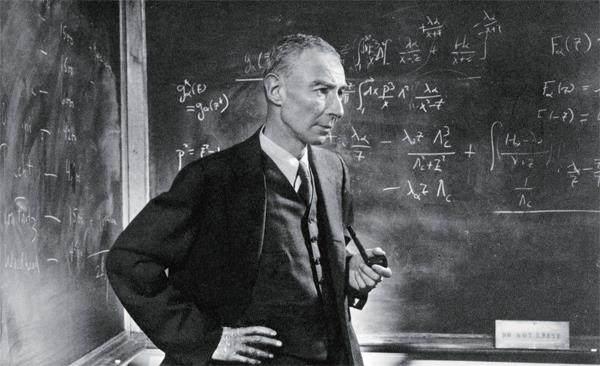
最适合领导“曼哈顿计划”的人为何是他?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作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登上了《时代》封面,成为全美最炙手可热的科学明星。
电影里有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景,时任总统杜鲁门在白宫里兴致勃勃地等待與奥本海默交谈,但走进办公室的科学家显得局促不安。他说,感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闻言,杜鲁门脸上的笑容顷刻间消失,换作了嘲讽,“你以为广岛或长崎有人关心原子弹是谁造的吗?他们只关心是谁投下的”。
杜鲁门对奥本海默的“良心谴责”不以为意,他更关心的是,奥本海默还能不能继续协助美国政府进行武器研发。答案是不能,不仅不能,奥本海默从洛斯阿拉莫斯卸任后,开始致力于用自身的影响力四处发表演说,呼吁原子能在国际上能和平使用,阻止美国政府为了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而制造杀伤力更大的氢弹。
事实上,奥本海默的一厢情愿早该破灭在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那一刻。诺兰认为,这是奥本海默生命里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时刻,电影的表现手法是,16个小时之后,奥本海默才从广播里与普通人同时获知这条新闻——作为原子弹研发计划的统领者,“他是如此地远离了他所制造的这个事物的后果”。
奥本海默的高调坚持使他成为许多人的眼中钉,最终让他身陷一场闭门听证会,被质疑对国家的忠诚,并被撤销安全许可。
这样的大型科研工程本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涉及对未知的探索。如果人为设置各种各样的禁区,会让科学家难以深入讨论,很难将研究推进下去。开放无拘的交流氛围、对科学家自主创造性的充分尊重无疑是科研工作者非常需要的环境。
《奥本海默传》中更详细地披露了这些细节,作者凯·伯德与马丁·J.舍温写作本书的时间长达25年,参考了美国及其他国家成千上万份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对奥本海默超过25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准确概括了奥本海默与核武器因果纠缠的一生。
方在庆用德语“ein unruhiger Geist”来形容奥本海默,即有着不安分的头脑。“他是一个急性子,很少能在科学的某一个点上钻下去,往往是对这个感兴趣了马上去做,过两天不感兴趣又转到另外一个。所以他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但正是凭借着对更多科学领域的了解,他成为了最适合领导“曼哈顿计划”的人。
“顶尖科学家是最难‘管理的。和顶尖学者打交道,要让他们能够得到尊重、能够自由表达,而奥本海默非常聪明也很擅长处理这些。”方在庆说。比如即便是与众人不配合、发生龃龉的泰勒,奥本海默也将他留下,容许他做当时还是空中楼阁的氢弹研究。
奥本海默努力为参与项目的科学家争取最大的空间。电影中,“曼哈顿计划”进行期间,军方三番五次向奥本海默重申应该对科学家进行“分区管理”,以避免泄密。但奥本海默与他的科学家同事们对此不以为意,坚持保持开放和深度的交流。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姬扬对奥本海默竭力维护的合作交流表示认同。“这样的大型科研工程本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涉及对未知的探索。如果人为设置各种各样的禁区,会让科学家难以深入讨论,很难将研究推进下去。开放无拘的交流氛围、对科学家自主创造性的充分尊重无疑是科研工作者非常需要的环境。”
影片之外的科学与历史
8月底,电影《奥本海默》在中国内地上映后,《中国科学报》采访到的多位科研人员都已在第一时间观影。观赏电影之余,这些“看门道”的观影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媒介,片中仍有许多对科学研究工作简单化、扁平化的演绎。
影片中英国科学家福克斯实际上是苏联间谍,姬扬注意到,电影中野外试验的福克斯总是在其他人将头低到防护挡板以下时,还伸长脖子想多看一眼,“这一编造的细节符合一个对科学不太了解的人对‘科学的刻板印象”。
电影将奥本海默从英国剑桥大学转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决定,压缩为玻尔对一个具备理论物理学天赋的年轻人的欣赏及提点。《奥本海默传》中更细致地记述了奥本海默在剑桥的抑郁挣扎,给老师放毒苹果确有其事,却并非如电影中那样。
曹则贤认为这是电影刻意表现的“科学”噱头。“这一段埋了3个‘梗:一是苹果代表着牛顿与‘引力,二是图灵死于氰化物中毒,三是奥本海默阻止玻尔吃时说有‘虫洞。”
电影《奥本海默》上映后,除了科学圈的人争相观看外,很多“诺兰迷”也迫不及待。“观影门槛”则是讨论热度很高的一个话题,社交媒体上有人称“3小时沉浸式观影”,有人说是“长达3小时的煎熬”,还出现了不少贴心的“人物关系梳理、时间线整理和幕后故事”帖子给观众做“预习复习准备”。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认为,这部电影对普通观众而言确实有些“烧脑”,但其门槛不在科学而在历史。“观众需要知道两个历史:一是原子弹的产生过程,这个过程中除了有科學,还有谍战;二是要了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的生态。很奇怪的是,诺兰对麦卡锡主义讳莫如深,3个小时的片长中有一半时间都在讨论麦卡锡对奥本海默的审查,但电影里没有出现过麦卡锡参议员,似乎要刻意回避。”
另一个观影门槛是,“电影的非线性叙事,画面和情节并非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并且出场人物相当多”。这部电影要处理的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如果电影仅仅讲‘曼哈顿计划,那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试验成功、原子弹造出来就可以结束了。但电影有一半时间在讲述奥本海默受审,后一个故事和前一个故事之间有联系,令电影的叙事变得复杂”。
“在观影前后了解一些相关历史是很有必要且很有意思的。”江晓原说,“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个核工程,‘曼哈顿计划群星璀璨,但大部分科学家在电影中只能一带而过,他们中许多人的故事都值得去了解。比如福克斯,这名英国科学家向苏联提供信息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信仰。虽然身份败露后被英国判刑14年,但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此后去往东德开启了崭新的后半生,升任科学院院士,于苏联解体的前一年去世。他的后半生比奥本海默幸运。”
电影的最后,还是为奥本海默这名悲情的普罗米修斯留下了一个善意的结局。希尔揭发了一手构陷奥本海默的施特劳斯,苍老的奥本海默于1963年领受了美国政府颁给他的“费米奖”奖章。
不过,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方在庆介绍,颁给奥本海默“费米奖”的次年,约翰逊政府为平息施特劳斯及其支持者的不满情绪,将“费米奖”的奖金减半。直到2022年12月16日,拜登政府才推翻了1954年那场听证会的决定,宣布当年撤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错误的。
这时距离奥本海默的骨灰撒向大海已经过去了55年。
◎ 来源|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