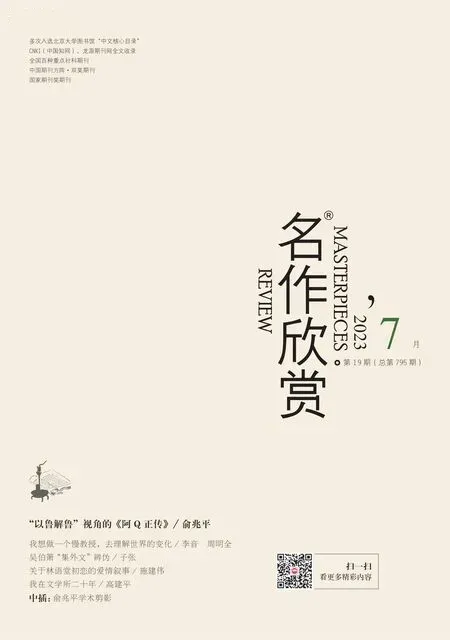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关于冒名骂人”:汪静之致王平陵的一封集外书简
江苏 金传胜
1934 年南京《读书顾问》季刊第2 期“通讯”栏以《“我已物故不妨冒用”——关于冒名骂人》为题刊载了汪静之致该刊主编王平陵的信函。经查,西泠印社2006 年出版的六卷本《汪静之文集》并未收录这封书简,有关汪静之的研究文章亦未提及。兹将原函整理如下:
平陵学兄:
昨天到一个朋友家中去,那朋友拿一份杭州寄来的《东南日报》给我看一段新闻,这新闻太奇怪了,是否真有此事?不知是何人冒了我的名来骂你,而你也不加考虑,便误以为真了。我搁笔已经六七年了,六七年来什么文章都不写,更那有闲空批评他人?
你手头如果有那几篇互相攻击的文章,请检出寄给我看看,看到底是怎样闹的。
以前也有两次冒用我的名字的事:六七年前黎锦明曾冒我的名字去看朱湘。近来听说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在报章上发表批评文字。(但我没有看见文章。)连批评你这一次算是三次了。何以冒名的人常喜用我的名字,大概因为我久不写文,以为我已物故,不妨冒用罢。
即颂
暑安
弟汪静之 八月十日
紧随这封书信之后,编者王平陵还特意写了一段文字作为“附志”,不妨一并抄录如下:
好久不曾通讯的老朋友汪静之兄忽然从青岛来讯,并附寄杭州《东南日报》一段文坛新讯,有下列的记载:
“《文艺月刊》编者王平陵在首都文坛上颇形活动,近被汪静之在首都某报出版的××周刊大骂一顿,一时附和向王诬骂者蚁聚,王亦不甘示弱,在他所编的《读书顾问》上向汪等反攻,于是笔战扩大!闹得不可收拾。最近因汪离开南京,事始寝。”云云。
像这种无根之谣,本不必利用《读书顾问》的篇幅,作多事的声明,但恐连累友人静之兄的令名,故为发表于此。
至于骂人的言辞,当然是不会文雅的。我曾在《读书顾问》创刊号中引用德国诗人霍德林Holderlin 一句论诗的句子:“Le poet est les Vase sacres ou se couserve le vin de la vie l’esprit des heros.”译出来是:诗人是神圣的花瓶,里面保存着生命的酒浆,英雄的精神。不知那位仁兄便很聪明地恭维本人为“花瓶文人”,本人貌既不美,姿态也不摩登,实属愧不敢当。但不知那位德国诗人霍德林的尊容是怎么样!一笑!
平陵附志 八,十五。
《读书顾问》第2 期的封面、版权页标明是“七月出版”,实际出刊时间显然不会早于1934 年8 月15 日。经查,上文引述的“文坛新讯”原刊于1934年7 月24 日杭州《东南日报·沙发》副刊,是在该刊连载的《文坛新讯》第62 则,题为《汪静之讽刺王平陵》(署“朱珠”)。原文完整内容曰:“《文艺月刊》编者王平陵,在首都文坛上颇形活动。近被汪静之在《新京日报》出版的《春风周刊》里来了一篇《花瓶文人王平陵的检讨》,在王的一篇作品里举出了八十处的‘欠亨’。一时附和向王攻击者颇众。王亦不甘示弱,在他所编的《读书顾问》上向汪等反唇相稽。于是笔战扩大,闹得不可收拾。最近因汪离开南京,事始寝。”①同年8 月22 日《西京日报·明日》转载了这则讯息。两相对照后不难发现,王平陵记入“附志”时对一些文字做了删节与改动。最大的删改是将“《新京日报》出版的《春风周刊》”改成了“首都某报出版的××周刊”,从而导致信息模糊化。此外,8 月24 日《东南日报·沙发》上登载的《写上海的十几个所谓作家(十四 汪静之)》(署“制群”)一文在结尾时写道:“但月前见其在南京某报痛诋王平陵,则其涵养工夫实在还未到家。”②其中“南京某报”亦指南京《新京日报·春风周刊》。
《春风周刊》是1934 年《新京日报》创办的副刊,由春风文艺社主办。春风文艺社的核心成员为当时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就读的孙望、程千帆等青年学生。孙望曾经谈到该刊的创办是为了反对王平陵在南京文艺界的权威地位:“这对于我们这些未出茅庐,还没见过世面的学生,颇不习惯。于是略一聚议,便组成了一个文艺社团,借《新京日报》副页,编了一个‘春风周刊’,以与王氏相周旋抗衡。揭竿发难的文章是《论姿势》和《中国需要的作家》。此后每期都刊登一些批评讽刺的稿件。那时还有《新民报》《大华晚报》等几家副刊,也写文响应,这就使得我们的‘青年文学导师’大为伤神。”③杨晋豪编《二十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中对《春风周刊》的评价云:“里面的文章并不见得好,只是以骂王平陵章衣萍出名。”④可见,《春风周刊》靠批评王平陵确实在当时的文坛积攒了一定的名气。孙望还在《我的自传》中透露,他以盖郁金、河上雄为笔名,程千帆以左式金为笔名,跟王平陵打了一段时间的笔墨仗。只是《春风周刊》无处可寻,该刊具体刊文情况今已不详。
《春风周刊》创刊时,汪静之早已不在南京。由汪静之的信文可知,他对《春风周刊》上多次刊登讽骂王平陵的文章并不知情,署名汪静之的《花瓶文人王平陵的检讨》实为一篇冒名作品。汪静之遭遇被他人冒名的情况,之前已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六七年前”,作家黎锦明曾冒汪静之的名字去看望诗人朱湘。1934 年12 月,上海《循环》周刊上刊登的《文坛逸话·真假汪静之》一文专门揭露了这段轶闻。据此文记载,诗人朱湘某年到沪后,赵景深欲前往访晤,适逢黎锦明在赵处,于是两人相约同行。黎氏早年曾为文批评过朱湘,因此托言自己是汪静之。数年后朱湘任省立安徽大学外文系主任,汪静之也被聘为该校文学教授。旧识来到安庆,朱湘连忙登门拜访,及至碰面,大为吃惊,“始知前在沪所遇者,为一冒名汪静之也”⑤。该文作者署名“朔青”,应是钱君匋的笔名。钱氏在《聊聊我的名字》中说过:“在三十年代写散文,我曾用过笔名‘程朔青’,这个笔名先是用了我母亲的姓氏,‘朔青’两字没有别的什么含义。”⑥目前尚未查到钱君匋署用“程朔青”发表的文章。“朔青”与“程朔青”仅一字之差,且出现在20 世纪30 年代,应当是钱君匋使用过的笔名之一。汪静之1927 年9 月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诗集《寂寞的国》封面就是钱君匋设计的。1928 年8 月,汪静之为钱君匋的诗集《水晶座》(1929 年3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热情作序。考虑到钱君匋与汪静之的熟悉程度,上述这则“文坛逸话”无疑是可信的。同在1934 年,赵景深在回忆朱湘的文章中叙及第一次与诗人的会面约在1927 年:“因为钦佩,便想与他相识,因之决心到青年会去看他,途中遇见黎锦明,他也想去看他,我们俩就一同去。”⑦只是并没有提到黎锦明冒名汪静之,也许是有所顾虑吧?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年之后,被他人冒名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黎锦明身上。1935 年8 月29 日上海《晨报·文艺周刊》第7 期刊出署名黎锦明的散文《从“西海”走出来》。9 月5 日该刊第8 期发表黎锦明的来信,声明此文并非他所作⑧。
《春风周刊》为什么会出现汪静之的文章呢?据孙望回忆,1931 年他在南京中学读书时,汪静之是其国文老师。在汪氏的影响与鼓励下,孙望与同学组织“洪荒文艺社”,“写过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⑨。第一篇短篇小说《天火》发表于《新民报·葫芦》,第二篇《残年》发表于1931 年4 月23 日《中央日报·青白》第469 号(署“孙自强”)。以汪静之、孙望的师生关系来看,汪静之如果为《春风周刊》撰稿是合乎情理的。既然汪静之否认《春风周刊》上的署名文章是自己所作,那么至少存在下面两个可能性:第一,有人冒充汪静之的身份给《春风周刊》投稿,没有被该刊编者孙望、程千帆等人察觉。第二,孙望希望借老师汪静之的文名以壮门面,故意冒用其名字发表文章攻击王平陵。至于真实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面对《春风周刊》上的攻击,是否确如“朱珠”所言,王平陵“在他所编的《读书顾问》上向汪等反唇相稽”呢?《读书顾问》第1 期刊有王平陵的《荒芜时期的中国诗坛》一文,在描述“五四”时期新诗坛的活跃气象时这样写道:“在当时,便有许多年青的诗人,应用白话来写诗,译诗;不到三年的努力,诗坛顿呈新鲜活跃的气象,较著名的诗人,有康白情俞平伯宗白华朱自清徐玉诺刘延陵汪静之于赓虞等,都是各尽其天赋,自成一家的风格,比到《尝试集》中所选录的各篇,无论在内质与外形方面都进步得多了。”这里对汪静之新诗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不过在论及当前“荒芜时期的中国诗坛”时出现了“徐玉诺于赓虞汪静之之流,更是消沉没落,离开了人们的注意”⑩的表述,语气之中就有点不太客气了。除这篇文章直接涉及汪静之外,有几篇短论可看作王平陵对《春风周刊》诸文的间接回应。《谈“骂人的艺术”》(署“高山”)中写道:“其实,写骂人的文章,是否就能作为自己有学问的表征,是疑问;读骂人的文章,是否能有益于自己学问的修养,更是疑问。”⑪《是非之争》(署“平陵”)一文则讽刺某些“太聪明”的中国人“对于自己从来不会说一个‘非’,对于别人从来不肯说一个‘是’”⑫。囿于文献,并不清楚王平陵是否将论争双方“互相攻击的文章”检出寄给了汪静之。
综合曹聚仁的《悼王平陵》《诗人汪静之》等文章,王平陵是曹聚仁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汪静之则与施存统同班,比曹聚仁低一个年级。因此汪静之称王平陵为“学兄”合情合理。王平陵在《新诗的勃兴与演变》中曾写道:“汪静之的《小鸟集》是他的处女作,我第一个看到他的原稿,确有许多新创的旋律,特别是抒情的诗篇。胡适之先生很欢喜这位小同乡有写诗的才能,曾为他写一首八百多字的短序,指出他的优点,就在没有传染到旧诗词的臭味,《小鸟集》的作者缺乏旧诗词的修养,不仅不是弱点,正是极大的幸运。”⑬因胡适曾在《〈蕙的风〉序》中评价说:“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⑭可知,王平陵文中提到的《小鸟集》即为《蕙的风》,《小鸟集》或许是《蕙的风》最初的名字。如此看来,汪静之、王平陵在浙江一师读书时就已互相认识,毕业后一度还有共事之雅。汪静之1930 年在《出了中学校》中提到自己“1928年春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1929 年暑假,因反对暨大校长,与同事数十人同离暨大”。⑮《汪静之自述生平》中明确交代:“1928 年春,我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学部当高中教员。”⑯同一时期,王平陵也在暨南大学任教,直至1929 年2 月应杭州一师同学、南京《中央日报》总编辑严慎予之邀,转任《中央日报》副刊部主任,主持《青白》《大道》两个副刊。汪静之1930 年春由上海前往南京,在南京中学教了一年半的国文。1930 年,南京《中央日报·青白》先后刊登过汪静之的新诗《墓铭》与短篇小说《红杜鹃》(即《伤心的祈祷》),表明同在南京的汪静之、王平陵继续有联系。1931 年8 月离开南京后,汪静之陆续在安庆、杭州、汕头等地的高校或中学教书,1933年7 月来到青岛,受聘于青岛市立中学。可能因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生活极不安定,汪静之与王平陵的通信一度中断。因而王平陵才会说“好久不曾通讯的老朋友汪静之兄忽然从青岛来讯”。
值得一提的是,汪静之写此信时,郁达夫正在青岛避暑。郁达夫之所以北上青岛,便是汪静之、卢叔桓等好友力邀的。汪静之不仅陪同郁达夫、王映霞及儿子郁飞由沪抵青,而且极尽地主之谊,“授餐设馆,款待殷勤”⑰。郁达夫《避暑地日记》(即1934 年7 月6 日至8 月14 日日记)对此多有记载。1934 年8 月9 日,郁氏在日记中有“午后,友人俱集,吴伯萧君亦来访”⑱的记载,这里的友人应包括汪静之等青岛本地朋友。据此推测,汪静之信函开头所谓“昨天到一个朋友家中去,那朋友拿一份杭州寄来的《东南日报》给我看一段新闻”中的“一个朋友”很可能正是郁达夫,“家中”则指临时寓所——“广西路三十八号骆氏楼上”⑲。郁达夫与杭州《东南日报》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身在旅途之中仍为它持续提供稿件。汪静之读到《东南日报》上关于自己攻击王平陵的相关报道后颇为惊诧,于是决定给王平陵写信进行解释。他显然将这份《东南日报》随函寄给了王平陵。
再者,汪静之信中“我搁笔已经六七年了,六七年来什么文章都不写”的说法并不符合实情。例如1932 年9 月至1933 年3 月间,汪静之在上海《申江日报·海潮》《现代学生》等报刊上曾陆续发表《对于国文教科书的一点意见》《作家与缺陷》《文学作家的大胆》(目录页作《文学家的大胆》)、《作家出身的阶级问题》《作家与经验》《从女权到男权》等文章。考虑到《申江日报·海潮》《现代学生》的编辑刘大杰是汪静之非常熟悉的朋友,这些文章显然不属于“近来听说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在报章上发表批评文字”的情形,只是它们没有全部被《汪静之文集》收录⑳。1933 年秋,汪静之与好友、青岛市立中学的同事章铁民等成立了青岛文艺社(亦称青岛文艺研究会),借《青岛民报》发行《青岛文艺》周刊,吸引了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为什么汪静之强调自己早已搁笔六七年,营造出远离文坛的假象呢?个中缘由与心态,颇耐人寻味。汪静之年纪轻轻就因诗集《蕙的风》(1922)名噪一时,1928 年因短篇小说《北老儿》中对女性性心理的大胆描写而再度引发争议。此后,在生活压力的逼迫下,汪静之到处奔波谋职,诗歌产量锐减,小说基本辍笔,在教书之余仅发表一些文论、杂文,编选出版了《白雪遗音续选》等。加上文学流派更迭,新人层出不穷,导致他确实慢慢被文坛边缘化,“离开了人们的注意”,成为某些青年眼中“落伍的诗人”㉑。从“五四”时期的名重天下到20 世纪30 年代的几乎被世人淡忘,巨大的落差多多少少会让汪静之内心复杂,产生寂寥之感。1930 年他曾发过“职业是损害艺术的,我希望在一二年内能够弃去职业,专事创作”㉒的志愿,然而对于民国作家而言,靠专职写作为生毕竟是不易办到的事情。
结语
编者飞白在《汪静之文集》“书信卷”前言《不消逝的涟漪》中说:“除《漪漪讯》外,保存下来的书信较少。这里收录的其他书信,是静之难得留下的一些信稿或复印件,少数收信人提供的信件,以及静之偶然离家时的家信。”㉓确如所言,“书信卷”除《漪漪讯》中汪静之、符竹因的来往书信(1922—1933 年)外,信件整体数量不多,1934 年至1940 年间更是付之阙如。《“我已物故不妨冒用”——关于冒名骂人》稍可弥补这一缺陷,既是汪静之青岛期间留下的唯一一通,也是与王平陵的通信中唯一存世者,自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汪静之与王平陵,两位文学观点、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现代作家看似各行其是,但其文学生涯、人生道路不乏交集。他们因同在浙江一师读书而结缘,在“五四”新文化的感召下先后步入文苑,一度曾有书信往来与文字互动,折射出现代文坛丰富驳杂的景观。这封新见书信不仅关乎汪静之、王平陵的交往,而且牵涉《新京日报·春风周刊》这份近乎被遗忘的文学刊物及其背后的文坛纷争。最后,信中披露的若干信息亦值得注意。例如“近来听说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在报章上发表批评文字”,说明除《春风周刊》外,当时还有一些报刊上署“汪静之”的文章可能是冒名之作。对于现代文学史上这种并非鲜见的假托他人名义的“伪作”“伪著”现象,今天的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①朱珠:《汪静之讽刺王平陵》,《东南日报·沙发》1934 年7 月24 日,第2038 期。
②制群:《写上海的十几个所谓作家(十四 汪静之)》,《东南日报·沙发》1934 年8 月24 日,第2069 期。
③周末报编辑部编:《情系金陵》,南京出版社1992 年版,第33 页。
④杨晋豪编:《二十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北新书局1935 年版,第794 页。
⑤朔青:《文坛逸话·真假汪静之》,《循环》1934年12 月15 日,第5 卷第1 期。
⑥钱君匋:《聊聊我的名字》,《随笔》1982 年第23 期。
⑦赵景深:《朱湘》,《现代》1934 年1 月1 日,第4 卷第3 期。
⑧《湘潭黎锦明来函》,《晨报·文艺周刊》1935年9 月5 日,第8 期。信中篇名误作《从西海大戏院走出来》。
⑨参见郁贤皓等编:《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 页。
⑩ 王平陵:《荒芜时期的中国诗坛》,《读书顾问》1934 年4 月,第1 期。
⑪ 高山:《谈“骂人的艺术”》,《读书顾问》1934年4 月第1 期。高山是王平陵的笔名,考证从略。
⑫ 平陵:《是非之争》,《读书顾问》1934 年4 月第1 期。
⑬ 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 页。
⑭ 胡适:《胡适文集 第4 册 胡适文存》,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37—1238 页。
⑮⑯㉒ 飞白、方素平编:《汪静之文集》“回忆·杂文卷”,西泠印社2006 年版,第15 页,第203 页,第16 页。
⑰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七卷 诗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0 页。
⑱⑲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60 页,第347 页。
⑳《汪静之文集》未收《对于国文教科书的一点意见》《从女权到男权》。《作家与缺陷》《文学作家的大胆》《作家出身的阶级问题》《作家与经验》是《汪静之文集》“文论卷”中已收《作家的条件》第二、四、五、六讲的初刊本。
㉑ 白桦:《汕头文化鳞爪》,《庸报·另外一页》1933 年12 月14 日。
㉓ 飞白:《不消逝的涟漪》,载飞白、方素平编:《汪静之文集》“书信卷”,西泠印社2006 年版,第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