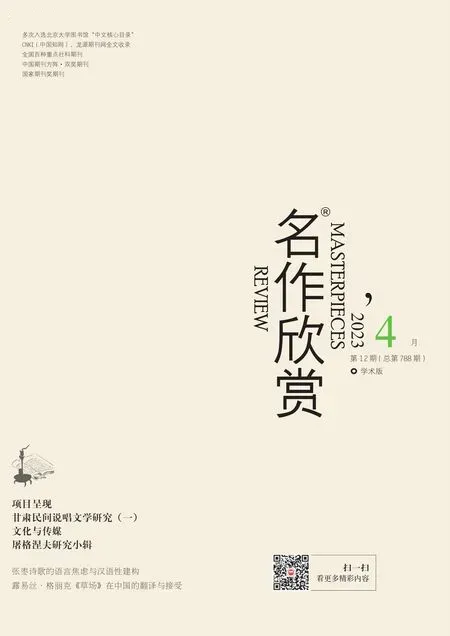消费时代的文学媚俗化:根源、表现与出路
⊙朱怡雯[贵州财经大学,贵阳 550000]
19世纪以来,工业技术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兴起,一方面,人们对娱乐消费的需求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得艺术的生产和商品的销售更为便捷。随着消费社会的不断扩张,“媚俗”(Kitsch)由此诞生。从词源来看,“媚俗”起源于德国,是由德语词汇“Kitsch”翻译而来。“媚俗”(Kitsch)一词首次出现是在德国慕尼黑的艺术品市场,在19世纪80年代,当地的艺术品商人把那些做工粗糙、廉价造作、迎合民众审美因而“易于出售的商品”称为“Kitsch”。到19世纪末,“媚俗”这个词便在艺术领域流传开来,形成与艺术分庭抗礼之势,媚俗成了“伪艺术”“非艺术”的代名词。20世纪初,“媚俗”的负面意义引发了当时一些学者针锋相对的抵抗之争。20世纪20年代后,对“媚俗”的审视逐渐理性化,“媚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雏形开始形成。对媚俗的谈论不再只局限于文学和艺术领域,而是扩展至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宏观领域。发展至今,学界对“媚俗”的关注已由20世纪初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延伸到了大众文化、互联网媒介、新兴艺术等领域,“媚俗”在当代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
一、消费时代文学媚俗化倾向的根源
媚俗是一种典型的伪审美现象,或者说,是传统审美无法正确回应消费时代审美挑战所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与欧洲》中指出:“媚俗就是把流行观念的愚昧翻译成美丽而富于感情的语言。”媚俗的目的是“向绝大多数人讨好卖乖”。我们可以对媚俗进行一个大体的概括:从生产机制来看,它是工业技术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机械复制的产物。从产生的目的看,它是为了满足人们潜在的欲望和逃避崇高的需求,具有市场化、娱乐化的特点。从表现上看,它是一种制造而非创造,呈现的是表面化、低层次的水准。从具体对象上,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现象都有媚俗的影子,从通俗文学、消遣性小说到流行音乐,从真人秀节目到广告、影视,“媚俗化”的现象无处不在,它消解了文化精神内容与大众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媚俗”已经从原本处于尴尬境地的备受批评的文化形式转向为一种较为成熟、较为体系的理论话语。
“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①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后工业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当剩余价值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成为促进社会大生产的重要动因。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时代中商品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比如对“洗衣机”这个商品内涵的变化分析,传统社会看重洗衣机的使用功能,而在商品社会中,消费者更注重洗衣机背后所象征的社会地位和高端生活品质的享受,对商品背后所代表的内涵的追求正是建构消费社会的重要因素。消费的实质其实是“符号消费”,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的本身价值,而是物背后所代表的阶层、身份、品位等。
在当代,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学也不能避俗。当经济利益被提高到至上的地位,文学这块曾经被视为超功利的领地也被市场化所浸染,文学原本的纯粹性、崇高性逐渐被消解。在消费时代,人们对文学需求不再是因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而是把文学当成一种修饰自己、抬高虚假品味的工具。消费时代的文学强调市场化、大众化、娱乐化,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属性,由追求崇高转向躲避或者亵渎崇高。文学作品从肩负“文以载道”到以读者的需求为指向,迎合某些人追求刺激的心态。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到,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心理追求导致了艺术标准的堕落,艺术的纯粹审美性被泛化,艺术被当作一种购买、消费的工具。在一个文化变成消费的时代,一次性、短暂性、瞬间性的工业文化代替了持久性和永恒性的精神文化,文学的神圣性被消解。消费时代文学“媚俗化”的出现一方面有其社会原因,直接诱因是市场经济下商品化的发展。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强调生产的社会被强调消费的社会所取代,商品的生产更多考虑的是消费者的需求,社会的潮流把文化符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卷入这场狂欢当中。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以意识形态启蒙为主的文学也受到了来自消费意识的挑战,从文本形式到作品内容都不可避免地为大众文化所影响。其次,面对外部环境的转变和作家身份角色的突围,文人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精神的冲击和认同危机。是坚守文学纯粹的良心匠心,抑或“下海”追随消费时代的时尚成为摆在当今时代文人面前的难题。最后,文学“媚俗化”的兴起还有文化背景。随着后现代的繁盛,市民社会兴起,整个社会也在走向世俗化,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幸福和世俗的体验。随着商业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诸多现代生活时尚和文化时尚相伴而生,大众影视、时装表演、流行文化、脱口秀等凸显了消费时代的特色。这些时尚的兴起释放了人们的欲望,解放了人们长期以来被各种规范和理性所压抑的天性,表现了人的本能和世俗取向。在快节奏的生活时代,人们更倾向于通俗易懂、浅薄、能在短时间内收获到阅读快感的消遣性作品。
在消费社会下,我们应对文学“媚俗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既不能固步自封把文学束缚在传统的藩篱,亦不可任其发展为商品经济的附属品,失去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认清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文学“媚俗化”现象,实现文学艺术性和商品性的统一,成为实现文学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接下来,本文拟从文学“媚俗化”的表现来分析消费文学“媚俗化”的面貌。
二、消费时代文学媚俗化的表现
(一)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
接受者和创作者之间进行的是有艺术特征的文学活动,他们对文学价值的共同追求造就了文学的意义。而文学的消费主要由消费者决定生产,文学不再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而变成了工业化下的批量生产,它具有一定的模式和套路,更多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个性和欲望。在产业化的生产体制下,商品性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属性。创作者和出版商都尽可能考虑市场读者的需求和欲望。在当今的文化市场,消费者就是上帝,消费者需要什么,市场就流行什么。消费者的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文学市场的方向,消费者的阅读兴趣成为文学市场上的经济杠杆。我们应当承认,大众文化有其兴起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也并不排斥文学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和欲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学的接受者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表层的快乐和赤裸欲望的满足,它还应该体现出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和美感追求。如果作家一味追求利益、放弃良知、逃避责任而只去创作“媚俗化”的作品,就会于无形中助长社会风气,降低社会的审美层次,腐蚀当代人的心灵。在追逐经济利益的消费社会,文学创作不可能顾影自怜,自说自话,脱离社会,它只有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有发展的可能。因此,当今的文学生产不得不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
(二)重制作轻创作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艺术作品由膜拜价值转变成展示价值,本雅明察觉到现代消费文化逐渐变成一种感官性的文化,美成为一种制造而不是一种创造。在消费时代,拼贴、抄袭现象层出不穷。消费社会下的利益诱惑和市场趋势,留给创作者单纯且安静的环境空间越来越少,很多创作者已经像流水线上生产的廉价商品一样,按照市场的套路和庸俗的框架模板进行文学生产。比如在一些网络小说里,特定的框架模板像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消遣性作品,大量的复制品涌入观众视野,作品的“光晕”消失。我们发现,媚俗文化与消费社会保持着一种同构关系——它几乎是替代性的消费社会的表象,替代性的消费社会的经验,是一种模仿,流于感官化的经验。在消费市场中,各种文学作品类型化趋势严重,通过标题或者“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盗墓”等提示语,或者作品开头的一段叙述,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对作品格调或者大致内容的把握,轻轻松松就完成一个文学消费的过程。媚俗文学正是通过这种类型化的操作完成其商业价值的,在标签、外观确定后,寻找可填充的内容,一部被“拼贴”起来的文学作品便迅速完成了。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所有被拼贴在一起的文化因素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被从精神、心灵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了出来,并被转换为操作性术语和问题。”
(三)文学批评的涣散
在文学“媚俗化”的过程当中,文学批评也朝着讨巧市场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说评论家们都沦为金钱的奴隶而放弃自己的文学良心,而是说很多批评家受到消费社会的商业思维影响而不自知,正如杰姆逊所说:“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为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
随着艺术商品化的不断发展,文学创作更加自由化、通俗化、泛审美化,文学商品的商业规则也把文学批评纳入其中,使文学批评成为“待炒作”文学作品、文学家的宣传手段,文学批评失去了其严肃、客观、公正地评价文学作品的权力。严肃的文学批评被同化成一种“游戏”:要么不深不透,隔靴搔痒,泛泛而谈;要么通篇美言,好话谄媚,宛若圣作;要么转弯抹角,宣传促销,活像广告。这种“另类”批评已经完全打破了文学批评的“生态平衡”,成为一种有弊害的“媚俗”批评。这是一个“文学批评精神”缺席的社会,靡靡之音代替了“激浊扬清”的正义感。
在这个物欲膨胀的消费社会,在媚俗的审美文化和“潜规则”作用下,有些文学作品已经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丧失了高尚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境界,代之以颓废、腐朽的精神霉味。这种现象,本该成为文学批评的靶子,然而遗憾的是,在众多名利的诱惑下,部分文学批评家失去了个性和对文学的坚守,成了“媚俗化”趣味的“鼓吹手”。消费时代是一种现实,文学批评是融于现实之中而非任意游离现实。“媚俗化”的文学批评也反过来影响了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好的批评导向作用。
三、消费时代文学“媚俗化”的出路
(一)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消费时代的媚俗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问题不容小觑;但文学依然要坚守文学的特性,艺术性、审美性、社会效益仍然应该成为消费时代下文学创作的重心所在。消费社会下的文学要实现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应该以审美性、艺术性为主导,兼顾商业性和市场化。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要考虑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才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要服务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社会价值要与历史的、人民的标准相联系。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作品的商品性和艺术性也并不冲突,同一个歌女,她在街头演唱的时候是非生产劳动者,而当被歌剧院老板雇佣为赚钱而唱歌的时候是生产劳动者,纳入了生产资本过程中。但无论歌女处于何种情境下歌唱,她的艺术水准是无差别的,在她身上艺术性和商业性实现了统一。因此,当我们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来分析消费时代中的文学“媚俗化”现象,它既可以受到金钱的驱使,但也要注重其艺术性,建构大众文化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正因为文学作品有着特殊的使用价值,即教育、审美、愉悦等,文学作品才能产生资本价值。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并非物质价值,而是诉诸人的精神价值和审美心理感受,是精神上的陶冶和升华。巴尔扎克也曾为了市场化而写作,但在其创作中留下了享誉世界的精品。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探析资本主义商业文化时提出:“金钱动机确实促使作者去写出更明白易懂的作品,但是,这种动机也常常促进高质量和文学价值的形成。提供娱乐的动机并非必然与作者探索具有思想深度、敏感和高品质的题材的能力发生冲突。”②
(二)借用媚俗的手段表达崇高的主旨
消费时代文学的媚俗化把人潜藏的欲望、创造力和破坏力极度释放,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机会和更多元的表现空间。“文学是人学”,创作者可以从丰富的人性中挖掘出更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如卡琳内斯库所说:“现今世界上没有人能幸免于媚俗艺术。”在实现真正美的艺术和文学的价值过程中,媚俗作为必要的步骤而出现。既然在当下的社会,媚俗无可避免,我们不妨利用媚俗的手段,去表现出崇高的主旨。崇高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个审美范畴,但在商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崇高被逐渐边缘化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追求媚俗,排斥崇高,躲避崇高,导致了崇高审美的堕落。其实,崇高和媚俗看似是对立面,一个是主流精神的弘扬,一个是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个表现真善美,一个则是投机取巧利益至上。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两者之间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媚俗也显示不出崇高,没有崇高,媚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消费文化催生下的大众文化兴起,文学“媚俗化”现象凸显,文学变得娱乐化、平面化、市场化,以严肃为主调的精英文学被排挤到边缘。颠覆英雄,恶搞经典,身体写作,凡此种种,让人们对崇高的态度由仰慕走向了相反面——消解和嘲弄。那么我们应如何从消费社会的媚俗化中脱离开来,重新走向崇高呢?笔者以《亮剑》为例,探析崇高与媚俗的和谐统一。《亮剑》塑造了李云龙、赵刚、秀芹、张大彪等一系列英雄人物,这些人物都展现出崇高的精神特质,他们身上有着对人性激励的品质。但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宏大叙事,采用英雄中心论、英雄无缺陷的手法,而是还原人性的本能,他们既英勇作战,作风硬朗,忠于祖国,又能大口喝酒,说脏话有脾气,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个英雄符号。作者在表现爱国作战的崇高主题时,不再拘泥于严肃、抽象的说教,而是消解了传统,颠覆神性般的英雄,把英雄平民化、世俗化,这是对过去的反叛,对历史的再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读者、观众审美趣味的一种迎合,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媚俗。因此,面对消费时代下的文学“媚俗化”现象,我们并不需过于悲观,就像在看过很多仿造凡·高的作品后,一个观画者或许最终有能力去欣赏一位荷兰大师的绘画真品。他也许最终会意识到,即使“艺术”被误解和利用,但真正的艺术也不会失去其价值和美学真理。谁说崇高和媚俗不能实现辩证的统一呢?
四、结语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景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媚俗固然是文学精神的堕落,但它揭示了以往文学对现实某种程度的忽略。在文学创作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被淘汰的文学媚俗之作里能否留下有营养的因子,成为后面文学成长的养料。
由此说来,媚俗也许并不可怕。借助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工业下的艺术生产能在短期内产生大量文化产品,虽然大多数作品良莠不齐,能称之为经典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作品还不多,但有些作品能够与时俱进,体现出当代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状态,为当代人发声,不可否认大众文化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如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光晕”消失了,但艺术品也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由艺术走向了大众。在当今消费时代,文学艺术发生变异、扩容、延异都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托马斯·沃尔夫曾坦言:“我难道会出卖我的艺术良心,把我写的东西卖给好莱坞,让好莱坞拍成一部影片?我的回答总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是的’。如果好莱坞要买我的书拍电影,以此来‘奸淫’我,我就不仅心甘情愿,而且热切希望诱奸者快快提出他们那头一个怯生生的要求。”
文学发展具有自在性和媚俗性,自在性可喜,媚俗性可忧。我们要进行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建构,与媚俗进行抗争,坚守文艺的底线,坚守艺术至上的生命体验。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精神的家园来安放漂泊的灵魂,我们依然要有对美和诗性的追求。
①〔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② 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