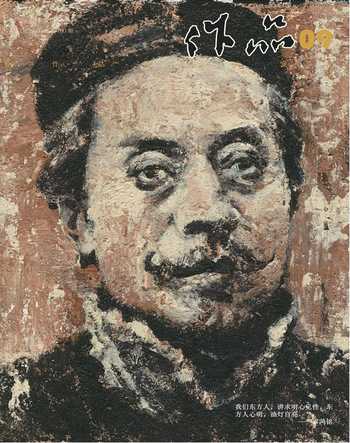割礼(短篇小说)
骆力言 姚海燕
推荐语:姚海燕(华南农业大学)
《割礼》创造了一个属于女性的鱼尾神话。世世代代,女性总在生命的延续和更生中自省和自我定位,在社会变迁的适应和抗争中重铸性别。在女性面临的所有难题中,家庭女性间的关系,特别是母女矛盾,是性别自省和重塑中无法逃避的话题。这一切主题都嵌入作者的文中,引人深思。
《割礼》将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爱与厌恶,紧凑又轻盈地表现出来,将各种意象,文化符号,神话原型糅合起来,还有湿漉漉的如藤蔓般蔓延的语言,蔓延期间的文学自觉与思考,构造出具有广东气质的,鱼水虫鸣的深山神话。
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深夜酣睡的人们的脑袋上总会盈亮出一汪厚厚的水,有人猜测这是梦的形态。无需要触碰,它们会自动淋落在床头,像条晶莹的蛇般深扎入地中。没有一个老人与我们说过这般神奇的事,但只要留心去看,便会发觉墙上每一条呲开的湿痕都有其形成的缘由,你可以抬手去摸一下它,能触到一股股呼吸,悲怆或是愉悦。
秋分已经过了,但母亲的菜园里大片的秋葵还未摘下,它们老硬尖锐地朝上空刺去。菜园里并没有可以红旧的树种,南粤的红土烧疼了北朔的脚,它不敢使力朝南。绿植顶多与秋葵一样由鲜绿而变得灰硬,作为对时季变换而兑守的最大承诺。屋子在菜园的幽深处,秋天灰蒙的天与树影一起蓋上来,仿佛活埋一般,死一样沉黑。台风刚从城的上空滚过,上了氡山的坡就一脚踩上了山口,山口那座用竹竿支棱起来的长桥碎在它的脚底下,正如它此前零碎地支起一条飘摇的路往着远邈的城,碎而远地被摧毁了。母亲说,该坏的,总有一天会坏。桥是通往城里的唯一通道,在修好之前我都没有办法和哥哥们一起回城里上学。我坐在房间里,并没有点着灯,屋外滴着水,窗户开半口,雨泥的腥气挤进屋子里。太阳过了秋分就下得早了,没了阳光的灼烈,天色很快就能被屋子吞入肚。它有一口冰冷狡猾的嘴牙,吸溜着白日的光,这种蚕食在傍晚尤为明显。好几次,我坐在园子里,看妇女们与母亲外婆吱喳完后走进屋时,夕阳染在她们的衣裙上,烧上了瓦头。接着我能看到天光缠在我的哥哥们的脚踝上,他们飞奔而来,闪进屋内,随之瓦上的红血与白昼糅成一团巨大的粉汹涌地滚了进去。哥哥们好玩,并不顾忌将近的返学日和未动的作业,也即使在雨后潮湿的田里,他们的打闹声都能杂着泥浆溅上我房间的窗户。我低下头,双手撑在床上,指甲挠着坚硬的床板,反复地又不使力,免着木屑插进肉里。门被人顶开了,我抬头,对上母亲脖子以上的那片耷垂阴影,她没吱声,沉默地把一沓衣服放在书桌上,桌上被压着的钢笔并未合盖。我扭头看了看窗户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
桥还没修好。
谁说的?
你爸。
我回头扫了一眼黑糊在屋内的母亲,她此刻漏出两眼莹白和灰色的嘴唇,它开合着让我出去吃饭。我没有答应,因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她又补了一句,吃好睡好再说。房间里依然没有点灯,屋子的地板上陈列着白日灰暗的死尸。有几只宿鸟在外面的枝丫上尖哑了几声,我又问,什么时候?母亲说,只是可能,都听你外婆的。我想回学校。我的双眼猛地热了,我想出去。咣当一声,菜园的大门被大哥合了起来。母亲有些动容,她上前,摸着我的头,没事的,乖,每个人都会经历。
晚饭的时候,母亲在外婆的耳边呢喃着,父亲扒完饭就点了支烟抽了几口。我坐在哥哥们旁边,他们的双腿在桌上女人一样大开着。突然门外传来一声扭曲的笛音,很快,仿佛应和一般,从另一个方向又传来另一声。哥哥们听到后讪笑着看我,我狠狠地瞪着他们,他们依然笑,笑得双腿豪脱地抖着,这样两条长而壮的腿,能够以相似的姿势抖着,在我六岁的不同时刻,在厕盆上蹲下时,由于我足够矮小,能够朝着贴近地面而霉烂裂开的缝里瞧见大哥和二哥的双腿抖颤的样子。他们各人都把头靠在大澡盆的边上,背斜着放空,澡盆不算深但相对是小的,我看不见他们的屁股,他们的黑腿溢了出来,像面条一样垂落下来。他们的双眼紧闭,下唇包紧将呼吸移交鼻孔司令,有节奏的喘息像发号施令一样,全身跟着抖颤,连脚趾头都抓紧,仿佛从半空掉落的蛤蟆,只能手脚紧攥,连毛孔都收缩起来。如今那些黑面条以嘲笑的姿态向我抖着,我无言地望向我的长辈。外婆在听到笛音的瞬间就神色凝重起来,她与母亲聊完后,笑着与我说,不急,再看看。我机警地看着老人的脸盈满了晶莹的汗水,它们渗进褶皱里,晶莹的小蛇爬满了老人的脸。
晚上睡觉前,我在浴室里刷牙,哥哥们刚用完厕所,即便刚冲完水,尿臭味依然蓬在里面,我缓慢地刷动着。牙刷的毛长而硬,我使劲撑开嘴腔,小心地刷着。树影在窗外摇曳了许久,等我反应过来,屋子内的烛火已经沉落下来,甚至能听到它们在空中崩断的清脆,它们碎成豆粒般在地上滚起来,滚进许多罅隙里。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了些鸟寐和狗叫进来荡几圈,推起了任何可以翻倒的物事,星光和月色尾随而入,照亮了不同房间盈出来的梦。梦从房内溢出来,莹亮地纵横在地板上。我依旧在刷牙,看着我的脸从黑屋里浮出又沉没,仿佛是另一种溺息。这时一声悠扬的笛音从很远的地方漾了过来,我赶紧咕噜了几口水后来到窗前。屋外墨绿的园里浮满水雾,高筑底泥墙被月光烧得灰糊的,长长地围在遥远的四周,似乎是一座巨大的陵墓,冗长的墓碑,刻满了死者的寐语。
氡山隔壁的湖边就是个乱葬岗,为了开发成一座花卉园,骨头被乱糟糟地用花盆装起来,以示生者对无冢魂的尊敬,可很快的,花卉园的花盆与这些小坟墓七上八下地被混在一起。母亲跟妇女们聊完后,便不再上湖边买春花了,园子里原先买的那几盆因种上了柚子和桂花,便设想着万物有灵,互相净化了,便也不再管。我小时候,会猎奇一般去盯着那几个墨绿的大花盆看。它们是瓷的,外面一层是朴素的漆面,光滑。摸上去坚硬冰滑,那时我坚信那就是死亡的触感。听人说学校操场也曾是一个乱葬岗,甚至还是日军的靶场。因此,它建筑的形状是一种有封印意味的符号,一个长的足球场突露在前方,观众席往后置在高耸的阶梯上,外面封了两三层大理石。
但最吸引我的并非是这所谓形状,而是那三幢高耸的观众席,学生们入场都需要上两层楼的高度,高得使人心慌,栏杆也层层包绕使人喘不过气。它们才真算是一种墓碑,那么庞大,崇高而有魄力地矗立在邈远的原野上。他喜爱站在最旁的一侧,衣服只扣到末尾倒数第二粒。每次他踮起脚板书的时候,我能看到那一片往上紧实往下神秘的肌体,这使我握笔的手焦躁地渗出汗来。
操场其实地势极为低洼,有许多旧积不散的水洼,经过长时间的雨季,它们长久地积在那,能肉眼可见地将地表侵蚀成一洼洼的坑,没有人在意,至少没有人会相信它会侵蚀成什么样子。慢慢地,它们浸死了围在四周的草,靠近树木的,能看到可怜的根垂绦在里面,烂得青黄发白。他高傲地抬起长腿越过萋萋的足球场和这些水汪深幽的巨眼,手执长笛,在晚饭前后,人影寥落时走上他的舞台。我坐在对面的看台上看他吹笛,日光烧尽的灰末淋在他的周遭,被堆埋起来,在冬天的暮色里,他时常被浇铸成一块滚烫的黑石。我长时间地盯着他,直到这块黑石在视野里发生了变形,似是在游走,似是在舞动,甚至像在朝我招手。
他大概因我作为一位准时的听众而注意到我了,也许因为我借着读书的理由跑到他吹笛的看台后大声朗读他教的课文。终于有了那天,我再忍不住,便斗起胆朝他的方向,走进了足球场内,半萎和绿黄的草没到我的小腿。我离足球场的中心很远的地方就僵住了,他所处的看台遥远而高耸地往上。但我依旧堂皇地站在红灿的天光下,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影子黑得浓烈,仿佛能在这片空寥的草地上灼出一个洞。他朝我走来时,我的双脚深陷泥沼无法动弹。
他有时与我同执一本书,他牵着前端,我拿着后端。他领着我来到看台后的走道里,走道连着野外的湖和树,草与废弃的建筑石料。灰白的冬日笼罩在这片圆形竞技场上,枝丫与细叶耸在白色的阳光里,黑枯得像幢幢人影,它们有的密集地匍匐在矮木上,有的突兀地立起撑开另一片黑影,而湖泊在后方终年墨绿着。我们伫在一汪大水洼前,他让我蹲下,让我低头仔细看这汪被雨水积得黑污的水洼,污渍淤了一层又一层,浓稠得使人看不到底。他指了指某个方位,那里,我发现过人鱼。可他所指的方位过远,我往前倾时啪地一声不小心朝前跪了下来。他的手温暖地压了上来,哑声道,别急,仔细看看。
那片水在冬日的白阳下显出一片灰黑的天,淤烂的污渍浓稠的水,风吹过也不曾动弹,仿若一潭死去很久的湖泊,黑而深。我感觉被太阳晒得有些热了,一摸头顶,烫手。这时,在日光下,从那个方向,粼粼地翻出了亮光,朦胧的,是一条黑色的鱼尾。当我试探地伸手碰向湖面时,他却紧紧地压着,告诫道,轻一点,小心。话落,似是被惊到一般,鱼尾又潜了下去,接着一股浓黑的发丝朝上涌了起来。他猛地将我拽起,我的手布满了潮湿的沙粒,我不舍地回头,瞧见水面上映出一副惨白的面容,这确实是人鱼吧。
我给他的信,被他漏在会议上。他的课被安排成了许多代课和自习课,而我之后就跟同学一道放假回了家,台风尾随而至。回家那一天,闷热得能使人窒息,全身的衣服湿漉漉地粘在皮肤上。路上能看见许多翻肚的蟑螂和已经成泥的断块蚯蚓,罹难者们被蚁群包绕。蚁群们绕过老人的枯脚,要去搬抬它们今晚将要在高处享用的食物,而老人们坐在屋外共同说道,打台风了。
台风其实并不猛烈,只一脚踩碎了竹桥,几场夜雨漫过氡山。雨后能听到许多人走动的声音,甚至全家人还没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门。母亲踏着拖鞋踩着红泥去开门,又踩回来,说了好几次都是送奶的人,可她的脸总不显高兴。妇女们在放晴的白日又爱来走动,尖笑与大嗓门齐力并发。母亲应付着,又应付雨后的菜园。
风将我的手吹得冰冷,我意识到已经站了许久了。月光透过窗直直地洒进来,软而暖。它湿沥地从我的脖颈上一直滑下去,一片柔软的野地,山丘软绵地拱起又落下,一直伸进暗色里的两条黑腿,它们羞赧地两个膝盖撞在一起,合成一种鱼尾的模样。
没有点灯,我挪开那沓衣服,最下面的一件已经被钢笔点染了大片的墨,但这似乎也无关紧要。我回头确认了房间外的寂静后才坐下来。月光循着我,又想要投进来,却被菜园里的树丫切割得细碎,惨戚地在雪白的信纸上踱出微小的足迹。我摩挲这片空白的页面,禁不住细想他读信时候的反应,他那几只粗大的手指笨拙地挑开信件的末端,该是多么的可爱。我提起笔,一口气写下一行字,很快又划掉。太俗气,要美些。我想邮差明天会来,即便桥没了,他也会来,坐船也好,总要送信的。我想着,手里挠着腿上秋末的几个蚊疙瘩,却不小心使错了劲给挠破了,便用衣服去擦。但衣服粗糙的质感压在身上时,顿觉一股骚动团在喉间,我又回頭确认了一番外头的寂静后,我回过头。重复地用手去抓衣服,也没有管挠破了的地方怎么样,就一直使自己的手掌与衣服相摩挲,这件衣服内层的布料像只巨大的纹路斑驳的手掌。我又回头再看了看房门外,然后,尝试用衣服去抚摸两条黑腿。这时我才惊恐地看到我被挠破的地方在大量地出血,稍一按压,血仿佛决堤一般激烈地呲了出来出来,血流很快便滑成条纹状,我尝试用衣服去擦,但却惊恐地发现衣服对血液并不起效用,甚至滴血未沾,我眼睁睁地看着血流迅速地交织成一片。伴随着血液的溢出,阵阵剧痛从皮肤的纹路中压出来,仿佛肉在被片片地剜开,因血液的滑溜我再也坐不稳了,猛地摔在了地上。腿脚刚一触地面,窗外破碎的影子便像饿急了的爬兽一般缠了上来,它们仿佛在吸食些什么一样,伏在我的腿上微微颤动。借着月色,我看到地上满是黑色的鱼鳞,它们如星屑般闪烁。
哥哥们的房间里此时倏然传来响动,随后父母的房门也开了,外婆的嗓音颤颤巍巍地摇着。
屋外的门被打开,有人走进菜园里,擦了火柴。现在我的腿紧紧地合在一起,皮肤上渗出了许多黑鳞,透着海洋的咸腥味。我想要站起来,我想要离开,也只是希望能钻个床底,但这条丑陋的鱼尾使我无法动弹。房门外扑腾起来的许多声响朝这涌来,母亲领着其他人撞开了房门,她看见那个只剩上半身的女儿下身甩着一条黑鱼尾。半晌的静默,使我能看到夜色的沙粒磨过他们的脸,不堪一摧的样子。我被他们架上了床,这时,我才看到菜园的花盆前火光一片,外婆穿着水绿色睡衣的身体烧在香烛里,化作了一泡墨色的湖水冰冷地覆在花盆周围,安静地叩拜。
我的手被哥哥们死死地摁住,月色灼亮了母亲手中的刀具,我张着嘴呼喊着,但我没有看到呼声被窗外的绿植攫住,像捕蝇草一样消进茎叶里。母亲辛苦地割着,那把银色的小刀磨在坚硬的鱼鳞上,每割一刀都会溅出数块鳞子,直到她气喘吁吁,满头满脸都是黑鳞。父亲见状便提了一把弯刀砍了下去,刀卡在尾巴上,血吐了出来,却没有断开的意思。我机智的兄长们,去厨房拿了一把刮刀,要将尾巴上的鳞片都磨掉。我全身汗淋淋地躺在床上,身上铺满了黑色的星屑,沾血的边沿映不出光。几经割磨,我的尾巴血淋淋地残碎了,但依旧倔强地微颤着。此时,父亲提议用伐木的铁锯,兄长们应允了,三人便出了房门。
我躺在床上,看见天花板上的霉斑咧开一条条崎岖的裂痕,像一朵奇怪的巨花。我转过头,看见桌上那支钢笔被月光烧得白灿。我的眼热极了,五官用力地曲折起来,但眼里却挤不出什么。我从床上爬起,让母亲将钢笔取来。我怜惜地抚摸着它又心痛地瞧着这条残尾。窗外的烛火燃了上来,火中飘摇的花盆里正不断地溢出黏稠的泥液,外婆背对着我呢喃。这时,我看到一块光滑的大骨从泥中浮出,粘着根与叶。在吟声落下的时刻,那块莹绿的骨头猛然迸裂,一条绿藤如虫一般爬了出来。我听见父亲走回来的脚步声,我再也不能等了,我拔开笔盖,用尽全身气力扎了下去。
翌日晚,我点着了我的第一支烟,吸一口后许久,才沉沉地睡下。剩下的烟头浸没在父亲的梦里,那条晶莹的蛇呲啦地尖叫着而蒸出了水汽。然后,我梦见了桥,它零碎地支撑起来,通向那邈远的城。
责编:周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