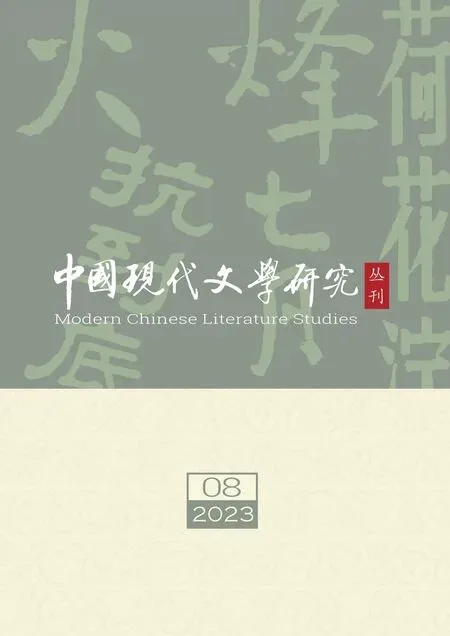危机时刻的历史记忆“发见”和修辞: 论抗战前的晚明想象与言说※
鲍良兵
内容提要:19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是日寇不断进逼。面对日益恶化的专制政治和严峻的亡国危机,作为深受史传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以古鉴今,鉴往知来,则是“晚明”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和记忆的重新“发见”。晚明历史经验亦成为知识分子观照当下的重要视角和思想资源。论文聚焦不同政治文化社群的代表性人物对晚明的言说和想象,梳理和勾勒了晚明的“风雅”、“异端”和“乱世”、反抗与暴虐、经世致用和强调气节等不同面向,认为围绕晚明诸面相的言说和不同想象背后,是知识分子对历史文化记忆的重构、挪用和交锋,其固然渗透着文学理念的碰撞、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亡国危机下文学和文人“何为”以及“如何为”的问题,寄寓了知识分子深刻的忧患意识,以及如何因应乱世的想象。
1930年代前后,中国的现实似乎又历史循环地进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政治时代。1927年,国民党在北伐获得节节胜利后发动残酷的“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1928年,随着“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开始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和思想文化上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在外交上则是不断对外妥协,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外患方面,则是更大的危机袭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1月28日,日军偷袭上海,破坏甚巨;1933年,进攻榆关,攻占热河;1935年则策划“华北自治”,试图进一步将华北变成另一个伪满洲国;及至1937年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一党的专制,政府的腐败,国事的陵夷,现实中的中国危机四伏,恰如周作人所言:“现在似乎又是明季的样子。”1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散文全集·5(1927—1931)》,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检视当时史事,晚明历史亦如“现在中国写照”。明末外有满洲异族入侵,内有政治腐败导致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而当时的中国则内有专制统治,外有日寇进逼,相似的历史情境赋予时人“明末”式的“政治感受”。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1933 年日寇进入山海关,当时知识文化界人士普遍产生如郁达夫所说明清鼎革的“活剧越演越像”2郁达夫在《山海关》一文中写道:昨天我们几个敢怒不敢言的穷小子,还在私议,说中国目下的现状,正和明末清初的时候一样,有南朝的天子,也有北地的吴王,还有洪承畴、钱牧斋,还有马士英、阮大铖,还有一班在议避讳、上尊号的读书人,色色俱全,样样都有,但只缺少了几个史可法、瞿式耜之类的呆人。现在山海关一开,这一出“明清之际”的活剧,越演越像,越演越来得起劲了,但我们的这些在台下看戏的人,都因为上了年纪,有了一点智慧,非但叫好不敢再叫一声,就是拍手也不敢再拍一下,战战兢兢预备着一副眼泪,好于大难来时也上台去演一出“哭庙”的悲剧。(郁达夫:《山海关》,《白河》1933年第2卷第16期)刘大杰在《笔话》一文中称:现在我们的吴王,总算双手开了那座玉门关。从今以后,我们也无须再去读王之焕那几句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了。想起当时清兵入关的情形,同这时候比起来,是有几分相像的。所不同者,今日的陈圆圆,比不上昔日的陈圆圆罢了。在我们这个春风得意的南国,好像也还都在弹冠相庆地过新年,争椅子坐。就是有几个穷苦书生,愁苦地望着塞北的烽烟,也不过叹息一两声而已。(刘大杰:《笔话》,《白河》1933年第2卷第16期)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晚明”史事来喻指当时局势已是抗战前后知识阶层普遍的集体心理。其中最典型的是1932年4月史学家陈寅恪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稍显奇怪”的短论:《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从此残篇中,陈氏总结出三百年前明朝“废兴得失的关键”在于“既不能力战”,又不敢“毅然自任”言和,最终“坐以亡国”。表面上他的评论针对的是明末清兵进攻东北,但其背后则指向当代日本攻占东北之事,实是以明末之史喻当世之变。具体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的忧惧之感,中国仿佛在历史的永劫回归中再次进入“天崩地坼”的危机时刻。本文所谓的危机时刻,与其说是历史嬗变之临界点的一种时间修辞,不如说是身处特定历史情境之下知识分子主体性紧张的心理状态——对一种可“怖”降临的持续焦虑。事实上,作为深受史传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其中的敏感者,通过与历史对话,以古鉴今、鉴往知来,是久之而成的思维模式。所以,面对日益恶化的专制政治和严峻的亡国危机,则是“晚明”这一历史时段和记忆的重新“发见”。晚明的历史经验也成为知识分子观照当下的重要视角和思想资源:“通过对过去的经历与认知,人们进而形塑了自己对当下、未来有关政治行为的态度和反应。”1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而作为一种方法,“晚明”诸面相的言说和想象背后,关联的是知识分子“深刻的忧患意识,以及如何应对乱世的思想模式、道德伦理、情感结构和行为模式等”2刘奎:《危机与救赎:一个新文化人的“南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其实,当时的知识分子基于自身立场,对于“晚明”的言说与想象是人殊意异,正如学者赵园曾指出的:“鲁迅与乃弟周作人的明代、明末的印象已大大的不同。……周氏兄弟对晚明的不同想象,与他们对当世的观感、处世的姿态无疑相关。无论周氏兄弟还是其他人,以晚明注当代,据当代读晚明,‘互文性’的根据,都在当时当世的时代空气与知识者的自我认知中。值得追问的是,不同时代的关联,是如何经由想象与叙述形成的?”3赵园:《叙述与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本文聚焦抗战前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晚明”的言说和想象,试图勾勒和探讨亡国阴影下,“晚明”展现出了哪些面相?这些面相的背后有着时人怎样的观感和心声?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和对历史、现实的观察又是如何影响其所谈论和想象的“晚明”?
一 “风雅”晚明与“亡国之音”
1930年代的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是晚明小品文热。这股热潮,一方面缘于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苦雨斋”师徒的大力表彰。另一方面则得力于林语堂等人在上海的创作和商业出版的介入。南北呼应,一时晚明小品成为阅读时尚,凸显了一个“风雅”晚明的历史图景。而这个“风雅”晚明的背后,则天然地粘连着“亡国之音”的政治性批判。
自1926年周作人为俞平伯重刊的明遗民张岱作品《陶庵梦忆》作序开始,到1928年分别为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燕知草》作的序和跋,以及1931年在给废名的作品《枣》和《桥》撰写的序中,“晚明”小品文与现代散文的关系一再成为周作人强调的重点。而真正使晚明小品文成为文坛热点的是1932年周作人和弟子沈启无的一次合作。1932年,北平人文书局同时出版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和其弟子沈启无编选的晚明小品选集《近代散文抄》。有理论支撑,又有作品示范,周氏师徒将现代散文的源流锁定“晚明”,勾勒现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紧随其后的则是上海出版界和文坛的介入,旧书重刊、小品文编选以及创作上的模仿。1934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有不为斋丛书》出版,收入丛书的《袁中郎全集》一版再版。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开始出版由襟霞阁主人(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共22种,内容以晚明小品、明清小说和笔记、游记为主。1935年到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推出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50种,包含诸多晚明小品文集。与旧文重刊的类似的是晚明小品文的新编选。1934年9月,北新书局推出刘大杰编纂的《明人小品集》。1935年3月,南强书局推出了王英编校的《明人日记随笔选》。1935年4月,光明书局出版了施蛰存主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1936 年7月,大江书店则出版了阿英编撰的《晚明小品文库》(4 册)。此外,还有朱剑心的《晚明小品文选注》。
晚明小品的选编与重刊,从传播角度看,方便读者的购买和阅读,而便利的背后则是晚明小品文形象乃至晚明形象的重新塑造。事实上,选本在其编纂过程中无形中渗透着选家的目光,从而厘定新的经典和重塑价值。纵观1930年代选编的晚明小品文集,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分上、下两册,以公安派和竟陵派为中心,收录了17人共172篇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晚明小品文的特征,以一种隐逸的态度寄情山水,强调生活的闲适的艺术化,展现创作者“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文学态度。而以《近代散文抄》作为一个评价标准来看施蛰存、刘大杰和阿英等人的选本,“更偏于闲适一边的是《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与沈编相近,而《晚明小品文库》更强调了晚明小品正经的一面”1黄开发:《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在这一波的晚明小品文热中,与旧刊重印和选本出版相比,小品文的提倡和写作无疑是至为关键的因素。而林语堂显然是其中最为有力的宣传者之一。一方面,他呼应周作人的理论,出版“有不为斋丛书”,表彰公安派“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的小品杂志,以文论和小品实践,提倡“幽默”“性灵”的“闲适”文学。
林语堂之所以提倡晚明小品文固然得益于周作人的启迪,从中发现了袁中郎的“性灵说”这一中国本土理论与其所表彰的西方表现主义理论相契合。“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1林语堂:《论文》,《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而在乱世之中,林语堂着力提倡看似“不合时宜”的“幽默”和“闲适”,除了考察其背后的文学理念之外,还有必要将其纳入现实政治环境和知识分子情感结构中审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林语堂逐渐从政治中撤退出来,试图做一个纯粹的文人。从《剪拂集》(1928)中的愤世凌厉到《大荒集》(1934)中强调由“草泽”而逃入“大荒”,可以看到他的转向:对于下一站是“十字街头”,还是“深林”尚有犹豫。“大荒”之中的林语堂无力正视现实的残酷,但尚未能做到遁世者全然“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无讽刺,另一方面则以出世的姿态,对倡导“血和泪”的革命文学也加以讥讽,将两者皆视为“载道文学”,“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2林语堂:《有不为斋丛书序》,《论语》1934年第48期。。以一种潇洒且平和如斯的心境,继而在“国势阽危”,不容“有闲情别致,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现实中,不无揶揄地反问:“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进而搬出科学“生理学”,强调“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3林语堂:《有不为斋丛书序》,《论语》1934年第48期。的需要,林语堂“理直气壮”的辩驳背后,固然有对现实政治的批评,但也与林氏自身无力面对逼仄的现实,转而欣赏晚明小品文背后的悠闲生活方式和情趣,为自己营造一个情感隐逸的空间不无关系。
于是,经过林氏的提倡,“一种经过西方绅士文化的节制与幽默的熏陶,以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静穆超然为底色的叙述方式和行文风格确立起来了”1裴春芳:《经典的诞生:叙事话语、文本发现及田野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47页。。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对其批评还是认同,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围绕小品文的文体特征与文化功能的争论,使得一种以林语堂为中心的小品文论述范型(以小品文为闲适、性灵的文学)被确立起来了。
随着商业出版的介入2施蛰存在《晚明二十家小品》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编这本书,主要是为了稻粱谋。“这一本集子的编选,我并不想曲撰出一些理由来,说是有一点意义的事在我只是应书坊之请,就自己的一些明末人的文集中选一本现今流行着的小品文出来应应市面而已。至于我为什么肯来做这个容易挨人讥讽的‘选家’,这理由很简单,‘箸书都为稻粱谋’,箸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粱谋’却是每日的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了。”,晚明小品文的出版,再加上小品文期刊的推波助澜,晚明小品作为一种传统中国文化人的精英趣味受到追捧。在当时的文化界,一时间几乎无人不谈袁中郎。小品、清言、山人、隐士等等,成为时人钦羡不已的艺术化生活方式。3陈子展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书架上不摆部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属风流;文坛上这个时髦风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头。”陈子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新语林》1934年第2期。而仔细分析这一波的晚明小品文热,表面上看其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有意识的提倡有关,但从根本上看,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不无关系。李万璋在《谈谈公安派的小品文》一文中从青年阅读的角度指出小品文流行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成功后“百花齐放”的状况因外患的加剧而受到抑制,“不幸民廿一年,九一八发生,国难临头,普罗书籍为政府查禁,左翼联盟文坛崩溃。恋爱小说为青年所卑弃,法兰西民族文学,刚萌芽幼稚时期。一时没有正确文学出现。青年们处于‘爱国不能,读书没有’的极苦闷时代”。正因如此,青年逃避现实,情感无所寄托,“于是读幽默文学后,感到刹那的轻松,瞬间的舒适,论语发行盛极一时,深为读者所欢迎”4李万璋:《谈谈公安派的小品文》,《期刊》1935年第5期。。小品文这一文体的背后深刻地关联着时代政治性。
揆诸历史,与晚明小品思潮兴起相伴随的是作为“亡国之音”的批判,背后夹杂着的则是对“明末亡国”的历史创伤记忆。从顾炎武批评李贽、公安竟陵派立异为高,徒事空文;再到四库馆臣对晚明小品的否定;及至近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对公安竟陵派的批评。1参见欧明俊《古代散文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4~148页。延续此种思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文人对晚明小品文热潮也多有批评。左翼作家认为在这内忧外患风沙扑面之际,小品文是消磨人心的“小摆设”,实在不宜提倡。而国民党文人则站在政府文化统制的立场上,出于对思想文化空间控制和重塑使之为国家政权服务的需要,对可能游离于国家政权控制之外的晚明小品以及仿写自然也不无批判和规训的意图。如王夫凡在《晚明小品杂谈》一文中,对于行销很好的晚明小品文集,肯定其清新明快的笔致以及对明前后七子的大胆反抗精神,但他话锋一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新文学建设中的一种毒素,“若任其滋生,结果将会影响到新文学的变质”。文中指出明末政治黑暗,“乱离之家迭见,文章之流于轻佻浮嚣,本无怪其然”。值得注意的是,“目今国事,正和明末相似,这种轻佻的浮嚣的文章之间重于时,也不是无因而致的。不过这种轻佻浮躁的文章,只是一种麻醉心灵的药剂,暂时可以忘怀了一切的苦闷,而创伤的溃烂毕竟还是免不了的,于国是更是无补而有害了。若说我民族还希望有救的话,这种毒质的注射,无疑的是应该加以排斥的”2王夫凡:《晚明小品杂谈》,《黄钟》1936年第8卷第1期。。而《汗血月刊》上的一篇《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文章则连带着批评士大夫空谈误国。其中说:“明代士大夫因为陷于卑下无耻,所以便致附和宦官乱政,因为流于虚矫偏激,便造成剧烈的党争,贻误抗清之大计,结果明朝社稷,便告颠覆;民族史上又添上沉痛之一页。”3本俊:《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汗血月刊》1933年第2卷第3期。将明亡的责任归罪于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以古喻今,指责时人对政府的批评,将争取言论自由、反抗文化统治的言行视作涣散民族意识进而导致“亡国”的自私行径。可谓混淆视线,颠倒黑白。
二 周作人的“异端”和“乱世”晚明
纵观1930年代国内的文坛,一端是国民党实施一党专制,加强思想控制,倡导“民族主义文学”,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外患”。另一端,随着后期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特别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他们站在“大众化”的立场上,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鼓动革命。在外一侧,则是外患加剧。对于现实的种种,周作人感知到的分明是“历史的循环”。在随感录《历史》中,他感慨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从历史中,他看到了“还魂夺舍”的事,“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1周作人:《历史》,《周作人散文全集·5(1927—1931)》,第371页。。认为对时局不能持乐观的态度,透露了他的历史忧惧——“故鬼重来”。1935年发表《命运》一文中,相比国民党提倡的读经运动,周作人不无讽刺地再次感慨读史的必要,“经至多不过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够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我自己读过一部《纲鉴易知录》,觉得得益匪浅,此外还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汇编》,这些也是必读之书,近时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盖因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2周作人:《关于命运》,《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1936年9月16日给林语堂的信中,对林语堂称赞他的散文与明末小品文风格相似,“知兄嘉奖拙文拙字,谓皆似明末”表示“惭愧”的同时,更表示害怕,“但又怕,怕的是时世又似明末,则大糟而特糟耳。虏患流寇,八股太监,原都齐备,载道派的新人物则正是东林,我们小百姓不能走投其中某一路者活该倒楣”。3周作人:《致林语堂》,《周作人散文全集·7(1936—1937)》,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正是在此“我生之后,逢此百罹”41932年3月20日的《莫须有先生传》序言中,周作人引用《诗经》中“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21页。,乱世之秋,周作人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溯至晚明小品文,关注“异端”和“乱世”晚明,其实背后自有一番用心。
晚明小品这一特殊文体形态的背后是一个乱世时空。乱世之中,知识分子何为?文学何谓?1930年代的周作人面对的是一个趋向专制的“政治世界”,所以,周氏关注“草木虫鱼”,强调“生活的艺术”,进而将目光回溯到晚明公安派小品,此一用心的背后,与其说是周氏喜欢晚明小品,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世变中文学”。他从公安竟陵派与时代的关系中仿佛寓言式地看到了自己与大时代的关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这个寓言中,个人形象通过大一统的裂隙变得具体可感了。因此,周作人和晚明、前清作家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说相似性,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批评的;与其说他们在文体上的变革相同,不如说他们都如出一辙地、以含蓄消极的方式,处理总体的社会、文化处境”1张旭东:《散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创造——论周作人30年代小品文写作的审美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在他寻找个体性的过程中,他对于时代与文人角色及文艺的作用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周氏强调“文学无用”,欣赏公安、竟陵派,是因为他们敢于超克唐宋八大家的经典权威,此一表彰的背后,攻击的目标则始终是“载道文学”。而周氏之所以不断攻击载道文学,当然不无现实意图,主要攻击左翼文学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2参见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因为在周氏的理论框架中,左翼的普罗文学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都是载道的“汉唐经典”。
正是出于对“正统派”禁锢思想的拒斥,周作人关注明末清初的那些人物,发掘了一条近代思想史上“异端”的思想谱系。明朝的末期,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大规模变动的背景下,随着“阳明心学”的传播,儒学内部产生了抨击程朱正统的逆传统思想,激发了儒学秩序的一次危机。在周作人看来,明末的公安与竟陵两派标志着与复古主义者的事实决裂以及近代文的真正开端。他将明末描述为“一种思想文章的解放时代”3周作人:《读〈晚明小品选注〉》,《周作人散文全集·7(1936—1937)》,第651页。,而从“阳明学”遗绪中脱身出来的李贽俨然成为这个时代思想造就的人物。
首先,对于李贽的思想,周作人可谓心有戚戚。周氏晚年的回忆中曾指出,“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的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4周作人1949年7月4日呈周恩来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在《妇人之笑》中,周作人转引容肇祖的近著《李卓吾评传》中的观点,赞扬李卓吾在男女问题上的思想通达。批评顾亭林在《日知录》中对李贽的苛评,认为顾亭林有学问但思想陈旧,为“正统派思想”所囿,表示自己“非不喜《日知录》者,而读之每每作恶中辍,即因有此种恶浊空气混杂其中故也”5周作人:《妇人之笑》,《周作人散文全集·7(1936—1937)》,第410页。。
其次,周作人对明末焦竑的“生生主义”也相当感兴趣。他经常引用焦竑对饮食男女之欲的观点:“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认为“此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1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周作人散文全集·8(1938—1943)》,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页。可以说,周氏从李贽和焦竑等明末儒学内部的逆传统思想中吸收养分,在思想上表彰日常生活的人情物理和通达。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批评“正统”派思想,“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2周作人:《〈永日集〉序》,《周作人散文全集·5(1927—1931)》,第568页。。
此外,在《文饭小品》中,周作人则称赞王思任的诙谐,强调其“谑”的背后,是对“载道派”的批判。认为王谑庵代表了明末新文学的一路,其思想集中展现在《怕考判》和《致马士英书》中,表彰他“与此载道家者流总是无缘也”3周作人:《文饭小品》,《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367页。。在《关于王谑庵》一文中,他表彰谑庵能“以臣而非君”,在古礼法上或不可恕,但很有见地,“我只觉得论明之亡而追咎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实是极正当的”4周作人:《关于王谑庵》,《周作人散文全集·7(1936—1937)》,第126页。。认为王谐庵敢于背负道德骂名指出明末腐败亡国事实,其勇气实在值得钦佩。在《关于傅青主》一文中,周作人称赞傅青主作为明朝遗老与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王山史野等品学兼优之人的不同。认为他思想上不是正统派,能“出程朱陆王的范围”5周作人:《关于傅青主》,《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870页。。在《老年》一文中则称赞青主兼通儒释、又自治庄列的思想通达,“所以他的意见很是通达。毫无道学家方巾气”6周作人:《老年》,《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879页。。周作人一再地发掘和表彰带有“异端”的文人言行,其目的显然是要反抗“正统思想”束缚人性,希冀重建活泼自由的主体。
而结合1930年代的现实处境,内忧外患使得周作人高度消极和悲观。1933年2月24日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周氏说及世事之恶与自己犹如游魂的心情:“寄寓燕山,大有釜底游魂之慨,但天下何处非釜乎,即镇江亦不易居也。……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7周作人:《与俞平伯书五通》,《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140~141页。文中“幽燕之地”当指北平,而“华夷之界”则喻指中日之间,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中日必有一战,“北平”必定“沦陷”的预感以及悲观压抑的心境。正是现实的危机和晚明相类似之感,使得周作人高度关注历史上的离乱经验,恰如他若干年后说的:“鄙人昔时曾恨不得遇身历乱离之人,听他讲讲过去的事。”1周作人:《北风集》,《周作人散文全集·8(1938—1943)》,第163页。这一点也从侧面反映出他试图以历史经验来因应现实的用心。而检视这一时期,周氏不断从明末清初的笔记中寻找读书人在乱离之世的处事经验,如此“读史”方法,也使一个乱离的“晚明”得以呈现。
在陶崇道著的《拜环堂文集》残本中,周作人特别择出明末官兵和虏的状况。他发现明末的官兵是将不知兵,号令不行,军备不足,守城“全恃火器,而能火器者百不得一”。士兵虽从四面集合,但“为鼠者多,为虎者少”。即便面对志在抢掠即逃遁的“虏骑”,明朝的兵也不敢追击,每使清兵“饱载而归”。士兵之外,高居庙堂的官员则是面对外敌入侵不能“尽力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牅尽为摧毁”。然后,只剩下“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2周作人:《明末的兵与虏》,《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778~780页。的窘态,不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关注明末外患之外,还特别关注农民的内乱。在读“年五十三岁,在南守制,值国大变,(缺四字)弃家而隐”的王湘客所著的《王湘客书牍》中,他看到的是“寇与虏的发展差不多全由于官与兵的腐败”。高居庙堂者奢侈腐化,“大老以仕肥家,田庐遂连滇黔两省矣”。导致民不聊生,“乱之本因民穷,民穷始盗起,盗起始用兵,用兵始赋重,赋重民益穷,民益穷盗益起,由今之道非策也”3周作人:《王湘客书牍》,《周作人散文全集·7(1936—1937)》,第149~150页。。在读《甲行日注》时,周作人特别关注《甲行日注》其中对当时乱离情状的记载。从“苏州不战而降,没有多大杀戮”的记载中,他看到的是“民族的老病来”4周作人:《甲行曰注》,《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299页。。除此之外,周氏对明末的结社士风也不无批评。指出东林党争的私心,只顾“门户门面”,而罔顾国家安危。转引明遗民张岱的看法:“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东林党的“兴衰”与国家密切相关,当其“党盛”时则成为党人的“终南捷径”,当其“党败”时则“为元祐之党碑”5周作人:《关于命运》,《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第562页。,肯定张岱的看法,认为正是东林党意气用事地排除异己,加速了明亡。
三 “暴虐”与“反抗”的晚明
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专制的恶化和日本侵略者侵略步伐的加快,两者互为表里,明末的乱世之感笼罩在知识分子心头。对此,鲁迅在1933年《致曹聚仁》的信中曾言道:“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然而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贤入孔庙,被以衮冕,现在却还不至此,……渔仲亭林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此时代不同,环境所致,亦无可奈何。”1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而其时虽然国民党着力强化党治文学,独尊“民族主义”文学2对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具体参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9 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进行文化统制,但文艺思想领域呈现出活跃的状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想相对立的局面,两大思潮之间论争频繁。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强调文章的“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在批判追求“闲适”“趣味”的晚明小品文的同时,强调晚明小品文写作者的批判和反抗的另一面相,同时发掘明末史事,也为阅读者呈现出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晚明”,从而消解了“风雅”晚明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腐败的晚明历史中,看到了底层民众的强大力量。
相较一般左翼作家批判晚明小品的“闲适”“性灵”,阿英则努力发现晚明小品文本身在“闲适”“性灵”之外的反抗和批判面相。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他指出袁中郎并非一味地隐逸。文中,阿英充分肯定袁宏道对“时事”的关注。他描绘出了一个“性灵”之外同恶劣的政治势力作战的袁中郎,指出了袁中郎在文学上的创造精神。认为:“中郎是可学的,在政治上,应该学他大无畏的反抗黑暗、反抗暴力、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在文学上,应该学他反对因袭、反对模拟、主张创造的力量,以及基于这力量而产生的新的文体。”3阿英:《重印〈袁中郎全集〉序》,《阿英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在《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中,阿英指出明末“道学派”和“清谈派”互相推诿“误国责任”。他认为两者皆有责任,“‘清谈派’固有责任可负,‘道学’亦不能卸却干系”1阿英:《明末的反山人文学》,《阿英全集》第4卷,第123页。。而衡诸其时,阿英的论文显然有所针对,一方面强调袁中郎反抗性的一面,消解林语堂、周作人对公安派性灵闲适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则指向国民党的文化统治。
与周、林提倡闲适公安派小品文不同,陈子展则将目光转移到讲气节和“发愤为文”的明遗民身上。他在《遗民的悲愤》一文中,展示遗民杜于皇的气节和坚守。杜于皇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但是即便再穷,也不会“奴颜婢膝,笑嘻嘻的投降满清政府”2陈子展:《遗民的悲愤》,《越风》1936年第7期。。在文中,陈子展指出杜于皇文章中透着对敌人的“嗔气”也即生气,肯定其是“带性负气之士”。在表彰杜于皇的气节同时,陈氏更指出杜于皇老实人的一面,肯承认自己是“扰弱凡材”,敢于承认自己不能抗敌救亡的弱点。其目的则是讽刺国民党妥协派面对日寇的侵略编造各种理论来掩饰自己的不抵抗。与强调“闲适”“性灵”的公安竟陵派相比,陈子展在遗民杜于皇身上看到了一个讲气节、强调诗文“发愤”作用的晚明。
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热潮,相比一部分左翼文人的断然否定,鲁迅的态度则更为理性。正如郝庆军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鲁迅最为关注的是“丰富多彩的晚明文学被哪些隐秘的文化机制刀劈斧削,最后怎样只剩下了‘性灵’?”3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对此,他深入历史典籍,对“晚明”思想、文学作重新考察,进而揭示出“风雅”晚明所遮蔽的另一个面相。
一方面,鲁迅和阿英一样,指出流行的小品文选本对袁中郎的“肢解”,肯定明末小品文的政治性:“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不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91~592页。另一方面,鲁迅对“晚明”思想、文学再做考辨,以“禠其华衮,示人本相”5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4页。。他在清代以来至1930年代流行的“晚明”叙述里,发现了两大遮蔽:一是对历史血腥的遮蔽。在《蜀碧》一书中,鲁迅发掘出来的是晚明的残暴。他在卷三中发现“流寇”张献忠所实行的剥皮刑法之残忍,“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0、172、177页。。与“流寇”剥皮相同的是,鲁迅从被禁的野史《安龙逸史》里看到另一段剥皮记载:永历朝的秦王孙可望,可谓“复明”大业的“擎天一柱”,如此“光明正面”之人物,却将弹劾他的御史“剥皮示众”,进而联想到明初永乐皇帝也曾剥御史大夫的皮,由此发现“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但这确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要竭力回避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2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0、172、177页。,这种“流寇”“大将”“皇帝”皆有的“残酷性”可谓表征了“国民性”黑暗。与此同时,鲁迅也把矛头指向“歌颂升平”“粉饰黑暗”的国民党文人,指出“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在“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无视“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反而单捧“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结果则是刻了诗集,但国也亡了,把自己也写进了亡国史中,而“韵事也就完结了”。3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0、172、177页。他还以自己阅读屈大均的《翁山文外》为例,在戊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中,他看到的不是“风雅”的晚明,而是“异族”统治下的民众的残酷生活。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他认为相比明人小品,《明季稗史》之类明末遗民的作品更有必要标点、翻印,给大家以刺激和警醒,“给大家来清醒一下”4鲁迅:《读书忌》,《鲁迅全集》第5卷,第618~619页。。
第二个被遮蔽的是历史上的血性人物和反抗精神。鲁迅举出的例子是明末的东林党人周顺昌被陷害入狱,激起数万苏州民众的公愤,上街声援。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却“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5鲁迅:《“题未定”草(九)》,《鲁迅全集》第6卷,第449页。这样存在于普通百姓中的反抗传统,从来都未进入过主流的历史叙述。
除了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的晚明小品文的批评,鲁迅亦通过晚明历史的观察,将冷嘲的笔调融化于晚明的言说中,展开对时局的批判。在《算账》一文中,鲁迅批判学者对清代学术的吹捧,认为清代学术“几页光荣”的背后则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1鲁迅:《算账》,《鲁迅全集》第5卷,第542页。,在对比中批评学者不知亡国痛。在《半夏小集》一文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告诉大家“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并不是要验证,“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人的奴隶好”。文中以“明亡”之后的士人表现:或当汉奸,或做“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痛骂汉奸”的逸民,或做抵抗的烈士。认为三者之中,汉奸可耻,逸民可敬,但更重要的是“默默抵抗”的烈士。文中对于“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2鲁迅:《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617、618页。的逸民不无批判。在《“立此存照”(四)》中以逻辑推论的方式指出《越风》中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有可能引发的“恶影响”。文章指出,高越天以批判明末汉奸下场悲惨来警示国人不做汉奸,“万一汉奸下场并不凄惨”则有可能导致价值观的混乱。他强调,卫国是“异族”入侵时的必然责任,不能“做值不值得”的考量。3鲁迅:《“立此存照”(四)》,《鲁迅全集》第6卷,第650~651页。除了对时人种种言行讽喻之外,鲁迅更是借用“晚明史事”批判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文章与题目》中,通过“晚明”的史事讽刺国民党的“安内与攘外”。文章指出对于“内忧外患”之际的中国,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而此种花样,征之于晚明史事,并非新鲜,“只要看看明朝就够了。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做了第一种。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于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卷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氏之先,原是轩辕黄帝第几子之苗裔,……咱们原是一家子云”4鲁迅:《文章与题目》,《鲁迅全集》第5卷,第128~129页。。文章以古讽今,字里行间,充分展现了忧患和批判意识。
四 经世致用和强调气节的“晚明”
1937年,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从晚明开始讲起。钱穆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不免有所怀抱,虽然“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但“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问也”,也不无自己心法:“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1页。所以,钱穆在此书中述及晚明,点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和吕晚村等人的学术思想,特别着意发扬其中的经世思想和忠义气节。
在书中,钱穆认为近代学者由于受“科学”和“民主”的时代风气影响,对宋学不无偏见。但在他看来,宋学和汉学并非泾渭分明,要将两者辩证联系起来看,否则难以了解汉学的精要,更不能“平汉宋之是非”。所以,书中开篇,他先是“略述两宋学术概要”。指出,宋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1页。。而宋学的这一精神为明末的东林党所继承,此一风气之下,“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强调“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于乾嘉治学,精气夐绝焉”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1页。。他彰扬宋明学者“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志向,对东林党更表认同。表彰东林党在国家危亡之际,用自己的“血肉撑拒”,可谓擎天一柱。认为他们敢于讲真话,关心国计民生,甚至不惜得罪皇帝。称赞他们“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0页。。面对朝纲既颓、阉贼日炽的时局,东林党人出持清议,可谓“忧时之士”的自然选择。对于东林党人的非议,他认为是“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十分可悲。在他看来,东林党一明是非立纲纪;二斥乡愿进狂狷,“东林诸贤皆深斥乡愿而进狂狷,即辨心术以明是非之本也”;三提倡节义,“故东林精神,即在分黑白,明是非,肯做忤时抗俗事。不畏祸,不怕损名,不肯混同一色,不愿为乡愿”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8、20、77、84、85页。,可以说十分可贵。而清初遗老深受东林党的影响,薪火得以赓续。文中指出,东林党人在“易代”之前,通过“裁量人物、訾议时政”来影响时局,等到“鼎革”之后,面对无可挽救的局面,他们转向于探求“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希冀能从中寻求历史经验以作为鉴。而导源于东林的顾亭林、梨洲等人一方面继承了其“留心实录,熟悉掌故”以省思历史的担当,但另一方面也超越了东林,“发为政论,高瞻远瞩”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8、20、77、84、85页。。对东林学派的政治改革思想的肯定,暗示着抗战时期读书人“对自己应将扮演的政治角色的重新确认”3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在论述吕晚村时,钱穆择发其学术思想之外,更是高度评价他的夷夏之防的志向。在介绍吕氏的行状时,指出“戊午,清廷举鸿博,浙省以先生荐,誓死拒之,得免”。后来又被郡守推举为“隐逸”,被逼无奈,“先生乃翦发为僧”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8、20、77、84、85页。。肯定他“不事二朝”的坚贞,最终在贫困中死去,强调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文中点评吕晚村的学术思想,通过比较其与陆稼书在阐释“朱学”上的贡献来突出吕氏的高洁。与康熙、雍正时陆稼书等清儒“仰窥朝廷意旨”,为了升官富贵,不惜“尊朱辟王”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晚村对朱学的倡导和阐发,目的在于发挥民族精神,激励民众“不屈膝仕外姓”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8、20、77、84、85页。。文中还比较吕晚村坚持气节的不“应试”而陆稼书则出仕清廷的不同选择。而正是因为坚持夷夏之辨,陆稼书死后,受到清廷的褒崇,还被列入孔庙祭祀。相比之下,晚村则遭遇“阖门骈诛,戮及尸骨”。他的学术著作也遭到禁毁,思想湮没人间。事实上,陆稼书关于“尊朱抑王”的思想“多袭晚村”。区别只是在于,吕氏的宗旨在于“戒人为许衡、吴澄”,而陆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8、20、77、84、85页。
钱穆还特别强调吕留良深斥功利之微旨。在钱穆看来,若是“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动以豪杰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顾小节’”,其结果则是风气大变,道德沦丧。钱穆特别指出,“晚村所谓‘作用’‘本体’,即近人所谓手段与目的也。引得一辈苟且无忌惮之徒,妄作妄取,辄以英雄自命。曰‘成大业者不顾小节’。外间靡所不为,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虽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总归于小人。即谚所称‘光棍’耳”。他认为:“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耳,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盖晚村之意,亦曰宋学主义理斥功利。惟此一端足以警惕人心,复明夷夏之大防,以脱斯民于狐貉耳。”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94~96、147、158、161、180~181、182页。钱穆强调气节,着意拈出吕晚村反对“作大事不拘小节”的“权变”,恰是强调在“国家危亡之际”的忠义的必要。
在行述顾亭林的学术思想时,钱穆特别强调明道救世是他的学问纲要,引其自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94~96、147、158、161、180~181、182页。。指出其学术有益于世的志向。他指出,顾亭林的《日知录》,最所用意的是论风俗的第十三卷。因为后世人只关心顾亭林的博学一面,既然他的“行己有耻”已被选择性遗忘,那么他关于国家治乱的“拨乱涤污,博考治道”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94~96、147、158、161、180~181、182页。就更是被后世诸儒抛诸脑后了。对此,钱穆说,这种学习顾炎武的学法,实在不得顾亭林的“讲治道救世为主”的本意,学习“‘博文’之训”可谓买椟还珠,“已为得半而失半”。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94~96、147、158、161、180~181、182页。
在评点颜习斋的学术思想时,钱穆肯定颜习斋对儒学之无用的质疑。钱氏指出:颜习斋认为儒学之无用,其为害最大者,“在静坐,在读书”。其之所以不喜多读书者,因其“不惟谓其无益于事功,抑且无益于知识”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94~96、147、158、161、180~181、182页。。强调要以“事功为主,知识之无益于事功者,不足为知识”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94~96、147、158、161、180~181、182页。。钱穆盛赞其能打破宋、元、明言心性义理的禁锢,将心性功利与实行融合起来。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学案的形式评述近三百年的学术,强调宋学的议政和理学风气,表彰明末东林党人的讲学清议,以及易代遗民之气节和经世致用的痛定思痛,可谓描绘和肯定了晚明讲求“经世致用和道德气节”的又一面相。
结 语
“晚明”作为中国历史中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因其内蕴着以夷变夏、儒学曲变、商业萌芽、农军革命等复杂形象与意涵而始终保持着与时代碰撞、对话的能量。是以,从清王朝建立开始,便不断地被不同知识群体重述和利用:明遗民的梦忆前朝和守正待后;西力(学)东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晚清人痛思国家大厦将倾,往往回顾晚明的骇人乱象”1胡晓真:《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导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2001 年版,第 1 页。;辛亥期间,革命党人则刊布翻印记录南明史事著作以号召排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作为文艺复兴的晚明2关于晚明与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关联的研究参见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刘春勇《从长时段视角重审五四与晚明之关联——兼论“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上、下)(《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2、3期)。……而在1930年代这个日益政治化和亡国阴影密布的时空中,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在危机时刻再次展开对“晚明”的想象与言说,发掘出不同的“晚明”面相,众声喧哗中形成别样的对话和角力。林语堂倾心“公安三袁”的小品文背后固然与商业因素和其来自西方表现主义的文学理念相关,但其大力表彰和书写实践,聚焦“晚明”小品文的“性灵”和“闲适”所展现出的“风雅晚明”这一面相,以及在当时引发的小品文热,其背后则是对险恶时事的一种反应。两者构成辩证关系,一方面,内忧外患的现状刺激了部分知识分子希冀从现实政治脱离出来,在乱世中寻找一方闲适空间;另一方面,此种“闲适”的文学观和心理也在无形中对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起到了消解的作用。而对比林语堂,周作人固然不无类似的“生活艺术化”的趣味及隐逸的冀望,但对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创作者主体性的自由。他在“晚明”这一末世废墟中发掘出清新性灵的晚明小品文,进而将现代散文的源头追溯“晚明”,排斥“载道”文学,试图从历史角度确立文学的方向。而阅读“晚明”史籍,勾勒乱世历史图景,周氏如此用心的背后则是在现实中看到的“恶历史”的“故鬼重来”。与之相反,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国民党文化宣传阵营则将晚明小品文视作“亡国之音”来转移舆论视线,着重压制文学和知识分子表达“异见”的空间和可能性,规训、重塑文坛秩序以应对日渐恶化的外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一方面不满于晚明小品文的消磨人心,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文化专制,内忧外患中则格外强调“晚明”的历史创伤和反抗性记忆,揭橥“性灵”“闲适”这一“风雅晚明”背后隐秘的权力机制,重新发掘被遮蔽了的晚明暴虐历史以及富有反抗性的民众力量,这背后亦是在危机时刻对文学、知识分子责任和底层民众力量的再次体认。而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着力表彰“晚明”东林党人的经世志向和气节,不无重新检讨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伦理抉择和使命的意图。由此可见,不同的“晚明”想象和言说中是知识分子对历史文化记忆的重构、挪用和交锋,这背后固然渗透着文学理念的交锋、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亡国危机下文学和文人“何为”以及“如何为”的问题,寄寓了知识分子深刻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