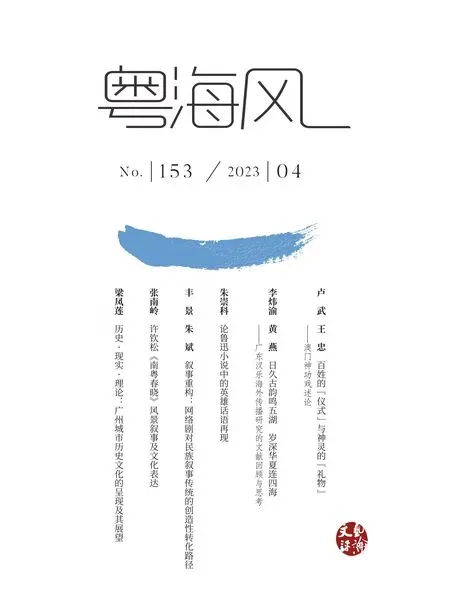叙事重构:网络剧对民族叙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文/丰景 朱斌
从表面来看,神话、传奇、志怪、话本、章回小说、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叙事资源,为网络剧提供了建构基底;而在中国文化中长久居于边缘的叙事资源,也与“作意好奇”的网络剧叙事特征达成一致。从深层来看,不论是美学维度还是结构维度,网络剧在传统的散点叙事、意象叙事等方面均存在极大的尝试空间。随着大众从“大屏”到“小屏”观看习惯的变化,曾经被冠以粗制滥造、低俗无趣的网络剧也将迎来内容生产趋于理性、优质的发展新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在回归民族叙事传统的过程中,网络剧有可能在艺术与机械复制时代,重新回到“中国故事”的活泼传统,找到另一种更广阔、开放的叙事方式。
进入现代以来,对进化论链条上先进性(西方)文艺新秩序的渴求,构成了中国文艺整体的现代性焦虑。寻根思潮伴随现代性反思一同诞生,并在植根于互联网的网络剧中得到新生。当互联网扁平化的信息传递与观看方式成为主流,更广泛的大众/民众位置与活泼泼的世俗世界浮出历史地表,并借由网络剧释放出传统叙事“以文化人”的当代意义。近年来,精品化网络剧向传统叙事靠拢趋势渐明。2022年出品的两部网络剧——《唐朝诡事录》与《梦华录》直接从唐传奇与元杂剧汲取“本事”讲述资源,便是道听途说、口口相传的前现代故事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再度演绎。而此前仙侠类型网络剧频频从《山海经》等神话资源中再造架空世界,形成了统一美学风格的“造世”叙事。
在网络剧日益普及的当下,重新回到民族叙事传统,有利于在更广泛的受众中形成潜移默化的民族共同体,以抵抗影视领域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叙事学的探求,其实早在明清小说与戏剧评点中即可见端倪。杨义与浦安迪的两本著作均以“中国叙事学”为题展开了理论建构与钩稽工作。在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如何以回归民族文化的姿态,创造出差异化的叙事理论成为关键。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叙事学应当尽量在西方话语之外,开拓出中国文化独有的生命意识,在单薄的、固定的名词之外,挖掘出叙事的动词性,也即叙事结构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结构‘哲学’”[1]。随着故事讲述与传播的媒介的演变,中国叙事学也理应从文本分析的框架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受众更广泛、更具动词性特征的网络剧讨论中。网络剧与传统民族叙事的隐秘连接可以概括为:叙事资源的借鉴、叙事结构的联结、文化意象的显现、叙事的散点化特征等。在后现代主义朝碎片化、狂欢化一路狂奔的当下,从传统中汲取资源进行自我调整与修正,已成为网络剧从边缘走入主流视野的重要路径。
一、承续与再造:网络剧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借鉴类型
传统叙事资源融贯于网络剧,可以产生跨越时间与媒介的再创作意义。一般认为,传统叙事资源既包括笔记、传奇、小说与史传资源,也包括活泼而驳杂的民间叙事资源。网络剧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承续与再造,可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志怪、传奇与话本叙事传统,民间神话、传说叙事传统,史传叙事传统。
(一)志怪、传奇与话本叙事传统
网络剧对文学叙事资源的借鉴,主要集中在志怪、传奇、话本等小传统(如表1所示)。志怪传奇叙事传统的奇异性、寄托性与虚拟性在网络剧中得以复活,形成了更符合国人审美潜意识的观赏场域。由于志怪与传奇带有非常态化的传奇性特征,主人公可以在“传奇时间”内获得时间与情节展开的自由性,这为网络剧叙事提供了在全新时空体内活动的想象空间;而志怪传奇专写“人间言动”的志人一脉,则为网络剧提供了人物叙事借鉴。此外,网络剧还在电视剧“拟书场叙事”的基础上,承袭了话本“入话”技巧,将故事、诗词韵文作为“叙事元始”,交代后续故事主题或背景。譬如,《河神》在剧情展开前,都有一段近似说书人开场的叙述,对整集进行提挈,吸引观众好奇;在《九州·海上牧云记》开头同样出现了类似说话人的“算命人”角色,完成了垫场的叙事作用。

表1 网络剧对志怪、传奇与话本资源的借鉴
(二)民间神话、传说叙事传统
中国具有深厚的民间叙事传统,民间叙事主要通过口头形式进行传播,且存在众多异文形式。原始民族将宗教与民间流行的神话进行结合,发挥了本民族心理传承的整合功能[2]。时至今日,网络剧鲜活的大众文化属性,使民间叙事资源找到了另一种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承方式。民间叙事中,传统故事经由多人层层打磨,在民间集体中得以流传,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传说、歌谣叙事模式。而网络剧则具有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多重特征,并在互动剧、弹幕等后现代文化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创作。
直接取材于中国民间神话与故事的网络剧,其创作转化路径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神话、民间传说、叙事歌谣等传统民间叙事形式进入网络剧,成为叙事本源设定或推动叙事的因素。例如:《昆仑神宫》中出现的西藏天授唱诗人阿克与千万字的格萨尔传奇故事,便承载了藏族地区承续千年的集体民族记忆,在潜移默化的叙事中将传奇故事、史诗与藏族民族记忆进行了钩连;《九州·海上牧云记》沿袭了邹衍的怪迂“大九州说”,目前该说法在《史记》《盐铁论》《论衡》中均有留存[3],代表了中国独有的神话宇宙观。二是新的民间叙事形式,如都市传说、奇闻逸事在古装网络剧中实现再创作。例如《河神》延续了河伯族的历史渊源、黄帝以来的河神崇拜传统以及自《博物志·异闻》与《龙鱼河图》而来的河伯故事传统[4],并将故事背景放在民国时期的天津卫,显示出现代都市传奇的叙事意味。
(三)史传叙事传统
《春秋》《史记》等史传叙事传统对电视剧的影响,具体可分为纪传体与编年体两种叙事体式[5]。此前受限于碎片化媒介特性与发展阶段,网络剧大多无法支撑起跨度较大的纪传体叙事,目前尚未有优质的正史、革命历史题材产生,而往往以宫斗、权谋代之。这与网络剧的文化产品属性相关:“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6],观众热衷于在充满矛盾感的叙事中获取娱乐快感,这一矛盾来自史传体叙述与对叙述严肃性消解的冲突,也来自真实的器物、仪礼建构起来的看似贴合历史的影像空间,与虚构演绎的娱乐化现代故事内核之间的冲突。但是随着网络剧精品化的发展,以时代切片展现社会史的类史传网络剧逐渐出现,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以见证乡村振兴的现实叙述,对乡村真实生活与问题的还原甚至颇有些史传传统实录精神的意味。
二、融合与重构:网络剧对叙事传统的影像化传播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网络剧与传统文化同为现代文化的相对面,两者均没有紧张的聚焦点,且存在象征/意象、去中心/散点、含混性/留白等一一对应关系,以上特点均与崇尚理性与主体性的现代主义相背离。体现到叙事层面,网络剧对传统叙事的融合与重构,则具体化为“作意好奇”“散点透视”与“以象表意”三个层面。
(一)“作意好奇”的叙事目的
胡应麟曾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唐传奇归结为“作意好奇”“尽幻设语”,是充满虚构感、光怪陆离的想象世界。古代传奇、话本与章回小说,均带有“作意好奇”色彩,其贴合民间娱乐需求,充满了活泼泼的世俗生活气息。鲁迅曾在《京本通俗小说》中,将宋元话本称之为“主在娱心”,道理亦然。网络剧承袭了这一娱乐性叙事目的,替代话本、通俗小说成为大众新的娱乐方式。与其用后现代文化的平面化与复制性解释网络剧的娱乐特点,不如将其纳入到中国“作意好奇”的大众娱乐叙事传统,重新挖掘根植于集体无意识娱乐与审美心理的叙事特点。优质网络剧叙事整合路径,在于打造融合“娱心”与美学兼具的“传奇故事”类型。“传奇”并不局限于唐传奇这一特定文体,而是延展为广义的文艺通俗类型,“唐人传奇文,宋诸宫调,元杂剧,明清长篇戏曲和西欧的‘罗曼斯’作品,都曾冠以此名”[7],至现代则变为一种情节离奇、节奏明快、人物行为超常的传说故事[8]。网络剧承接了传奇的通俗性、娱乐性、大众性特征,衍生出两条“作意好奇”的叙事路径。
一方面,以戏剧性与日常性叙事,再造古今市民传奇。传奇故事脱胎于市民传统与大众趣味,使传统文化与美学在故事中得以延宕与传播。日常性与通俗性均属大众文化的特征,且对生活艺术的回归,对家常琐事的叙述,更符合网络剧内向性、个人化的媒介体验。例如,《梦华录》脱胎于宋话本,对宋代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民俗着墨颇多,如茶百戏、点茶与斗茶,同时又在“救风尘”之外延展出多重戏剧性,使故事不至于沉闷。另一方面,承袭志怪与传奇传统,通过灵物/神仙/梦/变形的组合再现中国式魔幻现实。此类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热潮中曾风靡一时,乡土民间文化、习俗与神秘文化进入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视野,更出现了模仿传统志怪笔记的新笔记小说。因此,网络剧中的志怪与传奇因素不应因其猎奇心理全盘否定,问题在于如何在猎奇与美学、寻根与创新中达成平衡,在活泼泼的“娱心”叙事中注入新的表现内容。例如,《唐朝诡事录》通过虎、妖猫、巨蟒、鳄鱼等异兽与幻术的出现,将传统志怪与传奇因素重新复活。《龙岭迷窟》《云南虫谷》《昆仑神宫》等鬼吹灯系列网络剧,则将雮尘珠等民间传说与冒险题材相结合,为网络剧类型片的形成提供了有益探索。
(二)“散点透视”的叙事结构
散点叙事本是绘画空间领域的研究名词,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绘画多为写意,并不拘泥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在大跨度范围内自由组合;而西方传统绘画偏向于理性写实,有严格的构图与透视限制,聚焦性于外在性更为明显,而忽略了向“内”的审美体验。散点叙事方式经常与古典园林审美相联系,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了《儒林外史》的联缀式结构:前一个故事的要角将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个故事要角,单元式故事承载着统一主题,最终展现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众生相。“这种结构类似中国画长卷和中国园林,每个局部都有它的相对独立性,都是一个完整的自洽自足的生命单位,但局部之间又紧密勾连,过渡略无人工痕迹,使你在不知不觉中转换空间。”[9]
近年来,已有研究者运用散点叙事对电影进行研究[10],然而其分析依旧停留在不同叙事单元的连缀、非线性叙事层面,依旧未曾触及散点叙事的中心问题。散点叙事的关键,在于其与传统美学的潜在关联——只需拎起几个散点神韵,在自然的“游观”中即可展现整体的复杂性。网络剧可以在主题性焦点叙事之外,延展出美学、留白、意境等离散型叙事,在器物、仪礼民俗、生活方式的展开过程中,通过移步换景的自由转换,建构起宛如“平铺手卷”般的叙事结构。从《梦华录》中可窥见其与《东京梦华录》的隐秘关联:两者均不以文饰地表现市民生活,显现出宋代市井风貌与生活美学,从而带上了某种笔记体的离散特征,远离了唯一的叙事中心。此外,以单元故事结构为整体的《唐朝诡事录》《民间怪谈录》《御赐小仵作》《重生之门》《三悦有了新工作》等跨越不同时间、题材的网络剧,均属于连缀式结构叙事,单元故事在移步换景中组合成有机整体。《花间提壶方大厨》《卿卿日常》《珍馐记》等网络甜宠剧则不乏烟火日常,往往在叙事主题外旁逸斜出,用日常美食、喜剧因素消解了主题性叙事的焦虑。
(三)“以象表意”的叙事技巧
意象是中国独有的叙事技巧,在互动性较强的网络媒介环境中,意象的传递与破译在受众中形成了浓度更高的参与空间。“意象作为叙事作品中闪光的质点,使之在文章机制中发挥着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功能”[11],其可以穿越线性时间的叙事链条,实现意绪的、精神的意义传递。在意象的形成与破译之间,叙事的中介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即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审美意义。此前,曾有研究者对网络剧的自然意象、身体意象展开研究,却忽略了意象与传统之关联。先将网络剧的意象类型整合为以下几类:
1. 物件型意象。如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珍珠衫”和《西厢记》中的汗衫、玉簪等物品一样,“物”的意象承载了多重意义。《别云间》的“鹤簪”既是定情信物,也是最后太子萧定权自戕的利刃,为整体叙事增加了另一层悲剧性。《宸汐缘》中的“长生结”在男女主角之间的多次流转,将反复零散的叙事串联起来,形成了具有天命意味的循环叙事。
2. 文化型意象,如典故、诗词与戏曲。网络剧《长歌行》《如梦令》的名字均为词牌名,《一片冰心在玉壶》出自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皎若云间月》出自卓文君的《白头吟》,《今夕何夕》出自《诗经·唐风·绸缪》,《鹤唳华亭》出自《世说新语·尤悔》。作为意象的剧名同构文化意义的暗示与联想,跨越繁琐的解释形成不言自明的意蕴之美。《别云间》是夏完淳的一首五言律诗,网络剧《别云间》与本诗中“羁旅客”“山河泪”与“泉路近”等意象形成契合,暗示了故事的悲剧内核,为网络剧赋予了“味之长而言之美”的蕴藉感。
3. 神话/民俗型意象。神话意象是凝结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的天然媒介,“通过它,不同群体可以宣布加入到一种民族性的文化之中”[12]。近年来,在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叙事之外,更具象的神话意象逐渐出现,如《司藤》中万物有灵、植物崇拜的中国式的神话想象。从神话意象资源与组合策略来看,先民关于狼图腾、熊图腾、猪龙、熊龙、神圣猫头鹰、鸟兽合体(如鹰熊、鸮熊)的想象,同样是网络剧进行世界建构的意象资源。在神话之外,民俗意象背后承载了特有的民俗文化精神,主要可以归纳为节日惯例、人生礼仪、风土名物、建筑方式和劳动器具等方面,例如《河神》中的祭祀大典,《风起洛阳》中的馎饪、水席等饮食习俗,《星汉灿烂》中的婚俗、《沉香如屑》的上元节等。
4. 环境/空间型意象。西方叙事学的空间转向,是20世纪中叶以来才发生的事情,这与西方忽视空间、看重时间的传统相关。中国叙事文化中,空间的重要性更为前置,其环境意象不仅是表层的地理空间,而且承载了不同空间构造的叙事意义。网络剧对地理空间、环境的在地性延展,近年来得到质的提升,如《卿卿日常》中具有明显地理文化特色的九川、《在希望的田野上》中代表乡村振兴的白果村田野,《八角亭谜雾》中烟雨迷蒙的江南小镇,此类网络剧中的空间已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背景,而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场。
三、网络剧弘扬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作为后现代主义产物的网络剧,向民族叙事传统的回归,并非一个充满割裂性与错位感的问题。事实上,后现代与中国传统的相对面都是聚焦主体性与主题性的现代性,正如后现代主义学者柯布(John B.Cobb,Jr.)所言,“在根蒂深处,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13]例如,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概念、理性主义的批判,对“人是世界主体”的反叛,恰恰是传统文化的特性所在;其对创作过程中“象征”审美性的要求,与得鱼忘筌的“意象”相通,两者都没有明显的聚焦点,而是将意义隐藏在语言/影像背后。概言之,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可以作为拒斥现代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精神以及主体性哲学的资源。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随处可见的碎片化、狂欢化、个人化等解构性因素,可以在与传统的弥合中避免走向极端,规避过激之谈和片面性的弊端。因此,作为后现代文化的网络剧可以从传统叙事资源中获取生命力,从而在创造性转化中实现自我修正。
一是处理好“叙事之法”与“叙事之道”的双构关系。所谓叙事之道,主要指向的是文化哲学、道德叙事层面,也即网络剧的情理结构、感时忧人、公私之辨、家国天下等传统叙事主题。网络剧由于媒介限制,不免需要“作意好奇”的叙事之法吸引观看,部分还将神鬼之说视为猎奇叙事法则,将魅惑力夸大化,掩盖了中国传统故事的本来魅力。然而,正如同演戏作为中国传统乡村公共生活的文化仪典一样[14],网络剧对公众的组织与影响,也应对集体认同与社会共同体建立产生积极作用。区别于西方主题学——如死亡、爱情等题材类型和情节模式,中国叙事主题带有自身文化谱系的留存,如孟姜女、徐文长等民间故事主题,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怀,以及在说书、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生活流日常叙事。《长安十二时辰》与《风起洛阳》的家国叙事,《鹤唳华亭》与《别云间》感时忧人叙事均属在“道”与“法”间取得较好平衡感的剧作。
二是处理好抒情传统与娱乐叙事的关系。从“逻各斯”现代性到“爱洛斯”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大众情感消费需求与情感产业逐渐兴起[15]。网络剧处于娱乐产业之中,在粉丝效应中满足了公众情感消费需求,然而迎合过度容易导致叙事意义的失焦。回归到推崇至情的抒情传统,可有效避免娱乐性对情感表达的消解。中国思想史与诗学史传统中一直存在抑情论与尚情论说法,至晚明时期,确立了主情、尚情的本体地位,文学也从化成天下的载道之用,变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至真诗文。承袭这一传统,网络剧应当重视“自然本然”的情感表达与情感需求。主情传统总与“真”“私”“人欲”等关键词相连,对应着百姓真实而直接的日常生活。在三生三世的虐恋类型、浪漫之爱的虚幻类型、逆袭神话的爽文化类型外,网络剧需要对根植于百姓日用本然情感持续挖掘,从而规避浮夸、悬浮、碎片化的情感表达,展现出真实、活泼的情感生命力。正如《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一样,网络甜宠剧基本也不脱此类“至情”表达,口碑较好的《你好,旧时光》《遇见王沥川》《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最好的我们》《你在冬夜闪耀》等网络剧,无一不是脱离了外向度的悬浮情感,回归到真实的内向性情感。近年来网络剧受众对“工业糖精”的反感,也正代表了悬浮虚伪、剧情断裂的网络剧的实效。值得一提的是,“情”属于泛情感,并不局限于爱情主题,其在悬疑剧、主旋律剧等不同类型剧中均有所展现,并成为大众文化满足大众之本然情感需求的关键。
三是处理好文化工业与大众化叙事的关系。网络剧是现实态正在进行着的大众娱乐形式,其本身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网络剧需要在尊重商业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对大众文化的工业性、猎奇性与雷同性进行矫正,通过对民族传统叙事的借鉴,使其回到大众文艺普适性与民族性的轨道。延安文艺对“通俗化、大众化”的选择确立了社戏、说书、大鼓等大众形式的正当性地位。时至今日,大众娱乐形式早已从戏曲、说书转变为网络视听艺术。对网络剧的导引意味着新的大众形式的诞生,代表了新媒介场景下拓展记忆储存空间的全新尝试。正如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好莱坞在存储记忆、回溯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对于《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等影片,“年轻人是把影片中的画面当作对历史本身的忠实模仿而加以感知的”[16],网络剧同样凭借影像形式对历史与现实故事的重新讲述,形成新的群体性的视觉符号与记忆,从而修正文化产业野蛮发展的弊端,形成具有中国故事意蕴内核与历史经验的影像叙事。
结 语
在网络剧文化中,叙事传统依旧内含着民族集体无意识,而对这一传统的借鉴也将成为网络剧对自身碎片化叙事、狂欢化娱乐进行弥合与修正的方法之一。同时,这也是中国叙事学与叙事传统,在影视领域尤其是当下流媒体环境下的一次延展。从表面来看,神话、传奇、志怪、话本、章回小说、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叙事资源,为网络剧提供了建构基底;而在中国文化中长久居于边缘的叙事资源,也与“作意好奇”的网络剧叙事特征达成一致。从深层来看,不论是美学维度还是结构维度,网络剧在传统的散点叙事、意象叙事等方面均存在极大的尝试空间。随着大众从“大屏”到“小屏”观看习惯的变化,曾经被冠以粗制滥造、低俗无趣的网络剧也将迎来内容生产趋于理性、优质的发展新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在回归民族叙事传统的过程中,网络剧有可能在艺术与机械复制时代,重新回到“中国故事”的活泼传统,找到另一种更广阔、开放的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