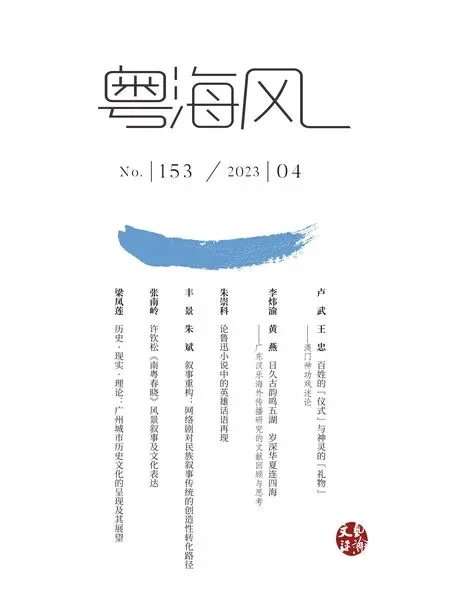论鲁迅小说中的英雄话语再现
文/朱崇科
引 言
母亲鲁瑞(1858—1943)收到长子鲁迅(1881—1936)寄来的照片后曾经对俞芳(1911—2012)说,“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非常刚正;他从小就不欺侮弱小,不畏强暴;他写文章与人争论,话不饶人;但对朋友,心地却很厚道,很善良的。”[1]所谓“知子莫若母”,这当然是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的性格中不乏英雄气质。实际上鲁迅的一生经历中不少时刻呈现出英雄情结,比如少时即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学骑马尚武术)、好打抱不平,留学日本时期的壮怀激烈与爱国情怀,在北京时期爱护青年,尤其是1926年“三·一八事件”中的仗义执言并据说因此被通缉,在广州时期“四·一五事件”中挺身而出爱护学生,以及在上海时期的以笔为旗、韧性战斗等都闪耀着英雄的光辉。
好比具有“革命家”头衔的鲁迅其实更多是由于其具有卓绝深邃的文化革命思考及实践一样,在鲁迅的英雄精神气质中也包含了文化英雄维度。或许我们不该忘记鲁迅的另一个身份是优秀学者——其古籍校勘(尤其是嵇康集等)、其《中国小说史略》关于古典小说的言简意赅的精深研究,都令人刮目相看,而这些研究对于敏感锐利的鲁迅来说,既是一种工作需要、精神寄托,又有一种反向渗透。如人所论:“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照,具有鲜明、独特的英雄气质。他对屈原、嵇康、阮籍的反抗精神予以肯定;对陶渊明诗歌世界中的英雄形象如精卫、刑天、夸父、荆轲高度赞美;对唐末、明末‘战斗’的小品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雄视角观照,是鲁迅自身英雄气质的反映和投射,这种气质,概言之,具有个性的反抗、决绝的复仇、孤独的牺牲等特征;鲁迅的英雄气质,既渊源于故乡越地文化特质的深远影响,也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界英雄元素的滋养,更是清末民族复兴的时代政治、文化思潮作用下的产物。”[2]
关于鲁迅书写英雄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本人的作品《故事新编》及单篇文本如《奔月》上,亦有学者的线性梳理,如阎庆生《试论鲁迅的英雄情结》(《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1期)。相关研究有勾勒、有细描,增益了我们对有关议题的认知,但亦有可以持续推进的空间:一方面,我们可以涵盖鲁迅全部小说中的此类书写,可以探勘更全面的思考;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英雄话语[3]理念研究其中的有关运行机制以及它与鲁迅书写的主体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然,这里的英雄既可以是一种立足于丰功伟绩基础之上的文化气质与精神贯穿,同时又是一种身份确认。
在留日时企图以文艺救国的鲁迅终究遭遇了连番挫败,比如《新生》刊物的流产,比如指望热卖的《域外小说集》的滞销,等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及这种落差,认识到了这种自我的英雄主义与严酷多变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说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实际上,鲁迅并没有放弃这种梦想,而是以更加韧性的方式前行:积极《呐喊》呼吁启蒙,可以独自《彷徨》,但一如《野草》般顽强生长,甚至在郁闷孤独时在《这样的战士》中抒发心志,也是他一贯的“立人”思想的表达。如人所论,“他以战士作为‘立人’思想的承载者、执行者和出口,显示出身为战士的坚守策略:有勇有谋、韧性战斗,同时他也揭示了战士的斗争策略及其中国遭遇,虽身处困境,但最终亦反抗绝望和各种限定性,他可以失败,可以死去,但是,战士韧性、理性、自信战斗的精神永存。”[4]
一、英雄气质:再造与强化
某种意义上,书写英雄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中至关重要。从宏大的层面来说,如何借此实现启蒙目标——“立人”从而凸显立国大业是其追求之一,“在文化启蒙的宏大工程中,破除固有的象征秩序是启蒙实践的重要任务之一。英雄崇拜作为人类持久的社会心理,理所当然地成为启蒙者整合与改造的对象之一。历史所积淀的英雄观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必然被改造之后进入新的文化系统。再造的英雄形象作为强有力的象征符号担当起重构象征秩序的重任。始终坚持启蒙立场的鲁迅,也在致力于英雄形象的再造。”[5]从微观层面看,这也是鲁迅内心深处英雄情结的外化,甚至借此也能够安慰同道,“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当然,如果更进一步,也是他为英雄们“立言”的实践,如《药》中对秋瑾(1875—1907)就义的纪念与铭记。值得提醒的是,鲁迅也借此方式表达他对革命(含刺杀)的态度——和而不同的韧性战斗而非一击毙命同归于尽。
(一)个性与创造
毫无疑问,文化英雄最常见的特征之一就是颇具个性和创造力,青年鲁迅对尼采尤其着迷,他在早期书写中也呼唤天才与摩罗诗人,在庸众与天才之间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他区分“个人”与“众数”,强调“任个人”“排众数”,“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翼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文化偏至论》)
相较而言,为了更好地“立人”,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精神多有采自西方现代性之处。从此角度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月光正浓时往往也最锐利,目光如炬,所以他可以洞悉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吃人”真相,但同时因其身上的现代性,假扮中医的刽子手并不能真正为其把脉且对症下药,而狂人本身却可以洞悉其奸——“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同样,《伤逝》中勇于反抗旧伦理道德,勇敢迈出第一步且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年轻一对——子君和涓生,也是既有个性又有勇气的,而他们的精神战斗资源之一就是文学巨匠们的战斗精神指引——“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一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
当然,所谓英雄,可能在沧海横流中才更显本色,但也可能倍受打压挫败而变得消沉。《孤独者》中的前半段的魏连殳可谓颇具个性,因为爱曾经相依为命的庶出祖母,表面上他接受了有关人士安排的传统丧葬礼仪的限定与约束,但实际上他有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甚至他死后,虽然在众人摆布下配上军衣军裤军帽,但“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实际上骨子里他并不妥协,在因为维生而不得不投靠杜师长做幕僚后却又自戕速死,清醒而痛苦,如人所论,“悖反在鲁迅的英雄小说中,具有至上的意义:神圣的理性呈现为荒谬的疯狂,时代的英雄,成为社会的公敌。换句话说,如果失去这种悖反,作品塑造的人物也就不能称其为时代的英雄。同样,悖反的孤独,才是英雄的孤独。”[6]
创造力往往也是判断英雄与否相当重要的指标之一。原名《不周山》的《补天》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是想“解释创造”:女娲在精力过剩相对无聊时造人,谁曾想不同手法制造的小东西们不断分化乃至异化,不仅不满意自己的神圣母亲,而且还因为私利开战,甚至搞得天崩地塌,女娲不得不奋力补天,终因精疲力竭而死,而死后的尸体却亦被小东西们利用,鲁迅借此写出了人性的丑恶,甚至也让女娲为此付出代价,但毫无疑问,作为神圣而巍峨的母亲,“创世纪”的女娲具有惊人的创造力,“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二)实干与牺牲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曾经深深体会到战时被日本铁蹄蹂躏的人们对“力”的渴望,然而,她毫不客气地回应称自己无法生编硬造出“力”来——“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7]这当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爱玲的小说为何历经时代变换依然具有生命力和广泛读者。实际上,在凡人和英雄之间可以共享某些元素或优秀品质,只是英雄们的涵盖性和程度更高而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元素就是实干和牺牲。
1. 平凡中的不凡。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实际上他在小说中也不乏对普通人身上不凡素质的状描。
《一件小事》中难能可贵地褒扬了人力车夫作为底层人士的善良、正直与担当精神,在发生轻微刮蹭而且“我”告诫他老女人可能撒谎时,“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头发的故事》中提及辛亥革命中的牺牲,他们都是普通人却主动前赴后继牺牲,终于铸就了改天换地的大事业,革命初步成功时当好好纪念他们,“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还有《药》,尤其是其中的暗线主角——夏瑜,他在牢里还劝人“造反”(其实就是一般人不懂的“革命”),在被牢头殴打时,反说对方“可怜”,的确令人震撼。鲁迅写道:“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最后他们只能以“发了疯”命名夏瑜,来掩饰群己的愚昧无知。
2. 英雄本色。当然鲁迅也塑造了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作为典范,从而期冀“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理水》中的大禹毫无疑问是个实干家,在众多官员贪污腐化、顽固保守之时,他苦心孤诣,脚踏实地,“这时候,局里的大厅上也早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同时他也有创意,抛弃过去的老法子——“湮”,而启用“导”的办法治水,而且这是他和同事们由实践得出的真知,“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铸剑》中的黑色人,作为复仇之神,其实颇有牺牲精神,不求报答,他对眉间尺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而眉间尺的头颅在鼎里和王头鏖战处于下风时,黑色人将自己的头斩落鼎中,“联头”作战,终于复仇成功,“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不难看出,黑色人言必行、行必果,勇于自我牺牲,颇具英雄风采。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非攻》,其主人公墨子不仅生活上艰苦朴素,还要劝说强大的楚国不要攻打相对弱小的宋国。外表上看,他其貌不扬,“墨子在这里一比,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作为英雄,他更高的格局是热爱天下和平,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所以当公输班说:“老乡,你一行义,可真几乎把我的饭碗敲碎了!”墨子回答说:“但也比敲碎宋国的所有饭碗好。”从此角度看,墨子有勇有谋有格局,胸怀苍生幸福安危,的确是大英雄。
二、英雄的泪与伪:剖析与批判
一般而言,所谓乱世出英雄,英雄往往和时代形成繁复张力:一方面,乱世可以成就英雄,但也可以验证其伪;另一方面,乱世又可以阻挠和打压英雄,让英雄落泪、有迟暮之感,乃至遭遇重大悲剧。当然,这悲剧本身也值得双向反思,“在这样的悲剧中我们一方面要反思庸众身上所体现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更要反思这些‘英雄’身上的劣根性,反思他们是怎样由英雄沦落为凡人甚至伪君子的。《故事新编》不仅是表层意义上英雄和先贤们的悲剧,更是深层意义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悲剧。”[8]
(一)英雄泪
不必多说,即使鲁迅自己,亦有面对失败清醒意识到自己局限性的时候,甚至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比如他企图以文艺救国,比如他的真诚牺牲遭遇了欺骗乃至诅咒,再比如他自己本身的中年心态以及每况愈下中的情况设想与努力突围,严苛真切细腻精致的自剖等等。而落实到艺术风格上来时,也甚至打上了中国语境中鲁迅特色的烙印,如人所论:“而鲁迅的自我解剖,则要现实、具体得多。在更多的时候,他都是深刻地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伪善和隔膜,正是它们扼杀了自身生命的完成,而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自觉不自觉地粘滞着这些令人齿冷的‘鬼气’。”甚至可以生发开去,成为一种主义——“恐怕也只有建立在鲁迅这种独具特色的精神苦闷基础上的文艺才是真正的不盲从、不伪饰的现代文艺,只有建立在这一体验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才是中国的现代主义。《奔月》的艺术风格也可以从此得以说明。”[9]
《奔月》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篇颇富意义张力乃至狂欢色彩的小说,鲁迅在其中最少设置了意义的三重世界:夷羿的古典神话、鲁迅的现实主体介入以及有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及其他方面哲理性的思考。[10]若从英雄泪的角度解读《奔月》,不难发现鲁迅投射自我的夷羿其实面临着双重困境。
第一重来自自我的衰落,所谓英雄迟暮。夷羿严格说来缺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他的鼎盛时期,未曾想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他于是回想当年的食物,熊是只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出去狩猎时,他可能由于(老眼)昏花,误把老太太的黑母鸡当成鸽子,“远远地望见一间土屋外面的平地上,的确停着一匹飞禽,一步一啄,像是很大的鸽子。他慌忙拈弓搭箭,引满弦,将手一放,那箭便流星般出去了”。而在妻子嫦娥飞升月亮后,他企图以射日弓射落月亮,“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结果月亮毫发无损,“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从神话中可以射落九个太阳到对月亮完全无能为力,从英雄主体角度来看,这更喻示了英雄的没落与穷途末路。
第二重困境则来自自我周边的伤害。其中一方面是得意门生逢蒙的背叛与忤逆。他通过流言话语[11]抢占夷羿的丰功伟绩,亲自上阵企图以箭射杀师傅,未遂后却又以言语诅咒,“‘真不料有这样没出息。青青年纪,倒学会了诅咒,怪不得那老婆子会那么相信他。’羿想着,不觉在马上绝望地摇了摇头”。另一方面则来自爱妻嫦娥的背叛,尽管夷羿在日暮途穷只能吃乌鸦炸酱面因此思考退路时提及:“我呢,倒不要紧,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升。但是我第一先得替你打算,……所以我决计明天再走得远一点……。”而在射月失败后又自我反省道:“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不难看出,其中彰显出夷羿对嫦娥的一以贯之的真爱。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探讨逢蒙和嫦娥的背叛是否与现实中的高长虹角色叠合,但毫无疑问,夷羿受到了巨大伤害,而作者鲁迅书写此文时也灌注了深深的忧虑:既是对自我衰老的忧伤,同时也是对可能的婚恋(尤其是他和许广平)的未来有一种悲剧性的预知,毕竟鲁迅的婚恋小说中主角的最后结果往往都是悲剧。[12]
《奔月》或许还可以做更深层的解读,那就是文化层面的精神资源寻找尝试。表面上看,夷羿不适合于新的时代变迁,作为旧时代的英雄,站在新时代的转捩点上他显得落伍而孤独,如人所论:“鲁迅笔下的后羿不是处在充满敌意的周围世界中,他们没有‘敌人’,是没有‘敌人’的孤独。鲁迅站立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中国’的土地上,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人生,并感受了人生的许多无常。他试图寻找中国现代精神界之战士却看到了无奈中的英雄和英雄的无奈。”[13]从新旧转换时期必须以现代性进行回应的逻辑思考,夷羿的没落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一如他射日时是英雄、射月时却无法面对/超克月的狡诈——传统文化无力拯救新时期的中国诉求。
英雄泪其实还应该包括坚守精神的纯粹与捍卫原则的失败。《采薇》中的伯夷叔齐若从历史进化论角度看或许称不上英雄,因为他们恍若开历史倒车,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真正捍卫气节至死不渝的存在,鲁迅对他们的这一心态和实践是尊敬的,同时也借不少反面例证加以说明:姜子牙的老谋深算、老于世故,小丙君的两面三刀、急功近利又沽名钓誉,山大王小穷奇的伪善粗鄙,阿金姐的平庸之恶,等等。从此角度看,伯夷叔齐还是可爱的,鲁迅虽然调侃和嘲讽他们的天真与顽固,但对于他们的精神节操还是赞许的,但遗憾的是,在乱世或转型期,他们必然是牺牲品,不得不死。
(二)伪英雄
在1927年所写的《小杂感》中,鲁迅以辛辣的讽刺口吻揭露了投机的卑劣心理——“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其中所谓的“英雄”也部分带上了贬义,因为它掺杂了不少虚假元素,背离前述几个英雄的基本特征与品格。
1.符号式借用。《风波》中的赵七爷统治的策略和资源恰恰是来自陈旧的传统文化知识——残缺不全的《三国演义》常识。面对社会转型,他的慨叹是:“如果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而对付质疑他的人,他却是借助英雄进行绘声绘色地恐吓和自我标榜,他吓唬寡妇八一嫂说:“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相当吊诡的是,这两个为民所敬仰爱民如子的英雄却成为赵七爷对抗现实中国及底层人的武器。
《阿Q正传》中则呈现出一个底层流民的有关思考与误用。阿Q所知道的民间戏曲的文化资源,除了《小孤孀上坟》就是《龙虎斗》,基本上就是欲望与权力的表征。尤其是辛亥革命时代,他挂念的却是封建时期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他陈旧的文化资源只能将现代的革命理解为“造反”——“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而在其幻想中对财产、女人的处理方式活脱脱显示出他根本不是英雄,而更多只是借英雄权势谋取私利趁火打劫的底层失败者的幻梦。
2. 刚愎自用。《起死》中的庄子本该是个英雄,但他却是一个刚愎自用不懂得善待苍生同时谨慎使用权力/法力的伪英雄。他想复活有生命历史记忆的500年前的骷髅,在他施法时,无论是鬼魂还是司命大神都劝他少管闲事,因为“死生有命”,他却执意不肯,强行要求复活,还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臣是见楚王去的,路经此地,看见一个空髑髅,却还存着头样子。该有父母妻子的罢,死在这里了,真是呜呼哀哉,可怜得很。所以恳请大神复他的形,还他的肉,给他活转来,好回家乡去。”结果复活后的汉子沉醉在旧时的记忆中要求庄子归还他的衣服与包裹等,甚至一言不合竟至于老拳相向。搞得庄子只好再度求救,司命大天尊无果,只好借助现代的巡士,结果巡士又得再找巡士帮助。鲁迅此文的书写当然有其深意,希望可以彰显传统文化资源难以拯救现代中国的道理,但作为主人公的庄子并未谨慎使用其英雄权限,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的认知和对自我的克制,才导致了闹剧的发生。
结 语
相较而言,鲁迅小说中的英雄话语的文本实践中,《呐喊》《故事新编》篇目较多,《彷徨》最少,只有两篇涉及。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呐喊》时期的鲁迅还是抱着启蒙、“为人生”的心态,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虽不是主帅,但也是勤恳耕耘的大将之一,他要为同志们摇旗呐喊,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而《彷徨》是新文化运动陷入低潮前后的产物,其风格也相对写实,呈现出书写与反抗绝望的特征,但整体而言,其悲剧意味浓厚;《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丰厚实践文本,既彰显出可借鉴的民族脊梁及其精神资源,同时又指出单纯依赖传统实现现代化的虚妄性,当然其中的“油滑”与对英雄的调侃既有反讽嘲弄,同时又有自我的纾解与减压,但无论如何都是其英雄情结的表达,如人所论,“英雄情结是鲁迅人格结构中潜在的情绪性冲动和意志张力,它为主体提供着行为的固定模式,为意识层面上的对应物——革命英雄主义思想、革命意志提供着必要的心理能量;它吸引着主体丰富的人生经验,固着于主体‘反抗’‘复仇’‘革命’之类的观念形式上,有力地强化着主体的意志,并经升华而汇入主体的革命思想和世界观里面。”[14]
在我看来,鲁迅在小说中的英雄话语自有其独特追求:一方面是状描与剖析英雄气质,如其个性/创造,实干与牺牲,借此实现对新人的强调/再造和“立人”思想的再现,同时另一方面他也以同情之笔抒写并自我投射了英雄泪,尤其是迟暮之感,当然他也批判了某些劣根性,既有借助英雄的符号化使用,又有滥权的伪英雄。无论如何,这些实践呈现出鲁迅的别具匠心与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