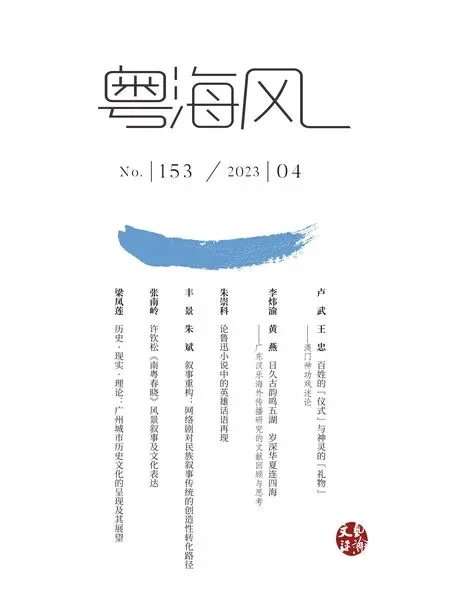海外题材电视剧中的灾难母题与中国想象
文/张伶聪 王玉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电视剧作为重要的媒介产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承担着这一文化使命,其中海外故事作为贴近海外民众的电视剧题材,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好评,不仅提升了海外受众对中国的信任度,而且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更增进了中外人民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当前对海外题材电视剧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视角展开。其一,从文化研究角度探究海外叙事产生的文化意涵。朱言坤从荣格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将情结作为透视中国人重要的观念意象和情感结构,以此探讨跨国流动中的中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表征和想象[2];周根红以海外华人作为切入口,探讨海外华人形象在历史钩沉中的演变、在异域空间内产生的现实迷失,以及与西方文化冲撞和共融的合力下身份认同衍变的不同面向[3];王玉玮以身份认同为理论视角,从他者审视、族裔对照和“世界公民”新塑来考察海外移民的心理变化[4];王玉玮和张伶聪还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分析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以及型构中华民族认同的电视话语表达方式[5]。其二,多以热播剧个案分析电视剧叙事的艺术创新。刘振和康思齐从类型创作视角分析了《猎狐》在题材元素上的跨类型组合和伦理诉求上的反类型尝试[6];蒋达和王刚既分析了《刑警之海外行动》复合叙事单元的结构创新,又着重指出了该剧在文戏设置、主题立意和人物形象等内容层面的创新[7];何天平和张榆泽则认为《刑警之海外行动》基于纪实美学的原则完成了对真实故事的艺术化创造和新时代平民英雄形象的重构[8]。
从上述两种视角展开的研究忽略了海外叙事的美学与文化意义的同一性,特别是中国如何在海外叙事中显影、如何实现文化在场的研究议题还鲜有分析。母题是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元素,是构成表现主题或情节的较小单位甚至最小单位,它成型于某个历史阶段,因其思想的指向性,常为后世文学所借鉴和沿用。陈建宪认为为数不多的母题经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数文艺作品,还能与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化形态相结合,它们具有人类共同体的共通意识,并构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识[9]。在当前海外题材电视剧中,瘟疫爆发、地质灾害、偷渡、涉黑涉恶等灾难事件被反复刻画,灾难构成了海外题材电视剧重要的文化母题,以灾难母题切入海外题材电视剧能够较为合理地勾连其内容与形式层面的分析,凸显电视剧话语中中国想象的美学意涵和文化旨归。因此,本研究从灾难母题书写出发,以中国生产的海外题材电视剧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关注如下研究问题:海外题材电视剧如何书写灾难母题?在具体的灾难叙事中如何实现中国在场?这种在场进而又表征了怎样的中国文化形象?
一、古典神话的赓续:社会伦理的崩殂与中国对海外侨胞的庇护
个体成为社会人的历程在神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常常表现为人类行为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一旦违反伦理就必然引发灾难的惩罚,这也就构成了伦理灾难母题。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一般伦理亚型和两性伦理亚型:一般伦理亚型常常与洪水神话有关,希腊神话中阿卡迪亚王国国王吕卡翁的伦理失范惹怒了宙斯,宙斯欲以洪水消灭整个人类,人类社会也第一次因为伦理失范遭受了灾难;两性伦理亚型与伊甸园神话有关,夏娃禁受不住诱惑偷吃禁果,将人类引向悲剧性死亡[10]。如果说一般伦理亚型是凸显男人生性好战与试图宰制他人产生的恶的苦果,那么两性伦理亚型则是着力表现女人天性贪婪与易受他人蛊惑产生的贪的厄运。这两种亚型在海外叙事中均得到了体现,主要表现为偷渡以及涉黑涉恶。对法律底线的僭越演变为违法犯罪,其结果直接引发犯罪者自身及社会关系的振荡与灾难,而化解危机的关键则是以警察、军队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崩殂的社会伦理的重新扶正。
第一,偷渡者对自我身份的消解与祖籍国对其身份的重新确证。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热”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身份焦虑和文化心态。有部分人错误地认为中国愚昧落后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而域外黄金遍地,只要出去就能实现阶层的跨越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不惜铤而走险成为身份失却的偷渡客。在《没有国籍的女人》中,诸如独孤梦、晓梦这样的青年女子做起了异域幸福梦、发财梦,中国身份和社会境遇成为她们生活的枷锁,前往异域是在“挣脱牢笼与拥抱自由”,迫切地完成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反叛,殊不知在西方种族歧视的社会语境下华人所面临的遭遇,并未显示出异域的优越性反而消解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正如剧中孟教授对晓梦的劝告,华人在异域的成功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是个别现象,文化和政治上的弱势时刻让华人处于被动。崇洋的心态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逐梦者们最终以非法偷渡的方式走出国门,与百年前华工“猪仔”般的命运形成映照,身处在祖籍国和住在国的真空地带,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夏娃式恶果——陷入死亡的边缘,只有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能在祖国的拯救与庇护下重新找回失落的身份。在海外题材电视剧当中,女性成为偷渡客的形象典型,她们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身份转变,从文化角度上看,对异域的向往与追求可以被视作是对过往历史遭遇的哲思和男权社会的反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常常落入男性主导的犯罪集团之中,最终反而是需要女性试图逃离的那个男权社会意识形态机器来拯救和庇护。正是在女性偷渡客身份的双向悖论中,对偷渡行为非法性的整饬和公民自我身份消解的反驳,凸显了作为祖籍国的中国在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身份上对失落华人的现实救治和精神救赎。
第二,恶势力对社会规则的僭越与祖籍国对其行为的制裁扶正。如果说海外题材电视剧中偷渡客的故事,常常展现女性作为主体所经历的受害和加害的矛盾变迁,“被动的恶”的艺术倾向使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拯救的对象;那么涉黑涉恶故事中的犯罪者多以作为警察和军队对立面的男性形象存在,他们的行为僭越、对他人的加害和对社会准则的破坏使其变成了叙事的客体和被暴力机器打击的对象。异域也不再是令人艳羡的富足之地,变成了法则失序的自由之地和偏安一隅的法外之所。《刑警之海外行动》以三个单元故事完美诠释了新时代异域形象在中国影视话语中的承继与转变。东南亚成了偷渡者和电信诈骗犯的窝点,中国台湾籍林国雄团伙就是以此为据点无情坑害中国大陆同胞,为了扩大“战果”还对赴东南亚旅游的中国游客进行绑架和人身自由限制,最终中国警察和当地警方合力惩治了罪犯。在此前的海外题材电视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中,东南亚的“法外之所”形象多有定型。《愤怒的女神》以东南亚排华事件为背景,陈文兰、黄亚美、谭阿娇三位妙龄少女不仅在屠杀和抢劫中失去了亲人,而且沦为东南亚黑帮性交易的工具。此后,《梦醒天涯路》《捕蛇行动》《今世迷情》等剧又着重刻画了东南亚各国法制层面的漏洞,东南亚成为了蛇头运送偷渡客的中转站。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美国犯罪率不断攀升,2020年美国的谋杀案同比激增超过27%,“犯罪浪潮”正在席卷美国各大城市[11]。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题材电视剧对美国的想象多为现实的折射,美国的政治博弈策略成为经济罪犯、政治罪犯寻求政治庇护的工具,美国政府对罪犯的接纳与包容使其演变为藏污纳垢的国度。《纽约奇缘》中,周雄因犯罪逃逸至美国,到了纽约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唐人街的霸王,敲诈勒索唐人街华人商贩,并不断与周边黑帮发生火并,整个纽约变成了罪恶都市,充斥着偷渡、卖淫、毒品交易,在周雄等人的金钱攻势之下美国司法体系变成了摆设。正是现存的司法漏洞,让许多在国内触犯法律的国人纷纷选择美国作为逃逸点,试图免于法律的制裁。《刑警之海外行动》中的宋成功、《猎狐》中的王柏林等人就是拥有这种心理的典型代表,但最终事与愿违,中国法律穿越太平洋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将这些犯罪者绳之以法,实现了司法公正。
二、共同危机的再现:原始部落的困窘与中国对异族兄弟的援助
自然灾害、战争与疾病是当前文学书写最常见的三大灾难。自然灾害作为母题出现得最早,源于早期人类以朴素的世界观敬畏与臣服于神秘自然力量,将其作为一种实在的集体表象去观照和遵奉,而随着人类能够科学地把握自然世界,对自然灾害的认知过渡到思索人与自然环境如何共生乃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12]。原始部落土著对于自然灾害的认知并非是一种知识的自然演进,而是在外力的介入下打破固有思维后获得的新知。在《一起深呼吸》中,第二批驰援扎尔岛的中国医疗队赶上纳努威火山爆发,岛上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当地友好医院闹鬼的传闻甚嚣尘上,令岛民心存忌惮,拒绝接受中国医生的救治,初步建立的现代医学认知和信任毁于一旦,当地岛民被重新拉回怪力乱神的信仰之中,随着友好医院解开闹鬼的误会,中国医疗队和救援队逐步帮助当地居民建立起灾害防护和现代医学的认知。
战争母题的存在成为人类文明演进史的隐喻。战争是由“部族冲突与融合、利益争夺与妥协、文化碰撞与调适”等多重因素构成,其产生的破坏性与创造性同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战争史也是人类的文明史,战争波及范围越广、影响力越大,所产生的文化代价也越大。战争母题记录战胜者部族可歌可泣的文化进程,也使战争具有了超越灾难的文化意义[13]。海外叙事对战争母题的再现不再以进化论的生物学思维凸显人类文明的文化学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以和平化解部落纷争与种族斗争。文化的进步与民族的交融不必建立在杀戮之上,残酷血腥的原始文化进程得到了修正。《维和步兵营》中非洲比拉部落和努巴部落常年因水源归属问题展开厮杀,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部落的饮水问题,维和部队帮助当地部落打井,间接地缓和了两个部落间的纷争。《埃博拉前线》中以黑石寨和桑宜村为代表的反政府军与政府军的对垒使百姓苦不堪言,在疫情爆发后,由于反政府军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造成疫情的大面积蔓延,在中国医疗队的积极斡旋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促成了两军的和平谈判与新政府的组建。
疾病母题带有明显的巫术—精神意义,巫医和患病个体的存在能够对所在族群产生强大的精神号召和情感动员。巫医对患病个体的救治过程实则是信仰仪式的传播过程,在巫医的指引下族群其他成员对制造疾病的神秘客体予以虔诚的敬奉,族群成员在治病仪式中得以团结。对患病个体而言,仪式虽然能够产生强大的心理慰藉,但对身体康复不起任何作用,患病个体沦为治病仪式中的祭祀品与牺牲品,死亡成为患病个体的最终归宿。海外叙事中对疾病母题的书写并非以现代医学完全代替巫医,而是采取文化交融的方式融合了西医的诊疗技术和巫医的精神抚慰,中医文化甚至成为同时能够医治身体和心灵的融合医学典型,契合土著居民对疾病、身体以及精神信仰的朴素认知。在《埃博拉前线》中,桑宜村酋长排尿困难生命垂危,巫医和西医均无能为力,情急之下郑书鹏采用孙思邈的芦苇导尿成功地救治了酋长。埃博拉疫情爆发后面对西医束手无策的窘态,郑书鹏劝说何东拿出中医诊疗方案,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起到了奇效。正如郑书鹏在结束援外任务的自白中所提到的:两年来在这里改变的是我自己,我学会了和不太熟悉的人拥抱,用卫生不达标的瓶子喝棕榈酒,学会了用木薯做一整顿饭,学会了用谦逊和尊重与我想法不同的人相处。战胜疾病不仅在于治愈身体,而且在于疗愈心灵,实现文化间的理解与交融。
在海外题材电视剧中,中国与原始部落构成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二元结构,原始部落作为愚昧、落后的存在,对自然灾害、战争、疾病始终处于原始的思维模式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对原始部落兄弟的援助间接完成了原始部落现代性、科学性思维的引入与转变。
三、多重灾难的超越:英雄情结的再塑与中国推动全球救援合作
人类正是在不断战胜灾难和超越自我中实现认知进化与社会发展的,解除灾难带来的危机往往借助于人类自我的纾困能力。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先民抵御自然灾害的常用手段就是寄托于神力的幻想,随着认知的发展,虽仍不能摆脱自然力量的束缚,但已渴盼出现拥有神力的人力挽狂澜,渐渐地这个拥有强大自我纾困能力的人类被神化为英雄[14]。无论是东方神话还是西方神话,英雄大都具有非凡的力量,能解救苍生于水火。英雄与灾难的天然相关性,产生了人类文化中的英雄崇拜与英雄情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里,英雄人物成为中华民族认知灾难的重要方面[15],现代心理学将“英雄情结”视作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文艺对英雄的塑造和崇拜则是集体造梦的过程[16]。众多的中西方文艺作品对英雄塑造呈现两极分化,中国英雄是在集体主义观念主导下以实现社会价值为主要目标的民本英雄,西方英雄则是个体主义思想引导下强调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本英雄。中国英雄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献身主义精神常常为西方自由人本主义文化所诟病,指责其泯灭了人性和爱欲,但是西方文化着意凸显的英雄超级能力和自我意识,也仅是面对灾难时战胜恐惧的心理慰藉和一厢情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17],我们当今的时代需要的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为正义和真理勇于献身,具有崇高思想、社会眼光、科学成就与艺术才能,在地球上建立人道王国的人”[18]。
当前海外题材电视剧通过对以警察、军人、记者和医生为代表的职业群像的再现,试图超越中西方二元对立的英雄形象设定,以既承继集体主义观念又发扬个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新时代中国式英雄成功地完成了对英雄情结的再塑。《刑警之海外行动》中的中国刑警海外行动组以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在东南亚、阿根廷和美国侦破经济犯罪、金融诈骗、拐卖人口和制毒贩毒等国际刑事案件,成功地展现了新时代的中国警察形象群像。在剧情设定上,六位人物的戏份比重相当,均处于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地位[19],在具体的人物能力设定上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为主,比如:组长高笑天包容、智慧且具有大局意识和掌控能力;沉着冷静的数据分析师武胜南和记忆力超强的侧写师萧红,共同助力高笑天的正确决策;尹志航作为海归刑警,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和国外工作经验,凸显其在异国他乡办案的跨文化沟通和变通能力;一丝不苟的神枪手魏子猛和细致入微的技侦专家古思淼相互配合,承担保护遣返人员的职责。由此可见,整部剧着力于塑造警察群像而非突出单一人物的英雄事迹。这种人物设定方式既重视集体精神,又彰显个体作用,实现个体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平衡。
与此同时,海外题材电视剧在超越灾难的文化意涵和影视话语表述中也提供了一种新全球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超越当前西方霸权主导之下的国际合作格局,而以平等开放、包容互通的新全球秩序共同应对灾难。《维和部队》《维和步兵营》《和平之舟》《莫斯科行动》重构了好莱坞电影形塑的“美国主宰全球”的政治格局,中国倡导和推动联合政府的成立,凸显新全球化图景背景下全球政治力量的统合,以全球人类的共生共存共荣实现了对全世界人民的政治动员,体现了鲜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海外题材电视剧的灾难治理,突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下的“休戚与共”,彰显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解决全球化难题带来的全新可能性。
结 语
灾难母题的产生始于人类对周围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人类发现自身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死亡、疾病、饥饿、战争、仇恨等充斥在周围,该如何解释和应对这些危机?先民将希望寄托于神话中,用以说明人生烦恼与灾难来源[21]。海外题材电视剧正是通过对灾难母题的细化塑造了当代中国的神话。在具体影像表达中,灾难母题进一步衍化成五类亚母题——自然灾难母题、战争灾难母题、生态灾难母题、伦理灾难母题和反灾难母题,突破了中西文化英雄情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中国式英雄的形象再塑和文化超越,也完成了对中国的文化想象。
伦理灾难突出表现为社会规则和伦理的崩殂,偷渡和涉黑涉恶等违法活动威胁着海外侨胞的生命安全,作为祖(籍)国的中国积极展开撤侨和庇护行动,体现了中国对于国民安全和海外华侨华人合法利益的重视;自然灾害、战争和疾病导致了原始部落的困境,也构成了中国和异族兄弟需要共同应对的危机,中国对原始部落异族兄弟的救助,凸显了中国患难与共、睦邻友好的国际形象;反灾难母题则表现为中国主导和推动世界共同应对全球化危机,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正是中国警察、中国军人、中国医生和中国方案的介入,摒弃零和思维和利己主义价值观,探索共赢共生发展之路,在危机出现时相互支撑共同应对,成为有效化解灾难的关键,“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成为中国在场的伦理标志和情感诉求[22]。中国电视话语整饬和超越了“西方霸权主导世界”的现实处境,形塑了一种新全球政治伦理,即全球政治力量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统合,为实现人类的共生共存共荣而携手并进、团结协作。由此观之,海外题材电视剧深刻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影像实践和文化撒播必将打破异文化间的壁垒,增进中外人民的友谊与理解,增强海外受众对中国的信任与认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