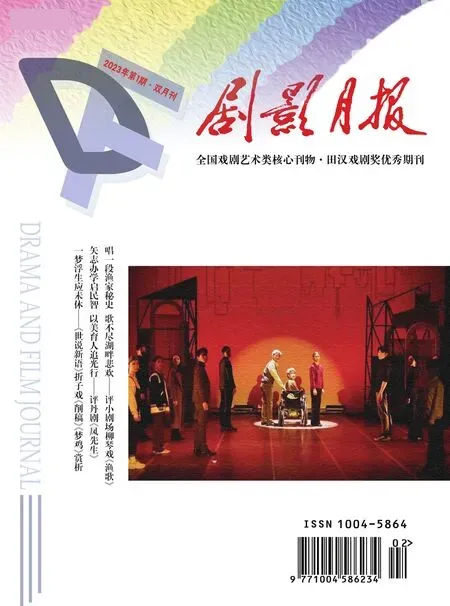情感视点与诗意修辞:浅谈《四个春天》的影像逻辑
■刘济君
2019年1月4日在中国上映的纪录片《四个春天》由非科班导演陆庆屹执导,以2013 至2016 年的四个春天为叙述时间节点,记录了一对相濡以沫且热爱生活的老夫妇,即导演的父母,可爱诗意的生活日常。纪录片符合非职业导演的创作风格,粗糙随性的影像状态贴合了老夫妇日常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作品表现出当下社会语境之下的家庭关系与情感羁绊,向观众传递出一种返璞归真的久违的舒适感,最终引发了观众对于家庭关系以及生命态度的忖量与追问。导演作为这个家庭的家庭成员利用摄影机重叠了自我的视角,贴合于维尔托夫倡导的“电影眼睛派”的拍摄方法。另外,这种导演主观的介入并没有剥离纪录片的纪实属性,这种恰当的介入方式又焕发出真实电影的审美趣味,再加上导演运用一些影像修辞创造出了纪录片的韵律节奏,成就了作品的诗意表达。
一、机器情感化的影像视点
1919年,吉加·维尔托夫使用平时保存下来的剩余影片,编成了一部放映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文献影片《革命周年祭》。“他发现摄影机可以记录‘真正的现实’,他要借此创造一种新的艺术:生活本身的艺术。他的这一设想到1923年完全成熟,形成著名的‘电影眼睛’理论。”所谓“电影眼睛”,就是借助影像的记录手段对可见的世界做出客观解释。导演陆庆屹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家庭生活为叙述内容,最可亲的父母及家人为主要拍摄对象,在素材的选取上便体现出导演试图通过摄影机这一媒介真实记录家庭生活几年光景的意欲。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身份之下,观众能感受到导演在家庭成员与摄影师身份之间的摇摆,而这种摇摆恰恰体现出导演对于影像内容介入程度的控制。而纪录片《四个春天》将四个春天的家庭生活与以往的家庭生活并置在一条叙事线索中,体现出的是导演通过蒙太奇组接等后期手段将影像元素与元素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建立起完整的叙事系统,从而创造“四个春天”式的家庭图景。而电影眼睛派主张利用摄像机进入或是捕捉有效生活中最有用、最典型的东西,之后再利用一些蒙太奇的剪辑手段,将一些有意义的生活片段组合成一个“新的世界”,导演可以通过创造这个新世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见”的实质。陆庆屹自我的家庭成员视角通过摄影机实现了扩张,将这样的“我见”扩大到了一种“所见”,将一个家庭的普通光景上升至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真实状况,形成了中国家庭情感的聚合场。
出其不意地抓拍,同样被导演在纪录片《四个春天》中重复地使用。电影眼睛派主张将摄影机隐蔽起来进行拍摄,维尔托夫“称这种方法为‘生活的即景摄影’,认为电影艺术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抓住生活的即景。”虽然大多时候拍摄者,即导演的父母和家人都知道自己是拍摄对象,可是时刻凝视着这个家庭的摄影机依旧捕捉到了很多出其不意的影像画面。导演并没有刻意地将摄影机隐藏,而是通过不间断地持续摄影来完成对于“生活的即景摄影”。例如,在父母送别自己的外孙时,摄影机首先将送别的画面纳入至视线范围,随着导演父亲与姐姐儿子的离去,画面中只剩下了导演母亲一人,母亲挥挥手亲手朝摄影机背后的导演说:“快去去拍他们”,随即进屋离开画面。镜头在此逗留了大概五秒以后,刚刚离开画面的母亲以为没有了摄影机的记录,偷偷地再跑出来目送自己的小外孙。导演凭借于自己对母亲的了解,耐心地为这段叙事内容预留了情感时间,而母亲对于摄影机的不知情更是深化了面临送别这一行为背后引发的情感的真实性。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触发了观众的心理机制,导演能准确地发现事件与预见戏剧性过程,因此在“偷拍”式的摄影机的捕捉下,真实的人物行动与人物情感得到完整的保留,纪录片的纪实性得到了最大化以及最优化的展示。
“真实电影”是法国的电影流派之一,指的是摄像机主动介入参与到被摄环境中去,成为“在场的”“参与的”摄像机,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具有互动、引导的关系。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摄影师与导演的主观介入。在纪录片《四个春天》中镜头时常是暴露的,导演经常直接介入到画面内容之中。其实从导演的多重身份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导演其实也是纪录片《四个春天》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家人围坐着吃饭的场景中,摄影机被固定,导演毫不忌讳地出现在画面内容之中,与画面中其他的拍摄对象建立起了情感联系,在一些即兴的人物对白之中,通过日常的寒暄话语将家庭议题放置在摄影机之前,将导演与拍摄主体的互动性放大,真实电影的事件讲究更完整和单一地直接拍摄真实生活,排斥虚构。因为导演的特殊身份使得导演本身就成为纪录片真实性表达的一部分,辅之单调的镜头,将真实感铺陈开来,观众不会因为导演的主观介入而产生任何的情绪怀疑与叙事怀疑,反而积累了纪录片的真实力量。调查意味是真实电影很重要的叙述特性。法国的人类学家让·鲁什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拍摄了一部调查式纪录片《夏日纪事》,对20 世纪60 年代的巴黎市民进行了一番社会调查,他们在巴黎的街头拦住每一个过往的人,提出问题:“你幸福吗?”这部纪录片成为“新浪潮”电影运动中三个分支之一:“真实电影。”纪录片《四个春天》的调查意味伴随着导演陆庆屹对于自己父母的采访彰显出来。导演有意地在几个叙事段落发问,试图摄取父母对于此问题的反映和回答。例如,在春节吃饭的段落中,导演有意提起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的问题,面对自己孩子的提问,父母在毫无戒备心理的情况下甜蜜地回忆了彼此的爱情往事,也将二人50 多年来的相濡以沫通过导演的发问得到印证。这种带有调查性质的问题让观众更顺畅地走近以及接受纪录片的叙述内容,从而更加熟悉荧幕中的人物,牵连出对于自我情感的怀想,也能在面对各种生活事件的时候,将拍摄主体的判断与评价呈现出来。这是导演选取的一种叙述方式,不是调查父母的生活,而是通过具有调查意味的叙述手段带出更加真挚也更加感人的影像内容。在这种调查性的情感问题下,拍摄主体有了情感宣泄的契机和平台,观众也有了引发共情体验的缘由。
真实电影的摄制组一般只由三个人组成,即导演、摄影师和录音师,并且由导演亲自剪辑底片。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摄影师、录音师都是陆庆屹。2012年,陆庆屹将两篇详细记录自己父母日常生活的文章,取名《我妈》《我爸》贴在豆瓣等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了很多读者对于这对老夫妻的好奇。从2013 年开始,陆庆屹每年春节过年回家,他都会拿起摄像机跟拍记录父母的生活。起初只是想为自己的家庭生活留个纪念,可是在拍摄过程之中他越发地感受到自己父母面对生活的乐观与积极,于是萌生了将自己的拍摄素材整合成一部纪录电影的想法。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陆庆屹自然而然地成了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导演、摄影以及录音师。因为不是专业出身,观众可能依旧能够看到影像的拙朴,可恰恰是导演的多重身份建立起了观众对于粗糙与拙朴的宽容。“三位一体”的身份角色为影像注入了更多的情感意蕴,观众会脱离对于影像语言程式的标准要求,而是将自我判断转向为一种感性机制中去,对于情感的挖掘弥补了多重身份下影像手法本身的不精致。
二、叙事诗意化的影像修辞
诗意美学在影像中最初的表达形式即为诗意纪录片,尼柯尔斯在根据纪录片发展的流变对纪录片进行分类的时候,首当其冲的类型就是“诗意”的纪录片,他认为:“诗意模式紧随着现代主义而出现,它作为一种表现现实的手段,偏爱片段拼贴、主观印象、非连贯动作和松散的关联结构。相对于现代主义的诗意理念,有些诗意型纪录片则回过头来追求古典诗歌理念中的和谐与美感,并在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它们的痕迹。”《四个春天》所采用的记录方式,以及将生活画卷娓娓展开的拍摄手法与叙事内容,与小津安二郎和是枝裕和的影像相似,都是在日常的稀松中探讨东方式的情感命题。
构图的韵律美。“在无声时代,叙事影像也需要节奏和韵律的表现实现自身的存在。因为单凭文字字幕呈现的纪录片因果叙事,在媒介形式上实在是太过‘喧宾夺主’,太过‘僭越’了,以致人们在纪录片中总是尽可能少用它们。”可见,影像作品需要除了文字字幕以外的节奏器,以营造影像的呼吸感。在这个诗意原理下,纪录片《四个春天》除了使用背景音乐与人物歌唱来实现影像的韵律,在构图技巧上也体现出导演的节奏感。在纪录片《四个春天》的画面摄取上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导演构图的巧思。并且,在画面元素与元素之间的比例协调中,创造出了纪录片的韵律节奏。导演将两个独立个体的画面并置在同一镜头之下,一边是母亲缝纫衣裳,一边是父亲在操作后期剪辑软件,运用“一堵墙”作为画面的分割轴线,再搭配上父亲操作的电脑里放出的音乐,音乐的线条似乎缝合了两个区隔的空间,创造出了独特的律动。在构图的有意控制下,导演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栖息地”的空间概念。例如,在片中频繁出现将人物构置远景中的画面,首先交代了导演老家的自然空间环境,其次将处在此地缘空间的人进行抽离化的展示,形成了庄子所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境。不管是影片中出现的导演家中的天井小院,还是家乡的山丘,抑或是清澈见底的水塘,都为父母亲生活诗意的展现提供了自由栖居的空间。这些温柔内秀的自然景色不仅仅包含了导演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也使观众能“移情”,勾起受众的浓浓思乡情,也使得生命回归到了久违的自然节奏和律动之中。纪录片的这种构图方式与风格将影片的质感与韵律构建起来,通过生命的渺小与自然的宽大之间的有机对比与融合,将人与环境的寄生关系全盘托出,从而实现人景一致的文化关照。
符号的意象化。“意向化”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韵律化表达,并暗示这一区别在于作品的内部,而非如同韵律化那样能够直接从外部形态上辨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象化表达在于对作品外部形式的一种“破坏”,一种“溢出”。《四个春天》的叙事线索的建立便依赖于春天的所指意义,片段化的后期剪辑好像是对于默片时代影像化诗意特征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一个个春天之间碎片化的叙事内容,抽象化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家庭故事,每一次村口河流的出现都似乎割裂和破坏了影像的流畅性,但是很快通过观众前面培养的情感认知填筑了这个空洞,形成了诗意表达。镜头语言不仅仅创造出片子的节奏韵律,也化身为一个个的视觉符码,实现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在纪录片《四个春天》场景转换的空镜头中,固定长镜头拍摄的那潭平静的湖成了四年光景的观望者。一家人在湖边缓缓走过反复出现,奠定了纪录片的平静淡雅的基调。水是时间的流逝,每一次春节,一家人都会在那片湖边缓缓行走,慢慢的见证父母地老去,和姐姐的离去,走的人也越来越少。依旧从哪走,湖面依旧平和,家中发生的大事,似乎都在被这片湖慢慢抚平,生活依旧,日复一日地重复。导演运用了一些诗意的处理手法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统一,实现了画面的指涉意义。影片中的“燕子在春天时归巢”与姐姐的第一次出场串联在一起,象征着在外的游子回归家乡,颇有中国古典美学的静谧温暖之韵。在之后的几个春天(几年光影)之中,“燕子”便承载着串联起时间流变的象征符号,它不仅象征着时间的流淌,也成了表达父母与子女亲情羁绊的元素。此外,片中被父母亲在阳台共同吹散的“蒲公英”更象征着父母对自然的珍视及对美好事物的真切向往。“蒲公英”随风而去时,母亲喃喃道,“好舍不得吹哦……”此时的蒲公英便替代了前文中的“燕子”来表达,父母之爱子女,尽管不舍,却为之计深远。“诗意达成要求观众把注意力从现实的、功利的、理性推理的方面转移开去,以使自己的情绪能够顺利宣泄。”导演通过这种意象化的表达技巧使得观众摆脱了对于画面内容的纯物质判断,而是率先建立起一种情绪感受,而这种“移情”使得受众在影片之外,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中得到情感的观照,形成观影上的高峰体验。
纪录片《四个春天》将真实且动人的生活场景与非功利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重返自然的质朴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父母与子女的纯洁之爱,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的温暖呈现,使人的心灵达到了一次净化与情感冲击。导演虽是非专业出身,但是依靠对于拍摄主体及拍摄内容强大的情感理解,实现了家庭影像的情感扩张。导演多重身份创造了影像独特的叙述视点,而影像修辞的力量将这些身份聚拢,化成一种凝视,它凝视家庭,凝视家人,更凝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