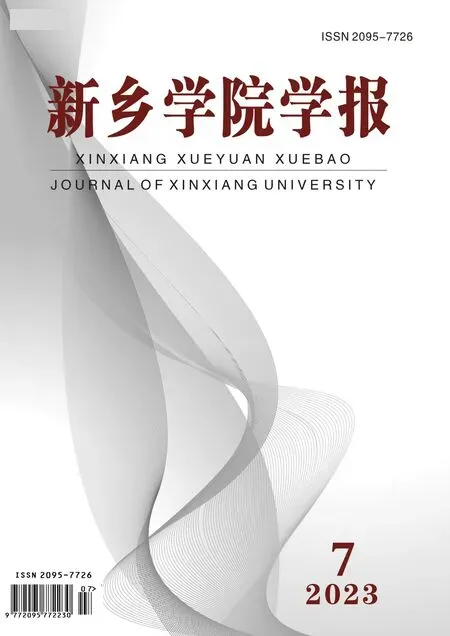钩沉稽索三十载,披沙拣金有新篇
——评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
孙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1991年,刘跃进先生接受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委托,开始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初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 在初版之后,刘先生旁搜广讨,钩沉稽索,推进增订,最终完成了《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的撰写。 增订版与初版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结构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 初版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包括《文选》与《玉台新咏》、唐宋以来总集、中古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综合研究,凡四章;中编“中古诗文研究文献”,有魏晋、南朝、北朝诗文研究文献以及乐府诗、其他诗歌研究文献,凡五章;下编“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分小说、文论、《文心雕龙》,凡三章。在原有的架构基础上,增订版上编将《玉台新咏》研究单独分章为五章,并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了《玉台新咏》的性质与价值、影响等内容。 增订版中编的重要变化,是将初版第三章的“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变为“十六国北魏至隋诗文研究文献”,原来只有三节的内容,扩展为九节,为研究北朝文学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史料;增订版第二章南朝部分,将初版的“宫体诗赋研究”扩展为“梁代前期”与“梁代后期及陈代”文学研究两节。 增订版下编重要的变化,是对第三章《文心雕龙》研究增加了“《文心雕龙》论著举要”一节。 这只是从大的结构上来说的,具体到每一部分而言,也有很大变化。 例如,在初版第四章第二节的“其他史籍”部分,增订版新补充、整合为鱼豢《三国典略》《九家旧晋书辑本》与《蛮书》、许嵩《建康实录》与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其他地方文献、中古佛教传记等内容。这些看似属于“史”的文献,却是当时文人生活、交流以及“文学”存在、发展的重要语境,是研究中古文学文献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
其次,问题意识更强,指导意义更大。 从初版开始撰写以来的三十多年中, 世界和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在史料发现与生产、文献搜集技术和整理方式、文献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等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刘先生《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产生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初版在出版不久,很快再版,成为文献学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目。 主要的原因是:该书既具有丰富的史料,又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同时兼具资料价值和论文选题指导意义。 这在二十世纪前后文学研究方法较为短缺、 文学资料较为匮乏的时代,无疑更显其学术价值之重要。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研究方法更加多元、文学史料更加丰富,如何开展全新的文学文献研究,就成为新时期学人思考的课题。 增订版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梁代以及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周、隋代文学方面, 该书在史料补充背后蕴含的很多课题都引而不发, 无不具有进一步作为选题深入研究的空间。这不仅将对初学者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长期从事中古文学文献研究的学者, 也有很大启发。 例如,十六国文学文献,或者有三十年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的原因,初版对此涉及不多。增订版补充了大量十六国时期的史料, 如萧方等 《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常璩《蜀李书》与《华阳国志》等史料,这些不仅是史学研究者关注的书目,也是文学研究者考察十六国北朝与中原文学交流、发展、变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借助这些史料开展文学文献研究,则是我们进一步着力推进的方向。 再如,增订版对河西走廊和五凉史料的介绍, 也为推进这个地域的文学文献研究提供了新思考。 以往较少被关注的隋代文学,在增订版中给予了详细介绍。尤其是“《隋书·文学传》所录文人”“《隋书·儒林传序》所录学者”“《隋书》单独列传文人”,既是研究隋代文学的宝贵史料,又开拓了隋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其中蕴含的文人及其文学活动、文学成绩,甚至隋代学术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都是值得深入开掘的课题。可以说,增订版提供的十六国北朝、隋代文学史料,为开展中古文学文献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必将成为中古文学文献研究新的增长点。
最后,文献搜集与补充更加全面,编纂方法更加合理。增订版对文献的搜集、补充更加全面、翔实,极大丰富、 拓展了中古文学文献学的文献形态与史料空间。例如,初版中编第三章第二节“北朝三书”为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颜延之《颜氏家训》,增订版将郦道元《水经注》调整为“第四节北魏诗文研究文献”,在第六节“东魏北齐三书”中除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颜延之《颜氏家训》外,又增加贾思勰《齐民要术》,这是合理的。《齐民要术》所引用的古籍有二百种之多, 对了解北魏以前古书保存与流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很有必要将 《齐民要术》纳入中古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视野。 再如,中编第三章第八节“庾信、王褒及其他”关于“庾集的流传与版本”,在初版千字左右的基础上,增订版补充了《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收录的六种《庾信集》,并有详细的介绍,更为全面、翔实。
从文献性质上说,与《庾信集》相比,《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齐民要术》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反而具有更多史部、子部性质。 但这些书目却是当时文人对“文章”认识的真实反映,也是后世所认识的“文学”生存的真实学术生态,增加这些文献,有利于对中古文学、历史的发展形成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增订版对“文学文献”的认识更符合历史事实,更有利于对中古文学文献的认识与研究。从学科性质上看,与“古典文献学”相比,“文学文献学”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更明确、清晰,学科意义更强。这对推进“文学文献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材料编纂方法上, 增订版并未采用以往简单的资料排列与分析的方法, 而是使用了带有一定研究视角的方法,总结、归纳相关史料。例如,增订版中编第三章第七节的“西魏、北周的文人群体”部分,作者在借助 《周书·庾信王褒传论》《北史·文苑传》《周书·儒林传》《北齐书·阳休之传》等文献对西魏、北周文学文献进行简要介绍之后,又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归纳、分析了“本土文人”“北齐遗民”“后梁文人”三个文人群体中著名文人的文学活动、 文学成绩与文献史料。 这种方法,既具有传统文献学史料搜集、整理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思维,使增订版更具学术深度和方法启示。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的出版,可以给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关于“文学文献学”的问题。 从学科分类上看,“古典文献学”一般被划入中国语言文学,与之对应的“历史文献学”则被划入历史学。事实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二者有时候界限并非如此分明。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在学习、研究、使用文献上,范围往往更加宽泛,除了文学类文献,传统的经、史、子部文献也经常被纳入文学文献研究者视野。 这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存在与发展的事实。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是后世产生的概念;而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如果要更加立体、客观认识这些“文学”问题,就必须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诸如经、史、子部,以及各种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诸如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都纳入研究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文献学”的提法,一方面更符合学科分类的称呼,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其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这是《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提出的新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二,关于“文献”与“理论”的问题。“文献”当然是原原本本的文本史料,但“文献”并不排斥“理论”,相反,“文献”中蕴含的“理论”命题,一方面可以成为研究者很好的研究选题, 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文献研究提出了“方法”的指导。 增订版中既有大量的文学文献,也蕴含着中国古代传统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例如,该书涉及很多传统的文字、音韵、版本、目录、校勘等理论,也涉及很多古书成书时代与作者考证、作品辨伪等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文献研究”往往被认为是枯燥、呆板的工作,“文献研究者”也往往被误解为不懂理论、不够变通。 事实上,经过文献学训练之后的研究者,往往更懂得理论的价值,也往往更擅长从一字之考证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命题。所以,“文献”并非简单的数据,而是“理论”与“方法”产生的前提。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学术传统。 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卷十指出,姚鼐论学“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词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主要是从方法论上说的,谈的是做文章、做学问的路径、方法,并不是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全部内容,并且后来桐城派在这个“义法”的认识上是有区别的。 但这个提法,也有它的合理性,并且成为当时及后来文人追求的最高学术目标。 我们今天研究文学文献学, 当然不能囿于桐城派提出的这个概念,但“义理”与“考据”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中国学术贵在传承,中国学人自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学人通过自觉的读书治学,始终贯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例如,在《王文成公全集》中,王阳明弟子们将阳明学说的思想渊源直接追溯至孔子, 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顽强、旺盛生命力的独特认识。 王畿称“凡待言而传者,皆下学也”,又称王阳明之学“虽入道之玄诠,亦下学事”[1],直接与孔子“下学而上达”联系起来。而邹守益又指出,“阳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统,历艰履险,磨瑕去垢,独揭良知”[2],是为了延续一种“学统”,恢复、维护儒家的“皜皜肫肫之学”。 “醇儒”是他们的学术理想,也是一种政治理想。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一书,其实也在继承、延续着中国古代学术的优秀传统, 其蕴含的学术道理、 学术精神、学术传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金开诚主编的《中古文献研究丛书》总序指出,三十年前,学界围绕“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证,在达成明确共识之后,提出了“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的观点, 并揭示 “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中, 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了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这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的二十大又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化建设目标,同时指出,要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三十年后,在同样的文化需要、同样的学术背景下,新时代对中国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 更新的要求。 增订版恰逢其时,一定会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影响力,推进中古文学文献的研究进程,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三十年来,国家、社会、学人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共同要求,充分说明一个道理:研究方法或有代变,学术观点或有更新,但文献永不过时。这也就是刘跃进先生所说的:“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史料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