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
郑天祥 王克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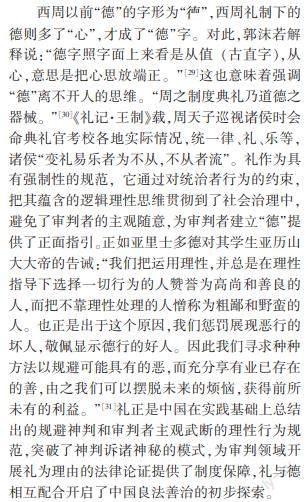
摘要:神判的思维是原始思维的研究对象,具有“神秘思维”和“原逻辑”特征,虽与当代法律理性相去弥远,却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社会。中国是世界神判史上的例外,快速进入了法律逻辑思维阶段。这得益于中国古代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一方面,礼的出现为中国在“绝地天通”变革中摆脱神的枷锁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大前提,启迪了理性的运用;另一方面,礼代替“神启”成为审判理由,为推进逻辑发展提供了反思思维的实践资料。以周公制礼为标志,尊重法律以及充足理由的法律逻辑规律终被掌握,使中国率先步入了法律逻辑的思维阶段。廓清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不仅可以完善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还可以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中国古代经验。
关键词:礼;神判;先秦;法律逻辑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041-007
盛于西周的礼不仅有伦理道德的内容,还包括法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法中发挥着精神和规范的双重价值。但是,关于先秦法律与逻辑关系的研究,学界仍多集中在成文法与逻辑的关系问题上,不仅鲜见关于礼与法律逻辑关系的探讨,而且常将法与逻辑的关系建立在礼制崩坏的基础上,似乎礼与逻辑没有关系,甚至阻碍了逻辑发展。逻辑史学家伍非百认为,邓析在郑国始创与古印度“因明”和古希腊“逻辑”齐名的“形名”,跟子产“铸刑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即郑国子产铸刑书颁布成文法的举措为审判提供了可援引的法律条文,一改礼制下“当官者以意断事”局面,“上可据‘刑书以断狱”,“下可据‘刑书以致讼”,促进了“辩”(逻辑)的产生。[1]主张形名学就是中国逻辑学、中国治学方法的郭湛波也认为,“礼的观念最先破坏,法治观念最先发生,所以形名学始于邓析,申、韩源于郑学”[2]。法律史学家武树臣在全面梳理法家法律文化中亦发现,名辩思潮与中国古代成文法的问世和成熟直接相关。[3]
逻辑学界和法学界对先秦成文法与逻辑关系的双向探讨,凸显了先秦法律与逻辑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交叉学科性质,对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这种以公布成文法与礼制冲突事件为中心的法与逻辑关系研究,容易使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处于尴尬的境地,导致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周公制礼”难以在逻辑理性中安放。事实上,先秦的礼并不与法律逻辑相悖。正如韦伯所强调的,从传统的、非理性法律向现代的、理性法律的演进是一个世界摆脱巫术控制的理性过程。当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视野走出法与礼之对立,转而投向更早的神权法时代,便可认识到正是礼制代替神判将中国法律思维带入了理性时代,而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正是认识该发生机制的关键。在中国走出神判的语境中,揭示先秦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完善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学科体系,补充礼与法律逻辑关系的内容,同时对正确认识中国法律理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中国率先走出神判
逻辑作为人类理性智慧的结晶,对法律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正如著名刑法学家B·H·庫德里亚夫采夫(B·H·Кудрявцев)强调的:“逻辑对于法学,特别是对于定罪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大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会像在法的领域那样,由于违背逻辑规律,造成不正确的推理,导致虚假的结论而引起如此重大的危害。”[4]但是在人类最初的定罪审判中,理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面对已经发生的案件,发现正义的责任常被寄托于神明,而非逻辑。
(一)普遍存在的神判
中国古代的“灋”字就表达了神判的含义。《说文解字》曰:“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廌”也称獬豸,相传是中国古代法官皋陶用来确定案件曲直的神兽,其角在审判时会触碰“不直”的一方,这是古代神判最具代表性的神话。所以,对于后世“灋”字中獬豸的消失,瞿同祖认为“与其说是神兽的绝迹,毋宁说是神判法的绝迹”[5]289。神判在世界各地曾被广泛使用,“沸水审判”“赤烙铁神判”“火焰神判”“冷水神判”“天平神判”“十字架神判”“吞食神判”“圣餐神判”“抽签神判”“尸棺神判”“誓言神判”“毒物神判”等各式神判方式,在人类的审判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这些通过“神”发现案件事实的做法,虽然能在心理上起到一定程度的威慑效果,但缺少理性。精通法律和宗教史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在其探究神判的专著《迷信与暴力》中指出:“被广泛采用的所谓神判,都可以归功于人类思想的这种趋势,充满疑问的人们一直都在尝试通过呼唤上天的协助,而使自己免于承担责任。即便这样做时,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中暗含的自鸣得意,而是自认出于完全的谦卑,将自己和自己的悲哀置于这伟大裁判者的脚下,这实质上是放弃了虽然有限却可以使用且并未被否认的理性。”[6]268
(二)神判的逻辑特征
神判的思维方式被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视为原始思维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如果单从表象的内涵来看,神判思维应当叫做“神秘的思维”。“原始人是生活在和行动在这样一些存在物和客体中间,他们除了具有我们也承认的那些属性外,还拥有神秘的能力。”[7]65面对案件,他们认为“这样一些存在物和客体”会有神秘的力量协助其进行裁判。列维-布留尔还指出,若以表象关联来看,神判思维等原始思维应被称为“原逻辑”,它不像逻辑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互渗律”才是其首先和主要服从的规律。“对原始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7]75,他们会把原因和前件混淆起来,从而错误地应用因果律。像獬豸等动物的角触碰诉讼一方、沸水对诉讼双方烫伤的程度、火对被告人的灼伤程度等与案件不相干的事件,都可能在神秘思维和互渗律的影响下作为裁判的依据,用于得出裁判结果。虽然列维-布留尔力图说明原始人的思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被当作儿童或精神病一样的思维进行研究,但人类无论是为了避免神判带来的火烧、沸水烫、冷水溺等酷刑的荼毒,还是出于对案件真相的追求,都是想通过理性的成长快速渡过神判时代,迎来理性的光辉。
(三)中国是神判的例外
亨利·查尔斯·李在神判研究中发现,神判这一“可能被看作一种人类进化途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能在最晚近的发展中被淘汰。然而……中国成了例外”[6]269。当然,无论是从獬豸神话,还是出土的大量商代的案件卜辞来看,中国神判的存在也无法被否认。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神判的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神判在中国的延续时间及其造成的后果都不能与西方的神判等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和马丁·莫内斯蒂埃(Martin Monestier)的《人类死刑大观》等众多著作,都展示了西方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的教会神法对世俗的荼毒。中国先秦虽然也经历了獬豸神判的时代,但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像西方常用的火刑等神判方式那样残酷,而且在时间上也没有像西方一样延续至中世纪,西周以来的中国古代判词就很少再见到类似西方的作为法定程序的神判。“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较其他民族为早,有史以来即已不见有神判法了。”[5]287所以,中国虽然符合普遍规律出现了神判,但快速地从神判的禁锢中挣脱了出来,由此中国被称为“神判的例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礼启迪裁判理性走出神判
系统反思中国作为个例早早地远离神判的干扰,对剖析中国人的法律理性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的无神论视角来看,我国率先走出神判得益于灌溉农业文明的发展。一方面,劳动力在当时农业生产和战争中的重要性为民众挑战神权统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生产需要探索自然规律,也有助于理性思维的萌发。然而,具体到审判实践,礼的出现则对我国率先走出神判具有重要意义。亨利·查尔斯·李认为中国能成为神判之例外,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道德的体系。[6]269同样,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马小红也认为“中国古人应该庆幸他们对‘神的明智态度,使他们避免了‘神的涂炭而享受到‘礼的温暖”[8]。礼义是道德伦理的内在精神,礼制(礼仪)是道德伦理的外在规范。礼与神判相对,起到了避免神判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功用,与它以人为中心是分不开的。神判是人将案件的审判权让给了神,人的理智在神判中得不到发挥,诉讼当事人得到的裁判结果是随机的。“等到人们能利用自己的智力来判断人的犯罪行为时,便不须神的裁判了。”[5]288而依靠礼进行裁判,则是运用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精神和规则,是人的智慧代替神发生作用的表现。所以,若要讨论逻辑思想是何时在法律实践中发生的,或法律逻辑思想是何时萌发的,从神判到人以礼审判的转变必然是最应被探讨的阶段。
(一)人代替神成为裁判主体
在中国,神判与人之理性的冲突首先表现在“绝地天通”的人神关系改革。“绝地天通”在《尚书·吕刑》有所记载,而春秋时期的楚国宗教思想家、大巫师观射父做了系统阐释。据《国语·楚语下》记载的观射父之分析可知,最初神与民的关系是“神民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即民与神有着明确的界限,民众有固定信仰的神,神明也会降临人间,男为觋,女为巫。这种情况下,民信仰神,神也有确定的人间代理,神判可以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方式并运行良好,起到维持社會秩序的作用。然而,神作为神秘的存在,无法像近代科学一样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来向其权威挑战者提供证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少皞氏衰落,九黎族乱政来临时,觋和巫的地位也就受到了挑战,出现了人人举行祭祀、家家自为巫史的局面。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人的理性已经开始怀疑神的统治,不再盲目相信神在人间代理的权威,而是认为自己也能够与神沟通。这种民与神的沟通显然也只能是徒劳,除了破坏原有的统治秩序,还会误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以,面对神与人的无序,统治者需要革新原有模式。
然而,“在此较强盛的初民部落中,甚至除神权政治外,不可能有别的统治形式”[9]。在新的统治规制建立起来前,神权仍是早期部落维持秩序需要使用的方式。所以,颛顼提出“绝地天通”的观念对神的统治进行变革,即切断平民与神的交流,结束“民神杂糅”的局面,将占卜与祭祀等与神交流的权力集中于统治阶层。这一方面能够继续发挥神权统治优势,有效避免民众参与占卜对神的权威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占卜这种不科学的方式对社会的误导。从思维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在这一发展阶段上仍旧用‘巫术的名称来表示所有的这些仪式,那就不得不把巫术分成所谓官方的和公开的巫术、民间的和合法的巫术以及秘密的和犯法的巫术。十分明显,最好不要用共同的术语来表现这些相互排斥的观念”[7]330。该阶段的神判已成为特定阶级从事的工作,民众仅是祭祀、占卜等仪式的观众,人的智慧或者说统治阶级的意志已经参与审判,审判不再单纯依靠神秘思维和互渗律作用。
(二)礼为理性裁判提供逻辑大前提
“绝地天通”改革后的神判,不仅有利于民众走出对神的崇拜为理性思考留下空间,更集中了一批专门的精英人士从事占卜工作。此时的“卜师是社会秩序的保卫者,他的职责是在于发现犯罪”[7]330。占卜师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同时,他们也会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利用好占卜等审判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此时审判虽然还有占卜等神判的仪式,但担任审判者的特定人的经验、情感、知识背景等因素已经参与审判过程,并且,由于神判形式赋予占卜者高度自主权,使得他们在神判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虽有皋陶使用獬豸进行神判的传说,但亦有“皋陶制五行”“皋陶造狱法律存”等传说,而且后者也更加符合皋陶被誉为“上古四圣”之一的历史地位,凸显了其智慧的运用。
如果断言此时占卜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利用司法权进行裁判,则又会走向极端,因为这些特定阶层的占卜者也有他们的使命,那就是合理解决争端、维护社会秩序。如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总结的,“这种纯粹的专制君主的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因为这些行为不遵循理性模式,而且不受文明规定的规则或政策的调整”[10]。但是,“历史上记载的大多数专制主义的形式,并不具有上述纯粹专制统治的一些极端特征,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惯例或阶级习惯一般还会受到专制主义君主的尊重,而且私人间的财产权与家庭关系通常也不会被扰乱”[10]。所以,此时的神判已经具有了现实的法的意味,法官个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互动已经在神判中发挥作用。
那么,具体是什么为占卜师的理性思维提供了类似当代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的前提,使得他们当时抛弃了对神的依赖,转而开始运用理性思考呢?“礼”无疑是该问题的合理答案。《周易·序卦》曰:“物畜然后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而泰然后安。”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风俗习惯的礼就会出现,履行礼的社会就会泰然安处。研究古代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的德国法学家赫尔佐克(Roman Herzog)针对统治者以礼等习惯法进行审判的实践指出:“历史上曾经,它们仅仅靠一套精心制定的习惯法法规去解决问题便已经觉得绰绰有余了。”[11]可见礼对审判的重要意义。《周易》“是对三代以上早期先民思维方式的理论总结”[12],《周易》对礼的重视,说明占卜时期古人就已经开始运用礼。理论上,占卜者在审判中也离不开礼。首先,礼作为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规范和农业社会的伦理共识,必然影响审判者,从而成为影响审判的因素。其次,礼来自长期生活积累的习惯,在长期的实践中自下而上形成,具有一定科学性和民主性。最后,当时民众在心理上广泛认同这些习惯,符合礼的裁判结果必然也更易于为诉讼当事人乃至社会接受,有利于维护审判的合理性。
(三)以礼裁判:裁判理性的启蒙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若言颛顼或皋陶时期的审判仍具有神话传说的成分,那么,有文字记载的殷商神权法时期之神判则为“绝地天通”改革后审判的模式提供了实证。“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商代审判案件一般采用卜或筮决定。《史记·龟策列传》曰:“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商代有专门的卜官负责烦琐的占卜工作,他们与商王共同构成了掌握国家政治、军事、司法权力的贞人团体。殷墟的大量卜辞表明,对罪犯定什么罪、处什么刑、处刑之后会引起什么后果,贞人都要在神前占卜。[13]43如:“辛酉卜,争,贞醢。”[14]意为贞人争问对某人处以醢刑是否可以。在司法制度的安排上,商王具有最高的审判权,“王占曰”的卜辞是审判中最高级别的裁判,虽然占卜不一定均由商王完成,但它们在以王的权力履行职责。对此,中国法律史学家胡留元和冯卓慧评价说:“神职人员贞人不过是商王的臣属,是商王借以欺骗人民的工具。”[13]44即神判已经成了裁判的外在仪式,真正推动裁判结果得出的正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的经验和意志。所以,张国华和马小红强调,从表面上看,这一发生于颛顼时期的传说与法(刑与礼)并无关系,但是推进神与人不杂糅的行动正体现了礼制的等级精神,“重、黎的传说,正是礼的实质”[15]129。
因此,无论是传说中的“绝地天通”变革后的神判,还是殷商时期的神判,均已与原始思维的神判有着明显区别,人类理性已经参与其中。所以,与其说商代是神判的时代,不如说是人主动利用神判的时代。人实际掌握了审判的权力,礼作为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已经为神判者运用理性提供了前提,为发挥理性维持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因而,礼的出现为中国古人摆脱神的枷锁、开启理性的智慧提供了机遇,让人有机会运用理性来治理社会。但商代的法律理性还处在礼启迪思维的萌芽状态,礼是否发挥作用、被运用还是被践踏,主要还在于统治阶级自己的抉择,缺少制度性的约束,商纣王的残暴酷刑显然就是统治者脱离礼和理性规约的表现。庆幸的是,礼启迪的理性同样也会发挥其功能反哺礼的发展,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下,不断推进制度的完善。
三、礼的制定:迈向法律逻辑思维阶段
正如新分析法学派首创人哈特(H.L.A.Hart)所指出的,“法律作为社会控制之方法的主要功能,并非是见于私人的诉讼或是刑事的追诉”,而是“在法院之外,法律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被用来控制、引导和计划我们的生活”。[16]礼在广阔的范围内充当着指引人们行动的理由,法官的审判只是其中之一。这种理由对逻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法律逻辑理由的礼
在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中,“理由”都是被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古代逻辑中,理由被称为“故”,《墨经》将“故”“理”“类”作为“立辞”的三要素,提出了“明故”“无故从有故”等论辩法则,并且区分了“小故”与“大故”,即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以评估论证。在古印度,“因明”是其逻辑学的核心成果,“‘因梵语为‘醯都(Hctu),含有理由、原因、知识之因的意思。‘明梵语称为‘费陀(Vidya),含义略当于汉语的‘学字”[17]。古印度将逻辑命名為“因明”更直接地表明了理由对逻辑的重要性。西方逻辑则有充足理由律[18],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中分析“故”时指出:“单用一个语句、一个论题把我们对于事物的判断表达出来还不够,充足理由律还要求我们把达到这样一个结论所根据的理由说出来,这样就容易避免主观的武断。”[19]即使是否认充足理由律是逻辑学基本规律的学者,也认为充足理由适用于论证。这对强调论证的法律领域而言,反而强化了充足理由律对法律逻辑的价值。
关于论证与法律实践,英格博格·普珀(Ingeborg Puppe)指出:“法律人的技艺,就是论证。越是能够驾驭得好这项技艺,就越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越能成为一名受尊敬的法官、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以及越能成为一个受到大家认同肯定的法学写作者。”[20]麦考密克(Neil MacComick)和魏因贝格尔(Ota Weinberger)也强调:“我们需要法律的技术人员……主要的就是进行正确的推理和有力的论证的技术。”[21]在我国至少可溯源至西周的审判史,理由也是古代法官关注的核心内容。法律史学家汪世荣在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指出,“理由部分作为判词的重点内容之一,可以说是判词的灵魂,是衡量判词质量的重要标准”[22],并强调当下判决理由部分的写作应当借鉴中国古代经验。
正是基于法学领域对论证的依赖和广泛实践,非形式逻辑先驱史蒂芬·图尔敏(Stephen E.Toulmin)确信:“如将逻辑作为广义法学,然后根据论证评价实践而非根据某个哲学家的理想来检验我们的想法,则会最终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的画面。”[23]“他(图尔敏——引者注)把传统逻辑重新解释成一种对思想过程和公开出具理由的规范性安排。”[24]在图尔敏基于法律论证实践构建起的论证模型中,理由与理由的支援构成了其论证六要素中的主要内容。同时,在理由与数据的比较中,图尔敏认为前者类似法庭上的法律问题,而后者则类似事实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作为理由的礼,实际充当了法律的功能,起到了链接数据与主张的作用。所以,在重视论证的法律领域,理由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充足理由律是法律逻辑不可或缺的基本规律;同时,裁判中运用礼,也为推动法律逻辑的发展不断积累着社会实践经验。
在原始思维的神判阶段,动物的行为等与案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件可以作为理由,为裁判结果的得出提供支持。这种放弃有限理性的做法,使裁判结果与神直接联系在一起,人的理性难以为理由提供支持。商代虽然还有卜筮存在,其理由实际上已经变成统治阶级的自由心证。在此,商代统治阶级借神判进行审判时,裁判结果的权威来源和理由已发生了分离:表现为法令形式的裁判结果其权威来自神的威严,即《礼记·曲礼》中所说的“敬鬼神畏法令”;但实际主导裁判结果的则是占卜者大脑里的理由,这种隐含的理由在神判中虽然为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秩序发挥着作用,但不会被明示,民众对裁判结果的认同依旧直接诉诸神的权威,而非来自裁判者对实际理由的阐释。也就是说,此时以礼为理由构成的法律论证已具有说服法官自己的效果,不再依据互渗律得出随机后果。根据新修辞学理论,商代法官已发现了“自我听众”(self-audience)。虽然这种以自我为听众的说理还缺乏普遍听众的理性限制,裁判结果还可以仅以单个语句的形式呈现,但此时以习惯法为理由的裁判已经有了法律逻辑思维的萌芽,一个以礼作为前提、以裁判结果为结论的可以说服法官自己的法律论证模式已经建立起来。
(二)从以礼裁判到法律逻辑思维阶段
“‘神权法就其形式而言是与法律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性相悖逆的。”[15]82在礼的启迪下,有理由的审判结果必然展现较神判不可预测结果的合理性。随着以礼为理由的审判实践不断开展,审判规律会被发现,主观武断的神判也将被抵制。“逻辑学的对象是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对思维形式进行研究、考察,也即是对思维进行思维,即黑格尔所谓‘反思。”[25]随着人们对以礼为前提的法律论证进行反思,先秦审判思维也就逐渐向逻辑思维阶段过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观察活动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从而逐步学会归纳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性东西。例如,春播秋收的生产活动年复一年地进行,长期的经验和观察就使人们认识到种子埋进土壤可以生根发芽,可以开花结果,一粒种子可以结出许多果实。这种客观变化及其规律逐步被认识和掌握,说明人的认识活动已从客观对象的直观表象认识上升到对对象内部因果本质的认识,也就从用直观把握对象的阶段过渡到了用思维把握对象的阶段,即过渡到逻辑思维阶段。[26]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远古到夏、商,礼经历了丰富的实践积累,周公制礼“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和规范化”,使之“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仪制)”[27]。“周公其人堪称中国法律史学的先驱和开拓者。”[15]4这说明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分析和综合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从对以礼裁判的个案直观表象认识上升到了对礼作为理由的因果本质的认识,掌握了礼的变化及其规律,并在建国之初就以法的形式将其确立了下来用于国家的治理。[28]所以,周公制礼是反思审判思维的结果,是中国步入法律逻辑思维阶段的标志。至此,中国通过礼摆脱了对神判的依赖,不再强调“敬鬼神畏法令”,不再借助占卜等神判形式,而是主张“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采用“议事以制”的形式,将审判权完全交给了人,开始强调人之“德”。
四、结 语
从中国率先走出神判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传统的“礼”具有重要的法律逻辑价值。夏商时期礼的萌发为人代替“神”成为审判主体提供了可以使用的逻辑“大前提”,启迪了裁判理性,开启了以礼裁判的理性思维,为走出神判积累了实践经验。西周早期“周公制礼”,主动通过制度完善来规避神判的原逻辑思维,体现了对以礼裁判的法律逻辑的反思,确立了尊重确定性法律和重视充足理由律的理性审判思维,使中国率先完成走出神判的任务,迈入法律逻辑思维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礼的重构,也进一步推进了成文法和法律逻辑的发展。因此,礼与法律逻辑是相待而生、相互促进的,礼的发生推动着法律逻辑思维的进步,而法律逻辑思维的进步也造就了礼的制度化和發展。中国率先走出神判展示的礼与法律逻辑的关系,一方面廓清了学界对礼与法律逻辑关系的误解,更加凸显了法律逻辑在法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提升我国法治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我国法律文化中悠久的法律逻辑传统,从而有力地驳斥了韦伯等人提出的“中国人未能理解逻辑的力量、中国法是‘实质非理性的典型”等观点,有助于增强我国法律文化的自信自强。
参考文献:
[1]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4.
[2]郭湛波.先秦辩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
[3]武树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43.
[4][苏]B·H·库德里亚夫采夫.定罪通论[M].李益前,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59.
[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美]亨利·查尔斯·李.迷信与暴力[M].X. Li,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27.
[9][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0.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44.
[11][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M].赵蓉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4-365.
[12]吴克峰.易学逻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4.
[13]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商承祚.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第14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328.
[15]李光灿,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一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16][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2版)[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7.
[17]虞愚.虞愚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34.
[18]陈波.逻辑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0-91.
[19]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M].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7.
[20][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前言[M].蔡圣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21][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31.
[22]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3.
[23][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M].谢小庆,王丽,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14.
[24][英]尼尔·麦考密克.修辞与法治:一种法律推理理论[M].程朝阳,孙光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
[25]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4.
[26]张世珊.辩证逻辑[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7.
[2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4.
[28] 陈金钊.认真对待明确的法律:兼论定义法治及其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50-68.
[2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36.
[30]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4.
[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颜一,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