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经典意识与“三言”的艺术品格
刘勇强
【关键词】话本小说 “三言”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经典价值 艺术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三言”是人们对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编《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话本小说集的通称。这三部小说集既收录了宋元话本小说(可能经过明人、包括冯梦龙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明人创作的作品。无论宋元旧篇,还是明人新作,“三言”的总体水平在当时就得到了很高评价,如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叙》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①从这样的角度看,“三言”不仅是冯梦龙所编辑的畅销书,也是他对话本小说作的一次经典化工作。在明刊“三言”前面,各有一序,尽管署名不一,一般认为都出自冯梦龙手笔。三篇序文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反映了冯梦龙话本小说经典意识的连续性与逻辑性。而他所作的编撰工作,则是其经典意识的体现与落实,这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典的筛选,二是对筛选或新创的作品作精加工,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经典。可以说,冯梦龙的经典意识与“三言”的艺术品格是密不可分的,是我们把握“三言”基本价值的关键所在。
对话本小说文体特点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
冯梦龙编辑“三言”,反映了他对话本小说文体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这首先表现在对小说的本质属性、也就是所谓虚构与真实性的论述上。
真实性一直是困扰中国古代小说家的一个问题,通常的思路是指出小说可以“羽翼信史”,具有“野史”的功能。这种依傍史官文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家的文体自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减轻主流文化对小说的歧视。关键在于,这样的说法没有揭示小说的真正的、独立的特点。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从话本小说发展的新高度出发,明确指出小说创作“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②,强调“触性性通,导情情出”之“理”,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之“真”,正是冯梦龙经典意识的核心。换言之,冯梦龙将真实性问题转化为小说对社会大众的艺术感染力问题,他在《古今小说叙》中甚至将话本小说的感染力置于儒家经典之上:

《警世通言叙》中还借《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对“里中儿”创其指而不呼痛的激励,形象地说明了小说巨大的感染力。
因此,在“三言”的编辑中,冯梦龙显然对那些能够激发读者共鸣的作品更为赞赏,如《范巨卿鸡黍死生交》描写了范巨卿与张元伯之间旷古难寻、流芳百世的友谊,除了进一步丰富这一传统题材的文化内涵外,作者更突出地渲染了他们为了信义打破时空束缚与生死界限的努力,将以死相殉的友谊表现得动人心弦,撼人心魄。在这篇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中,艺术真实是与艺术感染力互为前提的。
冯梦龙对小说文体的清醒认识与自觉把握,还表现在他对话本小说文体稳定性的贡献上。编辑“三言”时,他对话本小说的文体作了多方面的统一工作,原本适应现场表演的体制特点在“三言”中得到了整体性地继承与发扬。例如“入话”、“头回”的形式,在说话艺人表演时,除了能显示说话人的见识广博,衬托正话的内涵,同时还能起到静场的作用。对书面读物来说,后一种作用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小说家完全可以如同文言小说那样,直接进入“正话”的叙述。但话本小说的二元结构,确实有助于丰富接受者对小说的感悟,所以“三言”的很多作品都保留或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形式,如《范鳅儿双镜重圆》头回的“交互姻缘”故事,就很好的衬托了正话“双镜重圆”的故事。
同时,说话艺人表演现场的交流在话本小说文本中也转化为虚拟的对话。由于说话艺术现场表演时,叙述者与接受者同时在场,这必然使得二者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平等性、适时性,而叙述者会利用这种交流增强情节的感染力。在“三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拟想的交流,如《独孤生归途闹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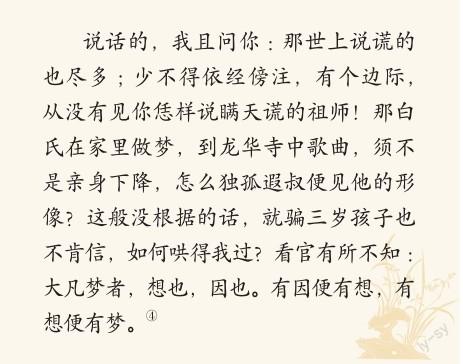
这里的对话就是小说家想象说话表演现象的情形而拟写出来的,意在解决接受者对小说真实性的疑惑,为小说叙述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拟话本”的概念,从“三言”的实际看,一方面确实保留了对说话艺术的模拟,另一方面,它们又不仅仅是模拟而已,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确立了更为成熟文体形态,小说家则驾轻就熟地运用这一文體表现新的时代生活,为话本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小说发展史中揭示话本小说的“通俗”意义
在《古今小说叙》中,冯梦龙简要地描述了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在此之前,像冯梦龙这样具有融汇古今、兼及文白的小说史观的人并不多。他认为明代小说“往往有远过宋人者”,因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⑤正是基于对“不通俗而能之乎”的意义判断,冯梦龙提出了话本小说“谐于里耳”“嘉惠里耳”的重要命题,这是其小说经典意识的一个出发点。
“通俗”有不同的表现与意义,首先是题材应为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所熟悉,接近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感情。作为经典作品,“三言”的时代特色极为鲜明,尤以直接反映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新风尚最为突出。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一篇现实性极强的优秀作品,它正面描写商人的婚姻生活,表现了商人从现实和人性出发的态度,突破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作品曲尽人情地刻画了王三巧的心理变化,她与陈大郎的私通,没有被作者简单斥为“淫”或不贞,而是将其作为现实生活中难以逆料却又自然而然的感情需要来表现。而作为丈夫的蒋兴哥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他在痛苦的自责中,原谅了妻子,同样显示出有别于礼教的新意识。
这样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性题材在以前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偶而有之,也没有得到细致、客观的表现,而在“三言”中却并不在少数。《卖油郎独占花魁》也是一篇正面表现商人生活的佳作,一个普通的小商贩,却充当了爱情故事的正面主人公,标志着商人以诚朴的形象走上了社会的大舞台;《施润泽滩阙遇友》则描写了一个小机户发家致富的经历,成为当时商品经济与手工业发展的印证;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虽然仍是宋元以来小说戏曲常见的妓女从良故事,结构上也无非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老套。但由于作者深入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尤其是突出地描写了杜十娘在绝望后的沉箱自尽,显示出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人格觉醒,使这篇作品超乎一般的爱情之上,折射出新的生活哲学与价值观念。
作为通俗文学,经典作品还应有适应大众欣赏习惯的艺术表现方式,其中语言的通俗化是至关紧要的一点。话本小说家们明白“话须通俗方传远”的道理(《范鳅儿双镜重圆》中即引用了这一套语),在白话文学语言的提练与运用方面,十分在意与在行。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这一番话将老鸨势利、粗鄙的口吻,表现得活灵活现。从白话的发展来看,明中后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而“三言”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同时期《西游记》《金瓶梅》等,共同构成了白话文学语言的里程碑。
努力寻求并夯实主流思想与世俗观念的平衡点
冯梦龙的经典意识还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在大力提倡通俗小说的同时,努力寻求并夯实通俗小说在主流思想与世俗观念之间的平衡点,从而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格与地位。
在《醒世恒言叙》中,冯梦龙总结了自己编辑“三言”这三部话本小说集的共同思想追求与审美意识,也就是所谓“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为了达到“触里耳而振恒心”的目的,他又提出了要使话本小说“为六经国史之辅”,这既是排除“淫谈亵语,取快一时”之类作品的道德底线,又是“导愚适俗”崇高目标的最高标准⑦。
“三言”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冯梦龙努力把上述主张落到了实处。《古今小说叙》特别提到“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⑧这个《玩江楼》很可能就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而冯梦龙显然不赞赏这篇小说的思想情趣与艺术格调,他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便在此基础上,对柳永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塑造。原作写柳永看上了歌妓周月仙,而周却恋着黄员外,不肯从柳。柳永便利用县宰的地位,吩咐舟人在渡船上强奸了周月仙,通过这一毒计得到了周。冯梦龙将此情节移到富人刘二员外身上,并加上批语“此条与《玩江楼记》所载不同,《玩江楼记》谓柳县宰欲通周月仙,使舟人用计,殊伤雅致,当以此说为正”⑨,同时,他还增加了柳永出八千身价,为周月仙除乐籍,让她与黄秀才团圆的情节,情节主线也相应地改为柳永与谢玉英的爱情故事。这种改写显然是为了维护“风流首领”柳永的形象。文字上,原作“谁家柔女胜嫦娥,行速香阶体态多”等“柳耆卿题美人诗”及其它浅薄之诗也被冯梦龙删除,随之增加了一些较为儒雅的诗词。经过这些修改,作品突出了柳永放浪形骸、纵情诗酒的精神品性,唾弃了原作与此不符的以占有、玩弄女性相夸耀的风流自赏,进而在才子遇与不遇、识与不识的反差中,抒写出失意文人的寂寞心理,并在“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的感慨中,表现了对世俗社会漠视、压抑人才的不满。
事实上,在“三言”与《清平山堂话本》同题材作品中,大多都有类似上面这样的不同程度的改造。《明悟禅师赶五戒》也是冯梦龙改动较大的一篇,作品弱化了原作五戒与红莲私通,终被师兄明悟点破的前世描写的比重,而突出了五戒与明悟转世投胎为苏轼、佛印后,佛印劝化苏轼归心向佛的内容,使世俗的趣味向文人的思理靠拢。
同时,增加劝惩意义也是寻求并夯实话本小说在主流思想与世俗观念之间平衡点的一个努力方向。如《错认尸》的结尾原来也有一点劝惩的意味,却放过了搬弄是非的王酒酒,《乔彦杰一妾破家》特别增加了一段,描写此人被乔俊鬼魂索命,并有眉批说:“少此项报应不得”,作者还借众人之口评论道:“乔俊虽然好色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惨祸,九泉之下,怎放得王青过!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⑩一方面描写“乔俊贪淫害一门”,另一方面又表现“王青毒害亦亡身”,两者相互补充,不仅使因果报应的描写更为彻底,劝惩的意义也更为全面、明确,其间追求的正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
至于一些明人新编的作品,更自觉得将新旧意识相结合,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叙述机户施润泽凭着诚实本份和辛苦经营发家致富的故事。他有幸两次掘藏,既是对他拾金不昧的一种道德化“奖赏”,又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图谋意外发财梦想的表现,二者在这篇小说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將面向大众的小说艺术追求发挥到极致
冯梦龙在编辑“三言”时,还表现出了鲜明的面向大众的小说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既是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结晶与升华,也有明代小说家新的艺术实践。
情节艺术是话本小说征服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诸如冲突的展开、悬念的设置、线索的贯穿、场景的安排等,无不与此有关。例如,《警世通言》中一篇《计押番金鳗产祸》可以说是话本小说情节艺术的一个范本。在这篇作品中,情节的进展几乎没有任何停顿,人物始终处于受命运摆布与对命运抗争的矛盾情势中。一个市民的女儿三次嫁人、两次离异,又曾与人私奔,围绕她的经历,先后有多人丧生,这构成了情节骇人听闻的主体,但作者却不只是矜奇尚异,徒然渲染情感与凶杀,相反,他更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女主人公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几乎遭遇了那个时代妇女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不幸,曲折的情节其实有赖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把握和高度概括。
二十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路,曾经导致了一个偏见,那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只重情节,缺乏对人物心理的深刻表现。但是,从“三言”的经典作品来看,冯梦龙是十分注重对心理描写的,极大地提高了人物刻画的深度,如前面提到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表现人物心理艺术手法方面,就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蒋兴哥与陈大郎在苏州的邂逅相遇,为小说增加了一个富于情感张力的空间背景,不仅使陈大郎得以吐露异地相思之情,也强化了蒋兴哥的反应。在外地得知妻子有外遇的事,空间的距离造成时间上的缓冲,使蒋兴哥的心理表现显然比在当地听说可能导致的骤然爆发要更有深度,人物内心的气恼、羞辱也因此表现得异常强烈。而小道具的运用也是作者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法,与它所依据的文言小说相比,《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增加了红纱汗巾和凤头簮子两个小物件,它们先是强化了蒋兴哥的愤怒,后又表现了王三巧的内疚,将人物不便明言,作者也难以复述的心理表现得真切动人。
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作者细致地描写施润泽捡到银子的情形,其中“拾起袖过”“把手攧一攧”“揣在兜肚里”等细节,生动地刻画出施润泽捡到银子后欣喜、私密的微妙心理,而他翻来覆去的盘算、推测,又将他思想斗争,具体地揭示出来。正是这种微妙心理与思想斗争,使施润泽作为一个小市民渴望发财又安守本份的朴实性格,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表现。
关于话本小说经典价值的当代性
文学经典从来就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虽然冯梦龙有对经典的自觉意识,也在相关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小说文本的经典化又是在接受与阐释中不断充实与更新的,因而有可能超越当时小说家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三言”同样显示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当代价值。
一般来说,经典作品应能揭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经验,而这种人生经验超越特定时空的性质,则是经典被不断接受与阐释的前提。实事求是地说,话本小说作为一种产生于市井社会、受商业化影响很深且面向大众的文学形式,并不热衷于进行富有哲理性的描写,因而对于所谓人生经验的提炼与表现,也往往以日常生活的得失为旨趣,当《错斩崔宁》这一题目昭示的社会批判意义,被冯梦龙改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时,“谨言慎行”的行为方式,便成为作者对读者的一个重要告诫。《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也都具有同样的意味特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三言”中的作品不具备哲理启示的可能性,由于一些话本小说是以文言小说为本事的,这就使得它在因袭文人创作的同时,还有可能继承甚至发挥了其中某种富有深度的人生思考。比如《薛录事鱼服证仙》来源于唐代传奇《续玄怪录》的《薛伟》,作品通过人的变形这种反常的形式,在精神与现实两个世界如梦如幻的交错中,表达了对社会与人生的独特认识。薛伟渴望自由却自陷危局,这一不自觉的背谬,构成了古代小说中少见的反讽描写。而精神与现实世界的不断闪回、重叠,也使作品触及了单纯的写实情节难以达到的思想深度。
不言而喻,经典的认定与阐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三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对有关作品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时,正是这种分歧,证明了经典作品丰富的内涵。《灌园叟晚逢仙女》叙灌园叟秋翁爱花成癖,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家中成为一个大花园。宦家子弟张委,发现秋翁家花枝艳丽,私闯乱采,秋翁加以阻止,张委就与众恶少将花园毁坏。秋翁对着残花悲哭,感动了花神,使落花都重返枝头。张委得知此事,買通官府,诬告秋翁为妖人,致使他被抓捕入狱,张委则霸占了秋翁的花园。正当张委得意之时,花神狂风大作,将张委和爪牙吹落进了粪窖而死。这篇作品当然描写了社会矛盾,但那种矛盾又带有传统文化的雅俗之争性质。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篇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秋翁遇仙记》,更突出的是其中表现社会矛盾的一面即所谓“阶级斗争”的一面。也就是说,作品的某一部分内涵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得到了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诠释和发挥。
事实上,具有被不断的再创造的潜力,也是经典作品的一个特点。《白娘子永镇雷锋塔》就是一篇始终处于演变中的作品。其原型可追溯到魏晋以来一些小说中有关蛇妖的描写,至“三言”,白蛇故事可以说已大为成熟。虽然这篇话本小说还残存着一些怪诞的描写,但作者又赋于了白娘子明显的人性特点,特别是女性的温柔多情,使小说的主题脱离了单纯志怪的范围,而具有了世俗爱情的色彩,至少现代读者更乐于把它看成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如果说在冯梦龙编撰“三言”时,由志怪到人情的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的话,那么,在后世的改编与传播中,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地发挥。且不说清代的《雷峰塔奇传》等戏曲小说对此一题材的推进;到了现代,由《白娘子永镇雷锋塔》定型的白蛇故事可以说是被改编最多的古代文学作品之一。从当代作家刘以鬯的《蛇》到李碧华的《青蛇》,再到不断翻拍的《新白娘子传奇》之类影视剧,随着社会意识与观念的改变,现代读者摆脱了古代通过蛇妖表现出来的性恐怖的观念,而对白娘子主动追求爱情的行为更为欣赏。有趣的是,刘以鬯据《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改编的《蛇》已收入《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雷达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典。这一事实表明,“三言”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古代文学遗产,它也以其经典文学的品格,参与着当代文化的建设。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冯梦龙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和多方面文化造谐的文学家,他编选“三言”,只是他诸多文化、文学编创活动中的一项,这也表明了他的话本小说经典意识实际上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如他在《叙山歌》中提出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著名观点,在“三言”中也有所体现。换言之,“三言”的经典价值,值得我们放到更宽广的背景下去认识与发掘。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释】
①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中册,第785页。
②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中册,第777页。
③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中册,第774页。
④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79页。
⑤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中册,第774页。
⑥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09页。
⑦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中册,第779-780页。
⑧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中册,第774页。
⑨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⑩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40页。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