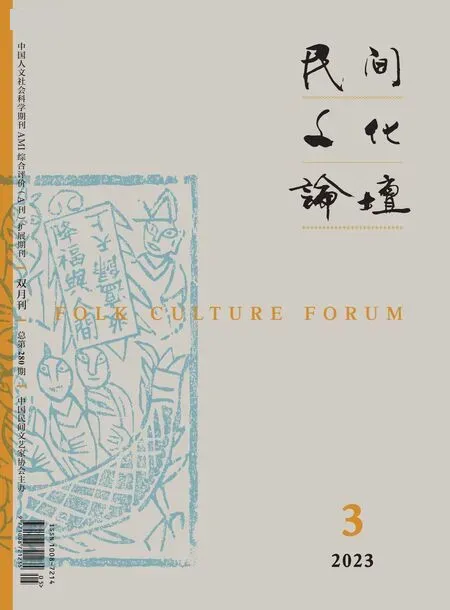人的历史比学科更长久
—— 岳永逸的燕京、辅仁民俗学史研究述评
刘晓春
1931 年初,在法国求学十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杨堃,偕夫人从巴黎乘坐火车,经柏林、莫斯科、西伯利亚返回北平(今北京),怀着对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满腔学术热情,立志在北平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无奈未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聘任,只好辗转任教于清华、燕京等高校,直至1947 年底受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之聘,出任云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8 年8 月,远在昆明的杨堃在上海出版的第六期《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一文,详尽地介绍了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时期、中山大学时期、杭州时期,以及中法汉学研究所、辅仁大学的民俗学研究,其中颇为深情地回望1938—1941 年间他在燕京大学指导的19 篇学士论文,予以特别推介,指出李慰祖的《四大门》、陈封雄的《死亡礼俗》(前八家村)、石堉壬的《性生活》(前八家村)、虞权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等几篇报告与此前的民俗学研究相比较,这些论文均采取“实际研究的方法”,也就是“采用民族学家调查原始公社的方法亲入农村,与农夫结为朋友,过着农夫们的生活。从自身的体验与观察之中以取得实际的资料。大部分的论文全是这样得来的实际的报告。文献的材料仅是供参考与比较而已”,①《杨堃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229 页。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及社会学界尚均未曾有过”,而且高度称誉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若与从前中大、杭州两处《民俗学丛书》相较恐亦是后来居上”。②同上,第230 页。
早在1936 年,在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创办、顾颉刚主编的《大众知识》创刊号发表的《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一文中,杨堃就已经阐明其民俗学理念,极为推崇这种亲身体验与观察获得材料的研究方法。在该文中,他辨析了folklore 的译名、民俗学的定义,介绍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关于民俗学的定义,他认为将folklore 译为“民俗学”是相较之下最为妥当的。民俗学是研究民众的知识或研究民众的科学,是一门活的科学,其内容“总是在不断的演变与不断的进展中”。他特别注意到法国民俗学家山狄沃(P. Saintyves,1870—1935)、汪继乃波(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中国民俗学家江绍原等人的“民俗学”定义,他认为山狄沃的民俗学定义最为中肯,因为指出了民间阶级为民俗学的主要目标:“民俗学是文明国家中的旧传及其法则之科学。但它的主要目标是在于民间阶级。”汪继乃波的民俗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特别以乡下人与乡村生活以及在工业与都市环境内所遗留的乡村生活之遗迹为对象的”,“在民俗学的各种定义中,这可算是一个较好的狭义的定义”。而江绍原则提议用“民学”代替“民俗学”。“‘民学’者,研究文化虽已升至较高的平面,然尚未普及于一切分子之社会其中‘民’阶级(及其所形成的更小群)之生活状况,法则,及其物质的经济的基础,观念形态,情感表现……及此等事实之来源,变迁,和影响者也。”
杨堃认为,自歌谣运动以来的民俗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取向。周作人的民俗学是趣味的、文学的,而非科学的;顾颉刚在民俗学上的贡献,“认真说来,亦全是史学的而不是民俗学的”,他所领导的民俗学,是“史学的民俗学”;江绍原从事的则是神话学派的民俗学研究,与弗雷泽相接近。不过,杨堃对于既往的民俗学研究评价不高,“我觉得已往的民俗学运动的失败,大半是在于未能深入民间,真正的与民间生活打成一片。”
鉴于以上定义和国内民俗学研究现状,杨堃从民俗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民俗学主张。
首先,民族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区别与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民族学/人类学与民俗学有各自的研究对象,野蛮社会的民俗学划归民族学(Ethnologie)或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范围,而民俗学则是研究各文明民族或历史民族的民间社会及其习俗的科学;他还补充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间社会”虽以乡村社会为主,但亦应包括都市社会的下层社会。二者的联系是民俗学采用民族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亲身研究野蛮社会的“局内观察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以此研究民间社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整个生活,并要注意到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不应再像旧日的民俗学者,仅研究民间生活的一方面,例如旧传,即算完事”。他还注意到作为生活文化的民俗与文字的关系,认为民俗学在采用“局内观察法”的同时,也需参考有关民间生活的各种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通俗读物。通俗读物不仅是史学的辅佐,而且是民俗学的直接的材料。
其次,他明确提出民俗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的观点,因而研究民俗学亦须要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英国人类学家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的《对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为他的这一理念提供了学理支持。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采用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情》一文所提出的原则和步骤。他还与吴文藻的“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这一说法进行了严肃的商榷。他认为前半句没错,后半句则有问题。在实地调查时,“须要将一切的理论完全暂时地抛开。要让事实自己呈现出一个解释来,绝不能勉强事实,逼迫事实,使它一定要去符合我们的理论。因为‘理论必须根据事实’,所以理论才是活的,是可以改变的。事实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如不能够改变事实,就只好去将就它,好让它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如何能勉强它去符合我们的理论呢?”
杨堃的民俗学主张,在今天已成常识。但颇为遗憾的是,杨堃予以高度评价的那19 篇燕京大学学士论文,连同这些论文的作者及其学术研究,随着时移世易,人事变迁,在后来的学术史中终致湮没无闻。由于历史与学缘的原因,民俗学史的书写,一直以文学的民俗学、历史学的民俗学为主流,而视社会学的民俗学为“支流”,同时忽略外籍人士的中国民俗研究。从2013 年发表《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堃博士旧文》开始,岳永逸积十年之功,系统梳理民国时期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他从学术“边缘”、小人物入手书写学术史,试图突破英雄史观和由果溯因的学术史写作模式,沉潜到民俗学史上被忽略的“边缘”“小人物”的学术世界,阐幽发微,还原学术前辈们的生命历史,知人论世,试图完善中国民俗学史的学术拼图,呈现中国民俗学的总体样貌。
folkways /礼俗/活的成训
通过重点研读20 世纪30—40 年代燕京大学43 篇毕业论文,加上另外42 篇有所涉猎的毕业论文,岳永逸认为这一时期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以杨堃、吴文藻、赵承信、黄石、黄迪为引领,是考现学与民俗学志的结合,追求科学、朝向当下,体现了民俗学的当下性、在野性、反抗性,实现了民俗学从史学、文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型,形成了以燕京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的民俗学”学派。
岳永逸的分析并未止于论文的内容,而是在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脉络以及中西学术交流的具体语境中考察那一段历史。他注意到,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引进的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William Sumner,1840—1910)的Folkways与晚清新史学之风俗观之间的暗合,以及留法归来的杨堃博士之“活的成训”的民俗学构想,共同形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早期传统中的社会学与民俗学的双重取向。在燕大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中,民俗学与社会学交互并存、互为依托、互相影响。
1927 年,社会学家孙本文出版的《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有一节介绍孙末楠的Folkways一书。1932年美国人文区位学大师派克(Robert Park,1864—1944)来华,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对孙末楠推崇备至。影响所致,1934 年,燕大社会学研究生黄迪的硕士毕业论文即以Folkways为对象,黄迪在论文中归纳总结了孙末楠所阐释的民俗的特征,诸如社会空间的普遍性、时间上的传统连续性、习得的无意识性、整体一致性以及社会控制性,等等。他还辨析了孙末楠反复使用的重要概念folkways(民风)、mores(德型)、institutions(制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民风即社会的民俗,那些为强有力的情操和信念所维护的民风,便成为德型,而德型中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为理性所认识和机构所执行的,便是制度。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德型、制度和民风的总和。
更重要的是,李安宅、吴文藻、黄迪、费孝通等人,他们都创造性地使用和发挥了孙末楠Folkways一书中的民风、德型和制度等概念,既用来重释“礼”等本土概念,也用来界定乡土、非物质文化、民族性,等等,影响深远。比如李安宅就认为,中国的“礼”好像包括“民风”“制度”“仪式”“政令”和“民仪”(mores)等等,“礼”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区区的“礼节”。①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3 页。从费孝通学术的两个主要领域“乡土”和“民族”中同样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孙末楠的影响,其中孙末楠关于in-group 和out-group 的区别,影响了费孝通对于民族认同意识之功能的认识。岳永逸认为,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继承了顾炎武的风俗观,邓实、张亮采、胡朴安等人的论述都强调风俗的“民族性”。这一观念的变化,虽然与孙末楠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孙末楠的民风、德型和制度三位一体、最终指向“民族性”的folkways 的学说暗合,异曲同工,而进化论则是二者共同的认识论基础。
岳永逸发现,孙末楠用于界定“民俗”的生活、需要、行为、心理、兴趣、动机、情感、满足、本能、个人、群体、习惯等概念,在燕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中被广泛运用于界定“风俗”“礼俗”,这些创造性的运用,明显区别于文学的、史学的民俗学,别出新意,但却被大多数民俗学史所忽略。受晚清现代性与外来学术的双重影响,基于“风俗”“礼俗”的重新解释,燕大师生在社区民俗的研究中强调平视平民、强调当下、强调过程与互动,可以称之为“礼俗学”。比如,邱雪莪在毕业论文《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吴文藻指导)中明确指出,“礼俗”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流行于民间,常常代表一个民族从古到今的平民思想。如此表述,与李安宅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所界定的中国的“礼”如出一辙。“中国的‘礼’既包括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关系的节文),又包括制度和态度。……‘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①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第5 页。
1937 年,杨堃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使该校民俗学研究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此前的燕大民俗学研究以“礼俗”为中心,试图运用欧美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社会学视野下的民俗学”,那么,随着杨堃的加盟,便脱胎换骨为“社会学的民俗学”,以“活的成训”为中心,实现了从对象到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自觉。
经过较为系统地消化吸收西方民俗学的理论之后,杨堃在1940 年第2 期《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了《民人学与民族学》一文,与1936 年发表的《民俗学与通俗读物》相比较,对于folklore 的译名、定义和对象,他已经有了更为清晰的学科自觉意识。
“民间成训”(la science de la tradition populaire)一词,可视作folklore 的法文译名。杨堃认为,无论是“民俗学”还是“民学”,都无法准确地反映“folklore”的内涵与外延。有鉴于此,他提出使用“民人学”取而代之。杨堃将“民人学”定义为一种综合的研究,分为遗留、成训与民间生活三说,颇为详尽地讨论了民间生活说,还阐明了民人学与民族学之关系,为民人学提出一个新的定义。其中英国的泰勒、安德鲁·朗、弗雷泽等人都持遗留说。法国学派则将民俗学定义为研究成训的科学。1931年,山狄沃提出“民人学是文明民族内并特别是民间阶级内,成训与成训的法则之科学”。持民间生活说的学者则研究民间或民人之生活。山狄沃认为民人学是“文明社会内民间生活之科学”。虽然他始终认为民人学的观点仍旧是成训的观点,然而他已将民人学的领域大为推广。最后,杨堃指出遗留说和成训说都失之过狭,这已成现代学者一致的公论。
他认为以上唯有民间生活说可以采用,不过也有几点需一一辨明。
(1)民人学是否以民间的整个生活为对象?英国学者大半相信民人学是仅以一人的精神生活或心理生活为对象,而不过问其物质的或技术的一方面,比如班尼女士。但德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德文Volkskunde 的习惯用法,即是以民间的整个生活为对象,连民人的物质生活亦包括在内。汪继乃波1924年出版的《民人学》已将民间的一切制度,不论是心理的或技术的,只要是“民间的”就全划归民人学的领域了。但英国的民人学也逐渐扩大到与大陆各国相一致。民人的经济生活也属于民人学研究的对象。
(2)民人学是否仅以文明社会的民人为研究对象?班尼认为,无论是野蛮的或文明的,我们全能发现出古老的信仰、古老的风俗与古老的传说来。民人之科学的研究,便是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将这些传统的东西加以正确的观察及归纳的推论。法国的汪继乃波、山狄沃,仅以文明社会的民人为对象。法国的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则认为野蛮社会也是民人学的研究对象。最能代表民人生活与民人文化的,乃是乡村而不是都市。民人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文明民族的民间社会及其文化。
至于民人学与民族学的关系,法国的汪继乃波、莫斯、山狄沃等学者都认为民人学是民族学的一部分。而杨堃对二者的关系却另有看法,一是民人的生活,从许多方面看,都与野蛮民族的生活极相类似,两者的心理表现与文化形态,亦极多相类之处;二是民人学家要借助民族学的方法,民人学者之所以失败,全是由于工具的不完备。
在此基础上,杨堃将“民人学”定义为:用民族学的观点与方法,以文明社会之民人及其文化为对象的科学。其中的核心概念是“活的成训”。何谓“活的成训”?岳永逸概括为在一个社区,或人群中——农民与都市下层社会——正在践行的有着历史性的活态的生活文化,即“活的成训”。①岳永逸:《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373 页。这种活态的群体性文化还支配、规训个体的身心、生命历程、日常生产生活,形成了群体共享的心性和惯习。
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杨堃的“民人学”主张指导下的学术实践。这些论文采用民族学的局内观察法,在功能论、社会均衡论的整体观观照下,以“民”为中心,呈现社区的整体社会事实。岳永逸称这些文本是“以民为主体,对民的生活世界、文化与心性带有暖意的叙写——热描”。②同上,第564 页。比如在邢炳南的笔下,平郊村的农具内在于村落社会之中,既具有服务生产、扩大经济生活范围、表现阶层分化的经济功能,也具有促进邻里和谐、服务婚丧、建筑、娱乐的社会功能,同时有制作、使用、修理等知识与技术传承的教育功能,还具有指向五谷丰登、祈求丰年的信仰功能。农具不再是静物,而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具有不同功能、意义、价值,被人们赋予不同社会生命的物质。围绕农具呈现的整体社会事实,可以看到群体性的文化模式、惯习和集体心性。岳永逸将这些文本命名为“民俗学志”,其特点是偏重于叙述,以近乎“裸写”的方式,叙述作为有机体、社会制度、整体社会事实的“民俗”,文本中鲜活的人及其俚语、俗说和故事,以及穿插其中的图片、表格,共同构成了一种超文类的“文本”,同时具有了趣味性、可读性、资料性、文学性和学术性。可以这样说,“社会学的民俗学”理念指导下的民俗学研究,是以“热描”的手法,整体性地叙写“活的成训”的民俗学志。
他者/土著
1936 年11 月,24 岁的比利时传教士司礼义(P. Serruys,1912—1999)在北京接受汉语训练之后,次年被教会派往山西大同,直至1943 年3 月被日本人逮捕,他一直在大同城南、桑干河畔的西册田一带传教,抗日战争结束重获自由后也在附近传教。出于对学术研究的“崇拜”,在近十年的光阴中,他对当地的语言、习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当地的婚俗、谜语、儿歌、民间故事、方言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岳永逸高度赞扬司礼义和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有关中国民俗的研究,认为他们“是传教士,是通常意义上的汉学家,更是对学术有着敬畏之心、将学术视为志业、严谨而勤勉的饱学之士;是‘由外入内’的自家人——土著,更是具有开创性而且成果卓著的中国民俗学家”③岳永逸:《土著之学:辅仁札记》,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 年,第20 页。。
岳永逸称司礼义、贺登崧为“中国民俗学家”,而且还是“‘由外入内’的自家人——土著”。我们既可将“中国民俗学家”广义地理解为研究中国民俗的民俗学家,也可以狭义地理解为中国国籍的民俗学家。此处不作讨论。随着岳永逸等学者的发掘和阐释,外籍学者的中国民俗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至于来自异域他乡的司礼义、贺登崧,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土著”的“中国民俗学家”,还是值得深究的。因为此处的“土著”,不仅仅是一个身份概念,更是一个学术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身份认同看。书写异域他乡,是人类学家的天职。人类学家困惑的,不是自己能不能研究他人,而是如何更切近地通过研究他人以反观自身,达成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人类学的洞察就是一种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本土/异域、自我/他者、中心/边缘,是人类学重要的观察视角。而民俗学,至少在其作为一门学问形成之初,在德国、芬兰、日本、中国等国家,是将本国境内普通民众口传身授的非文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并视之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阶级认同的重要工具。柳田国男将日本的民俗学命名为“一国民俗学”,钟敬文也提出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构想。在本国境内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一般称之为民俗学者,他们可以说是“土著”。对于异文化的他者而言,他们所从事的异文化社会研究,一般以民族志(ethnography)的写作获得人类学家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学术认同。至少在身份认同方面,他们应该是“他者”,而非“土著”。
其次,从民俗资料的采集途径看。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将民间传承之学分为生活外形、生活解说、生活意识三大类。生活外形可以通过观察采集、或者旅行者的采集获得,一般称之为“土俗志”(ethnography),各国的民间传承(folklore)研究一般不包括这一类;生活解说则是可以通过访谈、观察的方式采集,是通过语言知识获得的材料,柳田称这一类材料是介于土俗志和民间传承论之间的“边贸市场”;而生活意识,则是精神世界的采集、同乡人的采集,除了少数例外,外国人是不可能进行这部分工作的。①[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序言”,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年,第5—6 页。他还按照自然的顺序进一步将民俗资料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可视的资料,第二部是音声的语言资料,第三部是通过最微妙的心意感觉的表达才能理解的部分。第一部是旅人之学,蜻蜓点水式的旅行者也可以进行采集;第二部是寄寓者之学;第三部是同乡人之学,包括俗信在内,这个只有同乡人才能理解。②[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第84—85 页。
柳田特别强调,乡土研究的根本和难点,在于把握我们作为旅行者或是外部的友人而无法确切把握的内容,也就是上述的“第三部”内容。比如“村民的内心活动,女性或是寡默者长年藏在心底并且指导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的那些东西,即便不是起居于同一屋檐下的家人,也至少要长期生活于同一氛围之中,才可能知其全貌,进而如实传达”③[日]柳田国男:《食物与心脏》,王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0 页。。他以民间文艺为例子,认为作者们的心意犹如倒映在水中的影子,表现在言语艺术之中。那些语言不同的异邦的旅人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的。言语中的独特滋味只有本民族的人才能品尝到。④[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第114 页。很多的土俗志,虽然专门记述了异民族的有形文化,特别是食、住、装饰、工具等,但如果仅仅通过眼睛做短期观察,也很容易被看作是浅薄的观察者,其原因在于他们都不通晓研究对象的语言,他们的耳朵仅仅是摆设。⑤同上,第29 页。民间传承可以调查到精密细微的心理现象,而土俗调查却只能得到概况见闻性的资料。⑥同上,第37 页。
因此,对于通过究明民间传承以解答现实疑问为目标的乡土生活研究而言,柳田先生认为第三部的“心意现象”才是其学问的目的。“因为调查方法上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调查最终是外国人力不能及的。”①[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第313 页。他将心意现象又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识”,即人的所知,第二类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生活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第三类是“生活目的”,即人生而为何的问题。也可以说第一类是“科学”(science),第二类是“艺术”(art)。这三类资料,都是每个人在无意识中都拥有的。“信仰”“神”“道德”等在许多人看来属于第三类的资料,柳田认为也只不过是知识。人们对于未来的推测预想及其后果的相关知识,他称之为“兆”“验”“应”,以及应对灾难采取的“咒”和最后的自我防卫手段“禁”,都是民间传承中的“知识”和“技术”部分。②同上,第319—328 页。其中的“禁”,因其“不为”,故难以为外乡人所看到、听到,更遑论理解其中的理由了。“非乡人自身不能研究的,其实也正是这一部分。”③同上,第328 页。
柳田从调查者感受、经验、理解世界的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感官心理过程,结合资料的获得途径,将民间传承的资料分为眼睛可观察到的视觉资料、口耳可获得的音声资料,以及当地人心意感觉表达的无形资料。前两者外乡人可以通过参与观察和口述访谈获得,而作为心意现象的无形资料,外乡人则难以获得。也就是说,民俗或者民间传承中的当地人心意感觉部分,既无法为外乡人所道,更无法为外乡人所理解也。在柳田看来,心意现象的无形资料部分,对于土著来说都是难点,更遑论作为异文化他者的调查者了,至少,因为他们难以理解这些现象,所以无法达致真实的认知和把握。
那么,作为异乡人的司礼义,又为何被称为“土著”学者呢?岳永逸发现,司礼义对于山西大同城南的婚俗、谜语、儿歌的研究,最初仅仅是将这些资料作为语言材料收集的,从未想过用之于日后的民俗研究。司礼义对当地方言和方音足够熟稔,能够运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他在论文中使用的童谣很少标注汉字,强调读音和方言必标注出音标,这种过度音声化的方言和民俗记录,遭到有些学者的委婉批评。如果说这些只是从技术上保证资料的土著特性,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位异乡人,是否可以达成对当地文化的土著般的理解和认知。岳永逸将司礼义和周作人的民间故事研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他们都发现“赤子之心”是作为“儿童文学”的民间故事所具有的共性和根性。不同的是,周作人更多的是引经据典予以论述,而司礼义则是在一个具体时空的方言语境中,从故事的日常交流讲述实践以及民俗资料本身,洞察到儿童故事与成人故事的不同。作为局外人的司礼义,因其主位视角,而有了对于他者文化的同情的理解和认知。
司礼义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理解和认知,在于他在具体的调查与研究中能够自觉地实现人类学者所说的主位、客位的换位思考和视界融合。其实,对于土著文化的理解,柳田也并非一个他者不可知论者,他只是强调其“难”,而非“不可为”。他提出的统一的世界民俗学的构想,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弥合土俗志的他者“有形”记述与folklore 的土著“无形”记述之间的裂痕。1931—1933 年间,柳田讲授其“乡土生活研究法”和“民间传承论”,1934 年、1935 年先后出版了《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在《民间传承论》中,他明确指出土俗志学坚持外部观察和民俗学局限于内部观察,都是不合时宜和轻率的①[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第36 页。,其言下之意是,无论是土俗志学还是民俗学,外部观察和内部观察都是两者兼有的方法论和观察视角,而不应拘泥执着于单一方法。
柳田这一思考,比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派克(Kenneth L. Pike,1912—2000)1954 年首次创用emic和etic 两个术语明确表示人类学的主位方法和客位方法②Kenneth L.Pike,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2nd edition, The Hague: Mouton,(1954,1955,1960), 1967.还要早20 年。柳田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虽然强调心意现象非本乡人无以调查,但并未像主位方法论者那样,特别强调思维能力和语言形式对于行为的决定作用,进而将土著思想范畴的理解与文化行为的可预言性等同起来③[美]帕梯·J·皮尔托、格丽特尔·H·皮尔托:《人类学中的主位和客位研究法》,胡燕子译,王庆仁校,《民族译丛》,1991 年第4 期。,而是按照采集者接近对象的自然顺序,将民俗分为衣食住行、社会组织、生计模式、祭祀等有形文化,口头传统等语言艺术,以及知识、生活技术、生活目的等心意现象。在柳田看来,语言与行为之间不仅仅有因果关系,还有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就是“物与名”④[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第89 页。的关系。柳田认识到,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语言与思维等无形的心意现象,以及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等,都是研究者需要考察的范畴。
学者更多地阐发柳田建构一国民俗学的民族性以及揭示其背后的殖民主义色彩⑤[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133—165 页;[日]福田亚细男:《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四》,王京译,鞠熙、廖珮帆整理,《民间文化论坛》,2017 年第1 期;刘晓春:《民俗与民族主义——民俗学的视角》,《学术研究》,2014 年第8 期。,而更少弘扬其通过推进殊俗志、进而刺激一国民俗学的发展,最终实现统一的比较民俗学的世界性。在他的愿景中,世界民俗学是一种广义的人类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要求土俗志学者更积极地搜集资料,还要与各国的folklore 的观点相当接近,才能实现这个目标。⑥[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第36 页。柳田的世界民俗学实际上是殊俗志与民俗学的融合,从方法论而言,也就是主位与客位的融合,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融合。由此观照司礼义等外国传教士在山西大同成就的卓越的地方文化叙写,与其说是“土著之学”,不如说是互为主体性基础上的文化洞察。
知往鉴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句话理解学科史,意味深长。
围绕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研究的人及其知识生产,是学科史既成的“历史事实”,而围绕这些人物、事功进行“考古发掘”生成的叙说,则是学科史不断生产的“历史真实”。学科史作为历史叙写的一种,之所以不断被发掘、阐发、言说、叙写,乃是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借古喻今或者知往鉴今。也就是克罗齐所说,“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⑦[意大利]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修订版),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5 页。。学科史也不例外。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认为历史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而且是综合统一,不是抽象同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克罗齐将博学的、冷漠的语文性历史⑧同上,第14 页。,温情的、忧郁的、思乡的、失望的、听天由命的、满怀信心的、快乐的形形色色的诗性历史①[意大利]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修订版),田时纲译,第18 页。,以及表现道德意志的演说性、实用性和倾向性历史②同上,第22—23 页。,等等,统称为“伪历史”。历史与这些“伪历史”的区别在于,历史是“活的历史”,是“当代史”,是“思想行动”③同上,第8 页。,是“精神行动”④同上,第9 页。。“精神”是历史的原则,只有从这一原则出发,才能理解历史思维的实际进程,“精神每时每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全部以前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含有其全部历史,历史又同精神一致。”⑤同上,第11 页。在历史叙写者强烈的自我主体性的烛照下,那些确实的资料在叙写者熔炉般的胸中变为真实,“语文学联合哲学”⑥同上,第12 页。,历史得以产生。
从历史叙写的角度看岳永逸的燕京、辅仁民俗学研究,同样具有其强烈的自我主体性。除了强调从“小人物”的角度叙写学术史之外,他还特别强调燕大民俗学研究的在野性、反抗性。岳永逸在此处阐发的“在野性”,也许受到日本民俗学的历史与学术理念的影响。在1958 年正式进入大学体制之前,日本民俗学被称为“在野之学”。这一时期一直是在柳田指导下,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之外进行研究的学问,强调亲身调查,认为学问要对社会有所贡献。⑦[日]福田亚细男:《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四》,王京译,鞠熙、廖珮帆整理,《民间文化论坛》,2017 年第1 期。这一说法后来往往与学院派民俗学相提并论,并且带有一定的批判性。有感于民俗学越来越学院化,日本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菅丰等都提倡重归“在野之学”。菅丰更提出“新在野之学”的构想,旨在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他定义的“在野之学”包括学问的民间性、田野现场的重要性、利民的实践性以及与权力、权威、学院派的对抗性。⑧陆薇薇:《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民俗研究》,2017 年第3 期。如果说柳田时期的“在野之学”只是代表一种学问的非体制化的状态、经世致用的目的以及资料获取的方式,那么,菅丰所定义的“在野之学”则有了重返之后浓厚的意识形态取向,坚持田野现场、抵制体制规训、反抗学术权威、强调经世致用,等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岳永逸特别引用了日本民俗学者岛村恭则的民俗学定义,意在借题阐发民俗学从起源之时就天然地对抗启蒙主义、霸权主义、主流与中心的学术追求。
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精神”,他认为辅仁的赵卫邦1942 年发表的《扶箕之起源及发展》,表面看来似乎是与时事无关,但如果置于20 世纪前半叶灾难深重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则可发现赵卫邦将扶箕视为人类共有且普遍之文化的观点,这种出于对事实本身尊重的实证主义态度,体现了民俗学固有的不随波逐流的“反抗性”、内发性、在野性、跨领域性和世界性的本质特征。而燕大李慰祖、陈永龄、权国英等人关于四大门宗教、庙宇宗教以及家庭宗教为主体的乡土宗教民俗学志,不是将这些乡土宗教定义为“迷信”,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强调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看到它们对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的积极、合理的一面。燕大毕业论文对空间(房舍、村庙、四合院)民俗、时间民俗(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化)和“心意”民俗(乡土宗教)的“热描”,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来的诸多民俗学志,其中的民俗不再是乡村建设需要提升、整改的目标,而是民众正在传承、享有甚或创造的生活文化。他认为这些研究皆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原因在于体现了作者们对人性的自省和张扬,在于作者们将诸多形形色色的个体视同最普遍意义上的、有着生命尊严的大写的人。而这种意义,正是关注日常的、在野的、世界性的民俗学应该有、必须有、已经有的底色。
多余的话
民俗学究竟是学院的,还是实践的?民俗究竟是琐碎日常,还是华彩乐章?时不时会被学者用不同的话语包装之后拿出来讨论,以表明各自的学术立场。如果从民俗学学术发展的历史看,这些辩论,只是学术的不同声音,并不能代表哪一种说法就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不过,如果我们认同民俗学的底色(我姑且理解为终极意义、终极追求)是通过日常生活关注有着生命尊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那么,无论是学院的还是实践的民俗学,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至于是关注琐碎日常的一地鸡毛,还是华彩乐章的宏大叙事,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普通人在其中是否存在?普通人是否有自己的表达?究竟是单一的叙事,还是互为主体性的叙事?因此,在充满误解和冲突的当代社会,对于司礼义等人的外乡人文化叙写,笔者更愿意发掘其超越“土著”之上的文化间相互理解的意义和价值。在普通人的生命尊严尚待尊重、普通人的主体性尚待高扬的时代,更值得民俗学者从李慰祖、陈永龄、权国英、赵卫邦等人的“热描”与“冷静”中,学习领悟他们基于实证的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共情。至于学科的争执,在人的生命尊严面前,终将黯淡失色,毫无意义。毕竟,人的历史比学科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