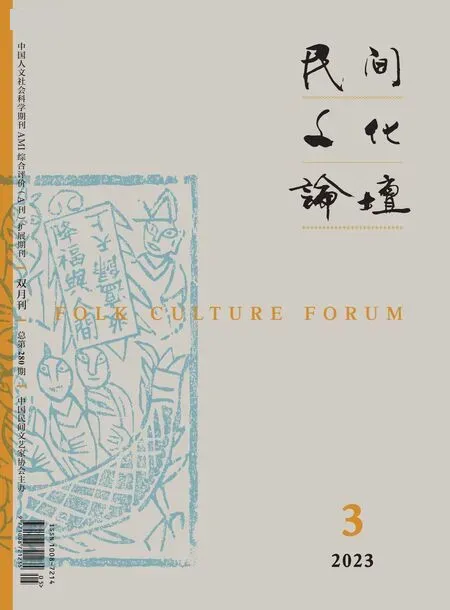抗战中和抗战后的成都学徒*
廖泰初 著 江璐、岳永逸 译
一
英文单词“apprentice”在中文中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学徒、生徒、徒弟;最常用的是门徒,则包含学习者和追随者两种含义;艺徒,通常指学习一种特殊技术的人;练习生、服务生,通常和表演性的服务业相关;招待员,是来自西方的词汇;师兄、师弟,通常是同辈学习者之间的称呼,他们视彼此为兄弟。所有的这些词汇都和“学生”完全不同。学生通常指的是,在其主要课程以尊重自己(respect for self)、尊重别人(respect for others)、对自己的行为负责(responsibility for all your actions)为基本原则,且极少动手的正规学校中的学生。
学徒又分为学手艺、学买卖的两种类别。①这里的学徒没有包括江湖艺人或者街头艺人学艺的情形。因为根深蒂固的良、贱两分的传统观念,学徒和学艺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但区别更明显。关于艺人学艺的具体情形,可参阅: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51—90 页);《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108—335 页)。——译注学手艺的,通常指学习某种特殊技艺的人,比如制作牙刷、制作银器、理发、修理钟表、修理自行车,或者做鞋。在以上情况中,人们会在作坊中学习某种明确的技术。学买卖的,或者学生意的,通常指那些学习如何做生意的人,即把货物从一些人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在门市,即柜里,学习规矩、写字、记账、礼仪和与做买卖相关的知识。
严格来说,学徒制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我们从食物采集、狩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的时代。然而,那时候的学徒总是被限制在独立的家庭之中,年长的男性成员始终是师傅,年轻的则是徒弟。教育在独立的小家庭里进行,经验也在此传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读书人的儿子还是一个读书人①即古语“士之子常为士”。——译注,一个砖匠(汉代的说法)的儿子仍是一个砖匠。在长时间的发展中,人们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摆脱祖先的职业。那时也没有劳动分工,学徒必须学会制造所有在家里用的器皿及工具。
随着人们定居下来,并且组合成一个类似于社区(community)的群体居住在一起,生产上的劳动分工就出现了。在唐代之后,学徒才走出家庭,并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定居。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类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制造篮筐、钉子、镐锄,或者织布制衣。那时,学徒制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原始社会的时代中出现了。
在过去的两千年间,中国一直保持着这种发展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她依然如此。在欧洲,工业革命导致学徒制的衰败。以大规模生产为业的大型商业公司和工厂逐渐兴起,最后催生出职业学校。然而,这一切显然没有影响到中国。此外,资本的集中是学徒制衰落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尽管外界在变化,中国仍依靠非常简单的工具保持其手工业生产。成千上万的人在生产我们如今称为“古董”的东西。工艺和技术都已经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且有着艺术品味。因为仍有许多类的手工艺品需要完成,学徒制度也依然运行着。机器传播至各处,然而中国的主要生产还是依靠手工。西方机器生产的日常用品的不断涌入,在战前导致一些沿岸小作坊倒闭,但绝对未能彻底摧毁这些小作坊。学徒制仍然完整健全地运行着。许多中国人仍以手工业为生。而且,尽管有着所谓的“经济入侵”,还在使用的大多数物品依旧是小作坊提供的。在上海、广州、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学徒。这些学徒机缘巧合地学会了一些英文单词,学过一些外国习俗,开始和西方商人接触。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的封锁政策成功阻止了许多物品进入中国。这就导致“自由中国”②指国统区。——译注中的学徒制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过去来自于国外的日常用品重新由小作坊生产,人们的热情越来越高涨,需求越来越旺盛。中国的小型工业经历了一个复苏的阶段。
成都,是以小型工业闻名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北京),并且是唯一一个在日本人侵略达到顶峰时还在中国人手里的城市。她接受了巨大的挑战,加快了生产规划——几乎为国内消费提供了所有的成品。因此,学徒的质量和数量都增加了。成品也在国内远近闻名,深受欢迎。
尽管没能获得关于中国学徒人数的相关统计数据,但我们认为这一定不是小数目。有人估计可能会有3000 万(占总人口的1/15)。在国内城市,甚至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是学徒,或者已经学完徒。在中国,没有优秀的技术学校或者职业院校,年轻人要么在田地里学习耕种,要么蜂拥至大城市、城镇或者乡镇,学习某个行当的知识。假设中国的总人口是5 亿。按照一般的人口分配来说,8-20 岁的年轻人至少会占到总人口的20%-30%,即1 亿到1.5 亿人。把2000 万的正规学校的学生(1942 年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是19015204,再加上61009 名所谓的职业学校学生)去除;这个年龄段里依然剩下8000 万到1 亿3000 万人。我们再假设这些年轻人中的3/4 在田地里学习耕种,那么依然剩下两千万到三千万的人在做学徒。
以成都为例。据估计1945 年在成都城内大约共有35000 个商铺和作坊(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在每一个店铺或者作坊内,不论它多小,都可能有至少一到三或四个学徒。较为保守地估计,成都城内可能有6 万(占据成都总人口的1/10)学徒。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一条很小的,名叫梨花街的街道上,总计有非常小的店铺和作坊53 个,学徒125 人。
过去20 年,国民党政府下的教育部把所有的时间和资源都花在了发展学校教育上,在1942 年一共惠及两千万年轻人,但却很少或者没有提到学徒。我们能够在政府宣传的各项法规和限制条例①在光绪二十九年,张伯熙在他的奏折中提到了管理学徒学校的规定——但这仍然只是一份奏折。中华民国成立后,有关学徒的简单工作规则被列入非官方的《商业汇编·中华民国最新商律》之中。[张伯熙,应为张百熙(1847—1907),清末大臣。1902 年1 月10 日,张百熙被朝廷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这里的奏折指的就是张百熙是年上奏的《钦定学堂章程》。——译注]中看到关于学徒的各种待遇,但实际上均未落实。同样,舆论在跟进这个问题上也是出奇的缓慢。经济部门会认为这是社会管理的问题,而社会事务部门又觉得这是社会教育的职责范围——都在互相踢皮球。在广义的教育观之下,我们就会为这种不可饶恕的忽视感到羞愧,也会为忽略人生如此重要的阶段而感到羞愧。一个生命对于我们战争中的经济是如此重要,而且无疑对我们的战后重建也同样重要。
在西式教育制度引入中国(1903 年)之后,我们旧式的教育体系已经退居幕后。然而,学徒制却岿然不动。
二、当前情况的分析
在1943—1945 年之间,我所教授的教育社会学(education sociology)班上的40 名学生,详细调查了成都城内的27 个学徒。这些学徒代表了15 个不同的行业。调查显示,27 人中有22 个属于勉强糊口的阶层,家里过得很艰难,仅能满足温饱。让人惊讶的是,27 人中的18 人都来自于成都附近的农村,最远的是灌县和金堂,分别距离成都城有53 公里和40 公里。他们的田地也少得可怜。18 个学徒中,15 个是贫穷的佃户。其余3 个,来自半佃户家庭,每家仅有数亩薄田。为了平衡家庭开支,这三家都得租种别人的土地。显然,这些人都不满足于自己的务农生活,更别指望他们能让后代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或者后半生都以农为业。对他们来说,孩子做学徒似乎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一条花费很少但却前程似锦的道路。这类父母把孩子送到城镇更像是出于一种赌博的心态,期待着有不同(更好)的事情发生。在27 个个案中,只有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其父在春熙路有一个很大的店铺。他的父亲对于现代教育非常没有信心,所以把儿子交给另一个店老板来照顾。②在此应该指出,交换儿子进行培养的做法被认为是明智之举,因为每个父亲都担心儿子在自己的照料下被宠坏。这种做法在北方更为常见。
成为一个学徒需要经过极为复杂的过程。首先,学徒必须和他想去的那个店铺或作坊的老板有关系,或者被社区的一位知名人士推荐,他的请求才会被考虑。有一个担保人能提供纸质的字据也很有必要,即担保人声明将为之后学徒可能出现的不良表现负全部的责任。接下来,就会由父亲确定认师或投师的日子,意味着学徒要被正式地介绍给师傅,并且要礼敬师傅。通常会有一场拜师宴,附近同行当店铺或作坊的老板都会参加,外加数位社区领袖和与这个店铺有关的成员。在一些地方,这个仪式会在学徒加入作坊后的3 个月举行。这是要确保经过了3 个月的观察和试验之后,师傅愿意接受这个学徒。在更早的时候,学徒还需要额外送给师傅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和几斤猪肉。这有点像学校的开学典礼。这天,学生要先叩拜孔夫子,然后叩拜自己的老师;学木工的会叩拜鲁班像;造纸行的叩拜蔡伦;染坊的叩拜葛仙翁;杀猪牛的屠夫叩拜桓侯;皮革行业叩拜孙膑;裁缝叩拜轩辕。这些神通常被视为各自行业的祖师爷或者庇护者。对这些祖先和神灵的尊重,通常以磕头的方式表达,或者是一个有许多蜡烛点缀的神圣仪式。①磕头不仅是拜师时的基本动作,也是传统中国常见的体态动作。对其文化意涵的释读,参见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302—346 页。——译注在那之后,学徒对师傅示以同样的尊重,这种情况被叫做“拜师傅”。在宴会期间,父亲通常会为儿子能被给予这样的机会表达深深谢意,并希望师傅能够用一切手段(包括惩罚的手段)来教育他的儿子,以此让他在未来某天能够独立。有时候会签“卖身契约”,这有些类似于奴隶契约。签下卖身契,师傅和老板会分掉所有的收益。卖身契会在所有相关人员的见证之下签署,声明如果有死亡、失踪、偷窃或者中断学习的情况,学徒的父亲,而非老板,将会为之负责并承担一切损失。显然,这个契约是极其鼓励与支持体罚的。在学徒被正式录用之后,引见是第二步。新人会被引见给其他成员,从师叔(和师傅同辈)、技师(技术员)、伙计(已经毕业的学徒),到师兄(和他同在店铺的同伴学徒)——有点像大学里的新生周。店铺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从属于一个明确的层级。学徒,则属于最低等级,需要听从他们所有人的指令。
从被认可的第一天起,学徒就开始了其人生的新篇章。早晨,他要比所有人都起得早,扫地、倒垃圾、擦干净每一个物件、生火、挑水,还有许多其他的杂事。根据店铺的性质及已有的人数,他的第一年学徒生涯可能在厨房里,或者在老板孩子的幼儿园里——和他期待的学做生意毫不相关。事实上,他就是店铺里的男仆。所有在他之上的成员都有资格差遣他。清理马桶、沏茶、洗衣服都是他另一种形式的任务。如果让他们,尤其是老板稍有不满,就会被打屁股、被踢,甚至被狠揍一顿。学徒晚上睡得很晚,比别人都晚,通常在十一点或者十二点之后。如果客人晚上要打麻将(在四川很常见),他就必须在桌旁侍奉,倒茶、点烟,只有在结束之后才能睡觉,有时候都快拂晓了。他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只能在能挪动的桌凳上铺开自己的被褥。第二天一早,他的铺盖就必须卷起来,放在看不到的角落里。他生活得就像前线的士兵,不是面对火力,而是不断受到惩罚的威胁。他学着如何受苦,如何经受艰难困苦,如何承受身体的折磨,如何忍耐。他也可以吃东西,只是要在其他人都吃过之后。盘子里剩下的东西——旧的、杂七杂八的剩菜,才是他的。难怪我们发现,大多数学徒都营养不良、缺觉、过度劳累,并且对生活毫无兴趣。②刘复教授的诗《学徒苦》对这第一阶段中学徒的生存条件描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发表在沈舟泥的《童工》一书中,在第1 页。[刘复(1891—1934),即刘半农。其《学徒苦》刊载于《新青年》1918 年第四卷第四号,第313—314 页。原文如下:“学徒苦!学徒进店为学行贾。主翁不授书算,但曰‘孺子当习勤苦!’朝命扫地开门,暮命卧地守户;暇当执炊,兼锄园圃!主妇有儿,曰——‘孺子为我抱抚。’呱呱儿啼,主妇震怒:拍案顿足,辱及学徒父母!自晨至午,东买酒浆,西买青菜豆腐,一日三餐,学徒待食进脯。客来奉茶,主翁惓时,命开烟铺!复令前门应主顾,后门洗缶涤壶!奔走终日不敢言苦!足底鞋穿,夜深含泪自補!主妇复惜油火,申申咒诅!食则残羹不饱,夏则无衣,冬衣败絮!腊月主人食糕,学徒操持臼杵!夏日主人剖瓜盛凉,学徒灶下烧煮!学徒虽无过,‘塌头’下如雨!学徒病,叱曰‘孺子敢贪惰?作诳语!’清清河流,鉴别发缕,学徒淘米河边,照见面色如土!学徒自念——‘生我者,亦父母!’”——译注]
所有规则都有例外。我们认识一个男孩是老板的近亲。因此,他受到了比一般学徒都更好的待遇。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学徒来自一个更好的环境,或者他知道和别人相处的技巧,或者和老板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他就有可能受到比大多数学徒好些的待遇。
在被收为徒弟后的第二年,学徒开始了他人生的新阶段。生意之外的工作逐渐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学习生意上的一些知识。例如,在面馆里学习如何和面,在中药店里学习如何研磨和切割药材,在铁匠铺里学习如何使用锤子,在杂货店里学习如何识别和摆放货物。但是,挨踢、挨打屁股就更频繁了,因为学习特殊的技能需要经验和技巧,而初学者必然会出错。观察和模仿是学习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学徒要先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再自己做。换句话说,他是在做中学。他在仔细观察师傅的做法之后自己动手,甚至细节也必须效仿。多数情况都不允许提问。整个学习过程不仅缺乏书面指导,甚至有时连口授也没有。在学习的第二年(其实是第一年),学徒只有机会处理几乎不需要技巧、只需要体力的事情,非常单调。他可能被要求把所有的事情准备好,再由师傅完成需要经验和技巧的部分。
就这样,一个学徒迎来了他学习生涯的第三年——对他来说是黄金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应该有机会从头到尾地完成一件作品。然而,一些理解能力不够、或者不受师傅待见的学徒,甚至都到不了这一年。杂货店里的学徒应该学着如何识别货物,如何分类,再以最优惠的价格拿下。他还要学习砍价的技巧、与顾客做生意的客套和规矩、账目的管理和结算,还有何时慷慨待客,又如何欺骗他们。在一个作坊里,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学徒可以学习他能观察到的东西,但是通常有一部分师傅会对所有外人保密。很多都是不可外泄的机密,诸如哪些不同的部分应该被组装起来,确切的数量,最后的润色等等。一个真诚的学徒不仅需要“偷师”,即通过不良的途径窃取这些技术,还要不断声明自己对师傅的坚不可摧的信任和忠心,以此来培养彼此的感情,期待师傅传授其所有的机密。在过去中国拳术的授徒中,师傅尤其会保留秘密。因为师傅如果把全部都教给徒弟,那就意味着自己终将被打败。然而,一个智力水平差的学徒永远不可能单独完成一件作品,不管他做了多长时间的学徒。①新近,北京青年作家常小琥的小说《收山》就生动地再现了北京勤行,尤其是烤鸭技艺在20 世纪后半叶的师徒传承错综复杂的情形。参见常小琥:《收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译注
学徒的毕业叫做“满师”,或者“出师”。根据常规情况来看,出师需要“三年零一节”(端午、中秋和春节这三大节)。但是,不同行当也有差异。在修表铺和中药铺里,出师可能需要5-6 年。不过,学徒的年龄也会有影响。如果七八岁就做了学徒,那他学习的时间就会更长。如果是18 岁或更大才学徒,时间就会限制在三年多一点。智力和勤奋也是影响出师年限的两个因素。如果一个学徒异常聪慧或者确实努力,时间就会适时缩短。根据我们研究的27 个案例,出师的平均年限是4 年零2 个月,最长的是6 年,最短的是3 年;学徒的平均年龄是15.48 岁,最大的23 岁,最小的7 岁。年龄上的极大差异,也会导致阅历、身体和心智发育的差别。
在长期的学徒生涯中,一个学徒每天工作12-14 个小时。他没有假期,除了五月初五和八月十五过节当天的半天,以及春节期间所有店铺都关门的那几天。在这几年之间,他一分钟也不允许离开他的工作,一步也不许踏出门口。除非他重要的家庭成员去世了,或者得了重病,否则不允许休假。他必须一天24 小时地工作(如在监狱)。这几年之间,老板会提供食宿,但没有分毫报酬。薪水制从来不适用于学徒。因为理发或者去公共浴室洗澡之类偶然的场合,老板也会发点钱。有时候,如果店铺效益很好,生意兴隆,学徒也能在过春节的时候得到一件新长袍或者一双新鞋。但是,这种情况实际很少,学徒不能抱有这样的期望。在饭馆的话,学徒可能会有客人给一点小费,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四川,不同工作阶层的人有一件事情很普及,叫作“打牙祭”,即可以在每月的初二和十六吃些猪肉。他们认为,一顿就可以补充营养了。
出师确实是从学徒期的解脱,也会迎来新的希望。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值得庆祝。在这些年的痛苦、艰难之后,学徒终于迎来了他期盼已久的自由。他现在可以自食其力、扬眉吐气、自由呼吸了。在出师之后,他马上就会收到一些工作邀请。这一点是很确定的。
依据父母或者亲戚的经济状况,学徒会确定在出师宴上邀请客人的人数。宴会则在出师那天的晚上。这也像一个发布会,告诉该行当的其他从业者,这里有一个已经掌握了行业技术的人正寻找一项满意的工作。当着所有来宾的面,学徒需要最后向他的师傅行一次礼——磕几个头,并且送师傅一套礼服,包括一顶帽子、一件长袍、一双鞋子和长袜。这一切是要向师傅表达感谢,感谢他的指导,也感谢他在这些年的责罚。在过去,作为回礼,师傅也应该送给学徒一套完整的工具(正如木匠行当那样),好让徒弟能够自己开一个小作坊,自食其力。在战争期间,我们从未遇到过师傅回礼的这种情况。
出师之后,学徒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师傅店铺里一段时间,领少量报酬(出于进一步的感激),但是地位完全改变。或者,他也可以被别的店铺雇为伙计或者艺正(可以领到正常薪水,享受所有福利的技师)。他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能够帮忙供养自己年长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了。“他终于能看到明朗的天空了。”而且,或迟或早,他能被提拔为栏柜、做客、吃份子、师傅、大司务,直到老板或者铺长。那时候就轮到他做师傅,选择和收徒了。这是我们研究中学徒们的最高愿望,10 个人里9 个都这样想。
有趣的是,大部分学徒也预先接受过一些学校的教育,在“私塾”(Chinese old-fashion schools)①“私塾”这是一个通称,译作“中国旧式学堂”亦无不可,它既包括当时的私塾、改良私塾,也包括清末在各地兴起而地方化的蒙养学堂、初等小学堂,尤其是私塾化的洋学堂等。对这些并存也是变化中的不同教育模式,廖泰初在《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尤其是该书的第一部分“汶上县的私塾组织”中,有深入的研究。——译注里读过两三年书。我们发现他们能够认识些报纸上的字,有的也能阅读几行。他们明白一个文盲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据我们的调查,27 个学徒的平均学校教育年限是2 年零7 个月。不过,中药店或者书店的里的学徒,在被录用之前无疑需要更久的学校教育。
三、学徒制长存的原因
这里详述三个突出的原因:
1. 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后不久,廉价的机造日用品就在中国四川地区泛滥起来,逐渐代替了那些在简陋条件下生产的手工产品。这无疑影响了手工技术。面对这种新状况,手工技术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幸运的是,外国商品的出现需要更多的人手进行销售。结果,那些因为进口货而失业的学徒,又因为这些商品的出现而重获工作。这类学徒没有停止学习,不过换了一个行业,学一些洋泾浜英语,加入许多买办商行。
2. 中国教育模式的一个主要的、公认的缺陷就是与现实生活的割裂。小学或者中学毕业之后(大约占据受学校教育学生的90%),学生没有学到足够的技术,可以让他们成为成功的商人、高水准的政客或者合格的农民。因此,他们变成了社区中游手好闲的人。这让其务实的父母非常失望,他们是卖掉粮食甚至土地去供孩子上学的。这种情况之下,不断的幻灭感为学徒制的重整铺平了道路。农民对他们原本的农业生活状态不满意,也对这些新学校不满意。
3. 尽管并不完美,目前的学徒制承担着为我们的工业和商业训练人才的重任,尽管中国的工商行业还很落后,但聊胜于无。在对中国私塾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学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孩子们之后进入学徒体系做准备,或者换句话说,提供一些“学徒前”课程,例如写字、记账、打算盘——每个准学徒都必需的基础知识。在中国,其他的事情看起来发展得很快,但是学徒制却没有衰落的迹象,它仍然发挥着作用。
四、教育的性质和类型
1. 学徒的首要行业准则就是学会在艰苦的环境里生存,忍受和经历苦难。这种想法来自于中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认知,意思是一个经受了最多痛苦的人,才能最终成为比别人强的人。因为中国人相信:这个世界绝不是一个幸福的世界;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面对各种磨难。只有那些经受过磨难的人才能幸存。这样来看,忍饥挨饿、过度劳累的学徒生活不会被看作是社会上的恶魔,而是一种训练的方式。
2. 对学徒的训练同样包括对生活的教育。学徒不仅要学习技术,更要学习一切的基础——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living)。这包含两件事情:处理日常细节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艺术。这两件事是体面生活的最基本要素。对在学徒工作时一直需要保持的体力劳动、完全顺从的态度和对谦逊的强调,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3. 生活教育也以一种实践的形式展现出来。学徒现在做的事情在他一生中要重复地做无数遍。所以,做学徒的过程不仅是为生活做准备:它就是生活本身。他现在做的事情将会用余下的一生去做。学习只能通过实践来完成。他学的不是通过符号的帮助来记住如何完成一件作品,而是通过实际动手来获得。不仅如此,师傅教的是师傅怎么做的,而学徒自己做的才是他学到的。学徒们是没有教科书的,甚至连口头指导也没有。学徒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旁边,观察、模仿和在不断试错中的做。
4. 个别教学(individ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是学徒制的另一特质。学徒们都是自己观察和学习,没有人与他竞争或者合作。其进步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学习意愿、体能和智力。就个人的问题和需求能够被关注到而言,个别教学是很好的。另一方面,学徒仅仅学到了一点能够让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的技术,却没有一点要为别人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群体精神是彻底不存在的。这充其量就是培养出了大量训练有素的个体,每一个都从事着某个特殊的行业,深耕于自己的领域,收获自己的成果。在其个人利益之外,不存在公民观念。
5. 惩罚是为了教育,但其本身也是教育。体罚给学徒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其有用的经历——他早晚会面对来自这个悲惨世界的各种痛苦。带徒弟时,几乎所有老板都认同这种哲理。当一个学徒被发现犯错时,没有人坐下来和他好好讨论,而是立马踢上一脚或打一巴掌。人们认为,这样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如果这种惩罚太过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导致一些学徒逃跑、受伤甚至自杀,也仅仅会被认为是为了生存的挣扎中的一场不幸和无法避免的意外。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的艰难让所有人都倾向于宿命论。区区一个小学徒的死亡,并不会被牢记多久。根据对《成都新民报》和《华西晚报》1945 年4 月1 日到8 月31 日(共153 天)的分析,仅成都这座城市就有124 个学徒逃跑或自杀。这些可怜的孩子被牺牲的情形可见一斑。然而,完全相同的情景正一天24 小时地在中国上演。
五、一个案例
李伯霖,21 岁。他是灌县(位于成都西北边53 公里的一个县)崇义铺人。母亲在他四岁时过世了,父亲是推独轮手推车的,属于仅能糊口的阶层。7 岁时,他在一个私塾里学习了半年,认识了些汉字,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就只学了很短的时间。之后,他立即开始讨生活了——自己选择去做一个小贩。在那样一个少不经事的年纪,他就开始分担供养家庭的担子。在之后的8 年之中,他一直是个小贩,从未提升,也未能找到其他工作。16 岁的时候(1940 年),政府征兵并将他派往前线。在江西、安徽、湖南、广西等地服役之后,他去年回来了,只想找到他深爱的父亲。因为年纪和天气,他父亲发生了很大变化,依然推独轮手推车,只能糊口,然而赚到的钱却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正因如此,伯霖想要做一个学徒,期待着某天能够赚到足够的钱,让父亲好好休息。
通过舅舅的推荐,伯霖在成都西门外的老荣盛酱园学习做一名掌缸师(制作酱、醋和腌菜的人)。
投师仪式是一个精彩的场面。在舅舅的帮助之下,伯霖准备了一席向师傅陈志三致敬的晚宴。老板、酱园的账房、行业里的其他优秀代表、那个地区的保长、甲长,都是这场宴会的宾客。在现场所有人的见证下,点上蜡烛,伯霖给师傅磕了头。随后,伯霖的父亲把他“交”给了师傅,意味着师傅不仅要教他做各种酱料,也要塑造他的性格,规范他的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采取所有的惩罚手段而言,师傅有绝对的自由。
伯霖已经在老荣盛酱园一年半了,盼着再有2 年就可以出师。目前,他刚刚能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么多大坛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在过去的18 个月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干活和做服务生的工作。一个刚被录用的新人接替了原本分配给他的工作。“我的麻烦是,”伯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小酱园里的‘老板’太多了。除了听师傅的,我还得听老板的、账房的、所有伙计的。我还得根据每个人的喜好跟他们处好关系。”但是,当他被问到觉得自己是一个工人还是一个学徒时,他保持沉默,并不断微笑。恐怕他的师傅也分不清。
至于学习的过程,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学习机会都必须自己主动争取。如果他没有任何学习欲望的话,他可能在这里待6 年,也完全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当问他学习的欲望从何而来的时候,他指着鞋子上的洞说,“甚至连它都张着嘴想吃饭了。”他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但是他从来不问自己做得是否正确。他的师傅,不知道怎么教学,没有任何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从来不“教”他。“他知道怎么把所有的酱做好,但是我觉得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教,教什么,”伯霖确定地说道。
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怎么做醋。他告诉我们,他的师傅对他不错,因为“我一直诚恳地干我的活,也听他所有的话”。确实,如果师傅对一个学徒的印象不好,甚至都不会给学徒观察和练习的机会。
最原始的醋的制作方式是这样的:
阴历5 月或6 月时,需要采集72 种植物。其中,蓼子草、过路黄是最重要的。每一种都被切成小片,按配额数量混在一起,放到阳光下晒。等完全晒干,和进一定比例的面粉、水之后,用模具将其分成药饼子。之后,将这些药饼子风干,一年后再混入一定比例的米粥。然后等10-20 天的时间,让这些东西充分融合。到那时,所有的东西都会沉淀在坛底。将这些东西拿出来,混入一定比例的麸糠,然后放进一个类似凹槽的东西里。一天翻两次,一个月之后把它们装进一个坛子里,在表面撒上一层盐,再将坛子密封。它被存放得越久(最好是在太阳底下),就越好。陈年老醋被认为是最好的。然而,完成所有流程的最短期限是一年。当需要过滤的时候,最先从过滤器中流出来的那些醋,称为头醋,是最好的。最后一步是加上各种不同的香料以产生味道。
伯霖只学会了制醋的流程。他对自己的技术很不自信,担心自己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步骤。除了制醋的常规流程之外,季节的变化、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都可能影响正在批量生产的醋的质量。事实上,这些最重要的点即使给他机会去观察,他也未必能观察到。如果他真的想要精通这个行业,在满师之后他至少还要在师傅身边待2—3 年。
一个好的掌缸师能够有光明的未来和理想的收入。他可能获得两个酱园的全职工作,或者自己开家酱园。这是伯霖期待的两个愿景。有如此光明的前景,伯霖愿意受苦、努力工作,为他的师傅做任何可能的事情。
六、结论
在对成都学徒的研究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进入到学徒体系的年轻人的数量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学徒制的发展史如此漫长且畅通无阻;战争对它的影响之大;我们的年轻人在努力获得某种务实的教育以谋生的过程中的生存环境之恶劣。
我们当前的教育只能培养出远离社会、不动手的特殊阶层。因为缺乏某个特别行业的相关技术,许多小学、中学的毕业生会失业。这给学徒制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佃农阶层十分不满意他们现在的生活,也不希望他们的后代满意。于是他们四处给小辈们制定计划。现代学校显然不是一个贫穷农民的儿子该去的地方。同时,既没有合适的工厂可以录用这些年轻人,也没有专门教人手工技能的职业学校。做学徒似乎是唯一开放的道路,尽管不完美,却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真实的机会。学徒教育可能不成体系、不科学、耗时,甚至有时会给年轻人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但它依然是最经济、最实际、最有益的一类教育,能够让一个普通人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
中国的手工业之前无疑是依靠学徒制来发展的,战争更加证明了其价值,因此它也被很多著名的领导者注意到了。1945 年7 月于成都举办的一场盛大的会议中,章元善①章元善(1892—1987),江苏苏州人。1915 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驻会常委,1945 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译注先生新近领导的手工业运动终达高潮, 60 位专家参加此次盛会。在长期讨论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并筹集了一定的资金来资助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会上,他们讨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1. 我们过去的生产资本非常小,是在无组织的、个人的努力之下完成的。华西协和大学1943 年的调查显示,一个小作坊的资金大约是5000 到10000 美金,意味着它们只能缓慢地适应先进的技术和模式,达不到国外消费品的标准,很少能在约定的时候按时交付。杨济川先生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师傅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只适用于本地的消费。四川生产的很多产品,例如,江安著名的竹制品、泸县美丽的雨伞、梁山的竹帘、荣昌的扇子、江津的陶器,都只能卖给四川人。“出口业”仅仅是一个术语而已。
2.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和手工业并不冲突。事实上,二者关系紧密,彼此依赖,相互助力。例如制瓷业和制衣业这两个行业,都需要十分成熟的手工工艺。而最先进的工业国,往往也有着最好的手工艺。
3.击败日本赢得抗战胜利,给了中国一个能够继续发展和推广手工艺的绝佳机会。中国过去的长久经验、艺术品位和廉价劳力,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优势。毫无疑问,这会发展出一个能够主导世界市场的独特的商业分支。
听到他们的讨论,我们非常满意,希望他们的设想某天能够实现。如果学徒制一直如此,那么中国的手工业就没有希望。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视角,培养我们年轻的技术工人和商人,以更好的合作与组织发展出更好的生产,从而迎接正在到来的机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