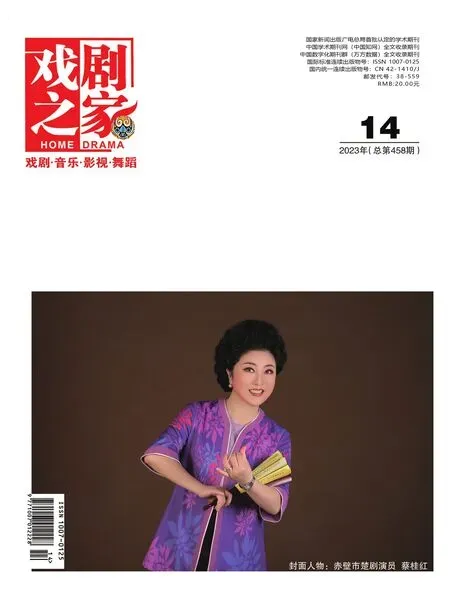论平民现实主义美学视阈下的人文观照
——以剧版《装台》为例
林纾朵,胡明贵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剧版《装台》由李少飞执导,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讲述了以主角刁大顺为首的“装台人”在台上工作以及台下生活中酸甜苦辣咸的故事。全剧以陕西西安城中村为点铺开,在陕西历史文化源流的影响下将人文关怀与传统艺术巧妙融合,在把握纪实性的同时又不失审美性,共情力与张力并存,“俗俗的人趣”和“风格化的追求”作为艺术立场,以“下苦人”的生活琐事一隅窥大时代发展下的社会众生相。
一、选取形象的圆形化和典范化
文学形象是由文学语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具体生活形象:人物、风景等的具体形象及其整体形象。
(一)人物圆形化
该剧的人物塑造多面立体,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大世界里的小人物个性鲜活,如主角刁大顺,人生不太顺,胆小怕事,懦弱隐忍,有着些许阿Q 式的妥协,面对各种无理要求时又“撅”了回去,“体现咱们农民工的尊严”。顺子认为有活干比什么都强,被算计自己咽,兄弟们平分工资,一视同仁,他吃苦耐劳且有侠义心肠;铁主任虽自私黑心,拿农民工的血汗钱买车撑面子,但在大雀儿走时也奔走筹款,为秦腔剧团费心费力,路过张家堡废旧礼堂时脱口而出的调调回忆起曾经的艺术理想;刁菊花缺失母爱,像一只刺猬,将自己和身边人刺得遍体鳞伤,从来不知道如何表达爱和去爱,与梅梅心存芥蒂却在得知她偷偷在山里结婚时掉下了眼泪,她逐渐学会了自我接纳,才发现其实她一直都被爱意裹挟着,是剧中与“装台”没有关联的“游离者”;八叔调戏女房客,复仇不成反被刁菊花划伤成了“疤叔”,看似不正经的他却是村中隐形的守护神,为观看剧团表演拉人,始终深爱着八婶;杨波是蔡素芬的学生,对蔡素芬有着近乎偏执扭曲的爱,害得顺子有家难成,逼走蔡素芬,却在最后主动退出他们的生活,帮助顺子找回了蔡素芬;装台的大雀儿,猴子,转转,墩墩,油饼等一伙人靠劳动赚钱,认为“装台也是艺术活”,坚持认为“搭台”和“装台”不同,维护着他们心中小小的艺术梦……
(二)景物典范化
刁大顺带着装台兄弟们四处拉活,走过陕北、陕南乃至最终进北京汇演,景物为剧情起到了很好的衔接作用和形象塑造作用,如大雀儿始终惦记着女儿丽丽想玩游乐场的旋转木马,而大雀儿在北京游乐场传回照片后彻底倒下了,与镜头背后熙攘欢乐的人群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乐景与哀情,为大雀儿的善与悲更添浓墨重彩的一笔。片头片中穿插的西安美食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也侧面向观众展现“陕味”风貌,裤带面,锅贴,麻酱凉皮,肉丸胡辣汤和腊牛肉夹馍……铁主任让“大家放开了咥”,恰是人间烟火抚凡心。刁大顺的三轮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以流动的视角将陕西美食、景色等尽收眼底,社会地理环境特色为全剧增添独特的人文色彩,剧情与现实密切互动,现实主义审美自然流露。秦腔团《人面桃花》北京汇演结束后,顺子在拆台时哼唱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引得众人落泪,暗喻大雀儿的离世。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具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1]。剧中采用戏中戏的形式一览人生百态,“别材”与“别趣”都做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二、表现语言的自指性和生动性
文学语言是一种具有多重含义和丰富表现力的语言。影视剧文学作为独特的文学文体形式,以代言体的方式讲述,同时,接受戏剧电影文学美学特征的影响与控制。
(一)自指性
文学语言的自指性是指文学语言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呈现自己的技巧、结构和特点,同时具有表意性的性质。剧中以对话为主,旁白为辅,带有地方特色的“陕普”生活气息浓厚,对“下苦人”这一群体的形象塑造提供侧面的非泛化描写。另外,巧用黑色幽默的手法为这一群体枯燥乏味的日常增添乐感,现实性得以显现,同时也体现了“苦中作乐”的无奈:如刁大顺与三皮为了追求爱情而进行竞争,镜头中二人走路回家各走各道却不忘相互追赶,始终与对方保持平齐。剧中多次采用类比、对比的手法,蝼蚁隐喻象征刁大顺的人生命运,从整体来看,将传统的文化赋予创新的形式;从角色来看,村口黑总手机不断响起的“支付宝到账一百万元”而顺子与兄弟们卖命赚钱却依然为生活发愁;从个人来看,刁大军由阔绰到落魄、以为能走出村庄兜兜转转仍囿于顺子的家,赌博与苦力挣钱的结局反差表明作者的审美立场。剧中墩墩和手枪在张家堡被追赶,在夜晚于破旧礼堂一个武,一个舞,极具荒诞性的组合是“下苦人”对现实的抗争:艺术,永远不败。
(二)生动性
文学语言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出具有生活形态的文学作品。文学语言由“代言体”的形式为情节发声:刁大军的离世与菊花的孩子三代的降生时间重合,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命得以不断延续,刁大军在生命的最后虽然物质匮乏,但他的精神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要富足——见到了他的初恋桃花,得到顺子的悉心照顾和大雀儿女儿丽丽的陪伴。浑身带刺的菊花在细腻体贴的二代的感化下,与之真正走到一起。刁大顺与铁主任是命运共同体,在老姚那拿到工钱,他不忘给铁主任好处,顺子从不亏欠弟兄们,他们也不亏待顺子——顺子犯痔疮在诊所治疗,兄弟们尽管被铁主任蒙骗去无偿磨砖,也不愿意让顺子操心。顺子活得明白,活得通透,懂得这人生就犹如一出戏,就像这装台的活,得互相帮衬。没有因为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2]。村中的“怪人”很多,有人上山修行,有人作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却把房子卖了,住在改装的小车里,有人认为“钱不是个东西”,家有煤矿却只想站在舞台中间唱秦腔,有人想靠彩票转运,有人愿意白天干装台晚上接私活……每个人都有对生活的选择,或许我们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平凡人生的真实映照,没有所谓的一鸣惊人、逆天改命,只有努力在自己的路途上活出别样的精彩。
三、创作价值的创造性和实现性
文学价值是指文学作品满足人们和社会需求的属性。它主要涉及知识、伦理与审美等价值,并且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整体。因为文学价值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所以本文将文学价值的创造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文学价值的创造和文学价值的实现。
(一)创造性
文学价值的生成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价值体现。剧版《装台》是植根于小说《装台》的再次创作,对其内容情节加以适度、合理修改,如将小说结局人物的“散”改为剧版结局的“聚”,实则是导演审美立场中人文观照的生动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国人对艺术作品传统的思维观念,用“乐感文化”营造“好人有好报”的主流思想氛围,为观众提供独特的精神力量并指导现实社会的实践。文学的价值植根于社会的价值,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3]。创作者通过对刁大顺等装台人为代表的底层人民工作、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行精细刻画,结合陕西特有的民俗风貌,真实展现了平民现实主义中的烟火与温情,将创作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赞美与尊敬全貌铺叙。
(二)实现性
文学作品的创造完成后,需要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人生阅历对作品所呈现的作者的审美价值做出自己的思考与抉择,从而完成文学价值的“二度创造”。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一点多面”的:“点”指的是所表达的中心思想点,“面”指的是通过多个维度进行创作。美食、陕普的地方特色通过“装台”这一冷门行业、劳动人民来表现,再将主角与配角间的矛盾、情感与之结合,让读者领略到了陕西的地域特色、劳动人民的质朴、秦腔文化的魅力以及对艺术生活的向往。此外,剧中各角色不论个性如何,其本质都回归于善,不论生活情况如何,都能够有一个大体圆满的结局。剧中流露出的平民现实主义美学中的烟火与温情和在劳动人民身上涌动的坚韧,是活生生的,是碾不碎的,读者通过自身的解读进行阅读接受,或更好地认识生活,使得文学作品的潜在价值得以显现。
四、审美意蕴的情感化和社会化
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更关注现实生活的真实状态和个体生命的人性建构[4]。以人为主体的思想转向丰富了创作者对本我精神的表露,因此审美意蕴的情感化和社会化的传递成为创作者和观众的双向探求。
(一)情感化
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观念,文学的审美特质不是对审美和观念的单纯补充,而是审美和社会生活在审美表达过程中的交织渗透。通过作品的形象与语言,再现或表现某种审美对象的品质、气质、精神,从而给大众以全新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5]。它直视当下,与时代、社会和人类命运密切相关,以复归性、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方式回应,体现了人们真实的生活面貌,触及生活的本质,人们共同的情感和对生存的态度。它触动人们的心灵和对现实主义的希望,也响应着崭新的关于平民结构化生活的现实主义思想和美学风范。文学作品通过影视化呈现,进行视听双层的直观形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为文艺创作的旨归。从这个层面来看,现实主义不是简单的关乎写实手法的艺术问题,而是一种依据“精神”“方法”与“视域”衍生出来的思维过程,是一种艺术对待现实社会的认知态度[6]。
(二)社会化
以对秦腔的传承关注为文化的基本精神面向,疏通中国古典与现代的血脉,在对现实生活的深沉书写中饱含对秦腔文化面临的与现代文化共存问题的呼号,其中依傍着人物鲜活的灵魂,也妥置着生活焦虑而无所适从的观众。除此之外,对于小世界中“众生相”的刻画,承载了中国古典文脉的要义:戏与人生。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7]。在陕地的文化视角下,展现了“下苦人”的苦难与希冀,冰冷现实与温情人性的斑斓图景。另外,鲜明的时代性也是赋予作品生命力的一大因素,21 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与20 世纪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大有不同,新写实主义以反映社会阴暗面与人性的卑琐为主调,从题材到作品的表现都带有厚重的拷问气息,现实主义在反思的同时带有轻快的活力,不是一味地控诉,而是在一地鸡毛里还能产生对生活的信心与力量,这正是社会中时代话语变迁转型的反映。
五、结语
剧版《装台》从小视角切入,用客观的审美刻画历史与现实、城镇与乡村的典型“小生活”,由秦腔的“小戏台”到人生的“大舞台”,是由中华民族所有劳动者一同创造出来的中国梦舞台。在生活琐事中寻找崇高,在悲欢离合中展现平凡生活的温暖与明亮。探寻人文观照的平民现实主义美学摒弃了对高、大、伟的英雄人物和对大喜大悲的传统叙事套路的雕刻,而选择采用低姿态的视角,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鸡毛蒜皮的小事,强调叙事的生活化来引起跨圈层的共鸣。电视剧将小说中较为严肃压抑的受难故事巧妙转化成底层小人物依靠奋斗姿态也能够拥抱美好新生活的故事,较完满地通过传播媒介的改变完成了对时代需要的主旋律文艺作品的改编创造,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突围。真诚、韧性、乐观,这是一部属于劳动人民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