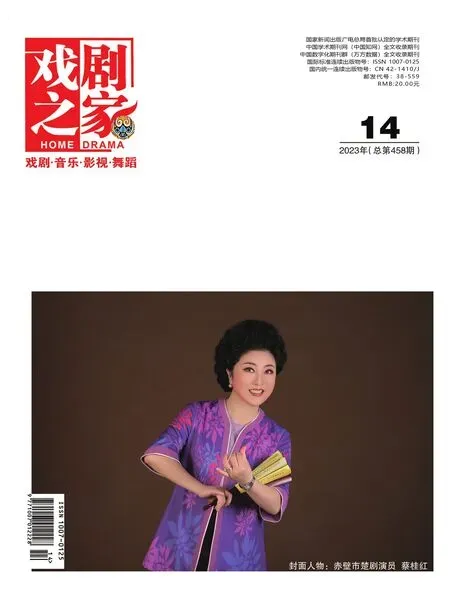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中“字”“声”“韵”的表达
张慧琴,李 琳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一、对作品谱面的研究分析
(一)旋律曲调
电视剧《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是骆玉笙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该曲目借鉴了传统京韵大鼓的韵律以及曲风,具备戏曲的风格,是著名的两栖唱段。
(二)伴奏
《重整河山待后生》借鉴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风格以及基础韵律,具备京韵大鼓的特点。其伴奏采取交响乐的形式,因此,聆听该曲目时,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传统的京味儿,也能体会到现代音乐的魅力。
(三)歌词
《重整河山待后生》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温中甲、雷蕾作曲,骆玉笙演唱。整首歌曲一共包含8 句唱词,共计48 个字,借鉴京韵大鼓传统的唱腔以及旋律进行作曲。与此同时,骆先生通过巧妙地运用高低腔转换技巧以及装饰音,起承转合,改变了原有曲调所存在的情感表达不浓等缺陷,使其情感渲染力十足。歌词如下:
千里刀光影 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 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 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 重整河山待后生
二、《重整河山待后生》“字”的表达
《重整河山待后生》使得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已然没落的传统音乐,尤其是说唱艺术。通俗而言,说唱艺术具备叙述性、声韵性、表演性三种特征。《重整河山待后生》旋律较为激愤、高亢、悲壮。它的说唱形式要求演唱者完备地体现其叙述性、声韵性以及表演性。因此,骆先生在演唱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字”的表达,以确保叙述性与声韵性的完备。
(一)“千里刀光影”
“千里刀光影”“以情带字”,骆玉笙以较高的音调奠定了整首曲目的感情基调,将听众带回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场景中。“仇恨燃九城”,通过叹唱,以愤恨的情感与语气表达出“仇”,重音唱“恨”,与“仇”结合,形成情感的高潮。在“良”字上作京味的延长,通过延长体现出京韵并且将情感逐渐舒缓,以此与京韵大鼓演唱特点一致,从“戏中”走向“戏外”,自由切换。
(二)“月圆之夜人不归”
“夜”字为高音,“人不归”为低音腔,低音使其呈现出一种余音袅绕的声韵效果。高音与低音之间的转化,表达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音调的转化体现出了情感的反差。“花香之地无和平”中“无”字借鉴了戏曲的“顿挫”唱法,“和”字为高音腔,高昂,“平”字为低音腔,高—低—高,音调的不断波动使得歌曲感染力较强,情感丰富。
(三)“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
“血”与“情”二字交相呼应,都隶属于中低音区域。骆玉笙行腔中通过对“血”“情”低音延展,将情感注入歌声中。骆先生的歌声缓缓讲述了作为母亲的心境,既表达了对于子孙仍要流血牺牲的痛惜遗憾,又表达了对于日本侵略者反抗到底的决心。
(四)“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去”是中心字,体现出了中国人民即使战死也要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精神。因此,骆先生斩钉截铁地演唱了“去”这个字。“重整河山待后生”是整段曲目的高潮,伟大的祖国需要后辈建设。“重整山河”中每个字都充满了骆先生的炽热情感,骆先生只将“山”字做了声腔的变化。“重整山河”每个字咬字清晰坚定,骆先生的吟唱伴随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后生”二字以低音强调结尾,浑厚有力,将对子孙后辈的殷切期望完全表达了出来。
现代民族唱法借鉴了美声艺术唱法,为了保持音色的统一,需要在同一种状态下唱出差异的字。骆先生采用传统唱法演唱该曲目,其演唱风格具备传统唱法特征,具有传统韵味。如“花香之地无和平”中“无”,音色偏暗沉、自然,而“和平”二字则与之相反,偏明亮,具有传统“依字行腔”的典型特征。
三、《重整河山待后生》“声”的表达
《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作品表达中,骆先生不光重视对“字”的表达,声音上也针对故事性,对每一句唱词的表达进行了特殊处理,使声音带动气氛,令听众进入歌词的故事所要表达的情境中。
上阕“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腔调为高音,通过高音渲染了悲壮的情景,突出了这个民族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则以较为平缓、低沉的曲调直抒胸臆,通过两句之间的鲜明对比,进一步表达了音乐所蕴含的情绪。“月圆之夜”是团圆之夜,渲染了情境,“人不归”与团圆形成对比,“圆、夜、归”重音的运用,唱出了惆怅、唱出了悲凉与伤感。“花香之地无和平”中“和平”二字糅合了京韵大鼓唱腔,自然转换唱腔,唱出了歌曲独有的韵味以及特点。骆先生所具备的“骆式”唱腔娓娓道来,字正腔圆,情绪饱满。
下阕“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中,“情”字演唱需用重音,以强烈的冲击力以及感染力渲染母爱的伟大。骆先生不拘泥于辞藻外壳,通过对比唱法的运用,进一步深挖以及传递其背后所体现的情感,凸显了群众的爱国热忱。“为雪国耻身先去”节奏偏快,音调较高,通过快节奏、高音调表达了悲痛的心情以及对革命先烈的崇拜之情;骆先生先用重音演绎了“重整河山待后生”这句话,通过灵活运用腔调的变化以及波动起伏,不断呈现给听众相关画面,使之感受到歌曲内在的真情实感。
四、《重整河山待后生》“韵”的表达
《重整河山待后生》既然借鉴了京韵大鼓的唱腔以及风格,其难免具备京韵大鼓的特征。骆先生在演唱该作品时,同样注重对“韵”的表达。她的表演融合了多种京韵大鼓的唱腔,从“字”“声”“韵”三个角度配合情景展现以及情感的表达,向观众呈现了悲壮的画面,传达了剧中的情感。
骆先生演唱“千里刀光影”伊始就将听众带入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抗战时期,使人感受到萧条、肃穆。“千”属于阴平,骆先生以高亢并且凄厉的声音为整首歌情绪的表达奠定了基础。“里”属于上声,起衔接作用。骆先生采用了走滑音演唱“里”,与“千”字相互映衬。“刀”字属摇条辙,阴平,演唱起来具备一定的难度,这也是演唱的重点。骆先生采用了余派立音的唱法,峭拔、明亮的同时又绝无突兀、飘浮之感;“影”字的唱法灵感源于京剧,借鉴了其口字方法,庚亭辙归入人辰辙,前鼻音归入后鼻音,咬字清晰,为较为高亢、激昂的第一唱句带来了几分轻灵、通脱之感。
“仇恨燃九城”中的“恨”字为重点,“恨”是人辰辙,去声,在湖广音中去声要挑,演唱起来难度颇大,骆先生借鉴了余叔岩《法场换子》里“恨薛刚小奴才不如禽兽”中“恨”字的唱法,以丹田气催动喉头,重点放在“恨”字的字腹,对于字头、字尾以丹田气托住,用虚音带过,咬字清晰同时灵活,既体现了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又能够为之后的演唱奠定基础,余韵悠长;“仇”字唱作京音,高唱,渲染了气氛,也为“恨”字做好铺垫;“燃”字是上声,骆先生唱作京音,在唱段中凸显了京韵大鼓的韵味;“城”字阳平低唱,走一湖广音,作为全句的最后一字,显得沉着、空灵,同时,这个“城”字没有采用京剧上口字的方法,而是使用北京语音,耍腔也富有京韵大鼓的艺术特色。
“月圆之夜人不归”中每个字都属于沉着、稳定的中低音音色,没有高昂的腔调,与之前较为高昂、激进的演唱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刚性与柔性相结合。运用余派胸腔共鸣的方法,骆先生将情感注入歌曲中,表达了母亲对于子女的深情。“花香之地无和平”中“和平”二字最为重要,“和”为高腔,“平”为嗽音,与上句中低音交相辉映,“和”字表达了浩然正气的浩瀚气概。
同时,嗽音的运用又营造出了空灵的气氛,使得歌曲一唱三叹,形成特有的魅力,“平”字配合着三弦等乐器的伴奏,凸显出京韵大鼓的风格,骆先生运用头腔和胸腔共鸣技巧演唱了“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使得中低音中隐含着高昂的劲头。这两句是骆先生艺术特色的最佳体现。“为雪国耻身先去”一句中,“为”是去声,骆先生走一湖广音,挑着唱,既轻盈又节省了气力,“耻”和“去”两字的劲头、行腔从京剧传统戏《武家坡》老生唱段中“连来带去十八年”的“去”字化用而来,沉着、稳重、结实、斩钉截铁,表现出了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重整河山待后生”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需要高低腔调灵活运用与配合以体现其情感。“重整河山”为高音,“后生”为低音,“待”是高音到低音的过渡音。“重”字高唱,“河”字腔调最高,“整”是上声走滑音,是高音到低音的过渡音。
综上所述,骆先生通过唱腔的起转承合,高低轻重,高音立、中音堂、低音苍的相互配合,使得唱腔韵味十足,平淡中蕴含奥妙。
五、结语
《重整河山待后生》恰如其分地将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融合,借鉴了京韵大鼓的“韵”,结合词所体现的意蕴与场景,巧妙地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字”以及“声”的技巧,其“声”的应用、“字”的表达使得歌曲魅力十足,经久不衰。本文从《重整河山待后生》所具有的“字”“声”“韵”特质出发,鉴赏歌曲所独有的魅力,体会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在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