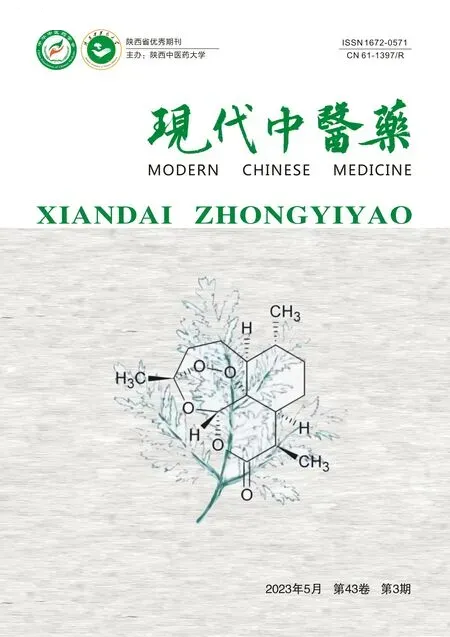NF-κB信号通路调控树突状细胞对肾虚体质免疫失衡影响的研究进展*
孙瑜嬬 胡一帆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2.陕西省中医体质与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陕西 咸阳 712046;3.咸阳市中心血站,陕西 咸阳 712046)
中医体质学说源于《黄帝内经》,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体质的基本特征、形成因素、变化规律、分类辨识、养生预防、易感转归、辩证用药及预后影响等问题的综合学说。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基础上,在生长发育和衰老过程中,形成的形态体态、生理特点、情志性格方面整体的、综合的、稳定的固有特性;在生理上表现为人体代谢和对外界刺激的个体差异,在病理上表现为对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传变性和转归的个体倾向性[1-5]。气血精液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基本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不同个体之所以存在脏腑阴阳、气血偏颇、情志活动和机能代谢的体质差异,究其根本,源于气血精液的盛衰变化,气血精液作为体质评价的核心要素,用于体质的分类辨识[6]。肾虚体质就是以肾中精气虚损、阴阳趋衰、脏腑功能低下为主要特征的病理体质,属于肾藏象理论研究范畴[7]。肾虚邪伏学说源于清代温病学家刘宝怡,侵入人体、未立即发病的病邪称为伏邪或伏气。肾虚邪伏,就是指因人体肾气亏虚,致使外邪侵入至虚之处耗损正气,久而发病。肾虚邪伏理论揭示了肾虚体质机体抗病能力不足、防御修复能力变差,对外邪和其他致病因素易感性增强,易招致外邪,罹患多种疾病,且多为虚弱性疾病、慢性疾病和老年性疾病的根本病因在于肾精不足、正气亏虚[8]。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肾虚体质存在机体免疫功能失衡,低下、紊乱的免疫功能是肾虚体质病理演变的核心[9]。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在机体错综复杂的免疫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固有免疫,在适应性免疫中更是至关重要,与肾虚体质免疫失衡具有重要联系,可作为改善肾虚体质免疫失衡的关键载体调节机体免疫失衡。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B,NF-κB)及其信号通路被证实对DC的成熟分化具有调控作用,能通过DC来影响整个免疫系统发挥免疫效应,肾虚体质状态下,NF-κB及其信号通路表达异常。因此,NF-κB信号通路调控DC异常,可能是肾虚体质免疫失衡引发多种相关疾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1 免疫功能失衡是肾虚体质病理演变的核心
体质的形成秉承于先天、得养于后天,与个体健康和疾病息息相关。人体之所以表现为亚健康状态,是受病理体质的影响。正常体质到病理体质的转变,引发了个体出现健康-亚健康-疾病的演变[10]。作为病理体质类型之一的肾虚体质,既是个体体质的病理改变,也是肾虚体质向肾虚证候转化的中间环节,具有肾虚证相关疾病发生的高度倾向性,是肾虚相关疾病发生的重要病理基础和前阶性表现。
中医学中肾的功能,不仅包括解剖学中的肾脏,还涵盖泌尿、生殖、血液、神经、内分泌、免疫等多个系统,以肾脏功能低下、气血精液亏虚为特征的肾虚体质必然伴随免疫调节失衡,发生多种与肾虚相关的免疫性疾病[11]。肾主生殖,肾虚体质免疫异常不孕症患者出现封闭抗体表达低下、免疫球蛋白、淋巴细胞异常和抗原抗体特异性反应的异常[12];肾虚型复发性流产小鼠子宫IFN-γ、CD4+、IFN-γ/IL-4、CD4+/CD8+表达升高,IL-4、CD8+表达降低,证实以肾虚为病因导致的复发性流产小鼠出现免疫失衡[13-17];肾虚质母体反复胚胎种植失败者中同样出现免疫耐受、T细胞亚群表达失调现象,经补肾中药治疗调节了T细胞亚群分化、逆转了Th1/Th2细胞比例漂移,从而改善母胎的免疫耐受和免疫失衡[18-19]。肾主骨生髓,肾虚体质与骨代谢息息相关,辅助性T细胞(Th细胞)可通过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促骨吸收细胞因子IL-1、IL-6、IL-17、抑骨吸收细胞因子IL-4、IL-10、双向作用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前列腺素等细胞因子通过NF-κB受体依赖或非依赖途径影响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成熟分化,影响骨代谢[20-21]。肾在液为唾,肾虚唾液免疫学研究发现,肾虚体质模型动物唾液腺发生萎缩、损伤,唾液腺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IL-6表达异常,证实肾虚体质唾液腺分泌异常,唾液免疫功能失衡[22]。提取肾虚体质模型动物外周免疫器官脾脏总淋巴细胞RNA进行免疫相关基因谱研究,亦发现12条与肾虚体质直接相关的免疫基因[23]。
综上所述,肾虚体质状态下,机体出现免疫功能的异常和紊乱,免疫失衡是肾虚体质病理演变的核心,促进免疫系统恢复平衡是改善肾虚体质的关键。
2 树突状细胞对肾虚体质免疫失衡的影响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源于骨髓多能造血干细胞,因其分化成熟后伸出许多树突状或伪足样突起而得名,广泛分布于皮肤、气道、外周血和淋巴器官,是公认的功能最强大的专职抗原递呈细胞,被誉为免疫应答的关键启动者、调控者,在抗感染、移植免疫、肿瘤免疫、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未成熟的DC表达低水平的协同刺激分子CD40、CD80、CD86、黏附分子、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分子,具有强大的抗原吞噬能力,但对T细胞的刺激能力较低;受到抗原刺激时,未成熟的DC对抗原发挥高效摄取、加工、处理、提呈能力,并分化为成熟DC从非淋巴器官迁移到淋巴器官,同时表达高水平的黏附分子、MHC类分子和协同刺激分子CD80、CD86,并大量分泌Ⅰ型辅助性T细胞因子(Th细胞)IL-12、IL-18,激活T细胞活化增殖,可诱导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lymphocyte,CTL)生成,表达IL-2R同时大量分泌IL-2,发生Th1型免疫应答,同时分泌对DC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趋化因子,进一步增强T细胞增殖、聚集、活化,也可直接将抗原肽呈递给CD8+T细胞,在活化的CD4+T细胞辅助作用下活化CD8+T细胞,发挥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24-26]。DC强大的免疫调节具有双刃剑作用,正常生理状态下,DC表达低水平的协同刺激分子,如CD40、CD80、CD86分子和MHC分子,结合抗原后诱导免疫耐受;在炎性刺激下,DC和外来抗原大量结合,协同共刺激分子和MHCⅡ类分子表达增强,DC抗原提呈能力相应增强,并迁移到T细胞分布更为广泛的次级淋巴组织,从而激活适应性免疫应答。
大量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肾虚体质伴DC异常,通过调节并恢复DC功能对肾虚体质相关疾病具有良好疗效。慢性乙肝发病符合肾虚邪伏理论,病因病机与肾虚体质相关[27],乙肝肾虚型患者占慢性肝炎患者80%以上,研究发现慢性乙肝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来源的DC出现成熟障碍和功能异常,DC表面标志性分子CD83、CD86、CD80、HLA-DR表达降低,DC分泌IL-12水平降低,抑制DC分泌IL-12且抑制DC分化成熟的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分泌升高,患者体内DC介导的免疫功能出现失调[28-29]。肾虚体质机体免疫低下、免疫失衡易发生炎症反应,导致肾脏DC表达和迁移出现异常。肾脏DC来源于骨髓中的巨噬细胞和DC前体细胞,主要分布于肾小管间质[30],肾脏DC细胞表面趋化因子受体CCR1可为DC提供抗原提呈和加工途径,研究发现肾虚肾小球肾炎患者CCR1表达增强,增强的CCR1使DC抗原提呈能力进一步强化加重细胞浸润和疾病发展[31-32];炎症发生时致炎因子刺激肾脏DC细胞从肾脏间质迁移到肾脏淋巴结,并同时向肾脏髓质区-T淋巴细胞区迁移,促进T淋巴细胞增殖并介导免疫炎性反应[33]。在肾虚免疫紊乱致小鼠溃疡性结肠炎的实验中,DC作为平衡免疫耐受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关键载体,可通过调节其亚群恢复正常重塑促炎因子与抑炎因子平衡,进而改善肾虚型溃疡性结肠炎的炎症反应[34]。肾虚体质者正虚邪实易引发肿瘤,肿瘤日久不愈又加重肾虚,肾虚伴随肿瘤发生发展全过程[35-37],DC作为一种安全性良好的天然佐剂,常用来诱导肿瘤抗原特异性记忆细胞和效应细胞,增强患者T细胞活性达到抗肿瘤效果[38-39]。
综上所述,DC对肾虚体质免疫功能紊乱具有调控作用,维持并恢复DC的正常生理功能是改善肾虚体质免疫失衡的有效途径。
3 NF-κB信号通路对肾虚体质及其相关疾病的影响
NF-κB是分子结构相关联的一组蛋白质家族,1986年,Sen和Baltimore最早发现并成功提取了NF-κB。现已发现该家族包含5组成员,分别是p50(NF-κB1)、p52(NF-κB2)、p65(RelA)、RelB和cRel。该家族成员在分子结构上均有一个由300个氨基酸组成的氨基末端同源区Rel,家族成员二聚体化、与DNA、κB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NF-κB,IKB)结合均发生在此部位[40]。Rel家族各成员之间可通过两两结合形成多种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形成的结构不同的二聚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对靶目标DNA识别亦不同,其中异源性二聚体p50/p65(RelA)几乎存在于所有细胞中,含量最丰富,是NF-κB发挥生理活性的主要形式,p50/p65(RelA)、p50/cRel可以激活转录,p50/p50、p52/p52则对转录具有抑制作用[41-42]。当细胞处于静息状态时,NF-κB与IKB形成三聚体复合物,以无活性的形式驻留在胞质中,当细胞受到不同的刺激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脂多糖、白细胞介素、病毒、紫外线、活性氧等刺激时,NF-κB被激活同时IKB被快速磷酸化,经短暂的泛素化修饰后被蛋白酶降解。激活后的NF-κB可诱导多种基因表达并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43]。
在对肾虚体质大鼠的唾液研究中发现,不管是肾虚体质还是肾虚证候,大鼠腮腺NF-κB表达均较正常组升高[44]。肾与生殖密切相关,多位学者对肾虚血瘀致复发性流产进行实验和临床研究,发现模型孕小鼠脱膜组织NF-κB蛋白表达较正常组升高;临床收集流产患者脱膜组织并采集血液进行检测,同样发现患者血清和脱膜组织中NF-κB均较正常妊娠者高;运用补肾活血方能靶向调节NF-κB通路表达,从而调节母胎免疫平衡达到安胎作用[45-47]。肾与骨相关,肝肾阴虚型原发性骨质疏松动物实验、细胞实验和临床研究均表明,原发性骨质疏松伴NF-κB信号通路异常,滋肾健骨方具有骨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调控了Nrf/HO-1/NF-κB信号通路[48]。肾虚血瘀为病机的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清中,NF-κB水平较健康儿童明显升高,经过补肾中药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后,可显著降低并阻断NF-κB信号通路而提高疗效[49]。
综上所述,NF-κB及其信号通路在肾虚体质及其相关疾病中表达异常,可能与NF-κB及其信号通路参与机体炎症反应相关;补肾中药可通过抑制或阻断该信号通路而缓解病情、提高临床疗效。
4 NF-κB信号通路具有调控树突状细胞的作用
作为功能最强大的抗原提呈细胞,DC在调控T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左右。DC抗原提呈能力和对T细胞刺激能力的强弱又受其自身分化成熟的制约,即DC越成熟,抗原提呈能力越强、对T细胞的激活能力越强;而DC的成熟分化,与NF-κB信号通路调控相关[50]。
作为一种多效的核蛋白因子,研究表明NF-κB家族几乎所有成员均参与了DC细胞的成熟与分化。相较于家族其它成员,NF-κB家族成员RelB作为与抗原提呈功能相关基因的重要转录因子,经刺激后可直接诱导DC分化,在DC成熟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51],成员p50(NF-κB1)、p65(RelA)、RelB和cRel可以通过易位参与不同的途径调控DC,从而发挥不同的生理功能[52]。NF-κB信号通路被激活后促进多种炎症因子释放[53],并上调DC的CD80/86等表面的共刺激分子,诱导DC的成熟和表达,上调的共刺激分子与细胞表面相应配体结合,作为第二信号提供给T细胞,随之大量的T细胞被活化,引发机体免疫应答,作用整个免疫系统发挥效应[54-55]。
5 结语
肾虚体质状态下,机体的免疫功能出现异常。一方面,DC作为功能最强大的抗原提呈细胞,对肾虚体质失衡的免疫功能具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肾虚体质状态伴NF-κB信号通路异常且NF-κB及其信号通路参与DC的成熟分化,可通过作用DC调控免疫系统,不仅作用于固有免疫,对适应性免疫应答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通过NF-κB信号通路调控DC,可作为调节肾虚体质免疫失衡的关键,这一机制的阐释,为中医药改善肾虚体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治疗靶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