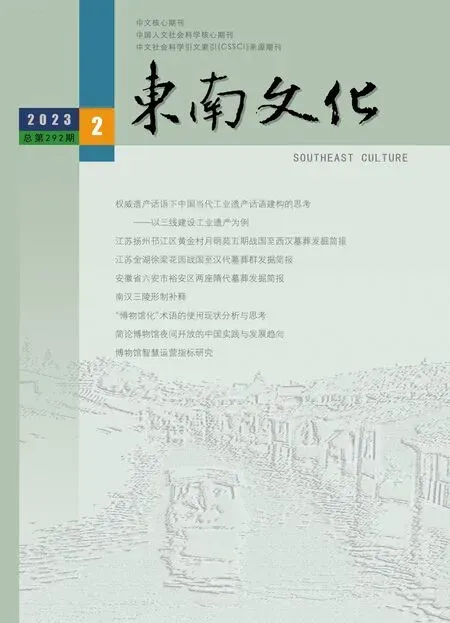“民族互嵌”视域下的民族类博物馆介入性艺术研究
褚 楚
(广西民族博物馆 广西南宁 530028)
内容提要:在“民族互嵌”理论的背景下,民族类博物馆因文化事件汇聚了精神的共鸣,可能成为一种动态的民族互嵌社区。为了维护动态社区多方交流、不断融合的性质,民族类博物馆积极引入了介入性艺术实践与理论。介入性艺术是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广泛实践,并在90年代形成自律审美体系的一种艺术的新样态。它强调民众在艺术实践各个环节的参与性和影响力,因紧扣社会议题,反映出艺术当下的政治功能。中国民族类博物馆中现有的介入性艺术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参与性展示、行为表演、社会活动,作为对国内外介入性艺术问题的补充,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材料,也为民族类博物馆跨学科实践提出一种衔接的思路。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当下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要的社会基础。“截至2020年我国的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和120 个自治县(旗)、44 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已建成县级以上的民族博物馆190家左右”[1]。加上全国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馆、民族艺术馆等相关展馆,它们一并组成了以民族文化保护传播工作为核心的民族类博物馆体系。作为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民族类博物馆面向民众开放的内容大致包括科研成果的阐释、陈列展览、社会教育、节庆赛事活动等,较好地满足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双重需求。但是,民族工作的新课题要求博物馆进一步体现各族文化生活交流、交融的本质。在“民族互嵌”视域下,怎样以各族群众为导向、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以多方参与为形式去开展社会实践,从而塑造民族的多方交流、不断融合的动态文化社区,成为民族类博物馆实践、研究的着力点。
一、民族互嵌视域下的动态社区
(一)精神共融促生社区的动态性
“民族互嵌”就是指不同的民族相互融合,它存在于居住的空间环境、生活生产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或精神文化内容等多个方面。2014—2022年的八年间,国家层面对“民族互嵌”问题进行了多次论述[2],将其纳入发展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国家战略,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持续的完善和补充。特别是2014年9月,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3],这段话不仅明示了民族事务“多元共存”的先决条件,也表达了民族互嵌问题中四个动态的共享维度。民族互嵌的基础理论将重点放在居住区域、民族比例、人群流动等物理层面的研究之上,主要分析在自然形成的民族杂居状态中,各族的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如何受到地域和居住情况影响而产生交集。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精神互嵌”和“文化共同体”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从国家战略视角来看,‘民族互嵌’绝非仅仅指代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关系的空间关系,更多地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形成自由交往、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4]。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F.Pettigrew)在“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中阐述了群体间接触的四个变化过程:了解外部群体、改变行为、产生情感联系以及群体内部的重新评价[5]。这提示我们思考,除了多民族聚集区的杂居之外,什么样的环境能够促成这种相互了解和情感发生,什么样的方向能够支持民族互嵌的国家表达——这就进一步关联到“民族互嵌”社区的灵活性问题。
只有一个动态、灵活且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社区,或说一种“动态社区的状态”,才能满足多样化的民族互嵌需求。这一点与西方政治学领域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从女性主义角度开启的关于“公共领域多元化”的评判相似[6]。传统意义上公共空间的固定性被质疑,它被认为“应该根据使用者重新组织和重新解释而变化”[7]。将“民族互嵌社区”与“公共领域”进行比较,能够更好地关注区域内的动态性和生成性。“公共领域被作为社会交流的产物和一种可变的社区结构……此种社交空间是动态的,由事件组成,这些事件产生了人、物体和空间之间互动的流畅网络,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松散、短暂的社会交往社区”[8]。这样,社区可能就会脱离原始“实体聚居”的概念,也不再单单指向“居民委员会辖区”,因精神交融形成的“即兴”的共享关系正是当下生发的新的民族互嵌实体类型。
(二)一种动态社区的可能——民族类博物馆
与博物馆相关的社区,“是指这样一些人群,他们对某些事物的意义享有或感觉享有共同的理解和认识,一个社区可以是一个地理区域中所有的人,这些人可以属于同一种文化,也可能拥有几种语言和文化。伴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剧增和人们对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日益关注,博物馆在社区文化认识方面的作用问题便显得更加引人注目”[9]。新时期的博物馆工作不仅仅关注、联系、服务于一种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社区”,本身也可能成为这种新的社区样态。民族类博物馆是能够构建动态的民族互嵌社区的机构:首先,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事件在一个区域内聚集、交流,汇集成为新的非居住的社区类型;其次,这种灵活的动态形式又是在“介入与参与”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它可能伴随着博物馆的短期文化事件快速地出现或消失;再次,它具有引导社会参与、讨论,具有干预文化发展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也就是说在临时的区域中,各族民众可以与民族类博物馆合作完成一些行为、事件,这些结果直接影响着他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发声与角色。综上所述,一种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并且不受传统民族社区体积、性质和人群束缚的动态民族互嵌社区出现了。
动态民族互嵌社区的生成性直接指向一种基于人类学的组织策划技巧和传播把关能力,也指向了“博物馆原有目的和价值基础之上的21世纪可以应对的可持续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挑战及责任”[10]。从全球的发展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征”和“社区”成为博物馆学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11],它们要求博物馆在传统收藏、研究、展示工作之外,思考藏品、博物馆实体以及公共服务对象的属性问题。因为博物馆囊括了携带政治信息的物件和观众、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民众文化属性等内容汇集成的复杂的表征系统。“博物馆充分表征原则要求博物馆应该充分地表现不同的公众区域的文化与价值,而让大众更平等地接近、使用博物馆作为一种政治需求,是我们积极思考利用博物馆权力的表现,它超越了传统的公众资源分配、娱乐教育的功能。”[12]作为区域内的文化展示传播机构和社区开展社会教育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伙伴,博物馆对于凝聚社会共识责无旁贷。在中国,从“差异多样”到“铸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注动态民族互嵌社区和围墙之外的观众,是民族类博物馆政治学功能的外在表现,也反映了其自我定位的内在变化。
前文提到基于社会资源、受众基础和文化传播功能,民族类博物馆拥有在一定区域内构建动态民族互嵌社区的能力,同时也兼顾在这个动态社区内充分表征民族多样文化的责任。近些年,全国民族类博物馆的社会实践已经从最初的民族文化及藏品的研究、展示和宣传教育等延伸到博物馆外围。但是,许多内容仍由博物馆主导策划实施,因为缺乏由下至上的民众参与方法和机制,某些环节依然存在文化内容的来源单一、民众反馈不充分、文化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民族类博物馆需要进一步正视各族民众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活的力量,以一种“弱姿态”激发他们在博物馆公共事务中的合作意识,促进动态民族互嵌社区生成。为了维护动态社区多方交流、不断融合的性质,民族类博物馆积极引入了“介入性艺术”(engaged art)实践与理论。“介入性艺术”从西方政治学、美学前沿理论中诞生,在几十年间结合全球社会实践类艺术的发展不断完善,并在中国得到了在地性研究的有效论证。它紧扣社会议题,强调民众自始至终的参与和影响,能够为民族类博物馆提供一种新的实践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思路。
二、介入性艺术概述及其审美讨论
介入性艺术是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普遍实践,并在90年代形成自律审美体系的一种艺术的新样态。“它呈现为在特定现场开展的、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混合媒介的事件性艺术”[13]。从这类艺术的其他名称——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参与性艺术(participa⁃tory art)、社区艺术(community art)、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对话艺术(dialogic art)中,可以看出它代表了一种积极的、以群众为导向的、以多方参与合作为过程的艺术实践方式。西方社会一系列促使公众融入社会的艺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历史前卫主义(historical avant-garde)[14],以及60年代后新前卫主义(new avant-garde)时期的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艺术创作、偶发艺术(happenings)、机构批判艺术(institu⁃tional critique)、东欧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参与性活动等[15],其理论内核则是发祥于法国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与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歧感效应”(dissensus)。关系美学的提出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法国“当代艺术危机”大讨论,伯瑞奥德认为艺术批评急需建立一套新的理论话语来应对当代艺术的误读,所以努力在社会语境中重建当代艺术的表征范式[16]。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种可以跳脱商品交换经济框架的“社会中介”(social interstice),而中介就是一种人的关系空间[17]。依据法国哲学家路西·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会面的唯物论”(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他建构了关系美学,表达一种通过艺术实践来呈现的事物持续会面的状态,在现有物化世界关系之外,实现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18]。而雅克·朗西埃的理论重新勾画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艺术与政治都是一种对事物存在和边界不自觉的感官划分,划分过程中的排他性产生了一种对原有感知秩序“治安”(police)的扰乱,即是“歧感”(dissensus),歧感效应阻断了政治意图和艺术效果的直接关系,否认了说教模式,这是“艺术介入”的关键[19]。
随后,许多学者相继丰富了介入性艺术的理论内涵。首先,研究“对话”与“合作”艺术实践的美国美术史家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质疑艺术家的主体地位,认为此类艺术不是指艺术家之间的合作,而是群众的广泛互动和分工劳动[20]。他的对立方英国艺术史学家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则认为参与性艺术的核心不是关系美学阐述的“协商”,而是“抵抗性”[21],她批评凯斯特只重视艺术合作中的伦理关系,不敢冒犯观众,从而失去了此类艺术不可回避的社会干预功能[22]。从命名到定性的争论一直在此类艺术研究中持续,是“参与”还是“介入”……其实并不会从艺术实践的微观层面影响一个艺术案例,但争论本身反映了社会少有的建立在定性之上的对艺术伦理的注目。其次,随着介入性艺术实践的展开,个案研究为美学原理补充了大量现实素材。美国学者苏珊·雷西(Suzanne Lacy)于《量绘形貌——新类型公共艺术》(Map⁃ping the Terrain: New Genre Public Art),一书聚焦了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一系列此类艺术的案例和批评,描绘出这一类型艺术“区别于传统户外雕塑环境”“解决社会问题而非美学问题”“弱实体化和永久性”“提升大众参与”“针对弱势群体而非富裕阶层”的现实特征[23],虽然这些问题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但已经可以用于全球“艺术介入社会”的讨论。
对比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内介入性艺术研究以中国群众特性为基础,在短短十多年间描绘出西方社会语境之外艺术介入社会的多样性。它们主要针对艺术史脉络、城市重塑和艺术乡建三个方向。(1)艺术史脉络方面。王春辰的相关著作从中国当代艺术特殊历史脉络出发,讨论了介入性艺术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24];周彦华从延安时期形成的艺术实践模式切入,提供了一种以“群众路线”看待艺术介入社会的新视角[25]。这些提示我们,除了个案研究,构建中国自律的介入性艺术历史脉络至关重要。(2)城市重塑方面。艺术介入城市余遗空间、介入社区主要是依照都市文化的内核,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在强调用“艺术和地方文化来建构新的城市形象”[26]的同时,研究公共艺术的社区治理能力。(3)艺术乡建方面。2000年以来,大量艺术家进入社区及乡村,针对艺术介入时的群众关系、个体“身份”和文化参与、发声、赋权等问题,“重新探索了城乡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可能性,实现对文明传统的再追索及当下社会的再修复”[27]。大家熟知的有山西和顺“许村计划”(2007年)、甘肃秦安“石节子美术馆”(2009年)、安徽黟县“碧山共同体”(2011年)、贵州桐梓的“羊磴艺术合作社”(2012年)、广东顺德“青田计划”(2015年)等。与艺术介入城市空间较多地借用欧美介入性艺术学科实践体系不同,艺术介入乡村倾向于参考亚洲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社区的经验,探讨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割裂问题。一些学者从中看到,“缺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或者民族志的方法,我们连理解乡村都是困难的,遑论通过艺术去进行乡建”[28],道出了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介入性艺术实践的必要途径。
从以上国内外介入性艺术的发展实践看:西方的介入性艺术理论从创造之初就附带政治对抗的属性,用以解决反体制化、反意义和反中心论的现代之后的议题,只有在对立矛盾之中,介入性艺术的某种能量才会凸显出来;而中国的介入性艺术发展倾向于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介入,倾向于将与艺术实施相关的所有力量与更广泛的人民大众划上等号(甚至缺少了新类型公共艺术理论背景下一些西方公共艺术机构一直对艺术家地位的据理力争),将介入性艺术功能运用在促进社会和谐之上。实际上,虽然表现面貌不同,但是它们同时面临艺术评判标准缺失、体制批判的能力的削弱[29]以及在政治功能和大众文化功能中矛盾摇摆的局限。此外,中国的介入性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城市、乡村这一地域格局为基础的分类中。在西方,“关注少数族裔的公共生活”是介入性艺术实践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而中国当下并未涉及这些内容,这使得丰富的理论框架无法作用于单一的实践分类。一些研究因直接挪用西方概念而被质疑——介入性实践的公众参与是否有效、中国乡村社群是否与西方社区概念等同,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的严重脱节等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随着介入性艺术中国在地性实践的不断开展,研究工作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将被逐步解决。
三、民族类博物馆中的介入性艺术
凭借动态民族互嵌社区——民族类博物馆内的各种实践渠道,介入性艺术可以将少数民族原生的文化与审美作为一种“非体制的体制依靠”,尝试以西方中心之外的标准,支持实践与研究。有以下两个事项需要关注:(1)原有介入性艺术理论研究反映了艺术变革的大趋势,总结了介入性艺术怎样在群体参与的基础之上,平衡观众、艺术家、机构等各方利益。但是,对于参与者的个案观察、记录相对不足,容易造成各方角色的模板化概念,从而削弱了这类艺术批评的力量。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介入的过程进行记录,有助于汇总少数民族区域交错的艺术实践情况,维护民族交往和艺术协作的共性。(2)与艺术介入乡村、城市相比,动态民族互嵌社区中的介入性艺术有更强的文化指向性。例如贵州“羊蹬艺术合作社”的发起者焦兴涛曾在讲座中谈到:“羊蹬艺术合作社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和目标,它提倡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工作方式。我只是希望通过与当地开展‘艺术协商’来一起发展艺术项目,促进长期的沟通和改变,使人们能够共同建立和体验更有趣的生活。”[30]这种艺术创作的纯粹与自由,以及被放置在首位的即兴体验能否在动态民族互嵌社区内即刻实现,还需继续探讨。民族类博物馆的介入性艺术需要在原有的艺术土壤中摸索与当下、外界相接轨的方法。
民族类博物馆现有的介入性艺术主要包括公共文化事项中民众、社区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事件与活动。根据国内外介入性艺术的规律,这些内容主要存在于民族类博物馆实体展馆园区内部(包括各区县级民族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博物馆外部的流动点(包括城市社区、商区、少数民族村寨、其他文化机构场地等),以及非实体的媒介(包括大众传播媒介、新媒介等)等多样的环境中。此外,依据资金来源、民族艺术家委任或自主创作情况、项目的参与方式、人员互动成效等方面的综合因素,现有案例的介入性程度也不尽相同。根据全国民族类博物馆实践情况,现有介入性艺术的案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参与性展示类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社区影像展映和少数民族艺术家自主策展等内容。从“展示”一词可以看出,它是公共艺术的一种传统属性,也是介入性艺术的一种不地道的描述。但是基于艺术史中视觉类别的霸权地位和传统机构传播方式的前序,我们不能完全割裂展示行为去分析介入性艺术。在民族类博物馆的实践中,展示活动依然是各项介入性实验的主要载体。与以往以静观式审美体验为主的展示项目不同,加入了行为和事件因素的展示项目能够有效地满足介入性艺术参与性的要求。前面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偶发艺术和70年代的观念艺术之后,艺术介入社会的实践从90年代关系美学中不断发展出对社会互动式的关注,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体制批判“出走”到寻找场外积极意义的“折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艺术机构的藏品和展览采取了互动和表演的方式,即使不是完全公开的。这种对艺术展览的社会关注隐含地承认了艺术表达普遍关切的能力,并鼓励艺术作品与周围环境、时代和观众积极对话的体验,……这些趋势有助于改善传统博物馆所面临的排他性问题,并让人们注意到艺术作品积极吸引周围人群的多样化能力”[31]。在民族类博物馆的实践中,这一努力主要体现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和少数民族民众艺术创作活动。
比起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民族类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关系更加亲密。民族手工艺人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角色就如同以往介入性艺术中的艺术家——他们是参与性展示的引导者。民族技艺口头传播和民族文物传世的特性,让这些艺术家有诉说、表达文物背后故事的渴望。2014年至今,广西民族博物馆基于少数民族手工艺人与其手艺之间的粘稠性,开启了一系列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事者主导的展示活动,其中五十余场被划入项目品牌“非遗天天见”。如2018年7月根据“拼布艺术与传统——人·物·生活”展的需要,馆方将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沙梨乡壮族村寨的手工艺人黄碧瑜请到展区。由她带领观众体验染布、刺绣、拼布等手工技艺,并从自身角度向观众讲述壮族纺织品中文化符号对于本族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思考。少数民族手艺人作为博物馆互动展示的主体、主讲人,有助于博物馆摆脱如同“被控制的、秩序井然的权力的庇护所,一种视觉上的、人类学、宗教学、阶级和性别上的白盒子”[32]的境遇。他们赋予展示项目基本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属性,同时也是活动的参与者,在歧感效用的柔性互动中实现自我认同与民族互嵌的双重价值。
如果通过技巧培训、平台建立和机构放权等方式,以上谈到主讲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就可能变为介入性艺术实践中的主导者——参与导演、策划、策展等环节。其中,社区影像作为一种以少数民族群众自主创作为初衷的艺术实践,展示了对社会的介入两种方式:拍摄创作的放权让少数民族群众“从失声的‘他者’,转变为有着文化宣示能力的表达主体”[33];民族博物馆内的展映过程设计体现了对于这种表达欲和互动性的保护。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落水村摩梭民族博物馆举办“摩梭电影展”在细节上突出了两种民众参与性。“电影展的展映安排,特别强调对摩梭人文化规则尤其是‘害羞文化’的尊重。排片的时候,几部可能引起争议与反感的影片被安排在晚间放映,避免了不同代际人群共同观影的尴尬……第二天,村里的年轻女子都去一户人家帮忙办丧事,于是尔青[34]召集了26 位20~40 岁的男人参加社区编辑。没有老人和异性在场,男人们畅所欲言。”[35]这些体现了后现代理论视域下艺术学与人类学研究视角、行事方法的交叠,不仅从承办方式上将少数民族群体置于先决位置,还细致入微地体现了不同群体参与艺术及社会实践活动时的感知特性,创造了动态民族互嵌社区内开放的交流氛围,也保证了参与性展示的有效性。
(二)行为表演类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节庆活动、生产生活表演、实景戏剧等内容,其中,可能包含具有古典叙事功能的戏剧形式,也可能是不涉及叙事范畴的、以表演者身体作为媒介的行为过程。“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审美意义生成机制强调艺术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实则是对艺术创作中剧场性的遮蔽。”[36]而介入性艺术中的行为表演类提示了艺术从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封闭自足)向当代主义之后艺术复归现场的进程。这对应了博物馆学在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发展的敦促之下,由“关注指定展场中的物”向“关联多元现场的‘非物’”的转型[37],从而引发了“如何走出二分结构的窠臼、进而在博物馆中适切地表征他者文化”[38]的思考。民族类博物馆内部实施行为表演艺术实践,探讨了表演主体、精神共情、机构把关等问题。就现有的民族类博物馆实践素材看,它们主要经历了节庆演出的初级阶段和实景出演的发展阶段。
广西民族博物馆从2012年开始承办壮族“三月三”节庆活动。这个全面覆盖城市乡村的重要民族节日先后经历了广西政府和官方文化机构的重新定位、包装。民族类博物馆作为执行方,保留了演出行为自下而上的民间参与性:从2012年小规模活动开始,全区民歌比赛中胜出的地方演唱者被引入庆典活动,保留了“老百姓自己表演过节”的传统。随着“三月三”节庆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庆活动加入了更多政府、官方机构的承办力量,但来自民间艺术表演者和团体一直是主会场庆典活动的核心。一直处在节庆迎客位置的马山会鼓团队成员就谈到自己习鼓的原生性:“在生活的区域,我从小在长辈打鼓的生活环境中耳濡目染,但是以前一个社区只有一面鼓,不让小孩子碰,到我十几岁因为喜欢才正式学习打鼓,最终加入了民间鼓队(壮鼓协会),才被组织到民族博物馆参加节庆活动。”[39]这种表演实践置换了少数民族表演的场地,让民族传统艺术介入都市生活。这表明该类艺术“不为了强化作品的现场性而强行干预现场;相反,它是在满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倡艺术和现场的整合”[40]。
民族节庆的革新一直引发社会关注和思考,节庆表演也受到资金投入、包装理念和消费目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果出现把关乏力,这种“复归现场”的表演实践反而会推助民族节庆往“节庆士绅化”的方向发展。此时,民族类博物馆对于介入性艺术理念的积极把握以及民间少数民族群体对于行为表演类实践的积极参与,不仅能够保证民族类博物馆文化传播的质量,还能保护民族节庆上下层交流的特质,这是构建动态民族互嵌社区的基础。
在发展阶段,这一分类出现了特有实践类型。2004年11月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开馆,村内表演队也开展了文化表演项目。根据参观预约情况,当地会有30 名左右的村民带着乐器去表演,整套节目包括打铜鼓、吹牛角、吹喇利、打陀螺、跳民族舞蹈等内容,演出长度大约为30 分钟;此外,生态博物馆也会根据需要组织展示其他生产生活事项,来访者也可以在寨子里看到这些活动[41]。在贵州,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分馆也曾有过类似的表演:在进寨门之前,盛妆的苗族姑娘在寨门前为每一位贵宾献上“拦门酒”,唱敬酒歌。在寨中开放式的舞台,寨中歌手唱苗族古歌,邀请观众跳高排芦笙舞[42]。在北方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展示中,鄂尔多斯的苏泊罕游牧草原文化活态博物馆也策划实施过“鄂尔多斯婚礼实景演艺”“七旗会盟大型原乡实景演艺”“苏泊罕大草原婚礼文化艺术旅游节”三项实景表演活动[43];除了多人大型表演,活态博物馆区域内也同样包含了挤羊奶、剪羊毛、擀大毡等蒙古族传统民俗活动,邀请观众成为民族文化的实景的一部分。由此看来,生态博物馆区域内的实景表演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聚集观看的需求组织的演出;另一种是以审美的方式看待生态博物馆区域内村民生产生活,将其视为一种生活“展演”。无论哪一种形式,演出环境都在少数民族生活聚集地内,参与主体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介入性艺术的语境下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
虽然这些演出涉及众多本地群众和其他资源,成本巨大,大部分因本地旅游业而兴起,又因观众不足和其他消耗因素,或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停止。但是,回溯这些演出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西方介入性艺术的表演与行为项目,讲究的是艺术家与观众的互动沟通,以创造出作品的即时走向,衍生出不在计划之内的新意味;而生态博物馆这类由乡民参与的实景演出,不仅突出了艺术事件的内部变化,更反映出民族类博物馆惯用的“他者性叙事”的转变——生态表演主要从还原生产、生活的角度呈现了一种新的剧场性艺术实体,这种社会实践的观演化有助于帮助民族文化事项从“他者”的视角中解脱,更直接地将少数民族的“自我”带到现实环境中,实现主客体立场的转换和互补。民族演员“出演自己”的间离效果实现了“主体间性”。
(三)社会活动类
这一类型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竞赛、社会艺术教育、博物馆与社区共建的其他艺术事项,甚至博物馆参与的社会活动等。介入性艺术将社会看作整个审美实践的场域,所谈论的艺术实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合作性质的社会实践。例如对美国纽约公共艺术机构“创意时刻”(creative time)的研究结果表明,该机构伴随的纽约公共艺术实践所走的是一条逐渐祛除物质性和艺术性的道路,在其介入社会的成熟阶段,艺术项目不再只是顾虑审美实践中的参与性问题,而是通过项目对各项社会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44]。
2019年春,云南民族博物馆协助昆明市官渡区太和街道和平路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主体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及来往群众约三百人参加了相关活动。活动包括烟盒舞、民族服装秀、锅庄舞、民族器乐吹奏等民族歌舞表演,民族知识竞答,剪影、剪纸、糖人、糖画、春联书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展演等[45],体现出博物馆与社会共同策划、参与的面貌。博物馆走入社区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但是从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动态民族互嵌社区权力的角度看,这个活动是民族类博物馆走出围墙、积极参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即通过介入性艺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现自身职能拓展的表现。该社区原本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合居住的老社区,社区建设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仅有多民族大家庭的老住户,还有不少来昆明工作学习生活的少数民族新住户[46]。将这样的案例从原本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体系中划分出来,以介入性艺术的角度进行思考,主要的意义在于介入性艺术的思考方式能够改变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角色位置,更加充分地考量参与者与项目的关系。这种方式不仅突破了博物馆和社会“施与”“教导”的师生关系的局限性,还解答了民族互嵌背景之下各族群众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它体现了动态民族互嵌社区灵活性——不仅仅出现在博物馆内部、民族村落,还有可能出现在都市文化之中。
相对于前文对民族类博物馆参与社会活动的形式的聚焦,另一种情况让我们聚焦项目负责人所属群体的性质和比例。在西方介入性艺术案例中,项目负责人所属群体的性质和比例是项目介入程度的重要衡量要素——民族类博物馆参与的社会活动类型需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组织者或艺术家作为发起人和主导者。参考这样的机制,民族类博物馆的社会实践类项目贯通了社会教育资源和地方性知识,在社会教育活动的审美性操练中,实现了对社会知识生产的积极参与。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农民画艺术馆为例,其针对独峒的小学、中学开展“农民画进校园”培训,每个班大概有35 个学生,老师主要就侗族农民画的起源、传承历史、精髓内涵等内容进行讲授,侗族画师还会带领学生自主创作农民画。通过培训班,农民画艺术馆与学生建立了联系,课后也有学生专门结伴到艺术馆继续学习画画。培训班的负责人表示,“这些活动加深了侗族小朋友们对侗族农民画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荣誉感,能够提升本民族青少年对这项技艺的传承意识,对培养新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产生促进作用”[47]。
因为以社会和民众为导向,介入性艺术一直关心知识的传播途径和获取方式,它扶持少数民族艺术传习者开展社会教育,对地方性知识传承具有补充作用。常规的学校教育体系并不能保证地方性知识的传授,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常能听到老非遗传承人“后继无人”的感叹。而省(区)市一级民族类博物馆则一般采用宏观的知识统筹方法和学术委员会审核制度来设计社会教育方案和脚本。现有的结果能够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信息和总体面貌,却不易把握地方性知识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处事规则。例如三江侗族服饰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就表示:“除了传统的技艺和审美,侗族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包裹这些内容的整体生活氛围。”[48]地方性知识的人际传播特性在介入性艺术实践中得到滋养,这也是之后对其进行传承、发展的关键。此外,从美育的角度出发,将青少年、妇女等群体纳入介入性艺术教育实践,表明介入性艺术塑造的临时公共场域不仅有生动、多元的特点,还保有了可划拨目标人群的功能。
四、结语
在民族互嵌理论和政策背景之下,民族类博物馆因为文化事件汇聚了精神的共鸣,可能成为一种动态的民族互嵌社区。基于博物馆不断更新的定义、职能,民族类博物馆具有在动态社区内充分表征民族多样文化的责任。在其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文化机构“弱姿态”的参与与动态社区中开放多元的意义相一致。为了保护这种民族互嵌社区内部交流的动态性和生成性,民族类博物馆积极引入了介入性艺术实践与理论。根据介入性艺术的审美机制分析和全球介入性艺术案例分类情况,本文介绍了民族博物馆中介入性艺术的三种类型——参与性展示类、行为表演类和社会活动类,它们具有以下特点:(1)能够塑造一种拥有“开放平等的交流机制”“间离自我的参与方式”和“灵活可变的目标受众”的民族动态互嵌社区;(2)兼顾探讨了此类艺术中作者、观众等多种关系的“间性”内核和人类学视角中“主体”“他者性”等内容之间的关联;(3)所促成的动态民族互嵌社区的发展,对现有民族类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和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当少数民族自发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机构的帮扶愿望产生出入,面对当下介入性艺术评判标准的举棋不定时,民族类博物馆的介入性艺术可以依据各族群众和少数民族原生的文化,将其作为一种“非体制的体制依靠”,尝试以西方中心之外的艺术标准支持此类艺术的探索。将“审美的枢纽”的功能运用在促进社会和谐之上,促进民族互嵌进一步深入。
此外,在现有研究素材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设计、实施新的介入性艺术项目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需要专业艺术家和相关机构的支持,还需要田野调查和具体少数民族社区合作创作的试点。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投入的公共文化服务展馆、设施以及民族类博物馆外围的园区环境等,为民族类博物馆介入性艺术的再次创建提供了场地保障,而博物馆当下的数字和信息化建设则为非实体环境中民众参与、多元互融的讨论提供了有力支持。最终,介入性艺术研究能够为民族类博物馆创建民族互嵌的动态社区提供可行性方案,凸显民族类博物馆的文化枢纽力量,对维护民族团结、传承多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